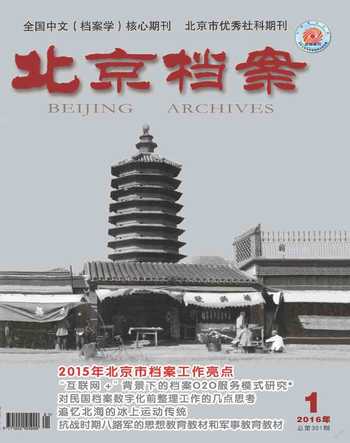北京智化寺渊源考
孙鑫
智化寺是宦官王振于明正统九年(公元1444年)建立的。该寺与王振关系密切,随着明清时期不同的当权者对王振的宠与贬,智化寺也随之经历了两起两落,从侧面反应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情形。清末至民国以来,智化寺的香火一直不很兴旺,主要依靠几位寺僧出租房屋和应酬红白喜事为生。建国后该寺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几经修缮,不再全部对世人开放。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述智化寺与王振及王振家宅的关系、智化寺由明朝至今的历史变迁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考证。
一、建寺考——王振“舍宅建寺”辨析
1.智化寺与王振家宅的关系
关于智化寺建筑的来源,长期存在着王振“舍宅建寺”的说法。由于王振家宅与智化寺都位于顺天府大兴县黄华坊(今北京市东城区禄米仓胡同),再加上智化寺的修造时间过短,于是便产生了智化寺为王振“舍宅而建”的说法。
其一,认为智化寺为王振舍全宅而建。以《天咫偶闻》、《明史考证》(黄云眉)、许惠利、朱桂辛等为代表。《天咫偶闻》载“智化寺,在禄米仓胡同,为明王振舍宅所建。”黄云眉《明史考证》载“智化寺即振旧宅”。许惠利在《智化寺建筑管窥》一文中从建筑角度判断,认为智化寺山门后檐墙与智化门前阶之间相距不过十余米,第二、第三个院落却都有三十至四十米深的院落,“头部”与“身躯”的比例失调。同时作为正四品司礼监太监的王振家宅应是门屋三间,厅堂各七间。这个数字基本符合智化门、智化殿与万佛阁的建筑体量。因此断定智化寺为王振舍宅而建。
其二,认为智化寺为王振舍部分宅而建。以郝黎为代表。他的依据是《明书》所载“振族党并诛,第宅没官,改京卫武学”,也就是说直到王振及其党羽被诛的时候,他的宅邸还是存在的。目前智化寺的西边就是武学胡同,可以为《明书》的这一记载做佐证。这就说明王振至多只舍了或者改建了一部分宅第为寺。
笔者以为智化寺并非为王振舍宅而建,而是王振在建家宅的同时或其后在舍宅附近新建的一座家庙。理由如下:
第一,从智化寺的建筑布局来看,完全是典型的佛教寺庙“伽蓝七堂”的形制。与普通官民宅院并不相同。何况轮藏殿、智化殿、万佛阁中都设有精美的藻井,更是不可能存在或改建于民居建筑中。
第二,智化寺碑文中记载“京城之东稍北,顺天府大兴县黄华坊,振之私地在焉。境幽而雅,喧尘之所不至。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这段史料引人误解的关键点在于对“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中“其”指代的地点的不同理解。持“舍宅建寺”观点的人大多认为“其”指的是王振私宅,是在王振私宅的“闲旷高朗处”建了智化寺。而结合上下文,笔者认为“其”指的是黄华坊。“境幽而雅,喧尘之所不至”是描述黄华坊的环境的,接着下文“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仍然是说在黄华坊的一块闲置的高敞的空地上圈起围墙,建起了智化寺。整段文字的主语都是“黄华坊”,这样才符合上下行文时主语一致的习惯。
第三,从《明史》载王振在得势后“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这里也是将王振家宅与智化寺当作同时或先后兴建的两组不同的建筑来记载的。
第四,《明书》记载“振族党并诛,第宅没官,改京卫武学”。从明代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北京城地图来看,智化寺旁边的确是存在“武学”的。如果《明书》的记载可靠的话,那么智化寺旁边这座方正的建筑才应该是王振的宅第,在王振死后被改为武学。智化寺与王振家宅毗邻,二者的修建时间可能很接近,但不存在互相包含的关系。
第五,《明书》中有记载“正统中,振作大第于皇城东。又明年,作智化寺于第左”。这里明确记载了智化寺是在王振建宅后的第二年、在家宅左边建成的。智化寺是建在王振家宅旁边的独立建筑,并没有建在家宅内部,因此也就不存在“舍宅”的问题。
2.智化寺的营建时长问题
(1)王振与智化寺的兴建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王振早年曾读过书,并由儒士而做了教官,由于在职期间没什么建树,按律罪当谪戍。然而当时朝廷特许其中一些没有功名的读书人自愿“净身”入宫,加入在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于内宫设立“内书堂”,教授内监读书。王振便趁此机会自宫净身入宫,并有机会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做了东宫局郎,深得太子信任。英宗朱祁镇继位后,对王振更加宠信,使其得以掌控司礼监。在太皇太后去世、杨士奇等五位辅君重臣或老或逝之后,王振的权力渐渐扩大到无人可以制衡。他不仅按自己的好恶处置大臣乃至宗亲,更越制建宅造寺,怂恿英宗佞佛。智化寺便是在王振权势极盛之时为满足他“追本、延福、庇后”的愿望而修建的。
(2)智化寺的修建用时质疑
王振所立石碑《敕赐智化禅寺之记》中记载了智化寺建寺的时间、地点及寺名来历:明正统九年三月初一(公元1444年3月20日),王振在顺天府大兴县黄华坊,也是他的住宅所在的地方,建成了一座寺庙,该庙落成后由明英宗赐名为“智化禅寺”。王振自述其建庙的目的主要是为祭祀先祖、祈福延寿。
“京城之东稍北,顺天府大兴县黄华坊,振之私地在焉。境幽而雅,喧尘之所不至。乃即其闲旷高朗处,垣而寺之……凡百工材之费,一出已资,盖始于正统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既而以闻,王嘉之,特赐名曰:‘智化禅寺。……而人欲效报于祖者,舍佛其谁能资其冥福哉。此吾一念惓惓在于佛者,盖以报本追远为主,其次增延福寿,济渡幽显于无穷也。”这段碑文显示,智化寺自开始修建至全部完工,整个工期不足两月,而且正值寒冬,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施工速度实在是匪夷所思。因此碑文中记载的修建用时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关于智化寺修建用时的问题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认为有可能在两月之内修建完毕。以郝黎为代表。他首先从《明史》中“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的行文记载推测,王振建宅第、建寺院极可能是统一规划。寺院早已规划完毕,而且宅第竣工后接着修建寺院,建筑材料也应该早已备足。因此修建寺院的过程只是纯粹的施工过程,这就大大缩短了工期。其次,再依据王振修建大兴隆寺时“日役万人”的记载,认为王振当时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修建寺院所需的人员、材料自会源源不断、绰绰有余,因此施工的速度自然不能以常理推测。因此短期内建成寺庙是有可能的。
第二,认为不可能在两月之内修建完毕,是碑文记载有误。以刘敦桢为代表。他认为碑文与事实不符,怀疑碑文所记开工、竣工年月,未必与事实符合。依据《明史》“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鼐势轻,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的记载,认为王振极有可能在正统八年就已经开始动工修建宅与寺了。
笔者赞同刘敦桢的观点。第一,《明书》中有记载“正统中,振作大第于皇城东。又明年,作智化寺于第左”。这里明确记载了智化寺的修建时间是在王振建宅后的第二年。根据《明史》“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的记载,王振建宅的时间应是在正统七年,那么智化寺的开工时间就应是正统八年,完工于正统九年三月。修建一座寺庙花费一年多的时间是比较合理的。
第二,从建筑来看,智化寺占地两万多平米,建筑又十分精美,佛像无数,还有三个藻井,就算当时王振权势熏天、统一规划、材料充足、“日役万人”,也不可能在不足两月的时间内完成如此规模庞大的工程。具体来看,智化寺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分东中西三路,主要建筑多为歇山黑琉璃筒瓦顶。中路又分为前后二部,前半部由山门、智化门、智化殿、万佛阁组成,建筑体量逐渐增大。后半部由大悲堂、万法堂及东北角方丈诸建筑构成。中央前半部的建筑只能由山门进入,后半部则既可由山门进入、也可由东西两侧旁门进入。而东西两侧的旁门各有甬道,东侧直达方丈处,西侧直达后殿(即大士殿,位于如来殿西北角的小殿)及西侧各平房。这种规模的建筑就算在今天也不可能只花两个月便完工。
二、寺运考——“土木”、“夺门”之变与智化寺的兴衰
1.“土木之变”之前的兴盛
作为权宦家庙,智化寺自建寺起就极尽奢靡,香火不绝。《明史》中载“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敕赐智化禅寺碑中载:“寺之建也,殿、堂、门、庑,各以序为,与夫幡幢、法具、疱福、廪庾之类,靡或不备。规制弘敞,像设尊严,涂墍坚完,采绘鲜丽……”由此可见当时智化寺的宏大规模与完备设置。
王振对于佛教一向是推崇有加的,明英宗对王振的行径偏袒不已。《明史》中有记载“初,王振佞佛,请帝岁一度僧。其所修大兴隆寺,日役万人,糜帑数十万,闳丽冠京都。英宗为赐号‘第一丛林,命僧大作佛事,躬自临幸,以故释教益炽。”在这种情形下,智化寺在“土木之变”之前一直维持着繁荣兴盛的景象。
2.“土木之变”之后的衰败
正统十四年(1449年),王振不顾大臣于谦等人的反对,力劝英宗亲征瓦剌,却由于缺乏应敌经验而大败,明英宗于土木堡被俘,王振也在此次乱军中被杀,并随后被抄家,其家中所藏金银珍宝数量之巨令人咋舌。智化寺受这次事变的影响,在失去了王振及明英宗的特权庇护后,渐渐衰落了下来。
3.“夺门之变”之后的中兴
王振死后,明英宗于景泰八年在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等的帮助下复辟成功,重新称帝,废景帝仍为郕王,史称“夺门之变”。复辟之后,英宗依旧对王振念念不忘,于是便在智化寺中大肆为其招魂祭祀,赐其蟒衣玉带,建祠立碑以表其“忠义”。随后的几年里,英宗又通过御赐佛教经典给智化寺等行为,显示了他对该寺源源不断的重视与恩宠。
在英宗为王振建祠立碑赐经之后,智化寺一度兴盛起来。寺内存有民间捐资修造的铁罄、铁炉等物可以为证,像如来殿内铁罄为弘治十年(1497)通州惠德乡驹子马房信女李慧聪造,铁炉为万历二十八年(1600)郝瞰造,另外还有民间捐造的铁钟等物。
此外,明清时期有太监或僧人对智化寺进行了几次修缮,也证明那段时期智化寺的生存状况还是不错的。分别是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司礼监管监事等太监聚资重修寺宇;清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住持宗果等再次募资重修。
4.清乾隆之后的衰微
智化寺的命运在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再次发生了转折。是年正月,协理陕西道事、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途径智化寺,见“其后殿西庑,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绝。殿西檐下,现有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对于这番景象感到十分气愤,认为王振“窃柄弄权”、“罪恶滔天”,民间却不明其罪恶反而继续在他的家庙中进行拜祭,这种情况是令人无法容忍的。因此上奏乾隆皇帝,拆毁了王振塑像,凿掉了石碑上王振的名字和颂文,以示朝廷对以王振为代表的权宦的打压。经此打击,智化寺的寺运日渐衰微。
5.民国时期的智化寺
这一时期的智化寺情况复杂。一方面,延续了清末以来的颓势,寺内僧俗杂居,僧人依靠出租房屋、外出应酬佛事为生。他们不能严守戒律,甚至有僧人拥有名义上的“妻子”。还发生了住持普远盗卖寺内藻井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民国时北平社会局等政府机构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寺庙登记制度,智化寺在住持、庙产等方面登记得比较详细,从此有效防止了寺僧瞒报寺产的情况发生,使他们无法再打倒卖寺产的主意,也为后人留下了较为翔实的史料以供研究。同时社会局还批准对该寺进行了几次修缮。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智化寺没能延续鼎盛时期的状况,总体而言是日渐势微的。
6.建国初期的智化寺
新中国成立后,智化寺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发生了许多改变。
(1)僧人情况
20世纪50年代在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等运动的影响下,寺僧们纷纷还俗参加生产劳动,相继离开了智化寺,寺中保存的古老的京音乐也随着僧人而流散。
(2)建筑情况
建国初期,寺内僧众继承了民国以来的传统,依然依靠出租房屋和应酬佛事为生。作为寺产的周边房屋也仍然为贫苦人民杂居。后来由于智化寺难得的古建价值,在寺内僧众还俗后,北京市文化局工程队于1955年进入寺中进行整修,同时迁走部分院内住户。1957年,智化寺被评为北京市第一批古建文物保护单位。1958年由北京市政府拨款整修智化寺,并于1961年被评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时期”,由于文化局的工程队一直在寺内进行维修工作,再加上智化寺属于文保单位而非宗教单位,才免于被砸毁的下场。寺内乐器也都搬至广化寺。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智化寺仍然很荒芜,现在智化寺的孙素华主任回忆,1981年她来智化寺工作的时候,寺内的草有一人多高。
至2010年初笔者根据北京市文物局划定的“智化寺保护范围”前往智化寺及其周边的胡同进行实地调查,发现划为文保单位的智化寺主体建筑本身在不断的修葺与文保人员的努力下保存完好,而作为寺产的小牌坊、武学、大方家胡同内的民居保存情况相对较差,存在较严重的私搭乱建情况。东路小牌坊胡同和北路大方家胡同尚能看到几座附属于智化寺的古建,西路武学胡同则很少能从外观上看到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了。
(3)寺内京音乐的保存
建国初,智化寺保持了清末以租房、做法事、承办停灵业务为生的境况。据杨书清奶奶回忆,智化寺当时给人承办红白喜事,鼓楼内就存放着红事用的轿子。她亲眼见过在智化寺内搭棚子办丧事,而且当时寺内存放着很多棺材,这与常人春记载的智化寺有“承办停灵暂厝业务”是相吻合的。另外,根据艺僧本兴的回忆,他曾给金鱼胡同的一个名叫那中堂的人上过白事。从文献资料及当事人的口述看来,清末直至建国初期,智化寺以承办红白喜事作为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智化寺京音乐也因此被广泛地应用于北京的红白事当中,颇有名气。
三、寺主考——问题的混淆与厘清
1.寺主传承谱系存在的问题
智化寺住持的代数问题从没有受到过质疑,每代住持姓名的出处不是史料就是僧人口述,似乎都有据可查。然而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是发现了不少疏漏和错误的地方。一直以来,通行的智化寺住持传承谱系的版本是:第一代,然胜;第二代,常钦;第三代,性道……第九代,隆铉苍公……第十一代,笃修德公……第十三代,宗果……第十五代,容乾……第二十四代,宗权;第二十五代,普远。
实际上,这个住持传承谱系存在许多错漏之处:
第一,容乾并不一定是智化寺的住持。该谱系中第十五代住持注明为容乾,此处的依据应是在寺中发现的康熙三十三年《音乐腔谱》上,写着“岁大大清康熙三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容乾记吉祥如意”,即此乐谱为智化寺僧人容乾所抄写。手抄乐谱的容乾为智化寺的僧人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仅凭此一份资料却实在无法断言此人必定为当时智化寺的住持。
第二,缺少了住持“定然”的名字。定然为智化寺第二十四代住持。北京市档案馆中的“智化寺财产登记表”中记载“民国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定然和尚圆寂,普远接充住持。”这段记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的确存在“定然”这位住持。第二,定然是在普远之前的住持。普远为二十五代僧人,那么定然就应是智化寺第二十三代住持。
第三,宗全并不是智化寺的住持。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根据庙产普查登记及后来僧人们的回忆:宗全为普远的师傅,因而想当然地以为宗全应该是普远的前一代住持。事实上,宗全的确是普远的师傅,然而宗全却从未担任过智化寺的住持。普远是直接从师爷定然手里接的法座。档案资料可以证明住持在定然、宗全、普远之间的住持交接问题:
“(北平社会局调查人员——笔者注)问:前报住持系普远,现报又为宗全,何以不符?答:宗全系我师父。我于十七年接祖师定然法座。因我师懦弱,不爱管事,故由我接座。已在公安社会局登记有案。今因我外出,我师故代为报登记。不知手续,故前后出现错误。”
这种说法得到了智化寺的老僧人关永年回忆的印证。关永年今年80岁,他因家贫而在8岁的时候被送入智化寺,一直待到十二三岁才出寺。据他回忆,当时寺里有九位和尚,分别为:宗全、普远、曾远、瑞广、法广、福广、俊广、云峰、祥峰,其中普远为当家的,宗全虽为普远的师傅,却不管事。
第四,漏掉了一位同治年间的住持——“师太祖”。在寺庙调查表中提到了同治年间,普远的师太祖首次领了庙产执照。如果普远为二十五代住持,那这位“师太祖”就应为智化寺第二十一代住持。
2.寺主传承代数的补充与纠正
由此可见,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前人对于史料考证的不甚严密,导致了错误的传承谱系诞产生并以讹传讹地流传至今。纠正后的智化寺住持传承谱系应为: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普远为智化寺第二十五代僧人,但由于他直接从师爷手中接的住持法座,因此应为第二十四代住持。第二,传承表中标有“?”的部分表明目前证据不足,尚无法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