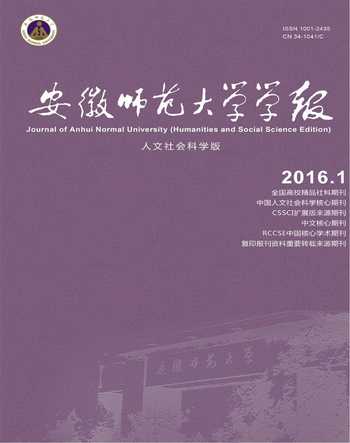教育体制改革的破局与立势
阮成武
“破”与“立”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运动而又对立统一的两面。新时期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四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等四个重要文件,直接领导和开展新时期以来四轮教育改革。其中,《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实现教育体制改革的破局与立势。主要在于:
一、破教育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局,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之势。
作为与《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配套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中心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小平同志指出:“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注:该决定第九条指出:“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中央将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作出相应的决定。”)《决定》打破长期以来教育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相适应的局面,“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将教育纳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来,“使教育事业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一个大的发展”,努力“把教育搞上去,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决定》开篇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要求“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首次提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应当说,此后中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优先发展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论断,都发轫于此。通过四轮教育改革,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固化和落实,上升为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破教育桎梏于计划经济体制之局,立教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改革之势。
改革开放之初,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百乱待理,教育作为“文革”重灾区更是积弊深重,但“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大学无论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胡启立语)。这与经济领域存在的“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是根本一致的。《决定》正是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决定提出的“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在遵循教育规律的同时,将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机制引入教育改革,建立更具活力的教育体制机制。
首先,基础教育实行“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因地制宜,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按不同进度和要求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以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办学的积极性。除大政方针和宏观规划由中央决定外,基础教育具体政策、制度、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对学校的领导、管理和检查,责权交给地方;乡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教育,并可以征收教育费附加。其次,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在城市要适应提高企业的技术、管理水平和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在农村要适应调整产业结构和农民劳动致富的需要”。第三,高等教育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高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赋予高校六个方面的自主权(有权在计划外接受委托培养学生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的服务方向和制订教学计划大纲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虽然这些政策在后来改革实践中历经曲折,甚至受挫和出现偏差,但它划出了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的道道底线,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确立了起点和方向。
三、破政校不分、政事不分之局,立政府、学校、社会间新型关系之势。
一直以来,各级各类学校由政府举办,经费投入、课程设置、教师配置、毕业生分配,由国家掌控。这一方面造成政府严重的财政负担和“统招统分”“包当干部”的人事负担,陷入“穷国办大教育”的困局;另一方面,政府对学校“统得过死,使学校缺乏应有的活力;而政府应该管理的事情,又没有很好地管起来”。教育行政部门对人、财、物统得过死,而真正需要协调统筹的事情却因条块分割而相互掣肘,学校缺乏自主权、社会缺乏参与权、学生缺乏选择权。
基于此,《决定》开始启动了政府职能向学校、社会让渡的破局之举,着手构建政府、学校、社会间新型关系。如:基础教育鼓励和指导国营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并在自愿基础上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职业技术教育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或与教育部门合办,接受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学生。高等教育改变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将用人单位委托培养作为计划招生的重要补充,允许在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毕业后推荐就业或自谋职业;同时,明确高校后勤服务工作社会化改革方向。此外,要求教育管理部门组织教育界、知识界和用人部门定期对高等学校办学水平进行评估;鼓励人民团体、社会组织、集体经济单位和个人积极自愿地为发展教育贡献力量;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教育立法工作。可以说,《教育规划纲要》确立的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教育管理体制,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学主体多元、办学形式多样的办学体制,我们已经从《决定》字里行间中听到它最初的脚步声了。
总之,“教育要发展,根本靠改革”。30年前,小平同志认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30年来教育改革实践,更是彰显了《决定》实现的教育体制改革破局与立势的历史意义与未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