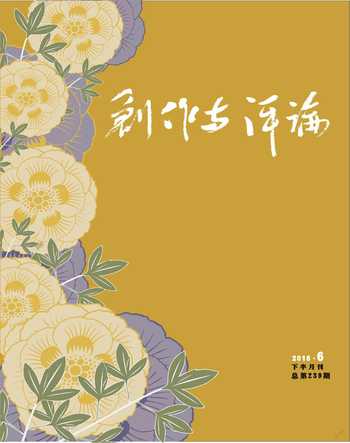《塔洛》:藏地的现实与诗意
陈伟
西藏之于大多数国人来说,通常代表着高远、圣洁、虔诚和神秘,从画面形象上来看,洁白的雪山,湛蓝的天空,圣洁的哈达,孩子脸上那一抹天然的“高原红”……对于很多国人来说,雪域高原西藏是他们向往的一块精神圣地。但西藏显然并非只有这一副面孔,它还有更多侧面。万玛才旦导演打开关于西藏的现实大门,用影像诉说着西藏的现实,并以此为根基追寻着超越于人们主观想象的藏地的诗意。他用“藏地故乡三部曲”推开了一道门缝,用《塔洛》完全将这扇大门打开。影片以简洁的叙事,独特的镜语,呈现了少有的藏地现实图景,含蓄的隐喻和冷静的哲思让影片充满了诗意。
一、 故事:藏地的现实图景和
精神空间
《塔洛》讲述了一个情节并不曲折的单线故事,留着小辫子的牧羊人塔洛去县上的照相馆拍摄二代身份证照片,偶遇了理发店的女孩杨措,产生了一种“类似爱情”的特别情愫。杨措希望塔洛带自己出走远方,塔洛经过几番犹豫,最终卖掉了自己的以及帮别人放牧的羊群,并把钱全部交给了杨措。但一觉醒来,杨措早已不知所踪,空留下塔洛孤独一人进退维艰。
导演万玛才旦以拍摄藏语电影闻名,并多次获得国内外的奖项。他导演的影片《静静的玛尼石》《寻找智美更登》和《老狗》被称为“藏地故乡三部曲”,影响深远,被认为是讲述了最真实的西藏故事。万玛才旦以一个藏族人的敏锐视角,坚持用藏语拍摄反映西藏人民生活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影片。与此前的“藏地故乡三部曲”的群体性关注不同,《塔洛》对个体生命进行了深度关注。塔洛身上拥有鲜明的个人符号,个人的简单、孤独,同时充满了关于身份认知的焦虑。理发店的女孩杨措尽管最终卷款而逃,但她对远方世界的向往、与塔洛的两情缱绻,却并非全是圈套的设计和信口胡言。
故事缘起于塔洛办理第二代居民身份证的经历。他在山上长大,帮别人牧羊为生,因为留有一条小辫子,所以别人都叫他“小辫子”,他自己对这个称谓已经习以为常,对于自己的真名“塔洛”反而已经不习惯。塔洛可以流畅地用汉语全文背诵毛泽东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并以文章的精神理念作为衡量自己、判断他人的最高标准。好人“重于泰山”,坏人“轻于鸿毛”,没有中间状态,这也成为他的人生信念。开始,他认为自己帮别人牧羊的行为就是在“为人民服务”,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重于泰山”的人。但当他私自卖掉主人家的羊群,钱款又被席卷一空时,他认为自己成了“轻于鸿毛”的人,信仰的坍塌让他再也不能流畅背出《为人民服务》的全文。 当身份证终于审核通过,他却因为剪掉了小辫子而被要求再去重新照相、办理新的身份证,刚刚获得的“身份”瞬间再次失去。当盗卖羊群的事情被拆穿,相信他会失去更多。“身份”,在他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空间中,均成为稀缺品。
经营理发店的杨措是塔洛见过的唯一一位梳着短发的藏族女孩,她身上的野性与柔情让见过女孩本就不多的塔洛坠入了情网。杨措喜欢唱歌、听歌,渴望去看外面的世界。她鼓励塔洛勇敢地带自己远走,当塔洛把一叠叠钞票依次摆在面前,她也曾心动,但随后的卷款而走让之前的所有形象都仿佛蒙上了一层玻璃上的磨砂,此前的一切到底是真是假?按照塔洛的逻辑,杨措绝非“重于泰山”,但真的就“轻于鸿毛”吗?模糊的面目亦如镜中映出的景象,有着令人生疑的虚假。
改变塔洛和杨措命运的核心事件是塔洛卖掉羊群,而推动塔洛做出这一决定的直接原因是主人的三个巴掌。羊被狼咬死后,闻讯赶来的主人连扇了塔洛三个巴掌,现实的骨感瞬间击溃了此前形成的美好与恬淡。第一巴掌,主人说, “你又钻到酒瓶子里去了” ?!掏出一瓶酒,“你喝啊”,瞬间扔掉摔碎;第二巴掌, “你不知道你就是个放羊的吗?”;抽一口烟,第三巴掌,“记住,你就是个放羊的”!这三个毫不留情的巴掌肆意碾压着塔洛原本卑微的尊严和平实的梦想,彻底击溃了塔洛自信,此举直接导致塔洛做出了卖掉了羊群的决绝之举。其实,无论是影像世界还是现实生活,在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中,被扇巴掌是对尊严和自信的最大伤害,多深的情谊都可能瞬间崩塌。
就空间而言,片中没有出现人们常规印象中的藏地图景,而是以冷静的写实主义手法呈现给人们一个正在转型和变革中的精神家园。在物理空间中呈现的高山没有了巍峨与神圣,城市在变革中与其他地区的景观逐渐趋同,人们的身份疑虑久未散去,出走的梦想离实现越来越远。影片跳出对故事的封闭讲述,以单一的线索,平实的情节,结合黑白影像和固定机位的致敬经典式的镜语,以简洁的故事为载体呈现了藏地的繁复的社会图景。
二、 叙事:镜像隐喻与诗意哲思
在追求4K甚至更高影像品质的技术语境下,《塔洛》采用了经典的黑白影像的表现方式,这一选择被导演万玛才旦解释为是为“凸显塔洛的状态,他的孤独感,他的外在世界或者内在的精神世界。他是一个很简单的人,他的世界也很简单。”{1}黑与白的色彩呈现及对《为人民服务》的信奉折射了塔洛的二元对立的思维世界,要么“重于泰山”要么“轻于鸿毛”。当斑斓的色彩被减至只有黑白,人物形象同时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普通的牧羊汉子和美发少女成为了“大写”的人。
固定机位的镜语运用让黑白影像有了更具张力的纵深空间。在电影发展史中,从固定画面向运动画面的转变曾开启了电影语言的革命。而在电影语言融合多变的当下采用固定机位进行叙事,这是对影像语言的一次溯源,也是作者风格的一次彰显。影片伊始,塔洛全文背诵《为人民服务》并和所长进行对话时,导演采用了十余分钟的固定机位与长镜头的结合,一气呵成,酣畅淋漓。
镜子作为隐喻手段在影片中的运用是《塔洛》的典型叙事特色之一。派出所的办公室里,理发店的墙壁上,镜子在影片中的出现如同有源音乐自然合理,既拓展了空间的物理属性,更从抽象层面上建构了诗意。
镜子作为隐喻手段,在中外的艺术创作中均有呈现,也成为艺术认知的重要范畴之一。溯源至人類哲学的原初时代,西方的柏拉图“用镜子作为比喻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模仿本质”{2},而在东方,比柏拉图早一百多年的老子、晚一百多年的庄子都用镜子比喻人之心境。在民间话语中, 百姓用想象出来的“照妖镜”完成对人与妖的辨识,用“明镜高悬”寄予对贪官的监督和对清官的渴盼等。乐黛云先生通过类比之后认为,“西方诗学都是用镜子来比喻作品,作为镜子,首先被强调的特征是逼真……逼真地反映内在心灵”,“中国诗学通常不是用镜子来比喻作品,而是比喻作者的心”{3}。镜子在电影中的出现也不鲜见,既可以作为实有物丰富画面表现的视角,也可以作为隐喻表达抽象的意义。比如在《一个勺子》中,“拉条子”每次从“大头哥”的车上下来,接下来的镜头大多都是汽车后视镜中“拉条子”形象的渐行渐远,隐喻着“拉条子”一次次地被抛弃与被忽略。而在《塔洛》中,派出所、照相馆、理发店等镜子首先是作为物理空间的日常设置而存在的,固定机位的拍摄手法和镜子的结合运用,首先从镜头语言上实现了视角的更新和空间的重构,特别是在理发店内,两块镜子的反射与真实空间形成了全新的互动关系,人物的行动实现了虚实之间的空间穿梭。其次,镜子作为一种隐喻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了反射。影片中有两处处理最为典型:一是塔洛将卖掉羊群所得的钱款一叠叠摞在梳妆台上,杨措走出镜像空间将钱悉数抱起,镜中反射出的诚惶诚恐的表情变化反映了她内心当中受到的震撼及瞬间的心动,而当她返身回来坐在旁边, 形象通过另一面镜子反射出来时,她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又变成原来的杨措了”{4}。第二处是在影片的结尾处,当塔洛再次来到派出所,准备取身份证时,墙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通过镜子的反射变成了反转的,而塔洛因为信仰的崩溃和内心的慌乱,眼中的世界已经开始颠倒,他也再不能流利地背出《为人民服务》的全文。
黑与白的影像处理,固定机位的设置,镜像隐喻的运用,让《塔洛》呈现出了简洁、宁静、含蓄的风格,加之故事内部节奏的舒缓,整部影片充满了浓郁的诗意,引人遐想与思考。
《塔洛》所呈现出的藏地图景与之前几乎所有的影片都不同,西藏不再只是外人主观臆想的精神家园,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结合导演本人的“藏地故乡三部曲”来看,影片所表现的现实愈加厚重、深沉,作为个体的身份焦虑愈加严重。同时,导演以写实的创作手法开始深入探寻民族精神的源泉,回到“黑与白”的简单,回到“为人民服务”的本真年代,重新定位社会转型期内的个体身份和民族认同的嬗变。导演没有落入浅表化的俗套,而是以冷峻的视角深度反映藏地的现实,并通过个人探索式的艺术表达,使影片呈现出了更为厚重和苍凉的诗意。
注释:
{1}④万玛才旦、刘伽茵、江月:《或许现在的我就是将来的他——与《塔洛》导演万玛才旦的访谈》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2}③乐黛云:《 中西诗学中的镜子隐喻》,《 文艺研究》1991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
——来处已然消失 归途无所觑见
——以万玛才旦的《塔洛》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