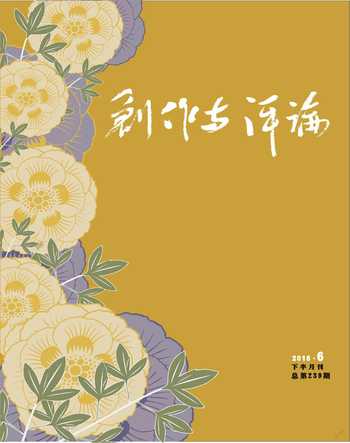思无邪,桃花源里可耕田?
艾翔
如果你以为这又是一个女主为了男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缠绵悱恻的情感泄洪的故事,如果你以为韩剧要统治我们的叙述方式,然后产生了阅读的震惊,那么你或许不会觉得我在夸大其词,戴潍娜的这篇中篇小说让真情的面目重新大白天下。
想去国际化大都市并政治中心北京的近郊十渡摆脱情感的困惑和人生思绪的瓶颈,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部分被放在了“引子”,后面不是要倒叙,仅仅是后来去漓江碰触梦幻般“精神艳遇”的叙述动因。从第一节开始,女主角朵朵就去了远离尘嚣的桂林,不是那个游艇汽车轰鸣不绝、旅行团川流不息、特产纪念品沿途不断的旅游城市桂林,而是一个人迹罕至、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在这个被称作“静水深流”的偏僻景点,路遇一片果园,色泽观感诱人的美果让女主角忍不住摘下饱尝,之后手足无措时受到向导老彭的宽慰,只要用小夹子将些许零钞晾在绿藤上便不会引起果园主人的愤恨。这就是叙述者带领读者领略的与世无争之地的第一印象,与之前那个喧闹的蹦极台判若云泥。天色将晚,女主角按照老彭指的方向来到老彭姑妈家,这个姑妈也是一个准时退休绝不留任的闲云野鹤,经她手的野菜让作者都不得不专门发明了“醉饭”一词形容。江边的千年古树让女孩产生了“原始的安全感”,并偶遇了裸泳的小男孩,女孩欢乐地称其为“小肥皂”。这里确乎是个充满神迹的居所,江边常有大鱼跃出,女孩一捞就有一只“重得坠手”的大鱼入怀,鱼也不挣扎,只是盯着人看。夜晚更有泛神的感觉,不但是能够和其间的花草鸟兽气息相通,更给朵朵带来了一个关于画展的神奇的梦。
凤凰古树下同“小肥皂”看似无法“并轨”的谈话,除了让女孩又一次露出纯净的笑容,更展示了女孩“脱俗入圣”的一个过程:表面上没有知识、阅历和逻辑的“小肥皂”其实成了反复教导言必称世俗言辞的朵朵挣离凡尘的“导师”,朵朵虽然理性判断“小肥皂”为童言无忌,但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自己思维的困窘之处。作者在后记中说《仙草姑娘》收录的故事都是“梦话”转述,“精神深流”当然带有梦境的色彩无疑,然而这个梦境却又并非是不真实的,并非先锋文学跳跃的梦呓表达,而是遵循着彻底的因果律、真实论。女孩远走桂林,就是因为十渡“忘却”的不彻底。抵达此一偏远景区后,一度欢愉的心情出现过“大叔”的闪回,严守着遗忘曲线。在与小肥皂的对话中,朵朵先“按照书上的说法背出来”针对小肥皂疑问的答案,被后者机智地否定后以宽容的笑默许了小肥皂的任性。
“背书”和“难忘恋情”本质相同,都是由没有主体身份的脆弱女孩发出的动作,要么依赖于知识的权力体系,要么委身于尊男的情感模式,而她自己要么以顺从的“无我”姿态出现,要么以敏感的“自我”形象示人。到了充满神迹的自然天地,主宰法则不再是世俗的权力体系,而是“思无邪”,是“别想多”,是“做自己”。所以桃花源里的朵朵表面上只是在以忘记历史的方式躲避俗尘,同时也是在完善自身。道士“发气”为其治疗身体不适,未尝不可看作借助世外之事修身养性。道士说自己“信道不信教”,女孩没有丝毫惊讶而追问,事实上作者也说过相同的话:“我信佛不信教,信道不信教,信基督不信教。”通过信与不信、接纳与拒绝的传递,建立真实的个体认知,并以此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干扰。
小说从对“大叔”的世俗之恋走向对“S”的精神之恋,始终都是男女爱恋的主题。如果说小肥皂预示了这种转变的走向与可能,到了道士这里转变就明确完成了,女孩因受“发气”而浑身舒爽时,叙述者在一旁淡淡地发表议论:“世间万物一比较就能高下立分,比起这份能把人融化的舒服,尘世男女一味追索的身体快感都只是隔靴搔痒,不痛不痒。”这或许是整篇小说最为“直露”的一句,也是最能表达立场的一句。除此之外文章都纯净得晶莹剔透,没有一丝邪念分散注意力,关注点始终聚焦在感情本身。说这是童话,除了其中虚幻飘渺的意蕴,这种洁化叙事恐怕也是很重要的一点。不过有意思的是,相比原版本《格林童话》充斥民间故事携带的大量色情、暴力、恐怖等因素后来所经历的不断修改、删节的过程,《那个名叫S的灵魂》带有鲜明的创作色彩,从一问世便是翠绿鲜艳的色泽。当然,这里可能涉及到关于“童话”指涉的“儿童”这一近代以来被“构建”出来的概念,如果不考虑启蒙运动以后“儿童的发现”,童话中的色情成分能否被容忍,以及多大程度的容忍,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戴潍娜相对格林兄弟大抵更接近安徒生的传统,文本更为澄澈,平淡而非离奇的叙述和其中的哲理意味更能吸引成年读者。但差异同样显著,首先是安徒生的作品大多色调低沉,充斥着较多哀婉、悲凉的负面情绪,戴潍娜则更为轻快灵动,《那个名叫S的灵魂》就很具有代表性,即使后来发现自己清新的“S”难觅踪迹,仍然维持着内心的丝丝甜蜜。此外,安徒生一开始就是明确为儿童写作,戴潍娜并没有明确的预期受众,这些玲珑的小故事用她自己的话是“從神秘奇诡的梦境中领出”。从成品来看,她应该还意图保存我们天性中那些最本真、最可贵的部分,抑或说是主动创造这样一种本真和纯净,作为我们面对不堪的现实最后的勇气、底气和退守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戴潍娜的小说似乎更接近由被“近代”追认的“儿童”界定出来的“童话”概念,是在为成年人想象中的“儿童”——或者说是被玷污的成年人对自己理想状态的幻想——书写这一个奇异的世界。作品同现实的儿童可能并无太大关系,孙郁教授的评价是“小说自成一格,有童心和神性的因素,带有出其不意的想象力。故事很感人,相是童话与神话的交织,意识流盼中多见奇气”,我以为是切中恳綮的。李贽在《童心说》开篇直陈:“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后有文气充沛的宏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童心不是幼稚,相反追持童心才是真正的成熟和独立,或者也可以说是“思无邪”,是“别想多”,是“做自己”,戴潍娜的“童话”正是“童心之话”。藉此我们或许可以反思高等教育的学科划分和专业方向,“儿童文学”定义导致张天翼、老舍、冰心等作家被人为割裂在两个专业方向上,无法形成整体形象与贡献认定,另外如豪夫童话、《格列夫游记》《西游记》等原本丰富的社会讽喻也遭遇窄化理解。童话应该只是风格或体裁的划分,而不是目标人群的界定,更不是文学等级的标志。
或许可以说,她笔下的神迹和胜境,不是亚里士多德转引索福克勒斯的话中所谓事物“本来的样子”,而是按照事物“应当有的样子”来描绘,事实上历史中不少被视为童话的文学作品都与浪漫主义有些许联系。《那个名叫S的灵魂》同作者的其他作品一样,带有浪漫主义风格和唯美色彩。即使后来朵朵发现再也找不到“静水深流”以及在那里遇到的各种人导致怀疑其是否真实存在,但她并没有否认乌托邦的意义,甚至将种种美好幻化成了一个人形,一个名叫S的魂灵,用以情感投射。恬静的自然,充沛的情谊,飘渺的梦境,天真的孩童,超然的老道和姑妈,淳朴的果园主人,审美化的生活,追逐迅逝的灵感,现在又多了一些神秘主义,所以当作者称她希望灵性修行能够获得推广,熟识以色列的通灵大师并获得其对自己作品的推荐,也就不会令人感到任何意外了。她以自己的写作提示着我们浪漫主义和童心之间的关系。
这篇关于情感的小说如前所述,通过一种形式上的逃避实现了女主角身份意识的觉醒。《那个名叫S的灵魂》所塑造的女性角色是一个遁世者,却也是一个找寻者。长久以来,我们对于争取真正的平等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性化、甚至无性化的“女战士”“女强人”和“女汉子”身上,通过减弱同男性的差别来实现权力的分享,积极意义之外或许也存在一种用古龙香水自我催眠的效果。戴濰娜笔下的朵朵保持着女性的温婉、细腻、感性、向往美好,保持着对两性之恋的神往,但不是一个配角,也不刻意强调两性的差别,有自己的勇气和能量。当然朵朵对性的淡化,并不意味着性意识的淡化,同时也不意味着作者对性的淡化。在《夜的政治:西非“性罢工”》一文中,戴潍娜严肃地谈论着性之于女性权力斗争的意义,关注被遗忘大陆的被遗忘群体。张莉在《为什么要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中提到:“女性作家固然书写的是女性生活,但同时也是对那种被时代潮流遗失的生活的记取,是对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的重申。那些沉默的、那些无故牺牲的、那些处于幽暗之地的种种能最终进入我们的公共生活、历史空间,是因为她们的倾听与书写,她们‘让那些看不见的看见,让那些听不见的听见。”戴潍娜坚信如此,只是由于明确的文体意识,在不同场域选择适合的言说方式。
如此种种风格和特质,我以为同戴潍娜的生长境遇密不可分。出生在南方的世代精英家庭,家境优渥,自幼受到艺术熏陶,著名大学受教,有海外留学经历,从事翻译、诗歌创作、小说创作和文学研究,作品被归入儿童文学序列,保有一颗纯净的“童心”和强烈的女性意识,关注社会问题,周身有宗教影响,甚至姣好的容貌和优雅的气质,就差一个社会学家的丈夫和一个互不对付的太太客厅主人,戴潍娜几乎成了冰心的翻版。近年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青年大多丧失了行动能力,以至于充满阳刚之气的《地球之眼》令人眼前一亮。戴潍娜笔下的人物,并未表现出行动力的丧失,因为他们本就很少强烈的行动欲望,他们“思无邪”,他们“别想多”,他们“做自己”,大多是在自己的乌托邦或拟乌托邦的神性世界里。认可独特性的同时,也该警惕冰心的局限性或许也会对戴潍娜形成一种魔咒,毕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想,戴潍娜更好的作品,也许还在未来。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