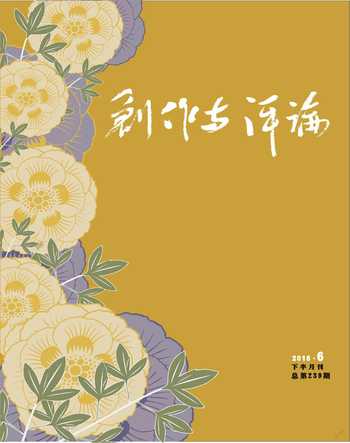熔铸生命经验确立整体观念
马新亚
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有文学作品及其传播、消费和接受以来,文学批评就随之产生和发展,并且构成文学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文学活动整体中的一种动力性、引导性和建设性因素,既推动文学创造,影响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发展,又推动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这就涉及到文学批评标准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由此帶来的时代局限性问题。然而,在一版又一版的文学史教科书不断推陈出新之际,在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批评家不断更新换代之际,我们始终能够将一些评论家牢记在心,将一些精彩的评论片段反复咀嚼。其实,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与批评的经典化往往是相伴相生、相得益彰:例如,金圣叹之于《水浒传》,脂砚斋之于《红楼梦》,鲁迅之于中国古代小说,勃兰兑斯之于十九世纪文学……抛开文学作品的经典化不说,以上的经典批评之所以穿越古今、历久弥新,就是因为批评家能将生命经验熔铸到文学经验之中,并将文学与文化之间的血脉打通,对文学作品进行整体性的观照,使批评既带有生命的体温又带有形上的追思,并进而借批评营造出作者、读者之间沟通、对话、碰撞的流动性意义空间。我想以上也可以为我们今天思考文学批评标准有效性问题提供一些借鉴价值,特别是在这个写作门槛降低、批评标准多元化的多媒体时代。
1980年代,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用“现代文化”代替“政治文化”的风潮,钱理群、王富仁、吴福辉、杨义、赵园、刘讷、许子东、凌宇等并称为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第三代的学者,他们在新时期将被社会意识形态所遮蔽和尘封的文学资产进行清算和重估的历史关口和文化行将断裂的历史情境中,以不可遏抑的学术激情和人文情怀参与文化重构,完成了一种对颠倒了的历史的再颠倒,并在这种重新认知与评价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文学史观与评价体系,完成了对过去的现代文学史观——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组成部分及其评价体系的解构,并为“重写文学史”运动拉开了帷幕。这便是他们那代人的学科贡献。就方法层面来讲,这代学人所操持的大多是文化心理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而这种偏重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话语模式也造成了这代学人批评话语的时代局限性;1990年代以来,“随着大学研究生教育培养机制日臻完善成熟,大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迅速涌入大学和科研院所”①,形成了庞大的“学院派批评阵营”。学院派批评以完整的知识储备和广阔的视野亮相文坛,极大地拓展了当代文学的阐释空间,他们多以西方的“新批评”为支点,以文学为本体,展开深入系统的专业性研究,进一步摆脱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模式对文学的干预,为文学创作和批评营造了更加自由的表现和阐释空间。但学院派批评所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于追求阐释学的深文周纳,而忽视批评家的主体性,忽视感性印象和直觉判断在文学批评中所起到的作用。当然,少数具有敏锐感受能力、自觉文体意识、强烈主体精神的批评家不在其中,例如:王尧、谢有顺。如果将最近几年崭露头角的批评家也包括在内,那么还应包括:梁鸿、张莉、李云雷、杨庆祥、房伟等。在这几年做编辑的工作经历中,我发现这些批评家往往是“多面手”:左手写评论,右手写原创;用大量的作品阅读和文学理论阅读来支撑评论,又以个体的写作经验来实证批评;对于理论,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极大地避免了批评的画地为牢和自说自话。例如,王尧不仅研究散文,而且创作散文,不仅从学术的立场为“文革”中的知识分子绘制精神图谱,还从个体经验的立场抒写了时代对知识分子的冲击以及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情感历程。王尧以生命经验所带来的情感力量和精神能量,逼视着过分精细化的学科知识所带来的理论僵化,以感性的颖悟和生命的体温冲决横亘在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厚障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批评应有的生命力,正如他在《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所坦言的:“我不明白,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消失。”②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作家,也适用于批评家。作为写作者,如果失去了对生活的个体化感受力,失去了对语言文字的敏感度,那么必然会被这个媒体语言无孔不入的同质化时代所吞噬,进而失去书写的有效性。那么什么是书写的有效性呢?以批评为例,我认为批评的有效性首先是“悟”,“悟”就是“不隔”,“悟”就是能够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熔铸到批评中,用感官、体温、心灵去贴近作者,贴近人物的血肉人生,用常理、常情去思忖。强调“悟”并不是要彻底摆脱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论、启蒙话语体系、后启蒙话语体系、后殖民主义理论、“新批评”理论等外部理论体系的束缚,而是要适当摆脱社会意识形态或学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的身份,放低姿态,摒除杂念,将“艺术经验”与“生命经验”相结合,用接近艺术本身的方式接近批评的真谛。
用生命经验去“悟”,并不是闭门参禅。单纯依靠个人的才情孤军深入,终有捉襟见肘、才力不逮之时,所以“悟”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整体观念,只有将文体细读、知人论世等功夫做足,才有望做到“悟”。在这一点上,李长之的批评观值得我们借鉴。他在《杨丙辰先生论》开篇就讲:“读读克罗齐的批评,便知作批评时当仔细注意作品,读读勃兰兑斯的批评,就知道作批评时当仔细注意作家生活”③,这显然就是强调一种整体论的批评观:首先,要通过文本细读,从语言文字的通道走进作家的心灵,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批评八股,才能避免国族、启蒙等话语体系对个人存在的遮蔽;其次,要做到知人论世,从生成论的视角深入了解作家之为作家的全部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家族、历史际遇、风俗民情、气质禀赋、精神、心理等等。例如,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对魏晋时代风尚的引入,就堪称经典;又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将鲁迅拉下神坛,从一个被时代造就也被时代碾压的“人”的视角,考察了鲁迅一生的几次重要选择以及选择背后的挣扎与矛盾,甚至对鲁迅精神深处的封建意识和填充于每次绝望之间的刹那主义,也丝毫不避讳。正是这种知人论世的批评观,支撑起了这部书的立论依据,也提供给鲁迅研究界一个与众不同的视点。
笃定流畅的行文、斩截有力的判断来自批评家对作家的全面整体的了解,来自对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掌握,也来自批评家对文化精神的宏观把控。这里所说的“文化精神”,既包括实体性的中西文化思想,也包括活的文化意识。19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学术观念甚嚣尘上,这种观念产生了一个误区:批评是文学内部的事,与思想无关。其实,文学与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批评与思想也是相辅相成的,正如邓晓芒所说的:“我历来不认为思想与学术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在我看来,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当20世纪90年代有人提出‘思想淡出,學术凸现时,这只不过是一些自以为很有思想的学界中人走投无路时的自我欺瞒的说法。”④在邓晓芒看来,1980年代“文化热”的弊端不是过分抬高了思想的地位,而是由于盲目追求“热点”,而造成学理的浅薄化。介于此,邓晓芒主张采用“新的学术思想”,即将严格的学术作为思想本身内在的风骨,引领思想的灵魂建立自己的基地、居所和世界,使思想真正成为立足于自身生命的、因而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独立主体。邓晓芒所说的“新的学术思想”就是整体意义上的文化意识,也即只有对中西文化思想有全面整体的了解,对活的文化精神有透彻的了悟,才能为批评找到结构性的支撑。造成批评与思想文化脱节的原因,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偏颇的学术导引之外,还要归因于学科专业的过度细化。中国古代教育的方向是“通才”:从横向来讲,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熟读文史哲;从纵向来讲,要通览典籍,融会古今。而现代教育的方向是“专才”,单是文学专业就分出古代、现代、当代数支。专业越是精细,专业之间的区隔化就越明显,对知识结构完整性的挑战就越大。于是,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况是:学古代文学的,对现代思想和文化知之甚少;学现当代的,对古今中西不能融会贯通。理论视野的窄化,造成了“就事论事”的普遍倾向,大大降低了批评的有效性。理论的窄化还以一种变相的面目出现:一些立论虚浮、观点缠绕的文章往往摆出一副扎实严谨的面孔,让人难辨优劣。其实,越是暧昧不清、温吞迟疑,缠绕迂回,就越是暴露出作者知识结构、才智气力的不足,而越是斩截有力、清晰明确就越是能体现作者在学识上的功力。李长之的评论经常是快人快语,利落爽脆,很少有含混之论,这固然与他过人的天资有关,但深厚的文史哲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更是他“在批评工作上毫无踌躇”的原因。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提李长之的批评观,确立整体性观念,贯通古今,融会中西,并在这个基础之上,打通文史哲,将文学批评纳入到文化批评的整体结构之中,确保文学批评标准的有效性。
注释:
①程光炜:《 当代文学中的“批评圈子”》,《当代文坛》2016年第3期。
②王尧:《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页。
③转引自郜元宝:《追忆李长之》,《读书》1996年第10期。
④邓晓芒:《学术中的思想和思想中的学术》,《学术月刊》2001年第10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文联)
责任编辑 佘 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