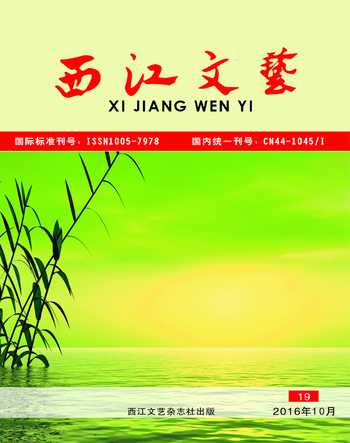民国甘宁青鸦片产业的畸形繁荣
杨钧期 杨志国


【摘要】:民国时期,鸦片种植在甘宁青地区开始泛滥,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种植区域之一。鸦片从广泛种植致使甘宁青地区民众吸食成风,鸦片专业市场开始勃兴,鸦片走私与使贩频繁,鸦片产业呈现畸形繁荣的局面,这也使得甘宁青地区由鸦片引发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变得异常复杂严重。
【关键词】:甘宁青;鸦片业;畸形繁荣
一、甘宁青鸦片种植的兴起
甘宁青地区土地贫瘠,社会极其落后。为改善生存条件,当地民众自道光末年起开始引种罂粟,最初“购种于陕,要试种之,居然成熟。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产烟最多,其味亦浓”。到咸丰时期,“各县皆种矣”。[1]而鸦片价格也随之上涨,受经济利益的刺激,甘宁青地区鸦片种植在清末进一步推广,根据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所言:清末鸦片弛禁之后,甘肃与四川、陕西、山西并列为全国四大鸦片产区。[2]鸦片的产量、品质都比较高,“甘肃所产之烟,名为‘西土与‘广土'、‘南土'交称'”,[3]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皋兰五泉山所产的鸦片俨然是地方名产,武威所产烟名“水浆”亦有时誉。种罂粟可比种植其他农作物的收益高三至五倍。烟土市价最高时,每“百两需银六七十两”,价低时每百两也“需三十余两”。[4]
鸦片种植在民国时期大规模泛滥开来。据相关资料统计,整个20 年代至30 年代中期,“甘肃烟田占全省农田四分之三,鸦片产额占农作物90%”。[5]天水“出城遍地是烟苗,东从校场至二十里铺、东泉、甘泉,西自坚家河、天水郡、太京、耤口、牡丹、杨家场等地的大片土地都种植鸦片,其中牡丹、杨家场烟农最多,几乎家家户户都种鸦片”。[6]宁夏城附近的通贵堡“农场作物,罂粟约占35%,麦及杂粮约占百分之三十,未种闲地约占百分之三十五”。[7]在中卫,“人们走过这个盆地时,从四面八方看去,凡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正在开着的白罂粟花”。[8]一收到获季节,“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9]1934年,宁夏鸦片产量为1196担,次年增至7140担。1935年,甘肃的烟苗面积达50多万亩,总产量2000万两。其中:伏羌(今甘谷县)种烟20余万亩,产烟达1000万两以上,有烟店200余家,每年销售800万两。榆中县种烟12000余亩,产烟42万两。“七·七”事变前,按宁夏官方的保守估计,常年鸦片种植面积为20万亩,烟土产量达7305万两。[10]1934—1938年甘宁两省的鸦片种植数量详见下表:
1934—1938年甘宁两省的鸦片种植数量统计表:
资料来源:《禁政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二(2)-342;《禁烟统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二(2)—334;内政部编印:《禁烟纪念特刊》,1939年6月。
二、甘宁青鸦片产业的畸形繁荣
(一)民众的鸦片吸食
甘宁青鸦片种植的泛滥,直接导致民众吸食鸦片成风。林竞1919 年3 月在甘肃考察时发现,“肃州人口全县计九万余,十人之中,足有七人吸鸦片”。[11]武威“据闻男子吸烟人数,约占百分之五十,女子较少,然亦占百分之三十”。[12]据统计,1937年甘肃全省总人口为5997325人,吸毒者则多达179651人,占总人口的3%,有的县吸毒者占(全縣)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0%以上;武威吸毒者最多,共17427人;皋兰次之,15755人;天水第三,12097人。[13]在不种鸦片的青海互助县,尽管鸦片“价贵值昂,购求不易”,但仍有“吸食成瘾者,约占全县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二以上。”[14]据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统计,甘宁两省烟民具体人数如下:
1935-1939年甘肃、宁夏烟民登记统计表
资料来源: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二十四年禁烟年报》、《二十五禁烟年报》、《二十六年禁烟年报》、《二十七年禁烟年报》、《二十八年禁烟年报》、《禁烟概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十二(2)。
与此同时,青海民众吸收鸦片现象也非常普遍。青海“当时社会上,尤其是汉人中间吸鸦片的恶习很盛,上自官僚地主,下至乞丐妓女,大都吸烟成癖,与官办以及私贩烟土者,结成不解之缘。还有不少福户子弟,不务正业,嗜好鸦片,以至倾家荡产,丧失生命。”[15]当时社会上,尤其是汉人中间吸食鸦片的风气很盛,上自官僚地主,下至乞丐妓女,大都吸烟成癖。不少殷实之家,富户儿郎,一榻横陈,百业不务,一经上瘾,则倾家荡产,鬻妻卖女,甚至沦为乞丐,冻饿而死。
(二)鸦片市场的兴起
由于甘宁青大量鸦片吸食群体的存在,鸦片买卖随之兴起,因此在甘宁青地区出现了专门的鸦片市场。据统计,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临夏地区,经营杂货的行店多数都行销鸦片,约有40余家,其他零星经营烟土的更是难以数计。由于烟禁的开放,宁夏的各大商号收购的土特产以大烟为主。每年农历五六月间,各商号派员随“牙行”(经纪人)下乡,甚至到田边地埂坐等收購烟浆。收购的烟浆运回商号以后,经晒制,切成75两或50两的烟块,用本号商标木模拓印后,再用印有本号商标的纸包装,名曰“板货”或“硬货”。然后,运至包头、呼和浩特一带,售于北京、天津和东北地区的烟商。[16]
在古浪县,“全县山川曾广种鸦片,每当收烟季节,商户云集近千家,或坐地收购,或长途贩运,鼎盛一时”。[17]在靖远县,罂粟种植较多者“因收割时间紧迫,多有雇短工者,农村出现了临时的人市。远来的劳力,清早集中在桥头或庙门,地户需要短工的到那里去叫。工资是有行市的,不用商量,用几个人就叫几个人。大的地户种百八十亩的要叫几十人短工,除管饭外,工资是付钱,无钱也可以大烟支付。今日割明天收,算做一个劳动日。每年的工资行市不同,大约一个工1两大烟,每元可买白面(面粉)30斤”。[18]随着收获季节出现的大量短工——刀儿匠的涌入,各种商贩、娱乐班子也纷至沓来,于是出现了临时的繁荣——烟会(烟场),周围群众逐渐形成了赶烟会的习惯。因此,一些集镇变成了鸦片市场。仅宁夏就有烟店千家,每家月纳烟捐20元,全省年销200万两。
热闹的烟场,将社会中的各色人等都吸入其中。在天水,每年五六月间便陆续开刀割浆,烟场也就开始了。“这时城市大量无业贫民和苦力劳动者,都到农村赶烟会打短工。小商小贩也备齐农村所需各样货物,到乡下烟场换烟土。城里说书的、唱戏的、算卦的、装水烟的、打‘泥娃倒的、‘打扳子的等,也都纷纷下乡赶烟场。尤其是唱秦腔的鸿盛社戏班子,这时也下乡演出,他们晚上演大戏,白天化整为零深入田间低地头,吹吹拉拉,清唱几段,讨点烟吃。县政府的官差衙役也趁此下乡,勒收亩捐借机发财,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19]在陇西,“收烟时引来陕西、河南等省形形色色的人来赶烟场,有富商大贾,有流氓乞丐,有妓女和各种杂耍,真是乌烟瘴气,盛况空前。”[20]靖远县,大烟收割忙时,“远近土客接踵而来,东路来客最多,兑来大批现金,坐地收购。庄客多半集中在县城西关,小贩和农民以烟求售,有牙纪行,名曰‘土店。这样的土店不知有多少家,每一土客,起码都收购万八千两。西关大街拥挤得摩肩接踵。有很多巨商在靖远作汇兑,兰州的万顺成就在靖远设有分号。土客的资金和政府的解省公款,动辄以万计,都是经过汇兑,可免带款被土匪抢劫”。[21]
(三)鴉片的贩运与走私
甘宁青地区的鸦片产量大,除能满足市场外,还大量运销外地。甘宁青鸦片一般经由绥远东运,在华北、京津一带销售。其路线大致沿传统的商业通道,即经黄河水路或由骆驼、马帮驮运至包头,后经铁路分销于华北各地。如1936年青海马步芳所运烟土,即“以骆驼或皮筏装见,越过河西走廊,与宁夏、绥远等地方势力勾结,直达包头,通过包头地区的军阀、土匪、流氓以及日本浪人,转运北平、天津出售”。[22]
由于鸦片外销有利可图,个人走私和烟帮武装贩运始终未曾停止。甘肃临夏为西北贩运鸦片的重要集散地,鸦片主要来自于川康一带的黑水、那娃等地。临夏烟贩被称为“马客”,百十人为一伙,后来一伙有数百人乃至上千的,该地贩运鸦片由于给马步芳家族交税(1938年到1949年十余年间“马客”仅烟土税就交银元达600万元之多),故实际上是公开贩运。到了40年代以后,河州鸦片的另一重要来源则是河西。由于巨额利润的诱惑,在宁夏吴忠、灵武地区出现了武装走私鸦片的“土客”帮。抗战时期,大烟价格,由“禁烟”前的每两不足1块银元,上涨到7块银元左右。当时吴忠镇每两黄金可兑换85块银元,在包头可购40两烟土,合每两烟土2块银元。而吴忠每两烟土7块银元,即每两烟土扣除成本后可获利4.5块银元。1匹快马可驮回600两烟土,在吴忠销售可得4200块银元,扣除成本,一般可净赚2500块银元。有的好马一次可偷运千两烟土,盈利也就更多。于是在1941年底,吴忠、灵武地区的一些商贾巨富们开始置马买枪,雇佣能骑烈马、打快枪的亡命徒,即贩运烟土的“土客”,来往奔跑于包头和吴、灵之间。武装走私贩运烟土成为吴、灵地区一些人暴富的重要途径。鸦片贩子雇佣亡命之徒,购买枪支弹药,组织成马帮,结伙从吴忠地区往包头贩运烟土。虽然官府、警察、军队围追堵截,但走私和烟帮贩运仍一如继往,照常进行,甚至手法越来越高明,规模也越来越大。
余论
民国鸦片产业给甘宁青地方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鸦片种植侵占粮田,严重冲击了粮食,造成粮食匮缺。与此同时,鸦片产业还造成地方财政的畸形发展,加重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鸦片产业戕害劳动力,恶化社会风气,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化。因此, 民国鸦片产业的畸形繁荣成为民国时期甘宁青地方社会畸形发展的一个缩影。
参考文献:
[1]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二十四)[M].兰州: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P13.
[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P464.
[3]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十三)[M].上海:上海书店,1986,P13.
[4]左宗棠.答王雩轩方伯.左宗棠全集.书牍(卷二十三)[M].上海:上海书店, 1986,P36.
[5]章有義.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P48.
[6]窦建孝.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64--565.
[7]陈雅赓.西北视察记[M].北京: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P73.
[8]王金香.中国禁毒史[M].上海:人民出版,2005,P112.
[9]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M].北京:三联书店,1957,P50.
[10]宁夏省政府秘书处.宁夏省政府公报[J].民国24年,27~28期,P33-34.
[11]林竞.西北丛编[M].神州国光社,民国20年,P198.
[12]陈雅庚.走进西部[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P169.
[13]刘敏.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39-540.
[14]顾执中 陆詒.到青海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P336.
[15]王剑萍 王中兴.民国时期青海禁烟内幕.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614.
[16]苗子安、安中甫口述 刘继云 徐世雄整理.宁夏八大商号.宁夏老字号[J].宁夏文史资料,第20辑,P4-5.
[17]古浪县志编纂委员会.古浪县志[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P56.
[18]张慎微.靖远的烟场.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75.
[19]窦建孝.天水鸦片流毒见闻.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65.
[20]陈仁.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81.
[21]张慎微.靖远的烟场.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册)[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P574.
[22]青海省志编纂委员会.青海历史纪要[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