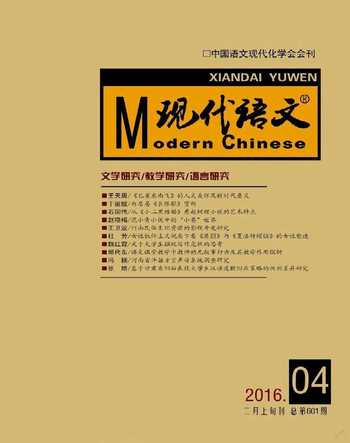悲悯的力量
摘 要:《孽子》在显性层面上表现的是父与子的冲突,而在隐性层面上关注的是同性恋这一特殊群体的观念与社会普遍维护的道德间的冲突。小说中父亲和儿子都经历了缓慢的精神演变过程,最终在人性的呼唤下互相得到救赎。在文本中一以贯之的是作家对生命存在的重视,对人世怀有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父与子 精神 存在 悲悯
《孽子》是作家白先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虽然在体裁上区别于之前的创作,但在题材上并不是重大的创新。《寂寞的十七岁》《玉卿嫂》《月梦》《青春》等早期作品都涉及到了同性恋问题。时隔多年,白先勇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同性恋的内容,而且《孽子》的写作断断续续用了十年的时间,从中我们似乎窥探到了作家对该问题持之以恒的关注和思考。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作家自身是位同性恋者,因此关系到自己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的社会问题会在创作中不断出现。尤为可贵的是白先勇将自我经验化为文学想象,为同性恋群体呐喊,呐喊中我们听到的是“人”的声音,是作家的人道主义和悲悯情怀。
《孽子》中父亲经历了由理性走向感性,从社会回归到个人的漫长路程,而儿子也经历了精神的洗礼,他们从脱离社会的自我发展到寻找生命价值的个人,被放逐的孽子最终也回归到正常社会。因身份地位的不同,矛盾之时凸显和谐。本文试图分析父与子的精神演变历程,同时揭露作家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实则是一种精神品格和情怀气质。
一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父亲类似于“本我”,儿子类似于“伊特”。“本我”所所遵守的是“现实原则”,因此父亲在现实生活中教诲儿子要遵守现实的生存秩序,在某种程度上是传统道德的捍卫者。而“伊特”所遵守的是快乐原则,他们逃离压抑的现实,寻求天性的舒展,挥洒生命的自由,生活得更加自我、本真。可能会孕育新的社会群体,凝結与传统对立的新的文化。父与子的矛盾和冲突随之破冰而出,而小说《孽子》在显性层面上正是通过描写同性恋群体的生活表现父与子的冲突。
小说第一部分的开篇就将父与子的矛盾呈现在读者面前。“他那一头花白的头发,根根倒竖,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射着怒火;他的声音,悲愤,颤抖,嗄哑地喊道:畜生!畜生!”[1]作者着眼于父亲面部表情的变化和口中重复的两个字,写出了父亲当时的愤怒心情。小说马上揭晓了父亲将“我”放逐的原因,原来“我”与学校实验室管理员的同性恋行为被发现曝光。《孽子》的第一部分被命名为“放逐”,以“我”——李青和父亲的冲突开始,其实只是众多儿子的被放逐、父与子矛盾的代表。
李青、王夔龙和傅卫都是因同性恋行为被父亲放逐,得不到父亲的原谅,或决绝地选择自杀,或长期在外漂泊、无所依归。作者对这三个人命运的讲述不是挥之即来的,而是从新公园里的一群同性恋者的遭际散发开来,因此我认为龙应台的“在《孽子》中,同性恋只是一个可有可无、装饰用的框子”[2]的评论是不恰当的。小玉、吴敏、老鼠、阿雄仔、阿凤等人作为台北市馆前路新公园的一群同性恋者,作家倾注了许多的笔墨,包括每个人的身世、家庭和现在的生活境况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可见白先勇关注的是这群被家庭和社会抛弃的特殊群体的命运,作者认为《孽子》的创作是在探讨“一个同性恋世界在大多数人世界的处境”[3]。同性恋世界就是李青、小玉等人生活的黑夜王国,大多数人的世界是以李青父亲、傅老爷子等代表的传统道德规约的集体社会。
可以这样认为,李青等人的同性恋行为使父与子关系破裂,这群年轻人被父亲放逐到社会,父亲的行为虽是个人举止,实则成为道德力量的帮凶。“这就是说,父亲与儿子之间对抗的经典形式已经由家庭内部转移到社会现实之上”[4]。作家讲的是同性恋,是亲情,也是群体的命运。读者却能从文本中看到社会道德力量对特殊群体的排斥、压迫,将父与子的冲突上升到同性恋世界与社会的冲突,也许这就是文本的阅读效应。台北市新公园内的大多数人在社会上的生存处境是尴尬的。李青、小玉、吴敏、老鼠等一群失去了窝巢的青春鸟提前进入社会,生存迫使他们只能拼命地往前飞,最终飞到哪里无人知晓。杨教头统治的王国并不能给予他们任何的庇护,安乐乡在记者的大肆宣传中最终夭折。王夔龙虽身在纽约,作为被父亲放逐的同性恋者同样过着麻木非人的逃亡生活。十年前的美国、现在的台北对待同性恋者都是坚决排斥、冷漠的态度,同性恋者被社会看成低人一等的异类。作家看到了即使跨越时空的界限,以父亲为代表的传统道德力量与同性恋特殊群体的冲突将长期存在。
二
前文提到由于儿子的同性恋行为致使父子关系决裂,按照世界的正常生存秩序和逻辑思维来看,同性恋群体和正常社会的冲突将无法和解。但是作家没有止于这一步,写作并没有终结,而是试图表现父亲和儿子精神世界的变化,从双方的变化中找到互相救赎的道路。
小说中的传统父亲区别于吴敏和小玉等人的父亲——或沉迷于社会污秽,或身份不明确、不在场。传统父亲如傅崇山、王尚德、李青的父亲,都是从理性出发,力图做一个纲常伦理的严格实施者,也是家庭道德力量中不可挑战的权威者。儿子的同性恋行为无疑给了他们致命一击,不仅挑战了他们捍卫的正统观念,而且给父亲们光荣的人生沾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理想儿子的形象瞬间破灭。因此“我”的父亲暴怒,称我为“畜生”,将我逐出家门;王尚德在世期间,不允许龙子从美国回来;傅老得知傅卫不可告人的事情后,当场晕死过去,不愿与儿子见面。父亲们对儿子们的态度更多的是理,将家庭中的情暂时搁置一边。匠心独运的是作者在小说中安排了傅老这个人物,在小说第三部分“安乐乡”中,一百四十页的篇幅始终离不开傅老爷子的身影,直到他去世,这一部分才完结。
以傅崇山为代表的父亲逐渐颠覆了传统父亲形象,开始从感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群在外流浪的青春鸟。而傅老爷子精神情感的开始转变源于儿子的自杀。傅卫的自杀使傅老感觉人生了无希望,儿子的脸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渐渐吞噬着他那颗无坚不摧的心。傅天赐的出现使傅老找到了精神寄托和救赎之路,是上天赐予他的另一个儿子,一种补偿心理和哀怜之心油然而生。可以说,李青、小玉、吴敏、老鼠这群在公园里沉浮的孩子能得到傅老的救助源于他们和傅天赐、阿凤相似的生存境遇。同时,小说通过傅老爷子之口间接写出了王夔龙父亲和李青父亲理性背后感性的一面,“王夔龙出事后,我去探望他父亲,才隔半年,他父亲那一头头发好像猛然盖上了一层雪,全白了——阿青,你父亲呢?你知道你父亲也在为你受苦吗?”[5]他们将情感埋藏在心里,无人诉说。只有傅老爷子经历了精神的蜕变,将情感诉求付诸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精神的自我救赎。
父亲们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从道德社会的理性到个人内心的情感诉求的巨大变化,相应的小说中儿子们的精神世界也在发生微妙的情感变迁。王夔龙、李青、小玉等人最初被放逐后,如同冲破牢笼的猛兽,不顾世俗的眼光,在黑暗王国里追逐爱和欲。但是他们没有继续沉沦在黑暗王国,而是走出来,面对这个世界。
李青在被逐出家门后,对弟娃的愈发思念使他感受到亲情的可贵。母亲的死使他想到“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始终没有找到归宿……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6],这种体验使他想要寻找一处精神的安身之所,从而不至于重蹈母亲的覆辙。在流浪的生活中,小玉、吴敏等人的父亲不在场的特殊家庭,对他们产生了相似的情感效应,即不断寻找理想的父亲。小玉不断认干爹,只为了寻找机会去日本,找到他的亲身父亲;吴敏卑躬屈膝、遭人冷落,只想留在张先生家里,感受有家的温暖;老鼠在乌鸦的数次毒打后,带着自己的百宝箱逃出来,而百宝箱里的物件可能是老鼠现实中匮乏的情感的具象化。这群青春鸟都在流浪中寻找,寻找精神的寄托。傅老爷子的援助和他的精神人格的感化作用,是龙子、李青等人精神蜕变的关键。在傅老的身上,这群年轻人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和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傅老的死使龙子幡然醒悟,对父亲的仇恨随风飘散,“陡然间,扑通一声,他那高大嶙峋的身躯,竟跪跌在傅老爷子墓前,他全身匍匐,顶额抵地,开始放声恸哭起来……于是我们六个人,由师傅领头,在那浴血般的夕阳影里,也一齐白纷纷地跪拜了下去。”[7]这一悲壮的景象象征孽子们对自我罪恶的忏悔,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小说最后一部分——那些青春鸟的行旅,是青春鸟走出黑暗的个人王国,回归到社会寻找自我生存价值的开始。
至此,父亲和儿子都经历了缓慢的精神成长过程,在成长中凸显了人性中善的一面、情的感化力量,以及人类自我的醒悟之于人精神世界变化的巨大作用。
三
白先勇在小说《孽子》中写出了同性恋群体不同于正常人的生存境况,从而表现了文学中不断出现的母题——父与子的冲突,而同性恋者的特殊身份又让我们看到了边缘群体与正常社会的尖锐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没有将重心放在父与子、同性恋者与正常社会的冲突上,而是力图呈现一种现实,也就是同性恋者的生存现实、精神轨迹,以及他们的命运,同时寻找他们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于是才有了文本中父亲和儿子的精神变化过程,有了人性中善的化身——傅老爷子。在小说中,人物的设置和人物命运的变化始终离不开作家的个人精神品格和情怀气质,我认为是一种悲悯情怀,一种人道主义。
作家说《孽子》是写给那一群,在最深最深的黑夜里,犹自彷徨街头,无所依归的孩子们。读完小说,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不是西方文学中如《小癞子》里的流浪汉形象,而是一群无所依归的同性恋者。白先勇大胆地描写了以李青为代表的同性恋者被放逐到社会后的生活,充实了文学中鲜有作家涉猎的领域。作者不厌其烦地对每个人物的身世、命运的介绍,使我们相信作家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是真诚而毫无偏见的。“把异性爱作为唯一标准的正统道德文化强行将人类羞耻感驾驭同性性爱身上,使得同性性爱长期处于被遮蔽、被异化的尴尬处境。”[8]白先勇打破了传统的道德观念,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和思考是他对这一群体生命存在的重视。只有承认这一群体,承认同性恋者也是“人”,在创作时才能以客观、冷静的姿态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作者才能和文本中的人物保持平等对话关系。李青、王夔龙、傅卫、小玉等人的出身、家庭环境不尽相同,但是都是作为同性恋者而走进了公园,开始了流浪漂泊的生活。作家对这些人物首先是认可的,其次是怀有温情和怜悯的。
“人与人之间,发诸自然的感情都是可爱的,自觉地去扼杀这些感情倒是侮辱人性。”[9]作家善于发现人性中的善和美。《孽子》中杨教头、李青、小玉、吴敏、老鼠等人生活在同性恋的王国里,互相扶持;傅老爷子对王国里的一群孩子和傅天赐伸出援助之手,不计回报;李青和龙子对小弟、罗平、小金宝等人如亲人般的呵护。他们的交往没有外面世界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多的患难中的真情。同性恋者作为社会的边缘人物和特殊群体,更容易受到排斥和冷漠,被社会上的恶势力同化而走向歧路。但是作者怀着悲悯的情怀在小说中设置了傅老爷子这个人物,不仅完成了傅老爷子自身的精神蜕变,而且挽救了一群青春鸟,给他们的生命点燃了希望。作家始终是以人性善的眼光看待每个人物和人物的命运,认为同性恋者发诸自然的感情是人性使然。
《孽子》讲述了同性恋群体的故事,同时从同性恋者的特殊身份着眼,也表现了父与子、特殊群体观念与传统社会道德的冲突。虽然冲突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力量,但是作家没有将着墨点放在历史或社会上,而是怀着悲悯的情怀,从“人”本身出发,从而获得了更有价值的人性力量。对于《孽子》这部长篇小说,白先勇曾说:“在我写作里面确实是我放最大同情心的一本东西。”[10]可见作家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怀着巨大的悲悯情怀来进行创作的。我想这种悲悯情怀和人道主义是一个崇高的作家创作时的宝贵财富,对于这样的作家,文学应该给他们留下一方空间。
注释:
[1][5][6][7]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第306页,第199页,第360—361页。
[2]雷达,李建军主编:《百年经典文学评论:1901—2000》,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08页。
[3]袁则难:《两访白先勇》,新书月刊,1984年,第5期,第19页。
[4]南帆:《冲突的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8]罗显勇:《台湾同性恋小说叙事策略的变迁》,华文文学,2003年,第4期,第49页。
[9]白先勇:《第六只手指》,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287页。
[10]刘俊:《文学创作:个人·家庭·历史·传统——访白先勇》,东方丛刊,2007年,第1期,第239页。
参考文献:
[1]白先勇.孽子[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2]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论[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
[3]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南帆.冲突的文学[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
(常玲 辽宁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11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