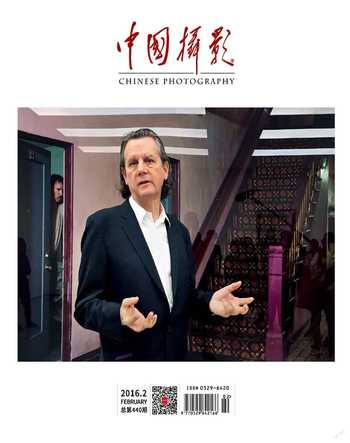纷杂难言的乌托邦情结
门晓燕
有时间,就有存在,于是就有了思考。纷杂历史中弥漫着乌托邦,此时此地,布列松的作品散发着当代价值,在当代艺术修辞诠释下,如同“神秘走失儿童”系列作品,呈现的不正是当代生命力吗?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sson通常中文译为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该书译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本文沿用此意。编者注)来到了维也纳。我静静地注视着他: 光亮的发丝,宽宽的额头,相机后面是那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深邃的眼睛。正是因为这双眼睛,才有了我书桌上的这本书,《Henri Cartier-Bresson》。我爱书,我爱精美的书,眼前这本书精致而简洁,大气的黑白封面是我眼里描述不尽的细腻色调。小心地翻到书的最后部分,果然,不出所料地是德国Steidl印刷装订。
《Henri Cartier-Brsson》,中文译本为《传奇布列松》,是蓬皮杜中心摄影部为2013年举办的“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大型回顾展”出版的一部图录书。这个展览历经10年精心筹划,以全新角度探讨布列松整体的创作。这本2750克重的图书装载着布列松的一生,以及蓬皮杜中心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10年的心血,不得不说它真的很沉重。它不是一块沉重的碑石,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2750克游动的风,吹动历史,吹动当今。
布列松对于中国摄影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甚至熟悉得有些不耐烦。不就是“决定性瞬间”嘛,怎么又搬出来啦?是啊,当代的人们或许更喜欢谈论的是当代摄影,陈词滥调有谁会愿意听呢?难道这本书真的只是无数本具有相同论调的关于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的书籍之一吗?作为译者,我认为这本书绝不是陈词滥调的炒冷饭,恰恰相反,它是要打破人们对布列松固有的认识,作者提出多角度理解布列松的观点,恰好体现了提倡多元化的当代艺术界潮流。虽然是译者,我却更愿意以摄影师的身份去体会作者的意图。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感受,与愿意读此书的人们分享一下。对于本书,我有四点主要认识,首先是本书作者克莱蒙·舍卢流动性的研究策略,其次是将从“决定性瞬间”标牌之下解放出来所做出的努力,再次是布列松艺术生涯中的数个开创先河。撇开书中论述的他最早实践了摄影设备和身体空间所暗示的权力分配,撇开人们普遍认同的他开创了新闻报道摄影先河,我个人认为,他还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摄影作为公共艺术的最早践行者,最后就是作者若隐若现地揭示出布列松那难以言明的乌托邦情结。
一、“此时此地”(Here and Now)—流动性(Fluidity):一种当代研究策略
本书的书名没有使用“决定性瞬间”或者“主要藏品”(Master Collection)这类定义式用词,而是使用了“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名字具有多样性意指,更加吸引我的是它的副标题:此时此地。这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Temporal and Spatial)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作者舍卢如此鲜明地暗示着流动性时空分析方法,而流动性和时空方法论正是当代学术研究的主要策略之一。显然舍卢要摆脱传统定式,事实上,这的确不是一本老生常谈的僵硬的套路书,而是另辟蹊径,重新探讨布列松及其作品。人们可以看到青少年布列松的成长和教育背景,感受他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分析文化思潮和运动对他的影响,作者希望从他的世界观形成角度,去诠释他的艺术生涯的演变。如此,读者可以看到热爱艺术并且颇有绘画功底却又不肯在深入训练中更多地受苦的富家子弟;还可以去了解既接受严格正统教育又追随自由思想有点跟风的青年成长过程。布列松崇拜过尤金·阿杰,热衷过超现实主义,跟随过新视野,不断地接受左翼思想,反对殖民主义,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等等。他在各种思潮和运动中始终积极活跃,决定了他作品呈现多样性的原因。从模仿阿杰拍摄巴黎街头,到超现实主义的白日梦者们,再到直接摄影和新视野的俯瞰,转变到摄影作为政治工具的辩证摄影(Dialeetic photography)。正如作者舍卢所说的“我们当下做出的决定,依据的是过往发生的事件,也由此确定了生活发展的轨迹”。舍卢通过探索布列松流动的人生来阐明他流动的摄影风格。布列松在舍卢的笔下,冲出了后人赋予他的唯一标牌的束缚,有机会鲜活起来。
这本书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开放的方法论。布列松曾经表示,基金会不要成为存放作品坟墓,而是要大门敞开。许多人将布列松同“决定性瞬间”画等号,将他的作品死死地订在这个标牌之下,这岂不是为作品造了一个坟墓,盖棺定论了吗?这样恐怕是布列松本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吧?舍卢认为“决定性瞬间”在当今看来是对于布列松做出的简单化和笼统化的总结,他通过全面论述,搬动了长久压在布列松身上“决定性瞬间”这块标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游走在历史变化中的摄影家,如何可以从历史走到当下。
那么,蓬皮杜中心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是如何共同将这块标牌搬开,让新鲜的风从作品里吹出的呢?
在对于布列松作品进行研究过程中,基金会敞开作品档案大门,为的是让人们看到更加广泛复杂的布列松的创造性作品。他们深谙这样一个道理:“作品若要拥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必定要欣然面对新观点”(序)。蓬皮杜中心和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基金会采用一种合作研究方式,对于伟大的艺术家,每个人见仁见智,且他们收集大量丰富的书信材料,可以共享,共同探讨;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拒绝重复过去对于布列松的研究,也就是拒绝陈词滥调。尽管布列松作品是不会变化的,但是对于作品的研究方向可以是新的,可以不同于过往的批评。
法国当代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何为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中强调“必须整体地去看待作者和影片”。他解释说,看上去这似乎会造成对于影片独特性分析的流失,不过这只有在我们把整体性看成是封闭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如果是开放的整体,便不会。《传奇布列松》不仅仅涉及了布列松的摄影作品,还包括他的绘画和电影创作。本书的设计思想如同作者所说,是“展示既完整又复杂的布列松一生的作品”,本书强调了时间和地点,作者“在这里所呈现的布列松从来就不曾被锁定在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时间里”。(序)事实上这正是西方学术界近些年的普遍研究思想。无论是后现代、后解构,还是后殖民等各种“主义”的研究,都是在西方当下语境中进行。举个例子来说,西方艺术家对于身份认同(Identity)问题的表述,是在他们所经历的二战之后、现代化、殖民化、种族和性别等各种历史问题的背景之下,发起的对他人和自我的重新认识的探讨。这与中国艺术家所讲述的身份认同是不相同的。 本书也正是采用一种历史的、背景的和反思的视角去探讨布列松。如此一来,布列松的作品定位会随之流动,便不会被固定在某一个历史时间和地点上。每个时代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当下的角度去反思布列松的作品。例如原超现实主义者,后加入共产党的阿拉贡曾对于卡蒂埃–布列松在1935年为“人民阵线”拍摄的作品十分赞赏,他站在共产主义宣传角度上认为卡蒂埃–布列松作品完美地体现出现实主义风格。卡蒂埃–布列松的作品也许无法改变其时间和地点性,但是其意义却可以在历史长河之中流动。因此在我看来,本书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在突破了“决定性瞬间”的框架束缚之后,带给我们一个新主张,那就是注重研究此时此地性。


二、“决定性瞬间”(Decisive Moment)—局限性(Limitation)
既然谈到“决定性瞬间”是一个束缚,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它是如何演变成一副枷锁的。
1952年美国出版商为卡蒂埃–布列松出书的时候,决定使用“决定性时刻”一词作为书名,为的是强调“运动中的影像”这个概念。后来这个词回译到法文变成了“决定性瞬间”。布列松在该书前言中首次提到摄影的“运动中的影像”(Image à la sauvette)这个术语,他使用这个词来定义在观察处于不断运动状态中的世界时,出现的一种理想时刻。布列松曾经说过:“圣经曰,世界之初为文字,可是,对于我而言,世界之初为几何”(It says in the Bible that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Well, for me, in the beginning was Geometry.)。“为了将被摄对象的所有特征都表达出来,必须要严格建立起这些特征之间都有条理都联系—摄影就是辨认表面节奏、指向和价值—构图必须是我们脑海中永远要记住的一条原则”(P31)。布列松坚持认为对于摄影而言,构图最为重要。他曾经说过:“没有几何构图的摄影是业余的和没有生命的”(Without geometrical composition photography is ‘amorphous and lifeless.)(P32)。人们都会有这样都感受,“当谈论‘决定性瞬间的时候,总是难以区分什么是事实(Facts),什么是个人制造的神话(Personal Mythology)”(P9)。 当布列松无意间看到马丁·芒卡西拍摄的一幅表现三个非洲小孩冲向浪花的照片时的那种激动不已,毫无疑问地影响了他后来的摄影之路。那是真实的非洲还是芒卡西制造的非洲, 或者是布列松脑海里神话的非洲? 在这个决定性时刻,通过取景器看到的内容,经排列形成兼具美感及富有意涵的图案,正是摄影师应该按下快门的瞬间。决定性瞬间是形式与含义取得平衡的时刻,它揭示着一个特定情景中的张力。用布列松的话来说,它相当于“在刹那间,同时认识到一个事件的重要意义及各种精确形式构成。正是这种同时认识,才赋予了事件自身进行恰当的表达”。德国作家和哲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的观点是:艺术家的天赋由其对特定情形中对最高瞬间具有对感知和记录而构成。有理由去这样理解,正是因为布列松将摄影的瞬间性问题引入到了艺术范畴,从此就可以阐述摄影的艺术性。我们知道,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摄影依然不被大多数人看作是艺术。如此看来,“决定性瞬间”不仅为摄影的术语,而且还为摄影在艺术领域取得地位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这个概念的重要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观察摄影师布列松的作品, 被批评家们用来概括他创作的“决定性瞬间”的所有作品,可以归纳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在超现实主义时期拍摄的“定格物影”(Fixed-Explosive)作品,在舍卢看来这只可以勉强算是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为马格南图片社工作时期拍摄的摄影报道作品,作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决定性瞬间”创作。而这两部分作品在布列松的整体创作中所占比例十分有限。只有研究这两部分作品,才会对于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即运动的影像有深刻理解。
为什么后人仅仅关注到了布列松拍摄的“决定性瞬间”的作品呢?是他创作的超现实主义作品不够好吗,还是他拍摄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够完美?如果仔细看一看“决定性瞬间”作品集中的两个时间段就不难发现,首先布列松的摄影理想形成于超现实主义时期,而那时的他,在超现实主义者的各种聚会中,不过是个常常坐在角落中一言不发的热血青年。“定格物影”形式的作品显示出卡蒂埃-布列松捕捉运动影像的天分,然而,即使他拍摄出了完美符合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图片,也被后人归纳到“决定性瞬间”风格中,而没有被当作时超现实主义之作。例如,《圣拉扎尔火车站背后》是人们最为熟悉的布列松代表作之一,跳起在空中的人的形态被恰好捕捉在画面中,这是公认的决定性瞬间。然而,这幅拍摄于1932年的照片,正是布列松着迷于超现实主义,并且熟练掌握超现实主义的定格物影之法时所拍摄。所以如果认定这幅照片是“决定性瞬间”,同时还应该不要忽略其实它还是典型的超现实主义创作。事实上舍卢也仅仅勉强认为“定格物影”可以被归纳到“决定性瞬间”风格。我认为,如果一定要这样归类的话,只能说是在画面构图上符合“决定性瞬间”风格,而从整体意义则显得勉为其难。
布列松拍摄的准确意义上的“决定性瞬间”的图片是在另外一个时期,即马格南时期。马格南是他开创出新闻摄影报道之路的时期,新闻摄影的瞬间捕捉和对于新闻事件的准确表达,才是布列松所称的“在刹那间,同时认识到一个事件的重要意义及各种精确形式构成”的确切体现,才是他所说的“决定性瞬间”。数百篇对于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报道和为世界上当时几乎所有主要的杂志社工作,使布列松成为了世界上最为著名的新闻摄影师。从1946年到70年代早期这段时期,布列松将拍摄运动中的影像的特有风格在新闻报道中极其成功地体现出来,这是他的摄影事业最为辉煌的时候。同时这个时期杂志媒体也是蓬勃发展,因而布列松在这个时期拍摄的图片被广泛传播。
人们忽视布列松其它时期作品风格的一个隐性原因,是二战结束后布列松本人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隐藏起来的同时,也隐藏了他曾经激情澎湃的摄影重要阶段。为了人人都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做出了少有人理解的举动,销毁了自己拍摄的几乎所有体现出他共产主义信仰的照片,闭口不提自己参与过的任何进步活动。不仅是他个人彻底地隐藏起自己的政治观点,1946年官方在对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清查的结果,似乎同时也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他1946年以前时期的创作风格避而不谈。个人的回避和官方的证实,也许是人们一直忽略他受共产主义影响的摄影风格而仅仅关注他在二战后新闻摄影方面报道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此一来,新闻摄影成为了人们关注焦点。这也是布列松为什么总是被锁定在“决定性瞬间”的原因。事实上布列松的风格不仅在不断地变化中,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连贯性。因此要将他从“决定性瞬间”框架里解放出来,就必须要全面地观看他的毕生作品,在历史特定背景下解读他。也许我们可以借用他自我认识的做法去认识他。他十分喜欢更换自己的名字,在中国时起了一个中国名字,Ka Beu Shun—一位事业有成之人;在印度他起了一个印度名字,一位武神;在法国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剥削时,他讨厌使用自己的姓氏卡蒂埃–布列松,用布列松作为姓氏,避免与自己的大资本家家族有任何联系;在日本又称自己是亨利·卡蒂埃。他一生中总是根据所处的时间和地点给自己起一个新名字,这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和世界的一种认识哲学,流动性的融入所处环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采用这种流动性来诠释布列松和他的作品,却非要把他锁定在单独一个“决定性瞬间”定义里呢?
三、公共艺术(Public Art)—现实性(Reality)
摄影的现实意义问题是我关注的另外一个话题。如何来看待布列松作品的现实意义呢?我列举本书中曾经描述的一个故事,在我看来,这个故事对于当今进行纪实摄影的摄影师们也许会带来启示。
布列松从事摄影的一生从未同现实生活脱节,总是紧密地挂钩于此时此地的现实。如果说在当下艺术是否肩负着为群众服务这个古老话题依然还在探讨中,艺术家还徘徊于艺术怎样结合现实,可以看一看在为共产主义报刊工作的这个时期,布列松是如何坚定地将摄影作为服务于政治的工具。他的创作风格从超现实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创作形式从拍摄图片转向拍摄电影,这些都是他的政治参与和信念的直接宣言。 我要举出的例子便是他为共产党刊物《今日晚报》拍摄的“神秘的走失儿童”(The mystery of the lost child)系列作品。这些照片在当时是一种政治宣传,放在当代艺术背景下,可以称为一个公共艺术项目。
什么是公共艺术呢?在艺术史上,人们认为美国女艺术家乌克勒斯(Mierle Laderman Ukeles)在1970年代左右开创了公共艺术形式。布列松拍摄走失儿童的时代,这个艺术形式并不存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位伟大的先锋艺术家乌克勒斯开创了怎样的公共艺术。
乌克勒斯从1979年至1980年,拍摄了纽约城的环卫工人日复一日的劳动场景,在拍摄工人劳动的过程中,艺术家与8500位环卫工人握手,她将这个过程用图片和录像的方式来记录这个握手行为。她还建议城市里的每一位市民与参与到这个艺术行为当中,见到环卫工人到时候,对他们挥挥手。她不是在艺术画廊或者博物馆展示作品供人们观看,而是将艺术空间搬到了大街上。让人们不仅看到而且参与到艺术创作过程中。她将这个艺术创作称为“手的力量”。她把握手环卫工人的动作和向环卫工人招招手的动作,转换为一种公共艺术行为,唤醒公众对于从事城市维护工作的环卫工人的认识。 乌克勒斯通过这样的艺术形式将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从此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产生了,人们称之为公共艺术。
美国艺术家、作家和教育家苏珊·蕾西(Suzanne Lacy)在1991年曾经这样给新公共艺术定义,它不是放在公园或者广场上的雕塑,公共艺术是活动家,通常是在机构之外进行创作,艺术家与观众直接互动,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社会和政治问题。许多艺术家会很敏感地发现一些社会问题,然而如何将这些社会问题通过艺术形式来表现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作为艺术家,当站在公共舞台上面对社会问题时,从政治角度和个人角度去理解问题是前提,之后才有希望以正面积极的角度创作出涉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作品”。
大多数摄影师会选择纪实摄影的形式来揭示社会问题,的确一些纪实摄影图片呈现了摄影师们看到的现实存在,他们希望观看者也可以从图片中看到他们认为的现实存在,于是这些照片的传播成为了摄影师对观者的讲述,有时甚至带有教育的味道。摄影师将自己定位在了道德制高点上。结果很有可能是视觉语言没有提供有效的证词,而观者对于说教却有着天然的反感。艺术家用艺术形式表现社会问题本身已经是一件不易之事,而唤起观看者参与其中并做出努力去共同探讨问题则更为困难。在我看来,用艺术探讨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与群众息息相关,只是这种探讨有不同的深浅程度,同时还有艺术形式的直白和含蓄之分。而其中当代艺术中最为直接同群众和社会问题相关联的艺术恐怕要首推公共艺术了。
按照蕾西的对于公共艺术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布列松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使用摄影参与了一次公共艺术的创作。 他为《今日晚报》报纸拍摄“神秘的走失儿童”,是带动社会共同参与的一次共产主义宣传活动。我把它叫做“儿童的力量”。这次活动是共产主义的活动者和艺术家联合起来,通过摄影手段,宣传当时蓬勃兴起的共产主义思想。布列松负责到城市贫困的工人居住社区随机拍摄数千名儿童肖像, 之后将这些儿童肖像在《今日晚报》上刊登,并附以儿童悲惨生活的故事。接着是让公众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他们让那些认出孩子的父母到报社来领取奖品,资助这些贫困的家庭。如此一来,许多普普通通的人就参加到了与他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中,这样可以让普通人群有机会了解共产党救民于水火的功劳。他们将儿童比喻为世界的未来,同时又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化身,通过寻找走失儿童,比喻只有共产主义通过自身的拯救,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未来世界。这个活动通过摄影师布列松的拍照,将照片通过报纸平台唤起众多儿童和普通大众参与到活动当中,让人们参与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的共同讨论之中。寻找“神秘的走失儿童”活动是一次成功的公共艺术。
四、一生情结—难言的乌托邦(Inconvenient Utopia)
舍卢始终坚持认为不能用一个概念来概括摄影家的一生,这也是本书在不断论证的重点。然而,在书的最后,舍卢出于某种原因,还是将布列松的一生勉强地使用了“拍射图片”(Shooting Photographs) 这个概念贯穿起来。我认为,经过了长篇多角度论述,最终用一个反复重复的基本动作,即拍摄图片的射击动作,一个单纯的肌肉记忆来贯穿布列松一生,容易造成对于布列松的研究滑入简单化的危险,这个贯穿真的是有悖于整书的探索。我想如果用布列松一生的基本世界观来贯穿会更加有效。布列松世界观中那难言的乌托邦情结,总是在不断地调整当中。这个难言的乌托邦情结在面对复杂的历史变化时,是流动的,也许这更能体现他一生。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的是永远保持着的对于那种最完美最高境界的不断追求。实际上这正是他世界观里的乌托邦意识的视觉体现,是对人类美好世界的向往。除了对“决定性瞬间”完美掌握,他一生的创作过程是未曾停止的乌托邦情结调整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正值青年的布列松开始了他的摄影早期生涯,他深受超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超现实主义风格,其时作品被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无论是定格物影、还是巧合、或是面纱后的情色,作品中无不体现出创作者梦一样的矛盾对立之美的追求。 这个年轻时候形成的这种乌托邦情结伴随着布列松的一生。
布列松乌托邦情结的形成,与他的家庭以及所接触的人群是分不开的。出生富裕家庭的布列松受到家庭熏陶,家中除去严格的教育还有开明进步的影响。在接触了超现实主义之后,他崇拜尤金·阿杰,因为阿杰作品所代表的是城市的“精致”原始之美,正如马丁·芒卡西拍摄的表现非洲儿童冲向浪花代表的是非洲的“野蛮”原始之美。布列松后来写到那幅照片是“如此强烈,如此即时,如此快乐的生活……”。(P29)受到阿杰的影响,布列松曾经疯狂地在巴黎的街道里等待发现心目中的天赐之美。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追求超现实主义提倡的“颤抖之美”(Convulsive),一种从内心向外挖掘的现实与乌托邦想象的结合。
超现实主义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的革命者群体,超现实主义的宗旨“改变生活”,这也正好合适了布列松的理想。年轻的布列松总是希望可以改变自己的那种在别人眼里看来是如此优裕的生活。 那个时候,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享有共同的理念,反对殖民主义,向着美好改变生活。1926年18岁的布列松接触到超现实主义,而那时正值超现实主义者们决定要加入共产党。自然而然地,他的理想也就转向了共产主义。带着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在后来二战前后的摄影报道中,他的作品无不体现出他对共产主义的热情和参与。从马格南的工作中,从他新闻报道涉足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出他的信念。他前去报道被殖民国家的反殖民运动,例如在巴基斯坦、在印度;报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例如到中国,到苏联,到古巴,这些都透露出他对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到坚持。即使对于自己的国家法国的报道,布列松也是专注于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的批判。他极其厌恶消费主义,甚至强烈反对马格南年轻一代摄影家,使用消费主义的语言来批判消费主义。他创作纪实摄影视觉人类学图片,看上去是批判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恰是他乌托邦情结的暗示。从作品中可以看到他也许从未改变的信念,即使深藏在心中,也可以从他作品的主题和视觉修辞手法中,看出他无处不在的对于改变生活这个信念的坚持,他早已找出将政治信仰转化为复杂的视觉语言的方法。
由于没有布列松是否领证加入共产党本的证据,舍卢只能通过卡蒂埃–布列松的书信和参加的活动,以及周围的朋友来反复论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介入的程度。例如,超现实主义与共产主义者在1930年举办的展览“殖民的真实脸孔”,布列松从非洲写信回来呼应这个展览,信中批判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将殖民主义描述为“阴险闹剧”(P135)。他参与各种左翼组织的活动,在左翼组织抨击事实的诸多檄文上签字。他还曾经在信中写到“我们什么时候会发动无产阶级革命”(P136)?在一封信中他曾经对父母说:“你们知道我对于政治局势是多么感兴趣—它是我生命的全部”(P136)。布列松为共产主义刊物工作,为“人民阵线”拍摄,他拍摄了大量的现实主义摄影图片。其中有一幅他自己十分得意之作,是利用叠加手法拍摄的一张一名儿童正在朝代表殖民权力的雕像撒尿的照片。“人们阵线”领导下,他拍摄了普通人民获得休闲机会的照片,其中许多照片成为他的传世经典之作。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了自己的辩证摄影风格。后来他跟随左翼导演雷诺阿拍摄电影,用电影形式取代了图片摄影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布列松曾经前往墨西哥和西班牙这样共产主义运动高涨的国家参加活动,并举办展览,拍摄电影。他在纽约参加受苏维埃政治和美学影响的左翼组织“纽约电影”的活动。他有时还会到华尔街,朝着豪车上吐口水。他在墨西哥参加“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活动,回法国后经常去聆听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他后来成为法国“革命作家和艺术家协会”的核心成员,他自我宣称“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他创建的马格南图片社,其合作体制在部分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自我管理、权利共享和利润公平共享。所有这些事实,让我们不得不相信他早已是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其实就是到底有没有领证而已。
历史变换不断地打击着布列松的信念。他后来放弃摄影报道,专心沉思的晚年,偶尔间去人群中观察,这些转变隐含着一种难言。在他趋于平静的人生态度下面依然可以感受到的是涌动着的乌托邦情结。无论是他的性格还是生活环境决定了他终究不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无论是形式迫使还是他自愿必须隐藏自己信念,他的世界观依然无法遮盖地在摄影作品中透露出来。在我看来,贯穿他一生的也许正是这个难言的乌托邦情结!
有时间,就有存在,于是就有了思考。纷杂历史中弥漫着乌托邦,此时此地,布列松的作品散发着当代价值,在当代艺术修辞诠释下,如同“神秘走失儿童”系列作品,呈现的不正是当代生命力吗?
作者为伦敦大学摄影硕士、维也纳美术学院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