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牧斋说“贺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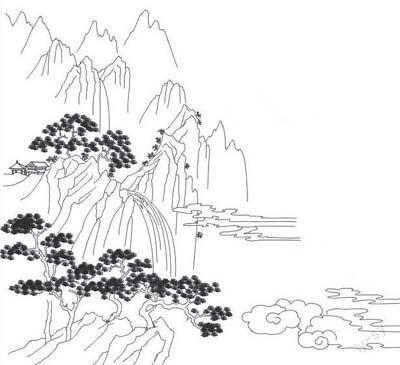
陈寅恪作 《柳如是别传》,用了很大的力量,引书之广,使人惊叹。但到底限于条件,有些材料还是失之眉睫了。例如藏在浙江图书馆里的柳如是原刻诗集两种、《尺牍》 一卷,就没有能利用,只见了传抄的本子。这是值得同情的。近来随便翻书,检出康熙虞山如月楼刻的 《钱牧斋尺牍》 三卷来看,觉得很有意思,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材料。内容的真确性是不容怀疑的。
钱牧斋这些信是写给朋友、地方官、和尚、亲戚……的。绝大部分是晚年所写。信札是很重要的研究资料,有些不可能见于正面的传状、文集,甚至也不能从反面的攻击文件中获得全面了解的情况,就往往保存在这些尺牍里。钱牧斋与朱长孺关于杜诗笺的纠纷,他与毛子晋的关系,与瞿式耜的关系……这里都有不少原始材料。至于他对诗文的见解就表述得更多,而且话也说得爽直,绝不吞吞吐吐。卷二有 《与君鸿》 一札,这“君鸿”不知道是谁,是他的晚辈,也并非亲近的熟人,为了他八十寿辰写了贺信来,他回信说:
村居荒僻, 翻经礼佛,居然退院老僧。与吾弟经年不相闻问,不谓吾弟记忆有此长物也。日月逾迈,忽复八旬。敕断亲友,勿以一字诗文枉贺。大抵贺寿诗文只有两字尽之,一曰骂,二曰咒。本无可颂而颂,本无可贺而贺,此骂也;老人靠天翁随便过活,而祝之曰“长年”,曰“不死”,此咒也。
这一节话说得深刻而痛快,也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尺牍中有许多都谈到为文债所苦,其中大半就是别人请写的墓志、寿文。他曾说,写这种文章很伤脑筋,有些人的生平没什么可说,有的虽有可说又不便说。例如有丑事就得转弯抹角地加以弥缝,实在不好写。但又不能不写,他是靠这项收入吃饭的。当时他的润笔肯定是异常丰厚的。他经常在信里哭穷,但这与下层农民的穷绝不是一回事,两种“穷”的标准天差地远。
祝寿本来就是无聊的勾当。西太后庆某旬“万寿”弄得民穷财尽,是人人都知道的。大地主比较“风雅”一些,除照例地大吃大喝、请酒送礼、唱戏取乐之外,还得搞一些纪念诗文,有人还刻了出来。幸而流传,现在都已成为“善本”。因为印好分送之后,谁也不去看,立即扔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了。这样就变成了“珍本”。翻翻“善本书目”,其中有一大批就是这类物事。但在历史学家看来,却自有其可贵之处。不过这是另一回事。
钱牧斋说的“骂”与“咒”,看起来似乎是“怪话”,但也不是没有根据。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这是天经地义,但在寿文中就不行。本来是恶霸劣绅,却要奉承说成是怎样的好人,这在本人看来,是比骂还要难以忍受的。钱牧斋还是清醒的,明白自己是怎样的人,所以他有此体会。至于“咒”的一点,那就体会得尤为深刻。钱牧斋晚年缩在家里,经常听见社会上对他的“评论”,在尺牍里也有不少反映,自知罪孽深重。一旦死掉,不但常熟的老百姓要说一声“阿弥陀佛”,全国的清流义士也都将拍手称快的吧。这一点,他是猜对了。看看清初诗人文集中吊牧斋的作品,就多半说的是“可惜死得太晚了”之类的话。
就这一点说,钱牧斋还要算是高明的。
(选自《绛云书卷美人图:关于柳如是》/黄裳 著/中华书局/ 201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