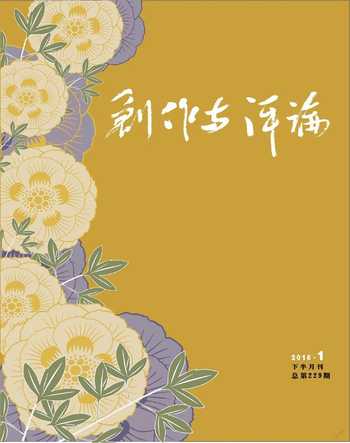艺术形式的多向度探索
王春林
2015年,因为很多作家专注倾心的缘故,长篇小说创作依然一如既往地保持延续着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陈应松的《还魂记》、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东西的《篡改的命》、何顿的《黄埔四期》、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须一瓜的《别人》、袁劲梅的《疯狂的榛子》、艾伟的《南方》、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王安忆的《匿名》、严歌苓的《护士万红》与《上海舞男》、韩东的《欢乐而隐秘》、杨则纬的《于是去旅行》、路内的《慈悲》、张好好的《禾木》、李燕蓉的《出口》、康赫的《人类学》、周瑄璞的《多湾》、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弋舟的《我们的踟蹰》、冉正万的《天眼》、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王华的《花村》、王凯《瀚海》、张翎的《流年物语》、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陶纯的《一座营盘》、陈谦《镜遇》、张者的《桃夭》、秦巴子的《跟踪记》、杨东杰的《一嘴泥土》、尔容的《相爱不说再见》、刘仁前的《残月》、刘春龙的《垛上》等,都各有其思想艺术上的可圈可点处。细察这些文本,就不难发现,其中一些作品在艺术形式层面上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多向度探索努力。
东西那部底层叙事特色明显的长篇小说《篡改的命》,艺术形式上最不容忽视的一大特征,就是寓言式表现手法的运用。所谓“寓言性”,其具体所指,就是作家在面对表现对象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拘泥于形而下生活细节真实无误纤毫毕现的再现,而是以一种概括性的笔触力图追求一种超越了生活表象层面的具有突出象征隐喻意义的艺术表现效果。“寓言化”的艺术审美追求,既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西方现代文学追求形而上精神诉求的一种影响结果。东西之所以要征用寓言化的写作方式,“表层的原因也许是由于文学落后于世界而表现出向外学习的强烈愿望,仅仅只用已有的再现手法和移植过来的典型再现手法已经难以深层地揭示民族‘伤痕的复杂动因,也难以完满地思考出一个古老民族在当代的生存哲学及其将如何步入文明的未来。”①其实,早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之初,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小说作品就带有明显的寓言性质。采用寓言化的写作方式,可以帮助作家跳脱开形而下生活的束缚,不但不用刻意地复制所谓表象世界的真实,甚至可以运用各种夸张变形艺术手法,以求得超越事物表象而直指核心与本质的真实。也正因此,寓言化写作之带有突出的抽象普遍性意味,乃是一种显见的文本事实。《篡改的命》尽管是一部反映当下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但细读文本我们即不难发现,东西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却无意于亦步亦趋地去复制生活的真实,去塑造刻画个性化特质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中的汪氏父子、林家柏等人物形象,都呈现出概括性特质相当突出的符号化特点。而符号化的人物的设置,所充分体现出的,正是作家东西一种寓言化写作的艺术追求。作为“三无”弱势群体的一个典型代表,汪长尺在他的人生路途中可谓四处碰壁,苦难已然成为他的生活“新常态”:高考无端被冒名顶替,父亲以死相求摔成残废却无钱医治,放弃大学梦到工地打工被拖欠工资,讨要工资反遭恶意报复……诸如此类,可以说,汪长尺的苦难遭遇,就是一个庞大弱势群体苦难史的真切缩影。在汪长尺遭受苦难折磨的时候,整个社会、甚至包括代表公平正义的司法机构却始终扮演着冷漠、不公与黑暗的角色。作为与汪长尺相对立的阶层代表,林家柏这一人物形象即是这种冷漠、不公和黑暗的代名词。毫无疑问,汪长尺从生到死再到死后投胎所经历的一切,都是以当下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生活为依托的。但由于作家东西在写作过程中普遍采用了不无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所以寓言化特点的具备,也就自然成为了小说最根本的艺术表征所在。这样一来,汪长尺的人生故事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当下时代中国底层人众一种普遍的人生寓言。
然而,同样是聚焦底层社会不幸命运的长篇小说,盛可以《野蛮生长》的艺术形式特质又有所不同。具而言之,盛可以的努力方向集中在叙事时间以及艺术结构的处理上。从叙事时间的角度来看,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中实际上存在着双重的叙事时间。其第一重叙事时间的起始点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主要人物之一李小寒的爷爷李辛亥降生于世的1911年。非常明显,李辛亥这一名字的由来,正与他的出生年份密切相关。从那一年起始,叙事时间一直延续到了一百年之后的2011年。这一年,差十天就整整一百岁的李辛亥终于一病不起,告别了他长达百年之久的苦难人生。然而千万请注意,虽然小说的这一重叙事时间的跨度长达百年,但其中的许多时间过程作家所采取的态度都是一笔带过。从叙述速度的角度来看,则盛可以的《野蛮生长》中显然存在着一个逐渐减速的叙事过程。所谓叙述速度,是“热拉尔·热奈特用以代替‘时长的术语。‘事件或故事片段的不同时间与它们在叙事文中的伪时间长度(事实上即文本的长度)之间的关系,即速度关系。‘所谓速度是指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的关系(每秒多少米,每米多少秒);叙事的速度将由以秒、分、时、天、月、年计量的故事时距和以行、页计量的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来确定。”②这里,很显然存在着一种恒定速度的设定。所谓叙述中的恒定速度,就是指故事时间跨度和文本之间的不变比率。假若一个人一生中的每一年在文本中始终都以一页的篇幅叙述,那么,以这个恒定速度为“基准”,我们就可以看到加速和减速这两种变动形式的发生。加速是用较短的文本篇幅讲述较长时间的故事。减速则相反,用较长的篇幅讲述较短时间的故事。用西方叙述学中叙述速度理论来观察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减速的存在,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文本事实。而这,也就意味着,盛可以的叙事重心,实际上落脚到了文本的后一个部分。小说的第二重叙事时间,也即由此牵引而出。具体来说,《野蛮生长》的第二重叙事时间的起始点,乃是发生于1983年的“严打”事件。可以发现,从这个历史关节点开始,盛可以原本疾驰着叙述速度就逐渐慢了下来。此前大半个世纪的故事时间,盛可以只是用开头简短三节的篇幅就叙述交代完毕,其余从1980年代起始一直到2011年爷爷李辛亥去世为止的故事时间,占用了剩余下来的全部文本篇幅。而这,事实上也就构成了盛可以的第二重叙事时间。虽然盛可以《野蛮生长》的总体时间跨度长达一个世纪,但作家的真正关切点,却是“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以来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现实。我们注意到,晚近一个时期,中国一些艺术触觉特别敏锐的作家,已经开始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开始了对共和国所谓的“后三十年”(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把1949年至“文革”结束视为“前三十年”,而把“文革”结束迄今的历史,视为“后三十年”。其实,这“后三十年”已经差不多要变成“后四十年”了)进行深入的批判反思。仅仅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情形来看,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作品,就有贾平凹的《老生》、阎连科的《炸裂志》、孙惠芬的《后上塘书》等。贾平凹在《老生》中把“后三十年”与此前的三个历史时期并置,阎连科《炸裂志》中对炸裂村由村至大都市膨胀过程的艺术呈示,孙惠芬《后上塘书》中关于“改革开放”原罪的尖锐诘问,凡此种种,皆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后三十年”的深入批判反思。而盛可以的这部《野蛮生长》,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大量征用1980年代以来的诸多新闻事件作为艺术想象虚构的故事原型,其根本动机显然就是要凭此而完成一部格外尖锐犀利的对于“后三十年”的批判反思之书。而这,也正是盛可以双重叙事时间营构所欲达至的艺术目标。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盛可以的这种艺术努力与曹雪芹《红楼梦》的艺术设定作一类比。《红楼梦》中最起码存在着双重的叙事时间。假若说关于那块石头“无才可去补苍天”以及“太虚幻境”“还泪神话”的叙述理解为第一重叙事时间,那么,作为文本主体部分存在的贾府与大观园里的故事叙述,显然就应该被看作是第二重叙事时间。究其实质,盛可以的根本艺术意图,正是要凭借第一重叙事时间所搭建的阔大历史框架,精准犀利地切入到第二重叙事时间的深处,进而实现对“后三十年”中国社会种种罪恶的真切诘问与深度反思。
问题在于,仅只是把这些社会新闻事件罗列到一起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优秀的小说文本,盛可以必须设法将这些处于散落状态的新闻事件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有机嵌入到自己完整的艺术结构之中。那么,盛可以在《野蛮生长》中所设定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艺术结构呢?盛可以所具体采用的,是一种第一人称叙事的家族式艺术结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李小寒,是湖南益阳李氏家族的小女儿。她的爷爷李辛亥,出生于辛亥革命发生的1911年。父亲李甲戌,尽管家在农村,但却在城里有一份工作。“我爹是一家之主,老婆和孩子是他的子民。妇孺的羸弱温驯,不但没让主人变得温和,反而助长了他的暴戾。”实际上,父亲李甲戌暴戾性格的生成,一方面固然与“妇孺的羸弱温驯”有关,另一方面却也与他和爷爷李辛亥之间父子关系的紧张对立密切相关。倘若细细追究起来,李甲戌暴戾性格的生成,与其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之间,也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内在关联。惟其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充满着暴戾之气,李甲戌方才会对家庭亲情采取如此冷漠的态度。但盛可以的关注重心,显然并不在李辛亥与李甲戌们身上。从家族的层面上说,尽管盛可以先后写到了李氏家族的四代人,但她真正所倾心书写的,却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李小寒这一代以及他们的下一代这两代人。实际上,从第四节“李顺秋”开始,作家的描写重心就已经转移到了后两代人身上。
但在展开讨论后两代人之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却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为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定位?《野蛮生长》应不应该被看作是一部家族小说?成长小说?或者女性小说?尽管说以上三种艺术定位方式均各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却终归没有能够抓住小说的根本要旨所在。首先,是家族小说。虽然说小说的主体故事依托于李氏家族的四代人而展开,但作家的关注点却显然并不在家族内部种种盘根错节矛盾纠葛的艺术呈示上。盛可以的根本着眼点,显然更在于李氏家族成员与他们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层面上。然后,是成长小说。说实在话,在拿到这本小说之后,我确实曾经为小说的标题而小有纠结:“野蛮生长”到底能否置换为“野蛮成长”呢?尽管说文学界向有“成长小说”一说,而且文本中也的确对于后两代人的成长过程有所呈示,但盛可以的书写动机,却显然更在于这成长与其所处残酷社会环境的联系层面上。也正因此,它便绝非“成长”,而只能够是“生长”。而且,这里的“生长”,显然也只是生存意义上“活着”的意思。接下来,是女性小说。或许与盛可以自己身为女性有关,相对而言,《野蛮生长》中的女性形象较之于男性更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尽管如此,盛可以此作的艺术旨趣却显然并不在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上。虽然说她此前的诸多小说作品如《北妹》《道德颂》《白草地》等均强烈地凸显着女性主义的性别立场,但《野蛮生长》的关注重心却非常明显地还是落脚到了社会现实的层面上。既不是家族小说,也不是成长小说,更不是女性小说,究其根本,《野蛮生长》只能够被看作是一部批判性色彩异常突出的社会小说。盛可以之所以会在一部字数不足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征用那么多社会新闻事件作为艺术想象虚构的故事原型,其根本原因显然在此。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群山之巅》,则以其一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而特别引人注目。所谓“去中心化”,就意味着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艺术聚焦方式来面对故事发生地龙盏镇的那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艺术聚焦方式的采用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作家的多少带有一点“齐物论”色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谓“齐物”,就意味着不仅地位身份不同的人们在迟子建眼里是等量齐观的,而且人与其他各类事物之间也都处于某种可谓众生平等的状态之中。举凡动物、植物,甚至包括自然风景在内,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皆不存在等级上的差异。众所周知,迟子建小说写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特别擅长于自然风景的点染描写。这一点,在《群山之巅》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比如最后第十七章中的一段文字:“但霜也有热烈浪漫的一面,它浸入树叶的肌肤,用它的吻,让形形色色的叶片,在秋天如花朵般盛开。松树的针叶被染得金黄,秋风起时,松树落下的就是金针了。心形的杨树叶被染成烛红色,秋风起时,它落下的就是一颗颗红心了。最迷人的要数宽大的柞树叶了,霜吻它吻得深浅不一,它们的颜色也就无限丰富,红绿交映,粉黄交错,秋风起时,柞树落下的,就是一幅幅小画面了。这时你站在龙山之巅,放眼群山,看层林尽染,会以为山中所有的树,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花树。”我曾经一度以为,迟子建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精彩风景文字,乃是因为作家内心中有着一种强烈的自然之爱。现在看起来,这种理解未免显得有些肤浅。自然风景点染描写的背后,固然有着迟子建的自然之爱,但更重要的,恐怕却是作家自己也未必能够清醒意识到的“齐物论”思想。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理解,迟子建“齐物论”的思想立场,一方面意味着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另一方面则意味着物的主体性的最终确立。因为“去中心化”叙事策略的采用,《群山之巅》自然也就成为了一部没有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悉数登场的那些龙盏镇人物,可以说都是小说的主人公,也可以说都不是小说的主人公。换句话说,每一个人物,都因此而获得了充分的主体性。伴随着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取,《群山之巅》也就成为了一部具有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长篇小说。我们之所以把《群山之巅》判断为一部“北中国乡村世界的生命浮世绘”,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所谓浮世绘,按照《辞海》中的解释,乃指“日本德川时代(1603—1867)兴起的一种民间绘画。浮世是现世的意思,故其描绘题材大都是民间风俗、优俳、武士、游女、风景等,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浮世绘一般以色彩明艳、线条简练为特色,因多数反映当时的民间生活,曾得到广泛的流传和发展,至十八世纪末期逐渐衰落。”这里,我们意在借用这一绘画术语指明迟子建《群山之巅》的基本思想艺术风格。
关于小说写作,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种看法:“小说,是个人想象的天堂,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是真理的占有者,但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③非常明显,米兰·昆德拉此处主要是针对现代小说发表自己看法的。在他看来,一部优秀的现代小说就应该是“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的一种基本情形。迟子建《群山之巅》对人物群像式展览结构的采用,小说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取,正可以被理解为“所有人在那里都有权被理解”的形象注脚。更进一步,假若超越文学的范畴,联系现代社会理论,那么,迟子建《群山之巅》中人物主体性的普遍获得这一文本事实,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对于现代民主权利的一种充分尊重。在这个意义上,细品“群山之巅”这一标题,则会有别一种感悟生成。我们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迟子建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依照作家自己的说法,在写实层面上,“群山之巅”的所指自然应该落脚到“群山之巅的龙盏镇”上。因为故事的集中发生地正是龙盏镇,而龙盏镇一个突出的地理特征,也正是处于巍巍群山的簇拥环抱之中。但是,在象征的层面上,标题中的“群山”是否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对芸芸众生的一种隐喻式表达呢?联系小说文本中作家对于人物主体性的普遍尊重这一事实,这一结论的得出显然也并非突兀。
只有与作家此前创作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布尔津光谱》进行充分比较,我们才能够廓清张好好《禾木》的艺术形式特征。相对于《布尔津光谱》,《禾木》叙事形式方面最显著的变化约略有三个方面。其一,是对“你”这样一种第二叙事人称的征用。就一般的叙事常规而言,我们所习见的叙事人称只是第一与第三两种。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使用第二人称展开叙事者,无论中外皆非常罕见。我个人有限的记忆中,只有法国“新小说派”的米歇尔·布托在其长篇小说《变》中使用过这种叙事人称。关键处在于,张好好为什么要征用“你”这样一种特别的叙事人称呢?张好好此举显然并非故意别出心裁。正如同第一人称“我”与第二人称“你”相对应而存在,二者之间有一种突出的彼此参照作用一样,就我个人的理解,张好好的第二人称叙事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变体,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自我分身效果。作家对于“你”的征用,显然有着一种拉开距离之后的“我”与“你”甚至包括整个世界之间的潜对话意义。之所以要拉开距离,乃是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自我审视的客观效果。这里,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心理前提即是,不管多么富有理性的智者,在涉及到与自我紧密相关的话题的时候,总是会本能地表现出一种自我掩饰与自我美化的倾向。这就正如同孔雀开屏时一般总是会把自己最光鲜靓丽的一面展示在公众面前一样,人在以第一人称进行言说的时候,也总是难免会存在一种不自觉的自我遮蔽状况。这一点,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伤逝》可以说是最典型不过的例证。张好好之所以要在规避第一人称之后,使用作为其变体的第二人称,其根本意义正是为了能够更加冷静客观地呈现主人公之一“你”的基本生存与精神状态。
其二,是对叙事时空彻底打破后的重组。《布尔津光谱》基本上是一种顺时序的叙事,张好好从海生与小凤仙这两个“盲流”从内地流窜至北疆小镇布尔津落脚写起,一直到后来的结婚生子,到三个女儿的成长过程,乃至关于三个女儿未来命运走向的某种预叙,所遵循的是一种自然的时间顺序。到了《禾木》中,自然时序被彻底打破后,呈现为一种现象层面上的凌乱情形,叙述者的思绪与讲述始终不断地游走于现在与过去之间。“你不知道为什么,年轻时会那样荒唐,那几年断断续续进山三四次,次次的晚饭都要喝醉,及至走到夜色的山谷里,天已经完全黑了。你所要寻觅的——那个人呢?”《禾木》开头第二自然段的这些叙事话语,就奠定了小说的两种叙事基调。首先,尽管全篇并非一味地简单倒叙,而是采用了一种时而现在,时而过去的彼此穿插互嵌式叙事,但从总体上说却保持了一种回望往事的姿态。其次,从“年轻时会那样荒唐”一句,即不难判断出某种“觉今是而昨非”的忏悔式叙事基调的具备。更进一步,如果说《布尔津光谱》的顺时序叙述与整部小说那样一种无冲突的谐和状态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那么,《禾木》之所以要打乱叙事时空,进而呈现出一种显豁的时空凌乱感,就与整个文本情节结构堪称紧张激烈的内在矛盾冲突密切相关。
其三,是一种充满内在紧张感的箴言式叙事话语的自觉运用。很可能是与作品那样一种无冲突的谐和状态有关,《布尔津光谱》的叙事话语不仅总体感觉平和、柔软,一点也不张牙舞爪咄咄逼人,而且通篇皆保持了一种平稳正常的语序结构。其中,日常生活气息的渗透与缠绕,是显而易见的一件事情。但到了《禾木》中,所有的这些感觉却都已经遭到了根本的颠覆与重构。不仅平和的长句为短促紧张的短句所取代,叙事的节奏与频率明显加快,而且,整个完整的故事情节也都完全被打碎切割成零散的93个带有醒目小标题的断片,不断地闪回跳跃,然后被作家根据主体表达的需要而进行重组拼接。尤其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禾木》的叙事话语在拥有日常生活气息的同时,更增加了一种具有形而上思辨色彩的箴言式语句的穿插互嵌。“艾蒿那么高,溪水那么清,木头房子是明黄色的,被亿万只草虫的呐喊包围,月亮在东山升起。那个充满魅惑力却纯洁的少妇的脸,和东山的月亮一样美,仓央嘉措如是说。”如此一个富有诗意色彩的小说开头,在写实性地单刀切入禾木这样一个北疆村落的同时,也象征性地寄寓着张好好对于理想生态世界的艺术性想象。其中,箴言式的段落与话语可谓随处可见。“伟大的事业只能是自己的良心和最终的爱情,还有纯洁这个单词,这个随时能把你掐死的单词。”“他以着天意,向你伸出手,拽你从泥浆里起来。他说,你是怎样的,我就会把你当怎样的人看。”“你们已经知道,虫洞,每一次都要抉择,选了这一条,命运的终点是一个样子;选了另外一条,就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可怕的,步步惊心。”细细推想,这种箴言式语言其实携带有鲜明的神谕或者神启的性质。正因为有着类似箴言式话语的普遍使用,所以我们才断定“小长篇”《禾木》是一种比较典型的箴言式写作。
或许与雨水过于充沛,日常被潮湿气息熏陶浸染有关,从一种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说,长期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的作家,较之于北方地区的作家,不仅艺术风格空灵细腻,而且也往往更加讲究小说的技术层面,可以被看作是技术型的作家。艾伟的情形也同样如此,他长篇小说《南方》的引人注目,就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层面上的多所用力。首先,是对于三种不同叙事人称的交叉使用。整部长篇小说共计被切割为85个小节,“我”“你”“他”三种叙事人称以顺序交叉的方式持续推进着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其中,第一人称“我”,是罗家双胞胎中的姐姐罗忆苦,第二人称“你”,是曾经在公安机关工作多年的老革命肖长春,第三人称“他”,则落脚到了那个天生的傻瓜杜天宝身上。又或者,遵循严格的叙事学理论,只有第一人称“我”也即罗忆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典型的叙事人称,另外的肖长春与杜天宝这两种人称,只应该被看作是提供了两种叙事视角。换而言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我”“你”“他”三种叙事人称,又可以被理解为是三种彼此交叉的叙事线索。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叠加,形成了一种立体性相当鲜明的叙事结构。
其次,是对于亡灵叙事手段的特别征用。以亡灵的形式现身并承担着叙事功能的,乃是第一人称的叙事者罗忆苦。在被曾经的男友须南国严重毁容并残忍杀害之后,罗忆苦的幽灵不依不饶地盘旋缠绕在永城的上空而久久不散:“我一天之前已经死了。”“我慢慢失去了意识。不,意识更清晰了,朦胧的往事像刚刚画出的图画,带着颜料的气息,扑面而来。”“如今,我已死去五天,这是我回望人间的最后的时光。不,在灵魂的世界里,已不叫时光,时光已经停止了。我停止在此刻。此后,我也许下地狱,也许上天堂。”“如今我成了一个亡灵,我对这一切有了全新的理解。灵魂是存在的,它有能量,会游动,它还容易被控制,被另一个更强大的灵魂吸附。”之所以要把罗忆苦设定为一个第一人称的亡灵叙事者,对于艾伟来说,肯定有其特别的用意。在有效借助已经处于某种非现世限制状态的罗忆苦的目光来犀利洞察人世奥秘的同时,真切传达一种存在命运的荒谬与虚无,进而赋予小说文本一种强烈的命运感,乃可以被看作罗忆苦亡灵叙事的主要功能之一。“多年以后,我成为一个成熟的女人,历经沧桑,我观察周围的朋友和熟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肚子辛酸往事。所谓的故事,其实是难以捉摸的命运作用在人身上的一本糊涂账。”“说沮丧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像我这样的人,任何词语都仅仅是一个词语,我比词语要复杂得多。那种身体被掏空的感觉是沮丧吗?溃烂的感觉是沮丧吗?命运的无力感是沮丧吗?内心对这世界的仇恨是沮丧吗?对任何人都失去了同情心是沮丧吗?我何时变成了这样?”细读罗忆苦叙事的那些部分,类似于这样一种感喟命运无常的话语并不少见。如此一类命运感喟的话语,若不借助于罗忆苦这样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便难以道出。此类具有鲜明超越性色彩的话语在《南方》中的出现,其承担的叙事功能多少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的“石头神话”与“太虚幻境”,意在传达作家对于人生命运的某种形而上体悟。曹雪芹可以水乳交融地把“石头神话”与“太虚幻境”编织进他的红楼世界之中,但对于艾伟来说,要想使自己的小说作品具有一种形而上意味,恐怕就得借助于如同罗忆苦这样已然摆脱了现世生存逻辑限制的亡灵叙事者,方才可能。
复次,是对于叙事时间的精心安排。小说的叙事时间共计七天,从罗忆苦的尸体被发现的1995年7月30日的早晨开始,等到故事结束,杜天宝的女儿银杏与冯小睦结为夫妻的时候,已经是这一年的8月5日。尽管从表面上看,《南方》的叙事时间不过只有短短的七天,但细究文本的内在构成,我们却不难发现,其实存在着双重意义上的叙事时间。其一,就是发生在这七天之内的当下故事。这其中,最集中的一条故事主线,就是罗忆苦浮尸在护城河中的被发现。既然罗忆苦之死很显然是被他人所杀害,那么,谋杀者究竟是谁?这个人又为什么一定要谋杀其实已经在永城消失很多年的罗忆苦?还有就是,这个谋杀者到底和罗忆苦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不可原谅的深仇大恨,杀了她还不解恨,还一定要毁掉她的容貌?以上种种带有强烈悬疑色彩的疑问,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向前发展。尤其不能忽略的一点是,艾伟所特别设定的“七天”这个叙事时间,既合乎于中国民间传统中的所谓“头七”习俗,也更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西方基督教《圣经》中所讲述的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也只是同样用了七天的时间。上帝用七天的时间创造了整个世界,艾伟在七天的时间里完成着《南方》的小说叙事,这两个七天,肯定不会是无意间的巧合。二者的区别很可能在于,上帝是在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新世界,而艾伟在《南方》中却是在表现着现实世界的颓废、堕落乃至于毁灭。一种末世情调在《南方》中的存在与弥漫,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其二,虽然当下的叙事时间不过只是有限的七天,但就在这七天的三种叙事人称的叙事过程中,我们却可以发现,叙事者总是在不断地从现在返回到过去,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完成闪回叙事。这种闪回叙事,从1950年代初期写起,一直延续到了故事终结的1995年盛夏时节,其时间跨度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之长。在这被明显扩展抻长了的叙事时间里,艾伟的关注重点又分别落脚到了1960年代与1990年代这两个社会存在形态格外鲜明的历史阶段。对于这一点,《人民文学》的编者可谓所见甚明:“长篇小说《南方》从‘死写起,一路串缀的死其实都是在表达‘生。奇异之处在于,这部作品的核心主题竟然是‘爱。亡者成为亡灵,七天里闪回的记忆现场,是一个驳杂而近乎迷乱的世界图景,禁锢年代的压抑和情欲的澎湃状态,开放时期的狂躁和精神无所依傍的恍惚,汇成一种向爱而生的生命观。故事里命运的烟尘使人咳喘甚至窒息,而小说里悯生的空气则供我们呼吸。”④尽管我们并不完全认同编者对《南方》的评价,但《卷首》所指明的作品对禁锢与开放两个不同时代的表现,却是毋庸置疑的一种事实。
但同样是亡灵叙事,陈应松的《还魂记》却又与艾伟的《南方》形成了鲜明的区别。正如“还魂记”这一标题早已经明确标示出的,陈应松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第一人称的亡灵叙事模式。其实,只要稍加留心,我们即不难发现,最近几年来中国小说界已经出现过若干部同样采用亡灵叙事模式的长篇小说。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诸如余华的《第七天》、雪漠的《野狐岭》、孙惠芬的《后上塘书》、艾伟的《南方》、陈亚珍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等长篇小说,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着亡灵叙事这种艺术手段。虽然说这些作家对亡灵叙事手段的使用,肯定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想艺术考量,但在我的理解中,亡灵叙事现象在晚近时期中国小说文本中的扎堆出现,无论如何都有着一种不应该被轻易忽略的社会学原因。余华《第七天》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杨飞,在餐馆吃饭时遭遇爆炸意外死亡;雪漠《野狐岭》中的众多亡灵叙事者,是百年前蒙、汉两支驼队在野狐岭发生火拼冲突事件后的神秘失踪者;孙惠芬《后上塘书》中的亡灵叙事者刘杰夫的妻子徐兰,故事一开始就不幸被自己的亲姐姐失手误杀;艾伟《南方》中的第一人称亡灵叙事者罗忆苦,在被须南国严重毁容后又残忍掐死;陈亚珍《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胜惠,被自己的丈夫王世聪无意间用一块砖头打死。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这些小说中的亡灵叙事者,皆属横死,绝非善终。某种意义上说,正因为这些亡灵内心中充满着愤愤不平的抑郁哀怨之气,所以才不甘心就那么做一个鬼魂中的驯顺者,才要想方设法成为文本中的亡灵叙事者。
与上述长篇小说中叙述者的非正常死亡相类似,陈应松《还魂记》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也即柴燃灯,也同样很不幸地死于非命。身为在押刑犯的他,在监狱中苦苦煎熬二十年时间,但在他即将服刑期满,眼看着再有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被释放出狱的时候,却因为刑犯之间的彼此报复而被三个同改整死在疵纱堆里:“一个人将我狠狠地摁住。”“两个人将我狠狠地摁住。”“三个人将我狠狠地摁住。”“他们仿佛都有四只手。还有兽脚,有尖锐似铁的爪尖。像鹰,抓住猎物,一动不动。”“那几个人用棍棒挤压我脑壳里的黄水,那个断颈的大头左右晃动,让我眼睛都花了。血糊着眼睛,我看到了红色。”整死“我”之后,“他们在我的颈上拴绳子,想制造我上吊的假象。他们把我拖进疵纱堆里,用疵纱壅住。”非正常死亡之后的“我”冤魂不散,顽强地从一堆疵纱中挣扎出来,飘荡向遥远的野猫湖故乡。在半夜,“我”的冤魂抵达了野猫湖:“一个声音暗示我说:你会慢慢明白,你的魂触到你的养生地,于是还魂现身。”何谓养生地?按照野猫湖也即楚地的民间传说,所谓“养生地”,“就是你的胞衣所埋之地。”当逝去者的灵魂触碰到标志着出生时刻的“养生地”的时候,他的灵魂方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复活”现身,如同生前一般地四处游荡寻访。很显然,倘若我们要寻找陈应松亡灵叙事的缘起,楚地的民间传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谈论鬼魂是我们楚人对故乡某种记忆的寻根,并对故乡保持长久兴趣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当下还是过去,让我们在许多沉重影子下生活下去的动力还是来自大地的力量。当大地神秘的生命在搏动的时候,我们会有文字和声音应和。”⑤毫无疑问,陈应松的这部《还魂记》,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应和大地神秘力量的文字产物。又其实,热衷于谈论鬼魂,正是楚地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早在《汉书·地理志》中,即有这样的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太平御览》中也说:“昔楚灵王骄逸轻下,信巫祝之道,躬舞坛前。吴人来攻,其国人告急,而灵王鼓舞自若。”楚地的这种巫祝文化传统,在屈原的一系列重要作品中可谓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由此,陈应松《还魂记》中对于亡灵叙事手段的征用,除了类同于以上作家一样的社会学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乃可以被视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楚地巫祝文化传统在当代的一种遥远回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还魂记》中亡灵叙事的艺术手段与西方文学影响之间的内在关联。或许正如一些敏感的读者已经想到的,我这里的具体指称对象乃是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那部曾经影响了包括马尔克斯在内的很多作家的中篇小说经典名作《佩德罗·巴拉莫》。《佩德罗·巴拉莫》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遵从母亲的遗愿,去往一个名叫柯马拉的地方,寻找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佩德罗·巴拉莫。本来怀抱着美好的向往,没想到“我”最终抵达的却是一个支离破碎、死气沉沉、遍布亡灵的柯马拉。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只有在阅读过半的时候,读者才能够搞明白,却原来,叙述者“我”事实上是一个躺在棺材中的逝者。都是亡灵叙事,都是在回返一个其实已经不存在了的鬼气森森的村庄,《佩德罗·巴拉莫》与《还魂记》艺术思维上的某种同构性显而易见。胡安·鲁尔福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一位代表性作家,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却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因此,陈应松的《还魂记》之受惠于胡安·鲁尔福,显然无可置疑。但是且慢,在强调陈应松接受胡安·鲁尔福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仍然不能忽视《还魂记》的亡灵叙事与中国本土小说传统之间某种影响关系的存在。倘若说《红楼梦》《金瓶梅》属世情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是家国叙事,那么,《西游记》《封神演义》此类超现实色彩鲜明的一类就显然是神魔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可以被归入到这一类。虽然基本的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极明显的差异,但陈应松的艺术思维曾经接受过神魔小说的滋养,却也是无可否认的一种客观事实。
以上,我们林林总总挂一漏万地对2015年若干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文本艺术形式特质进行了一番不失粗疏的分析。究其根本,艺术形式的恰切完备与否,只是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标准之一。一部长篇小说,要想足称优秀,同时也还需要有深刻浑厚的思想内涵,需要有具有人性深度的人物形象的刻画与塑造等诸层面的同时具备。这样看来,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努力探索,也只不过是优秀长篇小说得以最终生成的一个不可忽缺的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来看,2015年度内,诸多长篇小说文本中体现出的艺术形式层面的多向度探索实验,实际上就为优秀长篇小说更高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潘雁飞:《论新时期小说创作寓言化的历史根源和现代契机》,《湖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
②参见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365页。
③[捷] 米兰·昆德拉著, 孟湄译:《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5页。
④《<人民文学>卷首》,《人民文学》2015年第1期。
⑤陈应松:《<还魂记>后记》,《钟山》2015年第5期。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13&ZD12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