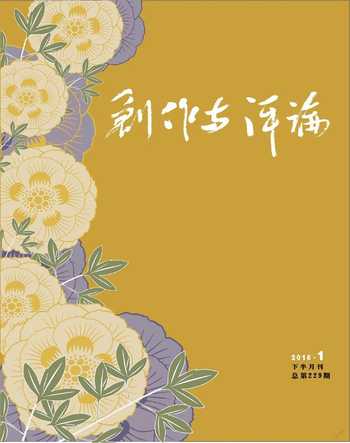表象的恐慌与本质的自由:对新媒体时代文学境遇的另一种思考
张晓琴

1975年生于甘肃,文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长篇小说研究。近年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南方文坛》《民族文学研究》《文艺争鸣》《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有专著《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研究》《直抵存在之困》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部生态文学研究”等项目。获甘肃省黄河文学奖、甘肃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奖、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项。从事文学批评的同时进行诗歌、散文创作,201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一
每代人总会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判断,或赞叹,或不满。往往是后一种判断出现的概率更多。黑塞为了表达自己对于那个副刊文字时代的不满,虚构了一个名叫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的文学史家,借他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副刊文字时代并非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他借切根豪斯之口说:“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毋宁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作用。”①它几乎是蕴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气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在他看来,副刊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最热衷写的题材是著名男人和女人的奇闻逸事或者他们书信所反映的私生活,这些文章都是匆匆忙忙问世的急就章,烙刻着不负责任地大批量生产的印记。与副刊文字同类的文化活动也开始盛行,连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的变体。
尽管黑塞用一种平静的口气掩饰自己的不满,但还是能看出他著述时的本意。他对副刊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持一种批评态度。他试图清理那个时代的文学,因为其时的文化生活是一种因过度生长而耗尽元气的退化植物,只得以衰败的枝叶来培植根株继续生长了。在黑塞的时代,报纸其实就是一种新媒体,这种新媒体让读者的目光从经典转向副刊,读经典,还是读副刊?这是个问题。然而,若是黑塞面对我们这个刷屏时代,他的灵魂是否更加纷乱? 今天,我们的焦虑已经变成:读经典,还是被刷屏?
每一次新媒体的出现,都会给文学带来很大影响,甚至恐慌。在此之前,文学就已经遭遇更多的威胁:所谓的副刊文字是第一次,迄今越来越热的影视是第二次,新世纪兴起的网络是第三次。此后是第四次威胁,即手机。手机只是网络的延伸者而已。面对此前的媒体而言,它们就是新媒体。一个有趣的现象就产生了,文学本身是一种艺术,而影视、网络、手机作为承载艺术的媒体,为何它们让文学如此惶恐?
事实上,当人类面对每一种新媒体的时刻,都会产生一个问题:文学活着吗?它还在新媒体中吗?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雅克·德里达。他在《明信片》中认为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ies)。其中被希利斯·米勒引用过的那段话很有名: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当然,这段话是借书中主人公之口说的。解构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耶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J·希利斯·米勒这样表达自己最初的感受:“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② J·希利斯·米勒曾写过一部书叫《文学死了吗?》③,从多个方面来探讨文学的存在。书中有一个小标题“印刷时代的终结”,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最为椎心而又无可奈何的声音。这也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尴尬。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文学界关于“文学终结”的讨论与J·希利斯·米勒也有关联。他在2000年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长篇发言,并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发表于《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其中“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 (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的论调成为引发“文学终结”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原因。童庆炳就此发言,他指出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不会消亡。因为文学自身也是永远变化发展的,但变化的根据主要在于人类情感生活变化,而不是媒体的变化。④当然,也有学者认为现代科技从根本上更新了艺术活动的媒介、手段、效果以及生产、流通与接受的方式,随着现代影像技术和音像技术的革命,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媒介优势逐渐消失。⑤
2006年10月,“梨花体”成为中国大陆网友质疑和批评的一个焦点。这个时候,叶匡政在新浪开博,他在第一篇博文中宣称:“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⑥,文章被新浪编辑推出后,几天点击量便达到数万,并被数千家网站转载。叶匡政又抛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四种死状》等文章论述文学的死亡。这是文学在新媒体时代的一声悲叹。
这样看来,文学在新媒体时代遭遇的命运就是消亡。然而,文学自然有它神圣且独特的地方,一如巫术或宗教对于人类一样,但巫术仍然隐遁于人类心灵的一个角度,宗教已然也在一变再变。如果我们将文学放在永恒面前,它到底代表了什么?它是否与永恒伴随始终?也就是说,当人类一经产生,文学是否就存在呢?或者我们这样设问:当文学消亡之时,人类也必将消亡吗?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没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非要拉着永恒的衣领,让他硬把文学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放在一起。
二
这样一来,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的作者问题,也就不能不提到后殖民主义学者萨义德和他的《知识分子论》。在萨义德以及葛兰西等人看来,当知识不再被少数人所拥有,当人人都拥有大量知识的时候,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便显得异常重要,知识分子也就成为少数拥有人文价值立场、敢于站在权威者的对立面、敢于对一切不正义的行为发出批判的人们。也就是说,当人人都成为大学里的受教育者,当博士、教授、研究员比比皆是时,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而是缩小为它最初的意义所指,即为人类的正义、良心和信仰而赴命的人们。于是,知识分子便成为先知、圣人以及与当权者持不同意见的领袖们。萨义德的这样一种观点虽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其站在第三世界的文化立场对强权文化的反抗,其站在时代的洪流中对人类亘古以来的精英立场的坚持是值得肯定的。
网络时代的文学显然也面临这样一种重新选择的局面,即网络的没有门槛使人人都成为作家,使所有的书写都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时,我们便有必要发问,什么是文学?那些人类由来已久的经典自然不用分辨,但今天产生的大量文本,哪些才是文学?显然,萨义德的方法与观点在这时便派上了用场。
今天的书写已经失去边界,在以往时代被文学的伦理禁锢着的魔鬼都被网络解放了。大量粗俗的流氓语言充斥网络,被认为是文学语言;所有的行为都可进入书写的范畴,人类原有的经典被解构一空,一切神圣、正面的价值体系在今天土崩瓦解;审丑、恶心、阴谋、罪恶、残暴都成为书写者们愿意精心打造的美学立场,与此相对应的存在则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尤其是在一些超文本的书写中,网民们将所有的不满、愤怒、恶语都喷洒在网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像这个时代这样价值混乱、美丑难分、善恶难辨、真假颠倒。这就是今天的写作世相。
在各种文本横行的今天,那些真正的文学不是多了,而是越来越少了。它们也许越来越趋近于最初的文学本质:解读真理、教化大众、以天下为己任,融文史哲于一体。
有人认为,网络全媒体时代解放了文学与人,因为人人都成为文学的受益者,成为作者。这样一种乐观的态度有其对的一面,因为它的确使很多有文学梦想的人开始踏上文学之路,也使文学成为文明时代人类的一种修养。但它其实是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人人都可以从事文学的时候,文学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被书写出来的文本,而是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包含着人类终极价值追求、透示着人性之根的那些罕见的文本。它们与知识分子一样变得稀有。
这的确是一个文本横行的时代。而一旦谈起文本,便不得不谈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罗兰·巴特原本的想法是要告诉人们,当作者将作品呈现给读者之后,作者就告别了其作品,作品自身有其万千个命运,而这万千命运是与读者共创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宣布,作者已死,作品因读者而活着。这样一种美学观点一直都有争议,但放在今天的命题上,似乎有了新的含义。
前面已经述及,网络新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它没有门槛,人人都成为作者。如果我们来分析文学史或作者史的话,将会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重大的革命。在孔子之前,文字和书写乃国家所有。孔子之时,天子之书流落民间,民间学术兴起,私人写作方兴。也就是说,孔子之时,写作乃圣人所为。圣人没后,写作便由精英知识分子来操持。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等皆为此列。报业兴起之时,恰逢封建制度结束民主思想兴起之时,大众得解放,神学体系瓦解,平民的人学体系建立,这个时候的写作便已然来到大众知识分子写作时期。作家群中,有精英知识分子,也有大众知识分子。文学史称其为“人的文学”时期。到了网络时期,精英知识分子被进一步推挤,大众知识分子开始一统山河,“人的文学”已经演变为“身体写作”“欲望写作”。就像福柯所说的那样,人被知识、欲望终结了。
传统意义上的神性写作者彻底死了。也正是因为他的死亡,旧的写作伦理才被打破,新的写作伦理得以确立,而新的书写者也才产生。这便是大量网民的书写。从圣人移到精英知识分子,最后到大众。这显然是一种下降的趋势。作者在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死亡方式,而其每一次的死亡,便是文学的新生。
但现在,我们要问,在大众写作时代,谁才是真正的作者?还有真正的作者吗?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做个判断:大众书写的网络时期,作者已死,无数的书写者诞生。书写者不再听命于神的召唤,也不再坚持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随心所欲的书写,是娱乐书写。
与此相关的是读者的问题。在传统文学的方式下,文学在维护一种自创世以来延续至今的真理、价值和信仰,所以,读者也便是在作家的指导下体会道的存在,体会神的意志,接受国家意志与人类一切正面的价值,从而达到自我的完善。但现在,人人都成为书写者时,人人也便成为读者。
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也死了。只有当读者超越这个人人成为书写者的时代,当他感到无比孤独时,他就会寻找新的精神护佑,他也就自然与其精神信仰之间签订新的合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才会发现作者并没有死去,一切都在那里,只不过他所站的地方太低而已。
三
如果用这样一种开放的方式来思考,我们就会轻松一些,就会得出一系列让人类欣喜的而不是痛苦的结论: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而存在,它或为声音而存在,或为文字而存在,或为某些符号而存在,甚至或为视觉而存在。文学在为人类立传,文学在为人类传承历久弥新的故事。也许人类学家弗雷泽、心理学家荣格的原型理论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那些开创性的经典就已经把人类所要经历的大概路径概括完了,文学不过是在经验上使那些原型故事根深叶茂、日日簇新、细节饱满。除此之外,它还能有什么呢?
从虚无主义的角度来看,它不过是农耕时代的日日轮回,是陕北放羊娃的生死轮回,是吴刚伐木、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它似乎毫无意义。但是,神话时代的吴刚伐木和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是有其道德与伦理意义,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活生生的细部,它是文学所要讲述的好故事。加缪一篇精彩的《西西弗斯的神话》把西西弗斯解放了出来,让西西弗斯将诸神的惩罚抛之脑后,而让他去重新回归大地,拥抱山川河流,让他重新回到拥有正义的现实与日常,于是,存在主义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就此显现。如果我们将《西西弗斯的神话》当成一篇哲学也未尝不可,但它的的确确是文学,字里行间迸发着巨大的热情、通透的生活感受,以及新的人生观的阐发。这就是文学必然要存在的一个理由。
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真的如此吗?相对于人类的精神信仰而言,文学也只是我们获得精神信仰和自我宣泄的一种载体。由西方的科学主义在对人类的精神进行去魅之时,整个世界就开始失去了想象,失去了光彩。不可否认,经典作品也可以在网络上阅读,但是一本带着纸墨香的实实在在的书和电子屏幕划动过后,哪怕是读者作了电子批注的电子文本本质上是不一样的。然而,如何在新媒体时代继续寻找文学的那盏灯才是更重要的。
任何一种新的媒体出现时都会对已有的媒体和文化形成冲击,但是毫无疑问,新媒体在加速文学的传播方面是有益的。新媒体让文学的传播变得简单,此前要读到一部作品主要通过纸质媒介,而新媒体让我们很容易读到原本不太容易读到的文本。与此同时,新媒体让这个时代变成了一个自媒体时代,许多文学作品的传播是通过博客、微博、微信等来实现的,在这一点上,网络作家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甚至需要重新审视。
众所周知,许多文学作品是在其影视版作品产生影响之后才引起文坛乃至社会广泛关注的。这样的例子很多,从20世纪80年代的路遥、莫言、苏童、张贤亮,到当前的严歌苓、冯唐等,其文学作品的传播往往与影视作品的传播紧密关联,当然,影视作品是否忠实于原著则是另外一件事情。事实上,影视作品有其自身艺术形式、时间(主要是电影)等方面的限制,不能以是否忠实于原著作为衡量其好坏的惟一标准。问题的关键在于,换一个方向看,透过影视作品看文学,则会发现真正优秀的影视作品中往往有很强的文学性,比如朱塞佩·托纳多雷导演的电影《海上钢琴师》,视觉和听觉的卓越效果背后,深藏着文学性的幽灵,没有意大利作家亚历山德罗·巴里科的同名小说,自然难有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就此,学者陈晓明在十余年前曾经撰文论述,他认为文学对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渗透,起到潜在的隐蔽的支配作用,所有以符号化形式表现出来的事物都在某种程度上以某种方式被文学幽灵附身。这就是“文学的幽灵化”⑦。
回过头来,我们要重新去回忆文字未经产生时代的神话传说、萨满的神秘语言以及那漫山遍野的咒语。那个时候我们有“文学”这个概念吗?我们都知道,没有。当文字产生之后,才有文学,于是,文学继承了语言的衣钵。影视对文学的解构在于,它用视觉来代替部分文学,使文学的娱乐性更强。这使文学的操持者们惊慌失措。事实上,人们已然忘记了,托尔斯泰的那些白描式的叙述,肖霍洛夫对静静的顿河以及平原上广阔大地的描写,几乎就是一个导演在讲他如何用摄像机来记录那一切。事实上,人们也已然忘记了,视觉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第一个也是最为直接的方式。虽然我们承认,文字乃神授,但难道视觉不是神授?文字需要学习才能得到其秘密,视觉不需要。因此,它和声音是人类的第一认识方式和表达方式。问题在于,视觉艺术的浅薄被我们夸大为其本质属性。这是人类的一种反抗,绝非理性判断。
文学在视觉艺术中就要消失吗?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所在。文学对人类心灵的护佑、表达也不会被影视等其它形式而消灭。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不能确信声音和视觉语言能完全代替文字,反过来讲,文字,这一凝练了音、形、义的神秘符号是在声音和视觉形式不能完全表达人类之时发明、成熟起来的,它也将长期伴随人类而存在。在人类的意识里,还没有完全废弃文字的可能。因此,新媒体时代虽然不时传来文学死亡的恐惧之声,但文学依然存在,以她自己的方式。
注释:
①[德]黑塞著,张佩芳译:《引言——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玻璃球游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据德国研究黑塞的学者推断,黑塞应当是以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隐喻罗马作家如乌斯·普里尼乌斯·西孔多斯及其批评罗马文化的思想。
②[美]J.希利斯·米勒著,林国荣译:《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③ [美]J.希利斯·米勒著,秦立彦译 : 《文学死了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⑤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的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年第6期。
⑥参见叶匡政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ab6b00100063l.html。
⑦ 陈晓明:《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记忆》2002年创刊号。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