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正在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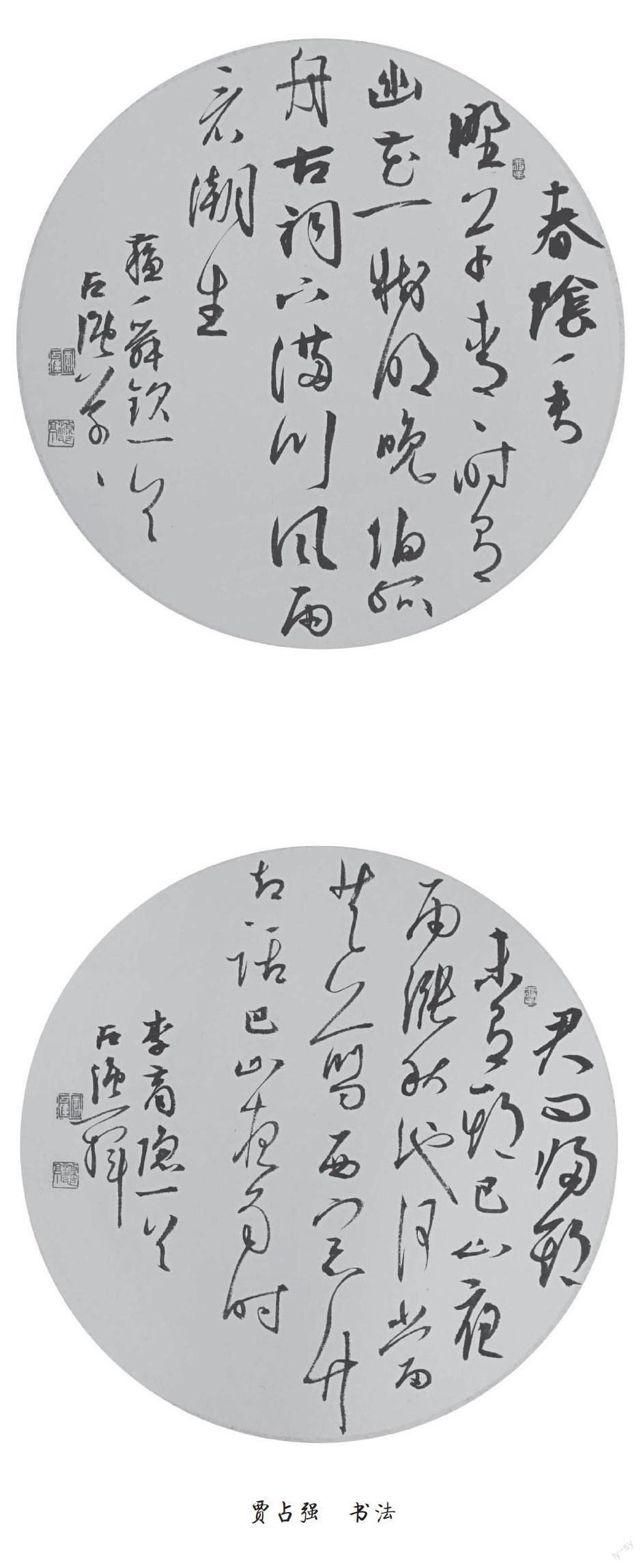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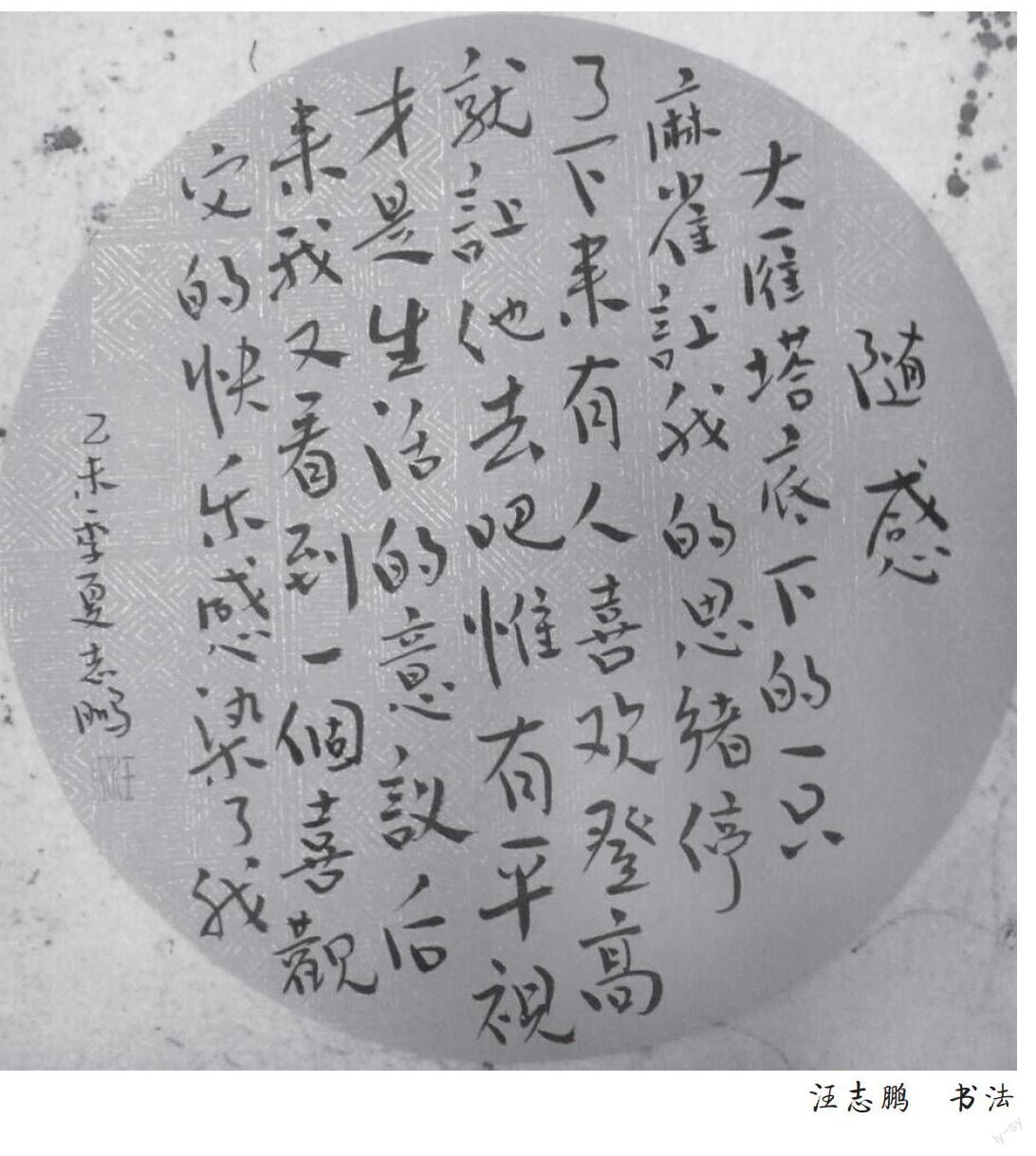
1
端午节回家,母亲说:“去锄一锄地吧,棉花要荒了。”我长久对着电脑,是该舒展一下筋骨了,再者几年未下地,着实对农耕生活念得慌,便欣然答应。
推开杂物室的木门,一股淡薄的尘土气味扑过来。阳光从窗子穿过,沿路和岁月的碎屑打着照面,我迟疑几秒还是跳进了飞舞的尘埃。铁钎、镰刀、斧头都落寞地倚着墙壁,像去到时光以外的亲人。我把锄头摇醒,拂去木柄的尘土,有些松动,便在他脚踝处缠上“绷带”,再给他穿好“铁鞋”。我扛着我这亲人,走向我们的棉花地。
这块地只有两三分,和相邻的几块地一样,原是合作社时代留来专门种菜的。那时相邻的两条街组成一个队,一起下地劳动,后来分地了邻里的地还是相挨着,这家见那家没有改种粮食,便也跟着继续种菜。邻居们常结伴下地干活,冬天到了,东家搭了西家的车,将几畦白菜收回去,过年和肉丸子一起煮,吃得喷喷香;而西家借过东家的铲,把那几垄萝卜挖了去,院子中间埋了以防冻坏,过年再挖出来,和葱姜猪肉一起剁。其他季节则有松土、播种、浇水、拔草、收蒜、拔葱等等,无论做什么都是相互帮衬着,也相互较着劲。“这家娘们儿真勤快,瞅瞅这韭菜多粗壮!”说话的男人在外挣钱,他女人听了就不服,担起扁带就挑两桶肥料过来,接着又浇水。过几天再看,嘿,两家的韭菜竟不分伯仲了。真是应了那句“人勤地不懒”。
那时我非常喜欢来菜地,这里的红萝卜水灵灵,就着井水一洗,满口清秋好滋味。除了吃,劳动时候的热闹和人们互开的玩笑也吸引着我。蜚短流长在自然的天地里自惭形秽,只有诸如“东头李毛家添了胖孙子,嘿,真有福气”之类的的细细碎碎,而这正是生活。
如今我又一次站在菜地,却找不到曾经那条瘦如脊骨的小路。它在岁月里遭受了没顶之灾,和水沟、老井一道被人们的锄头推平。大地又一次平整,几十年用丰收喜悦踏出的路,就那么无声无息被抹去了。如今改种耐旱作物,比如棉花、红薯。人们不需要经常下地管理,路自然不需要了。而水井是早就瞎了——这几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地下水位下降得厉害。
我穿过邻居的早玉米,他们的叶片抽打着我,很疼。力是相互的,他们也疼。这群守卫自己河山的将士,显得多么力不从心:两百米以外的塔吊旋转得正欢。长矛的红缨在风里抖动,像是说着英雄末路的悲壮;而他们的干粮总是鼓鼓的塞了一行囊,这土地肥沃慷慨又无奈,纵使送其赴死也要他们做饱死鬼。
来到自家棉花地,果然是荒草没膝了。母亲那般勤劳,没难想象她居然能容忍自己的庄稼荒芜。我吐了吐沫湿润自己的手掌,之后背对太阳挥舞锄头。我在母亲的土地指点江山,却没有运筹帷幄的底气:棉花太矮,我必须小心才不至于误伤。遇顽固之草我得集中兵力,多流汗水,多磨水泡,这如两军对垒多日,忽一方强攻,怎奈敌兵早有准备,于是伤亡惨重;遇身陷敌营战友我又得丢了锄头亲自出山,俯下身来轻拉硬拽草藤,这无疑是军师的唇枪舌剑,软硬兼施……虽汗流浃背,但总算是大获全胜,我再一次找到劳作的快乐,在夏日难得的爽风里环视疆土。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过是孤家寡人,心里无可遏制地生发滔滔寂寞,邻居们都到了哪里呢?你看那家汹涌澎湃的草浪,你看这家萎靡不振的烟草。现在是夏天,正是草木葱茏、蔬菜丰收的好时节。记得前几年,地里的人很多,蔬菜和人比着热闹。豆角垂地如杨柳,辣椒红红,黄瓜挂满架子,茄子压弯了枝头。尤其是下了一夜雨,雨里少量的硝酸相当于氮肥,第二天一大早,你必须拿了大麻袋才装得回去。可是后来,雨水酸度变浓,一下雨蔬菜必被烧死。这是人们改换作物的原因吗?
我和玉米一样,茫然看着不远处的塔吊。
2
每次回家都是周六傍晚,父母还在外村的工地上工。我煮些玉米糁,等他们回来。常常快八点了,街门才有响动。大热天的,他们归来时已经筋疲力尽,如果我不在,他们很可能就把晚饭凑合过去了。我上班之地是小城市,但节奏已经很快,早餐常常是在路上下肚,晚上还要义务加班,归来自是疲惫。这可以理解,城市向来如此,但村庄被快节奏攻占实在让我深感意外。想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父母早晨也开始匆匆行动,啃着硬馒头,三下五除二便把面汤倒进胃里,去村口等包工头的四轮车。
村口在清早和临晚是最喧闹的,去工地的泥瓦匠、小工,去县城工厂的临时工一拥而出,电动车挡了四轮车,自行车堵了面包车,于是喇叭群起,刺耳与闹市区无异。
最近几年,经济大潮从城市一路奔袭而来,席卷乡村,人们都喜欢了攀比,挣钱多的人鼻子都朝天。这种风气下人人想着挣大钱出人头地,于是小厂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无数。它们一律拥挤在通往城市的干道旁边,好似乡村的喉咙患了食道癌,害得农田一瘦再瘦。这些“肿块”多是为了配合城镇化进程,建筑业火得不行,那洗沙场、石粉场、木料厂必然要开个十家八家。
土生的厂子多是不成气候的,而被城市淘汰的电厂、橡胶厂等却可以盘踞一地,枝繁叶茂。它们极受地方欢迎,官人都要抢的,一旦抢到手就神仙一样供着,划地盖厂优惠多多。
邻村引进一座铅厂,开始官民两方都热捧它。失去土地的村民可以承包建厂工程,我某个亲戚就是其中一位。他把我父母及众亲朋招致麾下,大干一场,收入多少不知,反正在县城买了房子,也有车了。受到好处的人很多,能进工厂的都进了,村民大抵觉得当工人比当农民有光彩,过年过节还发大米,故而都欢喜。进不了工厂的,就在厂外开饭店、理发店,因为发展服务业也挺挣钱。
那几年原本僻静的小村简直成了经济中心,十里八乡的都往那里送货物。但是好景不长,最开始是几名小学生查出血铅超标,接着大家都去查,结果大为惊慌。谈判无果,开始堵村口,不让工厂的货车出入,激烈之时甚至砸车。全市武警出动,封村抓人。村民叫来电视台记者,该记者却被阻挡在警示线以外,最后怏怏而去。那时我上初中,有几位同学回家被拒,他们从麦地悄悄潜回自家,下午归来就成了焦点人物,各种小道消息飞传。而我确定的是,刚结婚几天的表哥被抓了。
后来风声过去,厂里开始招安,每个孩子一周发补助若干元外加牛奶一箱,因为牛奶可以排铅。然而村庄的毒素却是无法排出了,表哥去外村卖白菜,一说是哪哪村子的,人家扭头就走。村边的奶牛场据说也倒闭了,奶牛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用牛奶救孩子吗?于是孩子都去外地躲铅,小学倒闭了,我小时候和表哥表姐一起奔跑的那所小学,最后只剩下两个学生。
我在《焦点访谈》见到了熟人,村民们抢着控诉铅厂的罪恶。这期节目除了在十里八乡掀起一场大议论,再没有其他效果,而铅厂依然经营。
记得工厂奠基时,我和外公站在一起。那是四五月间,麦子已经抽穗,再有一个月就要丰收。然而时代是等不及的,推土机把所有绿色聚拢成堆。外公拾起一颗麦穗,搓开麦壳子细看,什么都没有。我那时不懂什么,但仍然感到疼痛。周围的人都表情凝重,守着自家田地,什么也不说。
其实,被推倒的何止麦子?当肥沃的田野埋于水泥,许多沿袭千年的东西都倒下了。进入工厂的人,也有保留土地的,但他们没有经营的耐心。一种叫“快”的毒素被吸入生活的肺腑,那么多人得了病。我很少再见到蹲着施肥的人,他们不怕脚麻,一手拂去作物周围的杂草麦秆,一手均匀播撒肥料。而现在用的都是机器,肥料浮在麦秸上,庄稼无法吸收也无妨,反正种地只是捎带的。收获季节,已很少见到各家抢占马路晒粮食的场景。你在村里走,根本看不到摊开的肤色麦粒或金子一样的玉米,它们被直接送进粮站,村民没有时间晾晒与扬尘。自家粮仓也不要存粮,没面粉了就去买一袋回来。就是面粉也是很少吃的,面条和馒头都有卖的。只是吃的不再是自己的粮食,没有以前那么放心、香甜;只是我再也看不见,去河边淘洗麦子的妇女,她们曾经那么耐心地淘啊淘,晾干之后还要细细拣出石子和草棒。而磨坊总有那么多人排队,鸽子从排气口飞进飞出。
它们飞进飞出,可飞出就再也没有飞回来。
3
与我一路之隔的那一整片土地已经被台商租下,说要搞科技、农业、旅游的结合体。塔吊就立在那里,它旋转着为泥水匠运去材料,供他们建造楼房。我去外围看过,原来躺着别人祖坟的地方,现在立了一座月季雕塑,周围繁花似海,挂果的海棠连成片,这土地从来没有如此美过。父亲说里面还养有孔雀等珍禽,以供城市游客戏耍赏玩。
我零星从网络搜到相关报道,说园区的投资额巨大,未来必能惠及周边村落。我知道这最起码要比铅厂好,可还是无法乐观起来。阿来在《被遮蔽的西藏》一文中指出,之所以出现“西藏热”是因为人们渴望一种与现实相反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精神上的、单纯的、浪漫的,然而这不是真正的西藏,只是外人的想象罢了。他还说,在西藏有一部分人愿意作种种展示来满足游客的想象,让人误以为西藏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而我眼前的园区无疑走了西藏路线,它要把工业化进程中伤痕累累的乡村伪装成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来向城市展示。
之前我在出租房墙外发现一张广告,内容是关于“开耕节”的:应广大市民强烈要求,现将滨湖公园辟为菜地出租,吃自家无机蔬菜,享受农耕之乐,您还在等什么?我很想笑,前不久去市郊,那里的工地正疯狂吞下土地,而这里却又开始渴慕回归自然了,这自相矛盾多么可笑。不过细想起来,矛盾中却又存在统一性,即两者背后都是经济大手在操纵。它让城市扩张,让农村交出土地,那你就得依命行事。这矛盾无从解决,所谓“农家乐”和“开耕节”只是商家挣钱手段,他们只会给人们呈现标本。
我在昆山打工时去过千灯古镇,那里是昆曲故乡,想象中她是江南锦绣之地,果然那里有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流水污浊,人家变商家,开足了高分贝的“伤不起啊真的伤不起”以招揽顾客。那里徒有古镇之貌,而填充物却是现代商业文明。也去过海淀公园,园内有一景叫“御稻流香”,说是曾经那里水好米好,皇帝喜欢。如今那里仍留有一小块稻田,周围有茅草屋与水车模型,作为小学生实践基地以及市民遥想农耕时代的参照物。
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推进着,村落许多东西都有消失的危险。假若几十年之后我们离开了土地,那些与生活水乳交融的耧耙犁铧、鸡舍羊圈从此隐退,我们也需要依靠标本来寻找乡村历史;假若空气不再干净,邻里不再互助;假若我们富有,却如无根草芥一般浮在风中……那完成城镇化又有什么意义?
冯骥才说:“有些村庄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遗存和历史财富非常深厚,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但没等我们打开,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了……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是啊,乡村的历史、道德观、文化无疑是另一块肥沃土地,乡情根植于此,我们不止挽留,还要供奉。
4
去过湛江一座小岛,只有镇中心那条通往钢铁厂的路比较热闹,其他街道却少有行人。有天我循着鸡鸣过去,竟发现与大街迥异的情景。原来楼盘背后是荒村,只有几位老者在门前。那些鸡肆无忌惮地扑腾着,芭蕉树遮天,阴森森。以前在别人文章里一看到村子空了、炊烟凉了之类的语句就烦,以为那是跟风编造,见了这荒村我马上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中原人更安土重迁,再者经济不比沿海发达,自然搬出村子的人较少。
虽然年轻人出去的不多,但是却都不再从事某些细巧或繁重的活计。木匠、银匠渐渐退出历史,我父亲一身泥瓦匠手艺,想传给别人却找不到徒弟,因为这活又累又脏还不怎么挣钱。至于种地的技巧,年轻人更是不屑于去学。我这次锄地算是稀奇事件,若是被熟人看见,还不知会怎么传播呢?所以回去前我对大街进行了好一番观察,瞅准了无人时机才敢离开。
母亲要去给外公送糖糕,我没有跟去。那个村子过年时我去过,铅厂已经倒闭。铁门不见,像落了牙齿的老人无力地张着嘴。水泥地面密布裂纹,荒草对落日,灰冷之光晃着我的眼。风很硬,吹出埙的呜咽。
也去过那所小学,里面终于一个人也没有了。
杜永利,男,1990年生,河南修武人。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作品见于《佛山文艺》《美文》等,获第六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大赛散文组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