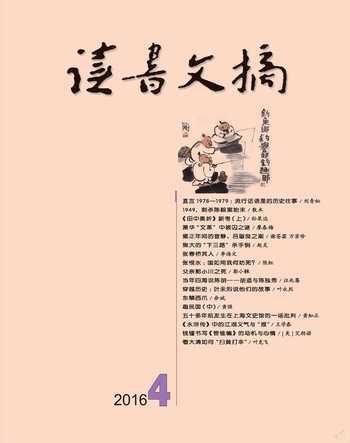五十多年前发生在上海文史馆的一场批判
黄知正
50多年前,正是国内走向“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旗帜高扬,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批判运动。1963年,在汇集了一批学养深厚、阅历丰富的老人的上海市文史馆,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批判,批判一本叫做 《思亲记》 的小册子,馆员们都卷入其中。如今,经历这件事的人都已不在,但了解一下这件事的原委经过,对我们应该有不少启发。
《思亲记》 是本什么样的小册子
《思亲记》 是当时上海一位工商业者孙忠本先生为纪念父亲自行编印的一本诗文集。孙忠本,号性之,原籍浙江奉化,当时任上海微型电机厂私方经理,1962年退休。解放前曾在宁波证券交易所做经纪人,先后在宁波、上海开设钱庄,与人合作创办长途汽车公司、银行,投资纱厂等。公私合营后,他投资的恒大纱厂改为上海微型电机厂,他任私方经理。他父亲孙德昭,号轩蕉,生前是奉化米店的老板,曾任宁波米业会董、奉化商会会长,1920年去世。1961年,孙忠本写了追忆父亲的 《思亲记》 文章,然后托同乡好友胡行之、孙宾甫、王晓籁、屠钓水等分头联络,征集唱和诗文,刘海粟、廉建中也帮着征集了不少,由胡行之、孙宾甫为之修改、编辑。诗文集共征得180人所题诗词180首,所写序、跋、传7篇。1962年12月编成,孙忠本自己出资印行。小册子共70页,竖排本,封面为沈尹默先生亲笔所题“思亲记题咏录”。
这些唱和的老人主要是浙江、上海、江苏的一些老年文人,绝大多数已年高赋闲,常以诗词唱和为消遣,既经介绍、征求,也就乐于应景赋诗,抒发一番。其中不少是名人,如沈尹默、黎照寰、黄绍竑、马一浮、钱崇威、刘海粟、王个簃、王晓籁等。孙忠本先生此时如此起劲征求各方人士诗文唱和,也有点要效法父亲,样样要“跨灶”(胜过父辈)的意思。因为其父亲孙德昭晚年爱好词赋章句,曾编印过一本 《四明唱和集》,他父亲做诗元唱,和者百余人。孙忠本编 《思亲记》,征集唱和,目标要达到两百人。
这些唱和之作,无非都是围绕孙氏父子的孝心和仁心表示赞叹。《思亲记》 主体部分是“思亲记题咏录”,开篇第一首是马一浮的五言诗:“跬步不忘亲,语语出天性,奚假文字传,积善有余庆。”第二篇是沈尹默的五言诗:“孝弟人之本,兹言故不刊,旧邦新受命,尤赖子孙贤。”又如馆员薛明剑的诗:“惶惶先德语,字字发幽香。孝悌传家远,和平处世常。清芬能恪守,遗泽自灵长。读罢思亲记,终留齿颊芳。”本来是应酬唱和,免不了对孙氏父子有一些捧场夸大之词,同时,也有一些对当时社会风气有感而发。这些在现在看来也是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当时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就成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一场“大张旗鼓,和风细雨”的批判
当时,对 《思亲记》 这本小册子的定性,是“一本反动的小册子”。“在近两百篇诗文中有一部分诗文内容很反动,竭力颂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文明,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的道德和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的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丑化得一团糟,并且号召这些牛鬼蛇神出来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狂澜”。
为了说明这本小册子的“反动”,对这本小册子的编者和积极参与人员,特别指出他们的“牛鬼蛇神”身份。如袁康年 (又名袁惠常),“原系总统府侍从少将秘书”;薛明剑,“原系国民党立法委员”;朱梦华,“原系荣毅仁家的家庭教师”;廉建中“历史反革命分子,判处管制,行政开除”;孙宾甫,“黄绍竑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的省府卫生处长”;张方仁,“酱园老板,创办‘乐天诗社,到处招摇撞骗”;王晓籁,“曾任上海市商会会长等职”;“还有汉奸、右派分子、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如李思浩、刘海粟、钱孙庵,丁方镇等”。
小册子连同孙忠本本人写的 《思亲记》 原文和题咏录最后的跋语,共189篇诗文,批判中说“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渴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这类诗文占极少数。第二类是虽然没有明确地反党、反社会主义,但充分流露出对现实社会严重的不满情绪,借‘思亲而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之家谱,发思古之幽情。第三类是由于作者的旧思想、旧习惯、旧道德、旧感情根深蒂固,因而在孙忠本‘孝思的感染下,引起了共鸣。这类诗为数最多”。“这本 《思亲记》,充分证明了我国当前国内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尖锐的。敌对阶级用各种曲折隐蔽的形式,无孔不入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对此,我们必须给以狠狠的还击。”
《思亲记》 的作者、编者孙忠本同文史馆原来并无关系,文史馆员绝大多数也都不认识他,只是因为通过中间人廉建中、袁康年、刘海粟等介绍、征求,馆员中擅长诗文者又多,所以有24位馆员为《思亲记》题诗撰文。1963年上半年,小册子散发到部分馆员手中,文史馆发现此事后,即向上级作了汇报。同时,于8月12日召开馆员座谈会,一方面弄清情况,一方面对馆员进行批评教育。8月26日,以文史馆办公室名义写的 《市文史馆对有些馆员吹捧资产阶级分子编印〈思亲记〉,歌颂封建道德,开展批评教育》 一文,登载于中共上海市人委办公厅委员会编印、专供党内领导参阅的 《情况汇报》 第90期,引起市领导的重视。9月10日,市委统战部王致中副部长根据市委刘述周书记、张承宗副市长的指示,召集几位馆长开会研究,决定在馆员中对 《思亲记》 这本反动的小册子开展“大张旗鼓、和风细雨地分析批判,进行阶级教育,从而使广大馆员提高认识,辨清是非,认真进行思想改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此,文史馆专门拟定了 《关于在文史馆馆员中大张旗鼓、和风细雨的进行正面教育,分析批判〈思亲记〉,加强阶级斗争教育的打算》 。
批判的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在馆员中的诗文作者中间开展,加上部分“积极分子”共33人。第二个阶段,从11月中旬到年底,在全体馆员中进行。在第一阶段,陈虞孙副馆长先后作了四次关于 《思亲记》问题的报告,参加馆员结合陈虞孙副馆长的报告开展分析批判,举行了18次座谈会。同时,文史馆办公室负责同志同“问题较严重的”馆员朱梦华、袁康年等,进行多次个别谈话,“进行批评教育,启发认识错误”。在第二阶段,陈虞孙又为全体馆员作了一次关于 《思亲记》 问题的报告,组织了多次小组讨论,进行分析批判。诗文作者仍单独编组,开展谈心并作检查。一些健康状况较差,不方便出门的馆员,则按照文史馆当时惯常的做法,组织他们分别就近集中某位馆员家里,进行座谈批判,文史馆派干部分头参加。
刚开始批判时,文史馆先将参与题诗撰文的24位馆员的诗文专门编印分发,供馆员分析批判。这24位馆员有朱梦华、薛明剑、沈隐濂、何振镛、贾粟香、高凤介、王震、吴斯美、黄遂生、吴湖帆、张公威、袁康年、黄葆戉、王个簃、张孝伯、周承忠、易克臬、曹竞欧、吴公退、项介石、陈谟、吴拯寰、蒋通夫、孙雪泥等。在分析批判深入过程中,又选出 《思亲记》 中“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宣扬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的诗文27篇”,进行重点批判。重点27篇中,除孙忠本撰写的 《思亲记》 正文和《思亲记题咏录跋》,还有钱孙庵、孙宾甫、廉建中、黄绍竑、胡行之、李思浩、孙表卿、张方仁等人的诗文,馆员朱梦华、袁康年、薛明剑的诗文也在“重点批判”之列。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对 《思亲记》 性质定得很严重,批判的调门很高,但同“文化大革命”相比,当时毕竟是在党委领导下,整个批判过程还是很注意掌握政策的。在按照市委领导的指示批判开展起来后,一开始的动员会上,陈虞孙副馆长就向馆员说明,对《思亲记》 的批判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也是馆员的一次自我教育,为 《思亲记》 写诗文的馆员,绝大多数是思想问题。在方法上,仍旧采取统一战线工作中一贯的方式,实行“三自”“三不”(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提高思想认识,“不作任何组织处理”。批判中明确三条方针:只分析批判思想,不斗争哪一个人;只开小会谈心,不开大会斗争;只对诗文作重点批判,不作逐篇逐首批判。“对极少数问题严重的”,进行个别谈心,帮助解除顾虑和提高认识。整个批判过程中,基本上也是这么做的。批判过后,没有对什么人做什么组织处理。批判只在文史馆内进行,没有推向社会,没有上报纸,这也多少减轻了馆员们的心理压力。
用阶级斗争思想衡量传统文化的内涵
《思亲记》 的主题是讲孝道。为 《思亲记》 题诗撰文的老先生们都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文人,他们的题咏当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宣扬,这便被认为是“竭力颂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道德文明”。有的老先生免不了对当下的社会风气发一些感叹和议论,那时不像现在,对当下社会是容不得一句批评的话的,所以就是“丑化和攻击社会主义道德和无产阶级专政”,“明目张胆地、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甚至从那些诗文中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直指为“渴望蒋介石‘反攻大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假‘思亲之名,行‘思蒋之实”。前面讲到的实行“三不”方针,在组织上是这么做的,但在思想批判上则完全谈不上了。
当时馆员们在分析批判 《思亲记》 中讲了些什么,因为没有原始的记录材料,所以不得而知。1963年12月1日,市委统战部上报了一份 《关于上海市文史馆组织馆员分析批判 〈思亲记〉 的小结》,写到了当时主要的一些批判的实例,可以从中看到对这些诗文是怎样批判的。
批判的头一个重点诗文,是钱孙庵老先生的《思亲记序》。这篇序开宗明义,起首就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接着阐述:“思亲者,追远也,不忍死其亲也;慎终,一时之事,犹尚其暂,追远终身以之则,为其难厚之至也。识者于以觇民德焉,非仅家庭之私也。”作者按孔子所讲,把对先辈的送终、纪念看作一桩有关人民风尚道德的大事,而不仅是一家一户的私事。因此,孙忠本的 《思亲记》追忆父亲,即是一桩关系民德的事。“知孝为天下先,不忘其本”,“足令民德归厚”。钱老先生很注意结合现实,但他结合的路子是只顾说自己的一套话语,所以招致批判也是不难想象的。他把《思亲记》 同当时统一战线中正在开展的“三个主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 教育联系起来,由提倡国际主义、爱国主义而讲到要发扬“民族意识”,并阐发说,民族意识“必以国家为本位”,而“国之本在家,国也者,家之积也;家之本在身,父母者,身之本也。诗曰,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太史公曰,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他又从民族意识讲到孝道,认为孝道为民族意识之基本。接着他对当下发了一通议论:“自近世竟言斗争中求团结,而以子证父,吾党有直;以父训子,且为世诫。父子不能相保,其仇甚于敌国。必须父子有恩,然后君臣有义。”“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自古未有薄其所厚而能厚其所薄者。”这里又由小说到大,不讲孝道,父子成仇,怎么还有民族意识,还能要人民团结爱国呢?“本实先拨国于何有,岂尚能言民族意识而望人民团结以爱国哉?必不然矣。”
批判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根本不顾及文章的整体,将其中词句割裂开来,有的对词句的原意也没有真正搞清楚,就说“钱孙庵提倡‘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骂共产党提倡马列主义是反‘慎终追远的,其结果必然是‘民德归薄,民德‘薄了,国家就要亡了”。“他说什么‘识者于以觇民德焉,非仅家庭之私也,反映了作者深恨其剥削阶级利益受到损害,号召大家共同反对今天的社会”。“所谓‘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分明是提倡家族主义,把身家置于一切之上”。对于“自近世竟言斗争中求团结”那一段,作为作者“反党”言论的要害来批的。作者本意是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如今讲斗争,就要求“以子证父,以父训子”,“父子不能相保,其仇甚于敌国”,怎么还能有人民的团结呢?其中说到的“吾党”,是指乡党,跟我们今天说的政党、共产党并无关系,但因为有这个“党”字,批判一口咬定,“这是向党开火。把允许‘以子证父说成是党的‘罪名”,“是引用 《论语》 中语以讥刺党的政策”。对于作者所说“自古未有薄其所厚,而能厚其所薄者”,批判不知怎么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人厚的究竟是什么?当然是资本家,是劣绅,是金钱,所薄当然是人民。”
钱孙庵在最后说到孙忠本 《思亲记》 中其父对子女的教育时说,“吾有感于今之青少年教育,无家庭教育以为之先,且不能收效于学校教育也。古者父严母慈,家庭教育父教为先,母以成之。若如先生不忘父教且为子孙世法,是学校教育毕业有时,而家庭教育且无已也。故亟表而出之,以为今之改善青少年教育者,庶几知所先务焉。”这个思想对我们今天反思当代教育,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有益的养料,应该也是很有启发的。而当时批判说这是“要同我们争夺青少年”,“用封建教育来代替对青少年的共产主义教育,狂妄之极”。钱孙庵的这篇序被说成“是明目张胆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有人说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纲领性文件”。
馆员朱梦华的 《孙性之先生思亲记跋语》 列为重点批判的第二位。朱梦华在跋语中夸赞孙忠本“生性至孝,年六十有四作 《思亲记》 一篇,屡述儿时依依膝下以及鲤庭训对之状,孺慕之情溢于言表”。他将孙忠本四十年后写追忆父亲的文章同古时欧阳修六十年后写纪念父亲的 《泷冈阡表》相比较,说“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欧阳修四岁丧父,“已不及孝养其亲,所以自勉者惟入世不染污浊,力学奋志功名,以为其先人增光,则所谓能尊其亲者也”。所以“终身慕(仰慕、思念) 父母者”,继承父母的品质以自勉,为孝的最高境界。最后,作者又发了感叹:“嗟夫,叔世以还,人心不古,有父言而子违者矣,父在而子去者矣,骨肉之间,乖戾时见,抑何弗思我而忘我之父,则我子亦将忘我。滔滔天下,谁挽狂澜?吾读性之先生 《思亲记》 而益有所感矣。”
正是这末尾一段感叹,成为批判的靶子。批判说,“叔世者,末世也”,将社会主义时代称之为“叔世”,反映了作者对新社会的极端仇恨。作者认为为什么社会败坏,是因为“人心不古”。“有父在而子去者矣”,是说“父在子就不应到外地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骨肉之间,乖戾时见”,批判说,这种情况往往出于封建家庭和资产阶级家庭,要改变这种状况,“正要大讲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风格,才能做到,决不是提倡封建道德所能谈”。“滔滔天下,谁挽狂澜”,批判说,作者认为“只有孙忠本有资格举起反革命的大旗来挽回‘滔滔天下的‘狂澜”;“‘益有所感,就是感激孙忠本能在此‘叔世敢于举起一面反革命的大旗”。
老先生们的有些观点,有些词语,是可以商榷的,甚至是可以批评的,但从以上的“批判”可以看出,当时只是一味地断章取义,望文生义,强词夺理,乱戴帽子,乱打棍子。再看对几首诗词的批判。
黄绍竑赋词 《千秋岁·题孙君思亲记》:“朵云天外,陡峭春寒退,闻盛事,心如醉。辛勤曾致富,济困囊频解。君不见,浙东泉口碑犹载。世事沧桑改,应有遗风在。今与昔,情何碍。曩得乡邦誉,史迹添光彩。春正好,年年桃李花如海。”词义很清楚,很连贯,本是对孙忠本之父的赞誉之词,批判却说:“虽然写得隐晦,但终究掩盖不了他的反动思想”,然后不管上下文,把词句拆散了进行批判。“‘朵云天外,陡峭春寒退,闻盛事,心如醉,是指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而言。如果仅仅是孙忠本请他题咏的信,决不是什么‘盛事,也决不致于使他如此‘心醉。”“‘应有遗风在是指蒋介石‘遗风,说明黄绍竑的‘故主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孙忠本同乡好友胡行之,又是 《思亲记》 的主要编辑者,他写的诗 《题孙性之先生思亲记后》,批判说“写出了他的变天思想”。原诗曰:“天地至情在性真,至情更莫逾思亲。鲤庭常炳千秋业,风木长留万古春。纳纳乾坤多聚散,堂堂文字寄精神。会心一笑垂垂老,共看人间墨色新。”批判说,“‘纳纳乾坤多聚散,就是说现在很混乱,世界要变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以后,他们就可‘会心一笑,一同来看用新的‘墨色写出的‘新的光景了。”
孙忠本另一位同乡好友,《思亲记》 的编辑者孙宾甫,写的诗 《读思亲记有感题赠性公》,全诗较长,主要讲的是与孙忠本两家本是乡邻,自小“俱各奋深造”,对孙忠本取得的成绩和其为人表示钦佩,如今都已衰老,但友情“益敦好”。接着写道,“君不见,纷华暂时鲜,俯仰之间呈微妙,坐令江湖心,浩荡起长啸,贤者贵知几,毋使中心悼。愿君持美修,年高德弥劭”。批判说,这是作者“认为现在的局面不会长久的,一霎眼,就会有变化。他还要他们这一班人‘贵知机,要抓住机会起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南京一位老先生龚剑书,写诗 《追悼孙老伯轩蕉先生》,诗曰:“持筹握算学而优,领袖群商孰与俦。子弟三千同绛帐,儿孙两代绍箕裘。鉴湖水冷遗施在,雪窦风高化雨留。处世持躬唯信义,高风犹自照神州。”全诗赞誉孙德昭的意思很清楚,但当时的批判习惯于穿凿附会。批判说,这首诗“不是追念孙德昭,而是追念蒋介石”。“‘持筹握算学而优,领袖群商孰与俦是要蒋介石在‘复辟运动中发挥‘领袖作用”,“鉴湖水冷遗施在”是说“蒋介石虽然走了,他的‘遗施还留在大陆”,“雪窦风高化雨留”是说“蒋介石虽然走了,大陆上的人民还在‘想念他”。
廉建中题写了两首诗,一首五言诗曰:“一卷思亲记,朗吟句亦香。践躬遵孝悌,至性重伦常。礼乐家声远,诗书世泽长。心平多积德,百岁自流芳。”另一首七言古诗较长,后半段中写道:“岂特教训孙与子,还当讽世千秋传。何物非孝伦常背,浇风薄俗化云烟。我愿青年诸子弟,各守家学孝为先。尊祖敬宗尽子职,吾辈今日共勉旃。”批判说这两首诗的主要目的就是“攻击现社会和反对青年教育”。具体的却也说不出什么了,只是认为“他在诗中骂‘浇风薄俗化云烟,这和孙宾甫的‘纷华暂时鲜,俯仰之间呈微妙一样的意思。”
对孙忠本本人的 《思亲记》 一文,批判其竭力为父亲涂脂抹粉,“说来说去,不过一个米蛀虫”,说明他“根本不懂剥削可耻”,而那些为之题诗撰文的人,“分明是在歌颂剥削了”。说 《思亲记》 小册子“主要内容是‘歌孝,颂德”,“是一本续封建主义家谱的小册子”。馆员中一些人题诗本是应酬唱和,有一些明显是捧场夸大的词句,如黄遂生馆员的“卓哉轩蕉翁,德大莫与伦”,沈隐濂馆员的“他年修邑乘,千古一完人”,还有以上提到的薛明剑馆员的诗,也被说成是“少数人借题发挥,大肆宣扬封建主义道德、孝行,发泄对社会主义道德标准的不满情绪,甚至为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进攻帮忙”。对马一浮、沈尹默两位老先生的诗也没有放过。批判说“孙家世代剥削,马一浮居然说孙家是‘积善有余庆;在新社会,劳动才是人之本,而沈尹默竟说‘孝悌人之本。都是错误的”。还说:“‘尤赖子孙贤,难道要我们的后代,做孙性之吗?”
这场批判可以说,是以阶级斗争思维摧毁传统文化中有关内涵的一个典型例证。这场批判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新中国难得的一个传统诗社——乐天诗社,就此销声匿迹了。乐天诗社是解放初上海成立的一个民间文学团体,汇集了北京、上海南北两地的一批爱好并擅于传统诗词的文化老人,其中不乏蜚声文坛的社会名流,如柳亚子、叶恭绰、沈尹默、刘海粟、吴湖帆等等,诗社办有社刊 《乐天诗讯》。1960年在董必武同志的关心支持下,经上海市委同意,市委统战部牵头协调,乐天诗社挂靠上海文史馆,并每月补助经费100元(关于乐天诗社的详情,可参阅陈正卿 《新中国上海第一个传统诗社》,《世纪》2008年第3期)。诗社负责人及骨干成员如贾粟香、沈瘦石、张孝伯、吴公退、张方仁、黄葆戉、孙雪泥等,除张方仁外,先后都受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参与 《思亲记》 题诗撰文的除馆员外,馆外人员相当一部分是诗社社员。当时征诗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根据乐天诗社社员通讯录开展的。屠钓水、廉建中是诗社中活跃的成员。随着 《思亲记》 被严厉批判,诗社也受到了严厉的指责,诗社担负上了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本来活跃于诗坛的老人精神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如何还有心思和兴致继续诗词的创作和吟诵呢?所以 《思亲记》 遭批判后不久,诗社也就停顿了。
(选自《世纪》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