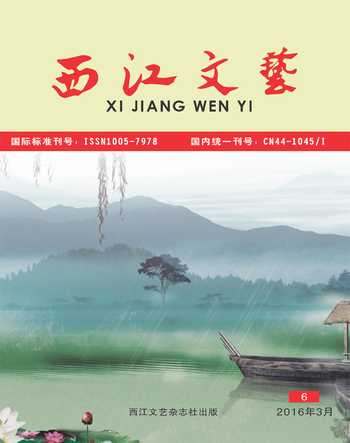浅谈文学和女性
蔡科
常常想象这样一幅画面:在某个夜深人静、月白风清的晚上,温柔的月光匍匐入室,留下半边桌影。耳畔依稀听到棕榈树宽大的叶片舞动出“哗哗”声,半开着窗棂的红叶帘蓦地掀起,须臾盖过桌影,地上不规则的图案顿时像极了瞬间跃起的浪涛舔舐桌腿。案上的孤灯不卑不亢,冲淡些许黑暗,房间里有青灯、长卷、月华,还有高大的墙影。此时,一位散发清香、妩媚可人、身穿红裙的女子,捧一碗温茶,神色安然地徐徐走来,她踩得很轻,生怕踏破了如梦一般的月华。
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景象大概如此吧,这是古今文人墨客期盼的美事,追求的目标,一朝梦里得到,醒后数日不忘,还为此劳心费神。于我看来,文学和女人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它们是那么相近,那么不可分离,就像鱼儿离不开水,动物离不开食物。如果《红楼梦》里女人太少,贾宝玉就不会那么遭人喜欢;如果《聊斋志异》里没有狐妖,那么故事的趣味就会减掉一半;如果作家尽写男人、政治、功名,那么作品就成了无聊的经文,作家当然也很快埋没于历史的烟尘,荒冢一堆,无人问津。世界上没有哪一位文学家不喜爱女人,不喜爱女人的文学家难得写出经典作品。文学家的风流韵事频频发生,范例就不一一举出,虽一时招人白眼,但多年以后反成了人们纪念他们的佳话,可见文学家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不需任何加工的艺术。
文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有人就有世界,有世界就有文学。一颗青草是不是文学? 植物学家看到的是种类,生物学家看到的是内部组织,普通人看到的是颜色和形状,而文学家看到的是有别于现实世界并赋予它以人的特性,草开始有了灵魂,万物皆有灵。人沮丧时,草便垂头;人高兴时,草便舞蹈。连一棵无关痛痒的草都要倾注感情,可见这人多么慈善,慈善最容易让人想起母亲,想到了女人,女人和文学这时走到了一块。你若不懂女人,那是做不得文学的。你看古代的文人为什么多和青楼女子交往要好,道理即在于在此。树叶飘落是文学,它划过空气的轻柔曼妙即是女人,所以诗人多半有一颗女人心。非此,他的诗篇是不会让你感到缠绵欲绝、如梦如幻的。用女人的情怀做艺术,它产生的效果必能撼动人心。
孩提时代,我很天真的认为,全世界的女人大概像我母亲一样贤淑,事实不然,时间告诉了我女人也分三六九等。上等女人是一首优美隽永的诗,她含情一笑,可以胜遍人间无数,甚至全世界的花开也是因为她笑的缘故。中等女人是一首清新典雅的散文,她素日生活的家务操劳,剪辑其温馨的片段,组编成幸福的画面,平凡之中呈现出不凡的品质,给人传达了深远的哲理。下等女人是一篇耐读而令人深思的小说,她人生当中的艰难困苦、起伏跌宕、爱恨情仇,演绎了世事沧桑和无常莫测。女人的美本质上接近于艺术的美,无论她的身体还是举止神态都充盈了艺术之韵。兴许有人问那女人为什么不都是艺术家,借用苏轼的话回复:“只缘身在此山中”。且艺术家也需要天分,并非每个女人都有。
文学是孤独者的幻想,是孤独者与上帝的对话,是一颗心对另一颗还没有出现的心的诉说。红袖添香是非常文学的事情,书房里用功的时候还有美女相伴,非诗即画,很难让人不生嫉羡。纵览古今文学大师,他们的言论无不谈到孤独之于文学乃至一切艺术创造的重要性,当一个文学家在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他的心神是容不得任何实在之物的,也就是说“红袖添香”的情景只能发生在文学家的创作进入化境时段——现实与虚构合为一体。照此看来,红袖添香的浪漫唯美大概只有外人和俗人之见了,或者是文学家处身孤独中的南柯之梦——想象罢了。文学和女人看似水乳交融,实质上是水火不容,兼得者难免多生困苦,像顾城,像徐志摩,像林清玄,像拜伦……这些文学家的情感阅历并不顺遂,因而“自古才子多风流”就不见为怪了。
有时,我害怕走进女人,唯恐失去了文学;有时,我也害怕耽迷文學,唯恐失去了女人。文学和女人使人愉悦,也使人痛苦,世间上的事情总是这么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