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香樟树
西洲
天气已经热了起来,春枝坐在窗户下,望着院墙上碧绿的爬山虎。风吹动爬山虎的藤蔓,风移影动,整个墙像是要游动起来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猫从叶子下风一样窜过。春枝一阵恍惚。此刻,风吹来了香樟花的味道,她想起花园街的一株香樟树。
那是一株很高大的香樟树,长在窗户边,香樟树的枝条遮挡了阳光,也遮住了雨水。夜晚,风吹过的时候,叶子哗啦啦,像在落一场大雨。
路辰就住在那扇窗户里。
他们分手的那一天是4月29日。
那天下午,春枝本来是要离开的,晚上的火车。吃了中饭,两个人看时间还早,就慢慢地散步去火车站。路辰带她沿着一条叫渡春路的街道前行。渡春路两旁种了许多洋槐树,这个时候,洋槐花落了一地的碎花,风轻轻卷起小碎花,空气中有淡淡的香味。
两个人默默地走在碎花上。春枝有些尴尬,她想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见过木棉吗?路辰忽然问她。春枝愣了一下。她没有见过木棉。
我在深圳的时候,人行道上都是木棉树,高大的木棉树,一到春天,红硕的花朵就落到地上,人踩上感觉很奇怪。花朵有时砸到头上、肩上,有种钝重的疼。没有等到春枝回答,路辰接着说了起来。
花朵还能把人砸疼?春枝觉得这疼根本就是他杜撰的,也许是正在沉思,被花朵惊动,心内恍惚吧。
说完木棉,他们又没有话说了。过了渡春路,往右拐是一个广场,广场上种满了樱桃树。此刻,樱桃淡黄浅红,一簇簇挂在枝头,即将成熟。樱桃树种在广场,春枝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些樱桃树不大,有她的胳膊那么粗,但结了很多果实。樱桃树周围是草坪,草坪周围用飘着彩旗的布条围拢起来了,大约是不叫人钻进草坪,采摘樱桃。但是仍有顽童跑进去用树枝够尚未成熟的樱桃。路辰在距离最近的那株樱桃树旁站了一会儿,仍是没有说话。
4月29日的下午,天空晴朗,云很多,一层叠着一层,像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了似的摊在天空,一副慵懒的模样。春枝抬头看一会儿天,有时候侧过脸瞥一眼路辰。他很严肃,眼睛盯着前方,仿佛在思考什么。像一个诗人。事实上,那会儿,他就是个诗人,但是他不写诗,他写小说。
并不是写诗就可以叫做诗人,有的人写了很多像诗一样的东西,写了一辈子,也不是诗人;但是很多人却以诗人的姿态活着,尽管他一首诗都没有写过。这是路辰曾经说的。
写小说的路辰,和别人都不一样,这是春枝自己发现的。后来春枝想,是当时自己没明白,不管写不写小说,是不是诗人,路辰都不会和别人一样,这世界上哪会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呢?
路辰很敏感,他时刻关注天气变化,但却从来不是为了出行穿衣。他从未因为自己关注到的天气而去添减衣物。有点傻。春枝想。其实是他过于专注而没有意识到天气变化会带来什么。有很多次,半夜他打电话给春枝:去看月亮。或者去看云。于是春枝在睡意朦胧中推窗看月。月亮又大又亮,而且很低,仿佛一伸手就能够碰到。有时候是云朵,月亮照出云朵的影子,风吹来,一棵树摇动它的叶子,哗啦啦,像落一场大雨。春枝握着手机,路辰在那端沉默,良久,似乎确认她已经看过了月亮并准备往回走的时候,才会说,再见。他从来都是说再见,说完不管你还有没有什么话,他就挂断了电话。
他们一路沉默地走到了火车站,才四点半。火车是几点的?路辰问。
八点。春枝之前说过的。其实,春枝的票是30号下午八点。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她总觉得他并不想见到她,于是她就顺水推舟说,本来就是路过来看他一眼。
你先进去坐一会儿吧。找个地方看书。说着路辰从包里掏出一本书递给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那是一本特别厚的书,不知道他的那个小包怎么装得下。春枝接过来,抱在怀里。
再见吧,春枝。路辰说。我们还会再见的。
春枝笑了笑,笑得很勉强。其实她心里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尽管都说还会再见的。路辰甚至说,我会去看你。春枝点头,但她心里知道以后不会再见面了。春枝突然一阵悲伤,泪水就涌出来了。
路辰上前抱住了她。春枝两手抱书抵在他胸前。他身上有淡淡的汗味。
拥抱(像个仪式)结束路辰说,春枝,再见。春枝一直低着头点头。等她抬起头,路辰已经转身走了。春枝看着他的背影,瘦瘦的,十分落寞。春枝一直看着他走远了才走进候车室。她决定混上车。
候车厅里人很多,一个空座位也没有,只有靠着电梯那边的墙边有点空地。墙是玻璃的,像谁家的落地大窗户。她把包垫在屁股下面,想到以后再不能谋面的,心里空得要命,眼泪仍在不停地落。太阳光透过玻璃照进来,眼泪滴在怀里的塞万提斯上,她一边擦眼泪一边翻起了塞万提斯。
这么厚的书。她那里也有一本,可她从来没有看完过,每次下定决心要看完,却总是将前言看完,再看十几二十页就不想看了。这个故事她不是不知道。她从前还恍惚看过黑白电影,在小时候的印象里,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
她不想从头看。这本书封面磨得有点旧,书页也有些卷,她抚摸着书页,随便翻开了一页。
她看到牧羊女马赛拉。田野里,回荡着马塞拉爱慕者的绝望的叹息,几十棵山毛榉的光滑的树皮上刻着马塞拉的名字;有的人在圣栎树或大石头脚下彻夜不眠,任思绪遨游,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有的人在夏天炽热的中午躺在灼人的沙土上,不停地叹息;有的人——那个叫克里索斯托莫,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又会观星相的小伙子为她而死。
再翻一页,就是清晨,牧羊人邀请堂吉诃德去参加克里索斯托莫的葬礼。她不想看他的葬礼,于是又翻了过去。
她其实心不在焉,她想从书中找出点什么,也许是路辰给他留下的什么暗示。即使没有什么暗示,有他的字迹也好,但是她胡乱翻着,并没发现什么。候车大厅里人很多,安检人员走过来,对着她和像她一样坐在玻璃旁边的人大声嚷嚷:这里不能坐,起来,起来!到那边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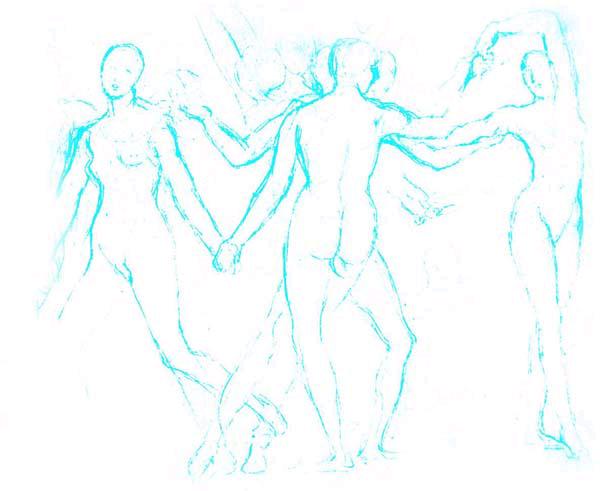
春枝站起来,看着乌泱泱的人头。有一趟火车正在检票。她看到一对儿年轻人抱在一起,旁边的人绕过他们往车站里面走。有人的胳膊、行李碰到他们,他们也无动于衷。春枝靠着一根柱子,一直盯着他们看。他们分开,那个男孩捧起女孩的头,给她撩头发,又擦眼泪。擦完又抱住她。这样反复好几次,仿佛在重播。广播里一遍遍地重播,请手中有车票的旅客注意,开车时间是……旅客抓紧时间检票上车,列车开车前五分钟,停止检票。
那两个人终于分开了,女孩倒退着往检票口走。男孩往前跟。
为什么不买站台票送进去?这样可以更好地享受离别,还可以看着列车开动,她贴着窗玻璃哭,你跟着火车跑。春枝这样想的时候,忽然觉得自己很刻薄,像是嫉妒。她没来由一阵伤心。
终于轮到她的火车检票了。她有些忐忑递去了车票,谁知检票员看都没看就让进去了。她本来以为会遇到阻挠,然后她就可以找借口再出来,也许可以回去找路辰。但是居然这么顺利就进去了。她叹了一口。随着人流往站台走。
她的包小得连塞万提斯都放不下。她肩上挎着包,一手拿着车票,一手拿着书,往火车上走。一切都那么顺利。外面的人那么多,可车厢里几乎可以用空荡荡来形容,她找了个座位坐下,把塞万提斯放在小桌上,她就那么盯着它。
她和路辰是怎么认识的啊,时间那么久远了,她几乎都记不起来了。第一次搭讪是因为什么?她想不起来。总之就那样断断续续地联系着,他们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
火车突然晃动了一下。春枝猛地站起来往车门口走,列车员已经将门关上正准备离开。她央求人家开门。那年轻的女列车员说,关了就不能开了,马上就开车了。春枝说,对不起,我坐错车了。春枝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女列车员斜了她一眼,但是没说什么,把车门打开了。
春枝逃一样地跳下火车。站台上一个人也没有,她看着火车徐徐开走,终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
他们两人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呢?
春枝记得,有一次他们站在长江边,她对着江水说:我爱你。她的声音很低,也没转头看路辰,但她知道,路辰听见了。在江水柔缓的拍击声中,路辰听见了她的我爱你。在余光中,春枝看到路辰的睫毛动了几下,他的胳膊本来擦着她的胳膊,在她说完那句话后,突然伸了出来,将她揽入怀里,比以往的每一次都要紧。
江水悠悠,有运沙船路过,他们盯着波光粼粼的江面,看见对岸的高高耸立的烟囱里冒出巨大的烟柱。低沉的汽笛声从空气中传入耳膜,天空瞬间暗了下来。
等哭够了,春枝就坐在站台旁边的台阶上,开始翻开手里的书。她自然不能去找他。
春枝泪眼朦胧地一边抽泣一边翻页。眼泪掉在书上,一滴一个泪痕。
翻书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在看。每一个字都好像不是原来的字,每一句话她都看着不像话,每一页纸上仿佛都藏着无尽的往事。
但往事其实乏善可陈。坐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她能想到的几乎都是她一个人的往事。
路辰经常打电话来,但即使打电话他说话也很少,总是叫春枝听听什么。有时候是风声,有时候是暴雨在下,有时候是某一首怪怪的歌。春枝第一次听说左小祖咒,就是从路辰那里,半夜三更,他打电话来要唱歌给春枝听:“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连风都不知道我,不知道……”那调子怪怪的,好像醉了酒的人在说什么伤心话。
你听火车与铁轨的撞击声。哐当哐当。路辰说。那是路辰去桂林的路上,在信号不好的车厢里给她打电话。
春枝坐过许多次的慢车,去看路辰,或者只是去他在的城市。夏天时坐慢车,尤其绿皮车是很遭罪的。车厢里潮湿闷热,有人打开窗户,风突然窜进来的呼啸声,像什么人的尖叫。窗外绿色的原野缓缓后退。树木浓绿得有些灰暗。风吹进车厢里,携裹着夏天的潮湿、闷热,但火车里积攒的汗被风吹干,变成了油。过了一会儿,有女人尖声叫嚷:关窗户,关窗户,孩子吹醒了!窗户无奈地关上,脸皮冰凉,油腻,一擦一手的灰,而面皮里仍然燥热。
坐在楼梯,春枝翻完了这本书。翻完书,也好像将路辰和她的往事翻完了。她合上书,屁股和腿都是木的,没有知觉,她慢慢地站起来突然决定要回去找路辰。把书还给他:我才不要你的书!
在晨光熹微中,春枝穿过冷清的火车站广场,穿过渡春路,拐进他们经常散步的小巷子。说是小巷子并不确切,那巷子的两边是人家的别墅,庭院,一排排的篱笆上无一例外种着蔷薇花,与篱笆垂直的,通往自己门口的边缘,有几户人家种了大丽花,艳丽的大丽花绽开了一瓣又一瓣。在拐角的那一户,小园子里种满了凤仙花。此刻凤仙花植株壮硕,骨朵儿都还没有开始酝酿。
春枝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想起去年她染过的指甲。路辰给她寄去的凤仙花的种子是在这里采集的吗?
前年夏天,路辰给她寄信的时候,在信封里包了一包凤仙花的种子。春枝,你把它们种出来,用它们染指甲。路辰在纸包的后面写。
她问楼下卖菜的阿姨要了一个塑料大框子,又到野地里挖回来几塑料袋土。回到家里,她用手细细地碾碎那些结块的土,将种子播了下去。她果然种出了一小片,夏天开花的时候,她欢天喜地地看着这许多花儿,预备去染指甲,却怎么也找不到包手指的眉豆叶儿。
路辰和她说起小时候用凤仙花染指甲的事儿。小时候她也染过,路辰也染过。别的男孩子绝对不愿意做的事情,他却乐此不疲,每次他的小姐姐染指甲的时候,他都紧紧地跟着,不管她是在自己家里,妈妈给染,还是到奶奶家里去染,甚至她到邻居家里去染,他也要跟着,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小姐姐有染指甲的想法,他就像她肚子里的蛔虫,总能在第一时间知道。第二天他带着一双染得有点橘黄淡红的手和其他孩子玩,或者跟着妈妈到亲戚家去。十分骄傲。直到上了小学,他才没有再染。
那一筐凤仙花开了很久,春枝没有收集种子,第二年它们落进土里的种子又密密地长了出来,但是今年不知道为什么,那筐里空荡荡的,只长出了几株瘦弱的野草。
春枝走到那棵香樟树下,天色已经大亮,窗户那儿仍旧黑乎乎的,香樟的花香在空气中飘荡。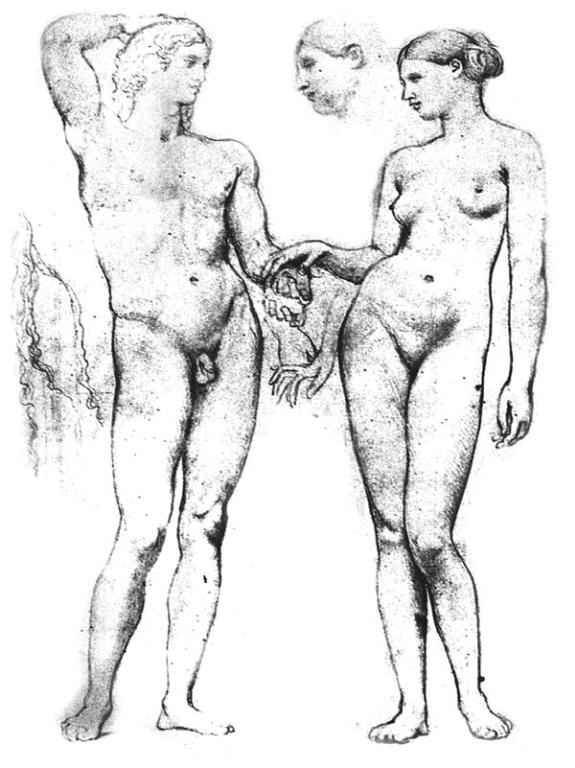
又回来做什么?春枝不知道见了面要说什么。把书还给你,我不要看?我不喜欢看?我看完了?春枝坐在树下发了很久的呆。有人来来回回从路边走过,他们急匆匆的,连多一眼都没有看她。
一个影子停在她面前,她抬起头,路辰正在看着她。她想对着他笑一笑,却一下子流出了眼泪。路辰叹了口气,把她拉起来。她抱住路辰,眼泪不停地流。
她又到了那间屋子里。屋子里陈设依旧,一张小床,一张旧桌子,桌子上有一个打开的笔记本电脑。一个旧货架,上面堆满了书。
一进屋,路辰就收拾起床铺,让春枝坐在床沿。
一晚上没睡?路辰问。
春枝点点头。他没有问她为什么返回来,也没有问她打算怎么办。
你睡一会儿吧。
春枝摇摇头。
他拉一把椅子坐到春枝的对面,握着春枝的手,两人谁也没有说话。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了。春枝想。他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怕的是,春枝自己也没有什么可说的。这种无话可说是那么尴尬,像一堵堵厚厚的墙。
这样的事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春枝不知道,可是她仍然爱着他呀。
过了许久,路辰松开手,像往常那样,拍拍春枝的肩膀:你还是睡一会儿吧。我等会儿要出去办点事。
春枝躺下,侧身朝里,眼睛酸涩,想睡,却十分清醒。
过了许久,她听见关门的声音,路辰出去了。
她躺在床上仍旧睡不着。从前,她睡不着的时候,路辰会读书给她听。
他的声音里有浓得化不开的柔情,带着不知某地的淡淡口音,那口音听起来让人仿佛置身夏夜,露水正从树梢叶尖上滴下来。
那次他读的是《我的米海尔》。
“巨石无权滚上山坡,应该顺着山坡下来,否则就不公平。”
“每个人内心深处无疑都珍藏着某些普通的愿望。”
“当我们沉浸在悲哀之中往往将日常琐事视为极其堕落的事。”
“整整一个冬天,耶路撒冷的寒风都在吹动着松柏,而风离去时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你是个陌生人,米海尔。你夜里躺在我的身旁,可你却如此陌生。”
路辰并不一页一页地读,而是随手翻,翻到哪一页随便看到哪一句就读起来。他从来不读诗,但听上去,这些句子都挺像诗,最起码,在不懂诗歌的春枝看来,这些句子都是诗一样的句子。仿佛觉得有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皮肤上有微微的凉意。
他的声音里有淡淡的解释不清的忧郁,他的这种忧郁,在很久很久以后,春枝想起来的时候,觉得有些矫情可笑。当然,当时她并不觉得。
如今,她在老地方,窗外的香樟树在暮春的晨风吹动下,枝叶婆娑,米黄色的准备开花的骨朵儿藏在叶间,有微微的香味随风飘送。
春枝起身,看见旧景:远处的居民楼,阳台上花草茂盛;色彩鲜艳的幼儿园,孩子的欢笑声不时传来;另一边,一片白桦树摇动树叶,像在落一场雨……
春末夏初,屋里已然有些闷热,那本《堂吉诃德》被放在了货架上。春枝铺好床,拿起包准备离开,到门口,又停住,她想了想,取出包里的钥匙,放在了《堂吉诃德》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