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向山行
谭岩
这是荆山山脉的一座最高的山峰,听说在航标图上可以找到它的名子——不过对并不需要上天入地的读者来说,这个名字不说也罢;因为它太高了,高得人烟稀少,那里的植被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可也更显荒凉;也因为它太高了,高得仿佛一下刺破了季节的安排,当山下已是一派鲜花烂漫,百鸟鸣唱的春意阑珊,山顶仍是一片冰雪覆盖,树寒木凝的严冬景象。这高耸云霄的景象亘古而苍凉,多少年来,那位居一方之尊的孤独的声名,也并不为太多的人所知晓。
随着电视的普及和发展,一座银色的白塔耸现在那高高的山巅,那是电视发射塔;当人们转动着电视天线,满是雪花的荧屏突然闪现清晰的画面,嗞嗞的电流噪音变成清泉一样流畅的声音时,那被遗忘的高峰便有了一个很实用的名字,发射塔;那蓝天的背景下青黛色的山巅耸立的一座银白的铁塔,从此成了一道优美的风景;源源不断传送着电视信号的发射塔,仿佛也成了百姓们生活中欢乐的阳光。
山巅不仅耸立着铁塔,塔下还支着一个发射锅,发射锅也刷上了防锈的白漆,在阳光下亮亮闪闪,像一朵对着蓝天盛开的花;这朵花旁还建有几间机房,就着山包围了一圈院墙,院墙按了一道铁门,荒无人烟的山巅从此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单位:挂在门口的招牌上正正规规地写着某某电视差转站。可是这个像模像样的站,也像这山峰一样孤独冷清,常年累月只有一人,一位站长兼值机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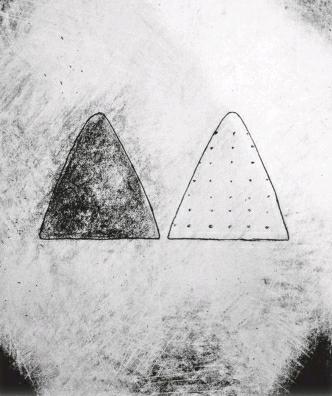
这个倍受人们敬仰的地方,却是一个十分艰苦的岗位。它不仅是在乡下,在山上,而且远离人烟。它高高耸立在半空,就像一座悬在半空的孤岛。除了密林中引颈窥视的走兽,在空中盘旋和落到树枝上聒噪的飞禽,除了一隔十天半月,偶尔从密林中钻出一个猎人,再不见其他的人影;它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漫山的松涛和孤寂中,一人呆守机房,守望着那座发射塔,那几台闪动着指针的哑巴似的仪器。这份站长兼值机员的工作,没有哪一个乐意接受。
于是这个差转站的岗位有了最公平的方式,广播局的年轻职工轮流上山,今年是张三,明年是李四;到了第三年,却不是顺理成章的王五,而是一名叫陈光宇的年轻人。
说他年轻,可已超过了局里规定的下乡锻炼的年龄;说他没有基层工作的经历,可他参加工作就在乡镇,就因为工作出色,年前刚调进了城。比他年轻的多的是,需要下基层锻炼的也大有其人,扳着指头怎么算,也轮不到他的名下。可是他的经验,他的资历,他的所有的优点,都让他成了差转站继任值机员的最佳人选。在他之前,价值连城的设备得不到保障,倍受关注的播出得不到保证,这个万人注目的小单位,已牵扯到电视事业的大形象。
况且让他上差转站,继任站长和值机员,还有其他的人都不具备的优势和条件,那就是他是当地人,他的家就在发射塔下的那个村。家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家乡也踏在他的脚下,至少不会因思乡念家,差转站出现这种那种状况,出现不该出现的问题。于是本不该上发射塔差转站的陈光宇,调进城还不到一年的年轻人,在一个晚上的“思想工作”之后,打起了背包出了县城,走上比原先的单位更偏远更枯燥的岗位。
说好只去干一年,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十几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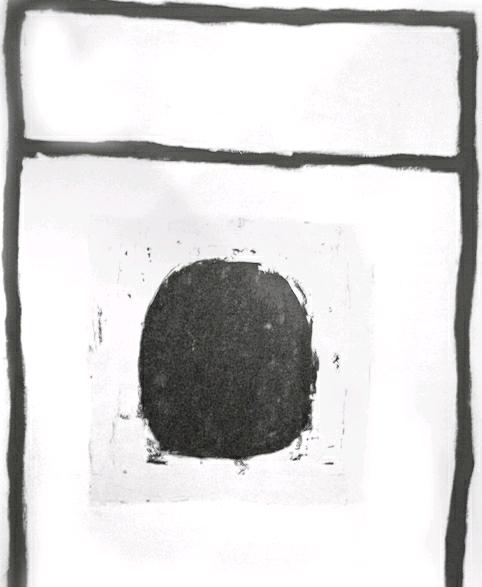
那一年的年底,一年工作的期限结束了,他把差转站收拾得干干净净,天天掐着日子,等待来替换的新人;他也像他的前任一样,例好了一个移交清单,工工整整放在了那个简易的办公桌上。可是等了几天,替换他的值机员没有来,局长却带着一班人,来作春节前的慰问了。慰问的局长给他带来了大米,猪肉,水果,一份备得丰厚齐整的年货。局长亲自帮忙搬下那些大包小口袋的春节慰问物资,亲自给他简陋的卧室安装调试一台新空调,然后拍了拍年轻小伙子的肩,推心置腹地说,这差转站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规,要找一个能替换你的,一时还真没有合适的人选。怎么样,再干一段时间吧?不说为单位,就算为我,支持我的工作?陈光宇望着那大包小包的过年物资,望着那好不容易爬上山来,泥巴和雪糊得一团糟的新吉普车,望着这一脸诚恳待人和气的一把手,他这个小小的职工还能说什么?
一干又是一年。
干完了两年,再诚恳的领导也不好再开口了;想到自己终于盼到下山了,谈了几年的女朋友也答应同他去拿结婚证了,一高兴,这个山上下来的年轻人就在全局的年底会餐上多喝了两杯,散了宴席,一路摇摇晃晃回到招待所。没有料到,推开门,已经有人在他的房间等着了,那是一对小俩口儿,都是他局里的同事,女的抱着一个还在吃奶的孩子,男的就是准备上发射塔顶替他的接班人。这小俩口儿一脸的愁眉苦脸,可一望见他,就像望见了救星。
第二天,这个开完年底总结会就可以留在县城的年轻人,一大早就又背着背包上了山。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人们知道这一次,是他主动要求去的;而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了下山的机会。
时间像云雾一样,一日复一日在山巅盘绕,流逝。他每天要保证三次开机,早晨,中午,晚上。三次开机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大半天的时间,可是这早、中、晚却像三个钉子,把他牢牢地钉在了发射塔下,钉在那流逝的云雾里。
局的那辆吉普车,每隔一两个月,总会上一趟山,沿着简易盘山道,颠簸着闪现着,穿过密林吃力地爬上山来。每次上山,不是戳破了轮胎,就是又颠坏了某一个部件。它给发射塔上的值机员送粮,送菜,还送来几个设备维修员。位置高,也是雷击的多发区,乌云翻滚,雷电大作,常有一团团火光沿着发射塔的天线嗞嗞奔窜;突然林子里一声巨响,又有一棵古树在一阵黑烟中被劈掉了一半。雷击的后果又是烧坏了设备,压断了电线;位置高,气候也最冷,积雪也最厚,不定在哪一个早晨,吱呀一声倒下来的树枝也压断了横在空中的光缆。维修人员有时带来了设备,只要一拆一换就成了;有时却要顺着那线路一直查下山去,如果运气不好,也得在这里住上一两天,甚至三五日,这个时候,陈光宇或许就可以回一趟家。
他的家虽然是在山下,在他的眼皮底下,可是却难有机会回去一趟,设备坏了的日子,才是他休息的假期。因为这山路看着近,一上一下的来回却要四五个小时,回去会耽误节目的按时转播。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会站在发射塔下,朝山下俯瞰。那些山脉山峰,全成了小得可怜的龙蛇,这些龙蛇都朝这主峰奔涌而来,仿佛这发射塔是它们的巢穴。山脉与山脉之间,就是一湾一湾的田畈,一户一户零散的人家。他常会站在山顶,瞭望着自己的家,那片山弯里,一幢远得如一块黄肥皂的房子,思量着自己又有多长时间没有回去看一看了。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送粮,送菜,送技术人员的吉普车已从那辆老式的绿色吉普,换成了银白色的日本三菱,那辆专爬这个发射塔的北京吉普,早已破烂不堪,再也上不了山;局里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来维修的技术人员也换成了一拨年轻人,他们像陈光宇年轻时一样,对这个初呈眼前的几乎原始的地方充满了好奇,到了差转站也更是兴高采烈,跑到这里摘几个野果,跑到那里惊呼着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这突然到来的热闹,让常年寂寞的差转站增添了生机,差转站那条常常趴在门口的岩石上,只能望见苍天白云的大黄狗,也跟着那些年轻人的腿边跑去跑来,高兴地撒着欢儿。可是常年守望发射塔的这位值机员,年轻的身影已变得有些苍老了,举手投足,再不像这些上山来的小伙子富有朝气。目光有些凝滞,神情有些沉悒,表情也有些木纳,见了生人还略显害羞。由于经常见不到一个人,说话的功能仿佛业已衰退。上山来维修的一帮小年轻,开口闭口都叫他老陈;他头次听见这个称呼不由一愣,这才意识到,曾经的小陈已人到中年,曾经黝黑的两鬓已经斑白,一个山里的小伙儿曾经红润的面宠,也像风干的肉样失去了水分,失去了青春。
人到中年的老陈,也早成了家,只是和他成为一家人的,不是那位他调进城就答应和他结婚的女友,而是一个只要男人吃着皇粮就很知足的乡村女人。
结婚的头两年,小夫妻算得上恩恩爱爱;陈光宇至今不知道,当初哪儿来这么大的热情,再晚再远,隔三差五也要跑回家一趟。值完了机,已是晚上十一点了,他兴致勃勃地打着手电筒,头顶满天的星光,边走边跑地穿过树林小道,也不管黢黑的林中有什么野物的嚎叫,滑坡的山道有什么坍塌的风险,一个劲儿地向山下那个甜蜜的家奔去。到了东边的天空刚发白,一头雾水,一身汗水的人,又会准时出现在发射塔下。就是在新婚的日子,他也没有耽误过一次开机。
在那段亢奋甜蜜的日子里,只要看见月光里的发射塔直指着满天的星斗,就知道这又是一个美丽温馨的夜晚。天上是满天的繁星,山下也是一片闪亮的星光,不过这山下的星光只要他的转播一停,就会一个接一个熄灭,那是看完了电视,乡亲们打着哈欠,要熄灯睡觉了;可是在月光下,某一处深黛色的山弯里,却像天上的星宿一样,亮着一盏不灭的灯火。暗夜里的那盏灯微弱却执着,他知道,那是正望着这山巅的温柔期盼的眼。那段时间,他总要上山来维修设备的兄弟们给他带电池,一带就是好几对,人们好奇地问他做什么,他嘿嘿一笑,并不作答。他的蜜月,留给他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一抽一屉子用过的废电池。
蜜月的结束是在一天雾茫茫的清晨,他从山下赶回来,发现他锁着的铁门被撞开了;看见那撞扭得变了形的铁门,他一阵头皮发炸。这里不会有人来;一定是野猪什么的闯了进去。他三步两步跨进院门,见院子的地上一片狼藉,机房的门也被撞倒在一边,陈光宇心里一急,忙跳进去,站在机房仔细地查看了好一会儿,才放心地坐下来,心还在呯呯直跳。还好,这屋里都不是吃的喝的,所有的设备都还是原样。
从此,陈光宇再也不敢大意了,不敢在值完机后,望着山下的那点星宿似的灯光,打起电筒就往山下跑了。他站在发射塔下,抽着烟,不安地走去走来,时而不安地望一眼那山下的灯光。他的身旁,月光下闪着星光的铁塔,头顶着一颗灯泡,一闪一闪地插在星空中。那是一颗航标灯。狗仿佛了解他的心事,安慰似的摇着尾,望着月光下不停徘徊的主人。电视转播完了,山下亮着的一片星光,也一盏连一盏熄灭了。可是那一盏灯总是要执着地亮着,亮得让人焦躁不安,挂肚牵肠。最后,这个徘徊了望的人,望望山下的那盏灯,又看看发射塔下的机房院落,心一横,唤上狗进了院门。随着哐哐啷啷的声响,夜色里传来一阵铁链栓系铁门的声音,夜安静了;可是进了寝室,躺在床上,那个手枕着头的不眠的人,在窗外夜风的松涛,秋虫的吟唱中,眼前晃动的仍是山下那盏微弱的灯火。
曾经一段不短的时间,夫妻俩人的联络就靠那夜里的一盏灯。每当陈光宇值完了机,关上了设备站在发射塔下,望着自己家里的一盏灯,随着一片灯火的熄灭也熄灭了,站在山巅瞭望的陈光宇就会知道家里一切正常;如果那一盏灯经久不熄,山下所有的灯火都灭了,它还睁着期盼的眼,站在山巅的人就知道家里出事了,不是小孩病了,就是年迈的父母又身体不适,或者家里遇见了什么大事,等着他回去拿主意。这个时候他就会急急忙忙,又去拿上手电筒。看见主人要下山,大黄狗也兴奋地跳了起来,可是没跳出两步,却被主人喝住了:
大黄!回去!
随即一阵铁链声响,大黄狗被栓在了院子里。它隔着铁门唔唔叫着,算是在嘱咐主人一路小心。自从出了那回野猪入侵的事件,陈光宇不仅加固了铁门,每次不得已下山,还把那条大黄狗关在院子里,算是替他值班看门。
有时也不用在晚上看灯,只要望见那山下的田畈绿了,黄了,这山巅瞭望的人也会心急如焚。他知道,播种,收获,又一个农忙的季节来到了,不知道自己的女人一人怎么应付那些抢时抢季节的繁重农活儿。他不像有些上班的半边户,星期天可以回家打帮手,就是不是星期天,也可以请几天假。可是他这个特殊的工作,连假也没办法请,只要设备完好,他就没有停播的理由。他望着山下的田野上,那些繁忙着的人们,心里像松涛一样,翻滚着种种的焦虑忧愁。
当然,妻子到他的发射塔也来过几回。她虽然生长在农村,也常上山砍柴,她的身体不能算差,但是她爬上这座山峰,仍是累得气喘吁吁,脸颊绯红。她惊奇地望着这差转站的一切,用手摸着这天天在山下望见,却从没有近距离观察过的冰凉坚硬的铁塔,望着机房挨墙悬挂着的,几条蟒蛇缠在一起似的粗黑的电缆线,望着那闪动着红绿指针的仪器,见自己的男人使唤他们就像使唤鸡狗一样得心应手,满眼的新奇又敬佩。
男人的活儿她插不上手,但是上得山来,总想帮他做点儿什么。可是站房收拾得一尘不染,一台台仪器也擦得能照见人影。女人环顾着这个简陋却十分整洁的院落,那些沉默却在各司其职的机器,这一片整洁和井然,让她体会到了公家,单位的分量;这种分量,让这个乡村的并没有什么见识的女人也感受到了一种肃穆和庄严。她本能地感受到一种纪律和约束,她走路变得轻稳,说话也不再大嗓门,甚至在那个机房,面对一脸认真对着机器的男人也不敢嘻嘻哈哈,仿佛荧屏里的人也在关注她;自以为增长了许多见识的女人,明白了这个发射塔就像建在村口的那座水塔一样,左邻右舍看的电视,都是从这里流出去的,而自己的男人正是在掌管这水塔的闸门。她感到了自豪,同时也才明白,男人为什么没有人管,也要一天二十四小时寸步不离守在这个地方,就是每次的抽空回家,也总像逃课的学生,既心神不定,又那样匆忙。
女人上一次山来,就像探一回亲。可是这女人来探亲的机会也少得可怜,就算不是农忙,家里也还有猪,有鸡,有老人,后来生了孩子,女人更是少有机会上山来了。
田里的农活,轻的重的,都压在了女人身上。一年,女人没有怨言,两年,女人也可以理解,可时间一长,种种的不便加上人生的许多不顺,找一个吃皇粮男人的荣耀,新婚伊始觉得一切都那么美好的虚幻,像水浸泡的沟堤,一天天坍塌了。当她在繁重的劳动中感到孤立无援,当她在漫漫的长夜感到孤衾难耐,当她身患疾病也无人来嘘寒问暖,当她在夜晚望着发射塔上星星一样的一颗灯光,一等半夜也不见那人回来的时候,这个女人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与其如此,倒还不如找一个就在家挑牛粪的!怎么说,也是出双入对,有个相互照应!
面对女人的抱怨,陈光宇有苦难言,他何尝不想像其他的人一样,一到星期天,一到节假日就能回家,享受天伦之乐,肚子饿了有热饭热菜,放下碗筷就有人递来一杯热茶。可是那是他的工作!他的这份工作,组织上给了他多大的荣誉!年年他被评上先进,戴上大红花上领奖台,那个当上副县长的前任广播局长,总要拉着他的手,让电视台的摄像记者专门来一个特写,他看见自己的那一张傻乎乎的脸占满了整个荧屏,和县长书记的特写镜头一样时,他陈光宇知道自己应知足了;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已爱上了这里的一切,这刚劲挺拔的发射塔,这干净安静的小站房,这些跟了他多少年的机器和设备,这音乐一样漫山的松涛,这了无一尘的蓝天白云;他孤独但并不空虚,他已成了这大山里的一部分,像空气,像树木;他总是把自己的每一天塞得满满的,按时转播,定点检查线路设备,闲下来时,还可去自己开的菜园忙碌一番,虽然总是迟于山下的季节,但是鲜红的西红柿,嫩绿的黄瓜同样装点出生活的情趣。天晴气清,攀附在发身塔上检修时,可以望见那蜿蜒远去的河流,盘山而去的公路。乡下人家办红白喜事的锣鼓鞭炮,也会时断时续随风吹到耳边。村里人的喜怒哀乐包围他,他并没有什么孤岛的感觉,何况他已习惯这一人的工作岗位,这单纯,自由,清闲的工作,也没有那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可是妻子偏要鼓动他下山,进城。他埋怨女人不理解他,不体会他的难处,不尊重他的荣誉;女人指责他的死脑筋,这差转站又不是他私人的,凭什么要在上面守了一年又一年,同是上班的,别人家里大事小事总有男人回来照应,为什么她家就搞不成?有一次,陈光宇又拿回了一张年底总结会上发的奖状,正在气头的女人竟然抓起来两把撕了。那一次,两口子头一回动了手。时间一长,两人的矛盾越来越深;陈光宇感到结婚初期的甜蜜和美,竟然恍如隔世,女人没有了那份羞涩可爱,她变得粗鲁和蛮横,有时简直就是一个泼妇;而在女人的眼中,男人也越来越不念家,越来越冷漠,常常一隔一两个月不回来一趟,即便是在家的有限时间,也常常像个哑巴不说一句话。还不如他的那些仪器,仪器还一动一摆,有个高了低了,冷了热了的反映,可这个家伙仍你怎么说,只是木着个脸,烦了,还吼你一句。除了他的发射塔,心里到底还装不装有这个家?!
俩人的矛盾越来越大,连局里的一些同事也听说了;他们知道这位大哥一年四季守在山上,对家庭带来的影响和不便;他们都像商量好了,一上山来,三言两句弄清了需要维修的情况,就夺下他手中准备帮忙的家什,硬让他回家去看嫂子。
如果是以前,一见那帮维修的兄弟们上来,他嘴上虽然还在客套,心里早已笑开了花。可现在一提起“回家看嫂子”,他的脸上就铺满阴郁,一种冰冷,从脸上一直钻进心底。
他回家多半是在夜晚,有时是放心不下家里的事回去看一看,有时只是为了送工资回去,让女人农忙时好请人帮忙。那一天深夜,把工资送回去,可是推开门,却见到了不该见到的事情。他血往上涌,随手抓起一把斧头。就在他感到万念俱灰,要狠狠的一斧劈去的一瞬,听见了一声让他从黑暗的深渊回头的声音,爸爸。
他扭头一看,是七岁的儿子,穿着内衣,打着赤脚,一手还擂着惺忪的眼睛。他听见了吵嚷声,从睡梦中爬起来。在他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在深夜的狗叫声中开门回家,他看见的总是一家团聚的喜悦。但今天,眼前是一副惊恐的场面。陈光宇呆愣了一阵儿,望着吓得大哭的儿子,慢慢放下了斧头。他把一叠钱压在了桌上,拉开了大门,在儿子的哭喊声中走进了寒冷的黑夜。
此后的陈光宇更是很少回家了,虽然他也常在值完机后,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带着他的狗在发射塔下徘徊,与其说是怀着一种监视探看的矛盾心情,倒不如说是站在这山巅,对着那满天星斗撕开自己的心肺,将孤苦和烦闷的苦水倾倒排遣。山下的那盏灯,不到时候熄了,种种的猜测会让他发疯;过了时候还亮着,种种的担忧也让他痛苦难眠。那段时间,他除了机械的工作,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修饰和衣着。他的头发深长,他的胡须野草般疯长;日益瘦削的脸颊,深陷的眼眶,带着血丝的眼珠,让几个上山来打猎的伙计大吃一惊。他说,如果不是为了儿子,那个家早就该散伙儿了。
女人也感到了天大的委屈,同样也想到了两口子矛盾里最极端的作法:离婚。男人长年不在家,耕田拉耙,挑粪担粮,甚至过年时的宰杀年猪,缺不了的是一个硬劳力。事情的发展虽然超出了她最初的想象,但是她觉得这怪不得她!谁家的女人既是女人又当男人,这个上百户人家的山弯就只有她一家。女人的后盾当然是娘家,可哭哭啼啼只说了半截,话头儿就被两位老人打断。两位老人的眼中,找的是一位好女婿,虽然不像别人家的女婿到了农忙,遇到了什么使力的活儿就上了门,可是这位心细的女婿到了农忙知道他们要请人,那些肉,酒,烟,要给自己家买的,也给他们准备了一份,委托那上山顶的吉普车还顺便给送上了门;因为这个女婿,两个没有任何本事的老头儿老婆子也受到了大伙儿的尊敬,收不到电视,或者转播效果差的时候,人们总爱上门来打听,仿佛他们也掌控着发射塔的开关,手握着人们看电视的生杀大权。更重要的是,这个昏了头的傻闺女,三十好几了,再到哪儿找一个月月雷打不动拿回上千元工资的公家人!来哭诉来求援的女儿被骂了个狗血淋头,并得到警告,如果还这样混账下去,就不准再踏进娘家的门坎儿!
女儿被骂回去了,两位老人还是不放心,终于有一天,两老搀扶着,上了这一生从没有爬过的发射塔,那座天天看见却从没上过的最高峰,亲自担当女儿女婿和好的说客。
碍于丈人丈母两位老人爬了一整天才上得山来的情面,还有局里领导知道后的热心关怀,陈光宇勉强答应了回家开一次家庭会。没有料到,女人一开口,那种撕心例肺的痛哭,让他心中的怨气和怒火渐渐熄灭了,泛起来的是深深的内疚和自责。
结婚十多年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他从没有伸过手;他的两位老人离去之前,都是卧床大半年,他也从来没有尽过一回孝,都是当媳妇的端饭送水,床头床尾地服侍;还有这十年来,哪个家过年不是夫妻相聚,家人团圆,只有自己的家人,近在咫尺又天各一方,女人带着儿子,望着那白雪皑皑的山峰,那座无言的发射塔,过了一个又一个春节。
听了女人哭诉出的种种细节,让只在为自己着想,从来没有站在别人的立场考虑问题的陈光宇垂下了头。他心里还知道,女人还有话没有说,她生日也在腊月三十那一天;他每年的生日不能回家,老婆都会背着一背篓吃的喝的,汗流浃背地来到发射塔,而他从来没有陪老婆过一次生日。女人常对他揶揄说,自己生了一个富人的八子,却是一个孤人的苦命。准备采取极端措施的陈光宇,心里有了动摇。他想起了曾经美好的生活;妻子的勤劳与贤慧;破裂的家庭即将带来的苦难;儿子无爹无妈的孤儿般的凄惨。况且女人一再赌咒发誓,她与那男人并无什么实质性瓜葛,只是出于孤寂无助,才在一起说说心底的苦闷;现在那男人已经出门打工去了。这让嫉火中烧的丈夫感到了一丝宽慰,或者本就善良的男人大多愿意从好处想吧,总之这次由局领导亲自派人参加的家庭会达到了预期效果,一个频临破裂的家庭又走到了一起。从心底感到内疚的陈光宇暗自决定,今年无论如何,也要在家过一次年,弥补年年春节让家人天各一方的内疚。
这一年的春节很快到来了。这年的春节和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仍是一入冬,耸立着发射塔的山峰就早早地落了一层白雪,将孤峰的景象衬托得愈加亘古苍凉;可是从来没有在春节收不到电视的山里人,到了腊月二十八,突然就没了信号,频道啪啪的怎么扭,架在屋顶上那一只蜻蜓似的接受电视天线怎么转,荧屏上也只是沙沙地像下着满屏的雪花。原来,从没在春节期间没有出现故障的差转站,设备冻坏了;还有更令人担心的传言,说是看样子还不是一天两天能修好。
没有了电视,没了那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三十晚上的守岁怎么办?多少年了,人们已经习惯在电视声音的热热闹闹中,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除夕之夜,迎来一个又一个的新春佳节。
令人担心的事情被证实了,那个从来没有在家过年的,进了村就又会匆匆离去的差转站的值班人员,今年竟有闲心陪家人在镇上采购过年物资,还亲自给老婆挑选了一件太空棉的新袄子。
陈光宇早已预谋好要在家过一个年,过一个十多年来从没过的团圆年,享受这人人都能享受的天伦之乐;可是在向局里报告设备受损,春节期间要停播时,还是不够理直气壮。毕境是个老实人,从来没有撒过谎。局长听完了他的电话汇报好像很吃惊,在电话那头顿了一会儿,接着对着电筒很大度地说,停播两天就停播两天吧,好在现在城镇都通了有线电视,造成的影响不是很大。也好,你也可以趁机安安心心回家过个年——陈光荣被识破了什么诡计似的,脸上一阵发烧,忙关了电话。
结婚这么多年,男人头次在家过个春节,女人自然喜形于色。她不再是望着别人团圆的羡慕,对自家孤清的自怜,这年的忙年她显得劲头儿十足,呼唤儿子的声音也变成了大嗓门儿,仿佛一个弯子的人都不知道孩子他爸回家过年了!
可是这个沉浸在喜庆里的女人又感到了忧虑。决定回家过年的男人,总是心神不定。闲下来的时候,明知没有信号,他却偏要打开电视,啪啪地扭着自家的那个电视机;心存饶幸的邻居找上门来,问那发射塔什么时候能修好,本应三句两语就可打发的男人,却说得吞吞吐吐,闪闪烁烁,仿佛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把人送走了,他会站在院场里,望着山顶上的发射塔,呆呆出神,孩子喊他吃饭也似没有听见;局长亲自打来了慰问电话,要他安心在家过一个年,他竟半天没有一句礼貌的话。吃饭的时候,准备喝两口的男人突然没了酒兴,本应高兴的场面竟变得有些沉闷。
天越来越暗,像天边吹扬着黄沙,这发黄的天气就像沙子一样又硬又冷。这是腊月二十九,女人从早晨就开始就围着灶台忙着,炸,煮,蒸,炒,灶膛里的火呼隆隆地响,锅里也嗞啦不停,一阵阵香味儿随着冷风飘出了厨房。到了中午,脚不停手不住的女人,端上了满桌的盛宴,陈光宇正疑惑这一顿还不到过年的饭,怎么搞的跟团年似的隆重,女人早已走出了厨房,递给他一钵打好了的面糊,要他去贴对联年画。
不是明天才过年吗——男人一脸不解。
女人望一望天,说看样子明天有大雪,然后又盯着男人,撩一撩耳边的一绺头发,露出他久已不见的嗔怪的笑容:你那点儿心思我还不知道?!看你这魂儿都丢在那塔上了——等到明天一封山,你想上就去不成了——我们今天就把年过了!
陈光宇没有听清似的,傻望着女人,接着咧开嘴笑了,是识破了某种小把戏的笑,是完全放下心来的舒坦的笑,是多少日子以来没有过的开心畅快的笑!他搔了搔头皮:
可明天也是你的生日啊——
女人瞅了他一眼,低下了头,无限温柔地说,什么生日不生日的,公家的大事要紧。说完进了厨房。
陈光宇心头一热,转身去贴对联。
一阵喜庆急促的鞭炮声,提前宣告新年的到来;接着眉开眼笑的人们,奔走相告一个让人欢欣鼓舞的消息,那提前吃团年饭的人是要上发射塔了,年三十有电视看了!
这不,那管发射塔的汉子已出了家门,要上山了,他的女人抚着孩子的肩头,站在院子里目送着他。天空飞起了雪花,撒满了年关的祥瑞,那个人们熟悉的身影,带着跳跃的狗,头顶着雪花渐渐远去了。
一片风雪的前方,人们望见的是那高高耸立的发射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