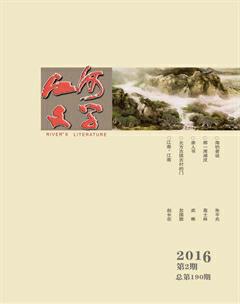总有一条小河在记忆中流淌
苏艳玲
李汉荣在《怀念——那条河流》中写道:我们不过也是游荡于河流中的另一种鱼。我们的记忆里,流淌着河流丰沛的乳汁。
阔别故乡多年之后,我发现,关于故乡最鲜活而持久的记忆,竟来自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曾经,它紧紧依偎着故乡的小村庄,日夜不停地流淌,吟唱。在村庄诞生之前,它一定已经走过了漫长而深邃的光阴,尽管容颜已老,步履依然矫健。它来自何方,又去向何处,没有人说得清楚。对村民们来说,这是一道无关紧要的话题。那时候,几乎每一个村庄,都有这样的一条小河,清澈、透亮、表情丰富、仪态端方,或从村子中央缓缓穿过,或紧贴着村庄安静地发呆和冥想。它们镶嵌于村庄饱满而结实的肌体上,与土壤,与村庄,相依为命,生生不息。被河流抚摸过的村庄,仿佛散落于天际的星辰,传递着相同或相似的气质:安详、纯朴、敦厚、温良。
与小河一起荡漾于记忆中的,是树,有白杨,还有垂柳,亭亭玉立于堤岸之上,层层叠叠,绿意葱茏,像两片丰润的嘴唇,将小河整个儿噙入口中。还有桥。有河流的地方,自然有桥,桥如彩虹,在自然与人类之间架起美妙而牢固的联结。它大概是世界上最简陋的桥。几段圆溜溜的木头,被坚硬的铁丝捆绑在一起,从河的这一头伸展到河的另一头,便成了桥,人踩上去,晃晃悠悠的,像荡秋千,又像安卧于岁月深长而绵软的摇篮里。因为危险,小孩子是不允许到桥上玩耍的。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乐趣可不在桥上,而在桥下,戏水、摸鱼、捉蝌蚪、捡泥巴……哪一样,都比荡秋千有趣得多。当夏天来临的时候,小河还是孩子们的露天游泳馆。农村孩子的水性似乎与生俱来,不需要专业指导,只要身体一进入到水里,便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弋起来。跨过这段桥,是海洋般一望无际的庄稼地。对河流之外的广阔天地,村民们称作“河外”,他们安身立命的土地,便扎根在河外。“河内”是闲散的,安宁的,舒适的,充满着家长里短,以及田园牧歌式的念想;而“河外”,则意味着劳碌、艰辛与收获。他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河内”与“河外”之间来回行走,脚步像河流一样,悠缓而轻盈。
正如生活总是苦乐掺半,小河也并不总是温情脉脉,偶尔,它会生气,甚至抓狂。莫言在《秋水》中曾这样描述:“洪水泛滥的时候,河水像野马一样涌过来……”野马一样奔涌的洪水我没有亲历,但许多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却亲眼目睹了决堤的河水在我家门外徘徊,它来势汹汹,不依不饶,仿佛满腔怨气的村妇,吞吐着刻薄而粗鲁的方言。每次洪水过后,小小的村庄满目狼藉。男人们自发到河边集中,争分夺秒地加固堤坝,脸上神情肃穆。女人们则一边揉着红肿的泪眼,一边清理着被河水侵袭过的场院,一张张愁苦的脸上,挂满对河流的怨愤,与恐惧。不过,也只是点到为止,他们像接纳生活中所有的苦难一样,忍耐河流带给他们的意外伤害,从神秘莫测的大自然中,汲取最朴素的生活智慧。或许,正因为河水偶尔的泛滥,让他们内心里始终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因为敬畏,他们小心翼翼,患得患失,一边守护着河流,一边守望着贫瘠的日子。
谁会想到呢,有一天,小河也会消失,且消失得毫无征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便隐匿于泥土与泥土的缝隙之中。不仅仅是这条小河,周边村庄的那些小河,也仿佛一夜之间,便悉数消失。河道空了,只留下一具具干瘪的残骸,如被扭曲的惊叹号,横亘于天地间。
我是在河流消失之前离开村庄的。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我演绎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有精彩,也有无奈,村庄,小河,似乎与我渐行渐远。可是,和大多数北方人一样,对河流,我怀有异乎寻常的渴望。有时,只是为了亲近一条传闻中的河流,我不知疲倦地长途跋涉。我曾在夜色苍茫中,流连于十里秦淮的游船上;也曾于细雨中,在周庄水乡的青石板路上徜徉,那些写满故事的河水,就匍匐于我的脚下,可是,它们无法给予我期待中的欣喜,它们滞重、暧昧,它们忧郁、疲惫,它们让我乘兴而来,失望而返。幸亏,还有故乡的那条小河,它不失时机地在我的记忆中复活,鲜活,欢快,一如从前。我差点忘记了,我也曾拥有过一段波光潋滟的美好时光。它已经流淌在我的生命里,它让我对故土充满深刻而恒久的眷恋。它是那样的寻常,又是那样的不可或缺。我不相信,它与我,会从此形同陌路,相忘于江湖。也许,失去是另一种获得?
当春风又绿故乡岸时,我又踏上了这条熟悉的土路。七岁的女儿牵着我的手。她是第一次走近这条小河。尽管我反复在她耳边铺垫,小河早已消失,但她的眉宇间,依然闪烁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当我们踏上堤岸时,出乎我的意料,一弯细流,竟跳进我的视野,我心头一阵狂喜。难道,小河又回来了?然而,我的喜悦没有持续太久。我很快发现,眼前的河流,已然不是记忆中的模样,它纤细、柔弱,奄奄一息,像一条草绳,在空旷的河道上艰难地蠕动,仿佛随时可能断裂。它不再清澈、晶莹,居然和牛奶一样,呈乳白色,浑浊而粘稠。一股刺鼻的气味,和着流水的节奏,无遮无拦地弥漫,令我直想逃离。不过,且慢,我还想寻觅那段简陋的桥,可是,根本没有桥,因为不需要,轻轻一抬腿,一条河流,便轻而易举地被丢在了身后。河道依然开阔,依然坦荡,只是,看不到葱茏的绿。在丛生的杂草和遍地的乱石当中,一座座簇新的房屋,正翘首林立,有民居,也有厂房,这条小河,就来自这些冰冷坚硬的建筑。是它们,毫不留情地撕碎了村庄的绿衣裳。它们让村庄富了起来,可是,也是它们,让小河瘦了、丑了。
女儿已经不再兴奋,嚷嚷着要离开。一个村民从我们身边经过。阳光下,他的面孔熠熠闪光,他一眼便认出了我,向我绽开温和而友善的笑容,很自然地呼唤我的乳名,而我,却想不起如何称呼他。好在,这条小河,让我们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话题。他告诉我,邻村已经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可是,为什么不从源头上切断污染源呢?面对我的问题,他哑口无言。或许,他在刻意回避,他向我抱以无奈的微笑,然后,拖着沉重的步伐,慢慢隐入稀疏的杨柳丛中。那些机器轰鸣的厂房里,有他一个位置吧?也许无足轻重,但聊以度日。悲凉感阵阵袭来。我想,我们都在面临一个两难的课题。
就在我们打算离去的刹那,突然,女儿尖声叫了起来:妈妈,快看,小树。
是白杨。不是一株,而是一株紧紧挨着另一株,在被肆意砍伐过的荒芜的堤岸上,见缝插针地分布着,它们羞涩、柔弱、精巧,可是,一根根脊梁,却挺得理直气壮,一片,又一片的新绿,摇曳于它们年轻挺拔的枝干上,生机勃勃,青翠欲滴。它们,何时出现在堤岸上的?是来自村里的集体行动,还是村民的自发行为?太多的疑问,大雁般掠过我心头。不过,无需解答,片片新绿,如一簇簇灵动的火焰,燃起绿色的希冀。它们,在见证我们的改变,从思维,到行动;从宏阔,到细微。这些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当那一天姗姗来迟,这条消失的小河,也会回来吗?我宁愿相信,它只是迷路了,就像人类一样,在时光的辗转中,偶尔也会茫然失措,但总有一天,会循着心灵的版图,踏上回家的路。
这天,从故乡返回城市中的家,女儿进卫生间沐浴,只片刻功夫,便湿淋淋地出现在我面前。以往,她总是鱼儿一样,在哗哗流淌的水里自娱自乐,千呼万唤不出来。女儿说:“妈妈,以后我也要珍惜每一滴水,保护环境。”是的,我们不过也是游荡于河流中的另一种鱼。我们理所当然地,需要河流温柔而多情的抚慰。我分明看到,有一条小河,正从我的记忆里出发,源源不断地,流进女儿水滴般纯洁的心境。
责任编辑:邓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