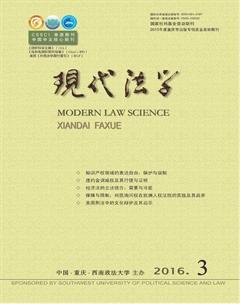保障与限制:对质询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其启示
孙长永 胡波
摘要: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审判实践中,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规定的对质询问权所应具备的公正要素,包括口头询问、证人出庭、平等武装以及官方义务进行了有条件的限缩,但同时也提出了“唯一或决定性”规则作为底线性保障。对于一项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欧洲人权法院的保障与限制,无疑关乎其对“公正”审判标准的界定。对质询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无疑也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对质询问;公正审判;证人; 唯一;决定性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3.10
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作为司法公正的“耳目”[1],其证言往往成为有罪判决赖以形成的重要依据。但同时,证人又因可能撒谎、遗忘、记忆错误或者曲解事实,甚至受到人为的操控,使得其陈述的可信性颇受怀疑。所以,让做出归罪陈述的证人在事实裁判者的见证下,接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成了应对证人陈述不可靠或证人不诚实的制度对策。而赋予被指控者获得询问做出对其不利证言之证人的机会,也恰恰契合了正当程序的原则性要求。因为,“一项关于事实认定的制度安排是否值得追求,其判断标准不仅仅在于它们产生准确结果的能力,因为对事实真相的追求仅仅是司法裁判活动的一部分,促进发现真实的价值,必须与法律程序的其他需求达成一种平衡。”[2]
《欧洲人权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6条第3款d项明确规定了被指控者应当享有对质询问权,即任何受到刑事指控的人有权询问做出对自己不利陈述的证人欧洲人权法院对“不利证人”的界定主要采用广义,并以证据的实际功能为标准,即是否是作证证明被告人有罪的人。因此,被害人、鉴定人、共犯、侦查人员都有可能成为不利证人。本文如无注明,均采用广义标准。。然而,作为具体执行《公约》条款的机构——欧洲人权法院,其对对质询问权的文本理解与实践适用之间却有所差别,其既要竭尽所能对《公约》条款做出最符合原意的阐述以保证公正审判权得以实现,又要在审判实践中处理各成员国对待这一问题的分歧以强化《公约》的统一适用。时至今日,欧洲人权法院通过一系列的判例,使得分歧正在逐步弥合。
一、《欧洲人权公约》中对质询问权的基本内涵
《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将对质询问权明确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对这一权利的用语表述却并不特定,而是交替使用包括对质(confront)、质疑(challenge)、提问(question)、询问(examine)以及反询问(cross-examine)等不同术语,以至于对质询问权往往与美国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中的对质权(confrontation)以及英美法刑事庭审中辩方对控方证人所享有的反询问权(cross-examination)相提并论。对质询问权的核心要求是使被指控者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去询问和质疑不利证人。而何谓“充分且恰当的机会”,欧洲人权法院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它对《公约》第6条第1款《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在决定某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或者在决定对某人提起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任何人有理由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到依法设立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院的公正且公开的审讯。…… ”做出了如下阐述:“所有证据必须在被指控者在场和公开听审的情况下,以对抗式的方式予以出示。”参见:Al-Khawaja and Tahery v.United Kingdom [2012]54E.H.R.R.23GC ,at[34].从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条文的阐述来看,对质询问权所要求的“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在理论上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性要求。
(一)口头原则
一般而言,口头原则不仅是发现实体真实的重要保障手段,也是体现程序公正的最佳方式。被指控者与不利证人面对面地对质被认为能够以公正的方式有效地揭示案件事实真相。所以,英美法国家以此为理论基础普遍建立了传闻规则;而大陆法国家不仅将其作为直接言词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还往往认为口头询问遵循了被指控者是诉讼主体而非诉讼客体之正当程序要求[3]。口头原则对于对质询问权的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指控者应当与不利证人“面对面”。“面对面”是对对质询问权的形式要求,即“对质双方应当到场,具备直接提问、辩驳和观察的条件”[4],体现了证人作证(陈述)当时,被指控者在场的必要性,同时应以知悉不利证人的身份为前提;二是言词交流。促进证人与被指控者的当面交流,能够推动解释和揭露、否认或者承认真相。而书面讨论并不会如言词交流那样真切,从而会直接影响到对证人诚实性及其证言可信性的判断。
(二)证人到庭
欧洲人权法院将刑事诉讼理解为以“控辩式三角结构”为基础的程序,也就表明询问证人应当在中立的法官面前进行参见:Ringeisen v. Austria, judgement of 16 July 1971, Series A no 13,(1979-80)1 EHRR 455,at[95].,法庭理应成为询问证人的重要场所。对此,欧洲人权法院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一是法律正当程序的角度。公正审判权源于英美法的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而后者的基本要求是“权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获得被听审的机会”[5]。欧洲人权法院对《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解释,正是将获得独立且公正的法官听审作为公正审判权的基本内涵,而这对《公约》第6条第3款下所包括的最低限度权利具有当然的涵盖作用。所谓“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应当包含被指控者询问证人的过程应当由独立且公正的法官予以全程见证这一实质性要求。二是证据可靠性判断的角度。基于法官的中立地位以及对事实判定的决定作用,被指控者对不利证人的询问处于独立且公正的法官主持之下,让其亲历询问证人的整个过程,有助于确定证言的真伪,从而实现公正审判。在卡尔多诉法国(Cardo v. France)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便强调:“询问证人最为重要的问题,是能够让法庭亲眼观察证人接受询问时的言行举止,从而有助于法官对证言的可靠性形成自己的内心确信。”
(三)平等武装
《公约》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平等武装原则,但平等武装作为公正审判的固有内容却得到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人权委员会的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毕竟,离开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这一前提条件,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将无从谈起。在奥夫纳与鲁普芬格诉奥地利(Ofner and Hopfinger v. Austria)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指出:“检察官与被告人的程序平等rocedural equality),一般可称为‘平等武装’,这是公正审判的一项内在要素。”
参见:Ofner and Hopfinger v. Austria[1962]ECHR,524/59and617/59,at[45].平等武装原则虽然不是一项具体的权利,但却致力于确保《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公正地得到适用。对于对质询问权,平等武装原则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知悉对方证据的权利,即应当让被指控方知悉不利于己的证人所陈述的主要内容,而不能由控方在辩方不知情的情况下提交法院裁判;二是评论对方证据的机会,即在知悉不利证人陈述的基础上,对该证言予以应对和反驳;三是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虽然根据《公约》第6条第3款c项的规定,被指控者既可以自行辩护,也可以选择由律师进行辩护,但对于询问证人这种需要具备相当法律技术水准的工作,辩护律师的参与直接关系到控辩对抗中辩护职能的发挥。事实上,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往往认为,辩方律师完全能够代表被指控者单独对证人进行询问参见:Pelladoah v. Netherlands[1994]ECHR,16737/90,at[41]; Van Geyseghem v. Belgium[1999]ECHR,26103/95,at[35].。
(四)官方义务
让被指控者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其前提是证人能够到场接受询问。由于被指控者往往缺乏促使证人到场的必要手段,确保证人到场的责任必须由官方予以承担,否则,对质询问权必将变为一纸空文。欧洲人权法院根据《公约》第6条第1款及第3款d项的规定,要求各成员国负有促使证人接受对质询问的义务,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证人能够到场接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但证人因客观原因,如生病、死亡、失踪以及在国外羁押等无法到庭的情形除外。因此,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往往重点审查被申诉国是否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证人到庭。在盖比利恩诉亚美尼亚(Gabrielyan v. Armenia)一案中,亚美尼亚国内法院为了能让证人出庭作证而延迟审理,同时要求警察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证人在下次庭审中到庭,但最终证人未能到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官方未能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证人到庭。理由是警察仅仅根据证人提供的住址去寻找证人是不够的,而且并无证据显示警察试图查明证人是否有新的住址以及离开旧址时的一些细节问题,包括旧址到底是长期住址还是临时住址,证人是否有可能在近期返回等参见:Gabrielyan v. Armenia,[2012]ECHR,8088/05,at[82].。该案最终因为官方未能尽到确保证人到庭的义务而被判有违《公约》的对质询问权条款。
二、对质询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审判实践中的限缩
虽然欧洲各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差异很大,但每一个签署《公约》的成员国都认为本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符合公正审判的要求。然而,作为最低限度权利的对质询问权,其公正标准却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被不断修正。
(一)询问方式和手段的多样性
如上所述,知悉证人的身份并进行“面对面”的询问是达到“充分且恰当”要求的因素之一。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审判实践中,却因个案的特殊情况而未能始终严格恪守这一标准。从其判例来看,缺乏“面对面”要素的作证行为往往会得到认可,其中又以匿名作证和远程视频作证最为典型。
匿名作证主要是指证人以隐瞒真实身份的方式作证,隐匿的范围一般为包括被告人在内的所有人。虽然匿名作证一直被视为特殊情况下的作证方式,但自从欧洲人权法院认可这种方式之后,“匿名作证案件数量的增长幅度却大得惊人”[6]。事实上,欧洲各成员国一般都有专门针对匿名作证的规定。英国《2008 年刑事证据(证人匿名)法》第4条规定,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1.为了保护证人或其他人员的安全,或防止财产的严重损失,或者为了防止对公共利益的现实损害;2.采取匿名措施与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相符;3、为了司法利益必须采取匿名措施,因为在法院看来证人作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没有匿名作证令的话,该证人不愿意作证。,法院才能够发出证人匿名作证令。《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06-58条规定,在符合下列两项条件的情况下,证人可以通过匿名的方式作证: 第一,重罪或者至少当处3 年监禁刑的轻罪;第二,公开证人的身份可能使证人、证人的家庭成员或近亲属的生命或安全面临严重危险。在符合上述两项条件的情况下,经共和国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申请,自由与羁押法官可以决定不在诉讼案卷中出现证人的真实身份。而欧洲人权法院在审查相关案件时,亦详细地讨论了对匿名证人进行询问的特殊方式,包括:将被告人暂时带离法庭;将证人与旁听民众和被告人隔开;在法庭外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询问证人;限制辩方向证人提出可能暴露证人身份的问题[7]。但不管采用何种方式,法官应当知悉证人的身份,被告人的律师应当在能够观察证人举止的情况下询问证人(可能导致泄露证人身份的问题除外)参见:Van Mechelen v.The Netherlands,[1997-III]RJD 691,(1998) 25 EHRR647,at [54].。允许证人匿名作证,主要是基于对证人及其亲属人身权利的保护,避免受到来自被指控方的威胁。但因无法知晓证人身份且难以面对面进行对质,使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并且不利于发现真实。为此,欧洲人权法院一般要求匿名证人必须出庭。在戴尔达诉法国(Delta v. France)一案中,申诉人戴尔达被控抢劫,被害人及其朋友因目击整个作案过程,对申诉人进行了指认并做出了归罪陈述,但均以匿名方式作证而且未能出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两名证人匿名作证且在整个诉讼程序中均未接受申诉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对质询问,全案的指控证据也仅仅是这两名证人的证言。因此,匿名证言的可信性以及证人的诚实性均难以保障,故判定该案有违《公约》第6条第1款和第3款d项之规定参见:Delta v. France[1990]ECHR,11444/85,at[37].。从该案的判决结果及理由不难看出,欧洲人权法院对匿名证言的可信性采取了更为严格的态度,即定罪不能完全依靠匿名证人的证言,同时,匿名证人的证言之间亦不能相互补强。
出于与匿名作证方式相同考虑的远程视频作证,由于具有“可视”与“可听”的优势,往往能够拟制出“面对面”的场景因素,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认同。在维拉诉意大利(Viola v.Italy)一案中,申诉人是有组织犯罪集团成员并涉嫌谋杀。为了保护证人,意大利国内法院让证人采用了远程视频的方式进行作证。欧洲人权法院在对该案的审理中认为,“在已有的判例中,依靠远程视频作证符合立法本意,而通过这种方式所取得的证据能够达到《公约》第6条关于遵循正当程序的要求。”
参见:Viola v. Italy[2007]ECHR ,45106/04, at[67].根据证人的不同情况,远程视频作证一般分为双向可视和单向可视。匿名证人有时便会采用单向可视的方式完成整个作证过程。但远程视频作证的许可范围却远不止于此。在少量涉及远程视频作证的判例中,欧洲人权法院明确了几种可以适用的情形:一是证人身处外国,或者对亲自出庭感到恐惧的证人进行询问参见:King v .Unite Kingdom[2005]ECHR ,13881/02 ,at[38]; Zhukovskiy v .Ukraine[2011] ECHR 31240/03,at[45]; Ahorugeze v.Sweden[2012]ECHR ,37075/09,at[122].;二是在性犯罪案件中,为了充分尊重被害人的个人隐私而对其进行的询问参见:W.S. v. Poland[2007]ECHR, 21508/02 ,at[122]; S.N. v .Sweden[2002]ECHR ,34209/96, at[47].;三是对重病中的证人进行询问参见:Lawless v .Unite Kingdom[2012]ECHR,44324/11,at[23].;四是为了保护尚未公开身份人员的安全而进行的询问参见:Papadakis v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2013]ECHR ,50254/07, at[91]-[95].。欧洲人权法院容许远程视频作证的初衷是为了保护证人、被害人的生命、自由以及人身安全不受侵犯,遵循司法程序在合理时限内完结的要求以及在各方利益权衡下最大限度保障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得以实现。但由于这一方式并非实质上的“面对面”,从而让人担心“图像和声音的失真”是否会给法官以及陪审团对证言“语言性”特征的探知能力造成影响,比如声音的音调以及证人的肢体动作将会与当庭作证不同;另外,基于视频传输过程中所造成的远程图像和声音的迟滞而影响被告人与证人之间的言语交流,也成为远程视频作证广受诟病的原因之一[8]。
(二)询问阶段的非特定性
被指控者在公开的法庭上对不利证人进行对质询问,不仅被认为是对抗制诉讼的固有特点,也是最有利于实现公正审判的方式之一。所以,“被告人对质询问不利证人的主要场域应为法庭审理之中,对质询问权主要是一项法庭上的权利”参见:Baber v.Page,390US719,725-6(1986): “The right to confrontation is basically a trial right”.,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英美法国家的认可。欧洲人权法院在其较早的判例中也认为,“在对抗制下,所有证据原则上应当在公开且控辩双方在场的程序中予以出示质证”参见:Barbera,Messegue and Jabardo v. Spain [1988]ECHR ,10590/83,at[78].。这无疑否定了在审判以外其他场所进行质证的做法,同时强调法庭才是进行对质询问的最佳场所。然而,“原则上”的表述为欧洲人权法院实际处理案件开辟了例外的通道。
考斯特夫斯基诉荷兰案(Kostovski v.Netherland)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考斯特夫斯基是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成员之一,他被指控参与一起持械抢劫案件。在侦查阶段,两名证人因担心遭受报复,以匿名方式向警察以及预审法官(examining magistrate)做了具有指控性质的陈述,且没有让考斯特夫斯基及其辩护人参与询问过程。随后,在证人均未出庭的情况下,法庭采信了证人的庭外陈述,并对考斯特夫斯基做出了有罪判决。欧洲人权法院虽然最终判定该案有违《公约》第6条第3款d项的规定,但理由却是申诉人及其辩护人未能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获得询问证人的机会,而非仅指庭审环节。欧洲人权法院强调,所有证据原则上应当在被指控者出庭的情况下以对抗的方式进行公开的听证,但并不意味着为了采信证言必须让证人当庭作证,只要尊重了被告人基于《公约》赋予的权利,采信证人的庭前陈述并不违反《公约》第6条第3款d项以及第6条第1款的规定参见:Kostovski v.Netherlands 1989]ECHR ,11454/85,at[41].。
参见:Van Mechelen v .Netherlands[1996]22E.H.R.R330, at[69]-[76]; Bricamount v. Belgium[1989]ECHR,10857/84 ,at[81]-[86].,欧洲人权法院的这一态度变得更为明确,即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被指控者在侦查中曾对不利证人进行过面对面的质问或有此机会,就能满足对质询问的要求,而无须在审判程序中再度进行。为了能够使判决结果更加契合《公约》第6条第1款以及第3款d项的规定,欧洲人权法院虽然一再强调,对证人的询问应当以对被告人做出的有罪或无罪判决的关键环节——庭审或主要的听证程序中进行为原则,但实际结果却是庭前询问的情形显著增多[3]343,以至于欧洲人权法院最终不得不将询问证人的诉讼阶段明确为“判决前诉讼程序中的任一环节即可”(at least at one stage of the proceeding)。
(三)中立者在场的非必要性
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不断强调,被指控者对不利证人的询问需要以对抗式的方式进行,这无疑表明整个询问过程除了控辩双方参与,还必须有中立的司法官在场见证。如果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满足上述条件似乎顺理成章,而一旦证人无法出庭,在审前程序中接受询问是否还能达到这一要求?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中,所有涉及《公约》第6条第3款d项的案件中,几乎没有因询问证人时无中立者在场监督而被判违法的判例。笔者认为,欧洲人权法院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态度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欧洲人权法院对“中立性”的认定不够明确。事实上,欧洲人权法院对“中立性”的阐述和分析常见于对《公约》第5条第3款《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3款的内容为:任何依据本公约第5条第1款c项需要逮捕或者羁押的人应当立即带到法官或者其他经法律授权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面前,并且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接受审判以及在候审时获得保释的权利,保释应当以保证到案为条件。进行适用时而产生争议的判例之中。在席瑟尔诉瑞士(Schiesser v.Switzerland)一案中,申诉人认为对其做出羁押决定的地区检察官不仅从属于检察官办公室和苏黎世州政府,而且具有侦查职能,不具有中立性,故不属于《公约》所要求的“其他经法律授权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公约》中所列明的“法官”和“其他经法律授权的行使司法权的官员”分属两个范畴,虽有所区别,但基于职能的同一性,后者理应具备前者的部分属性,中立性显然是其中之一参见:Schiesser v .Switzerland [1979]ECHR, 7710/76,at[31].,但即便如此,本案中的地区检察官仍然符合《公约》要求。首先,所谓司法权并非独指裁判权,还应包括法官以及检察官所行使的其他权力;其次,从属的性质并不影响地区检察官的中立地位,因为其决策完全是独立做出的,而且检察官办公室和司法部很少就羁押问题向地区检察官发布命令和指示;最后,地区检察官享有侦查职能并不意味着其不可能中立,因为他既要收集对被指控者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有利证据,而且不履行具体的公诉人职责参见:Schiesser v .Switzerland [1979]ECHR ,7710/76,at[28]-[34].。然而仅仅五年之后,在德·库伯诉比利时(De Cubber v.Belgium)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却判定审前程序中的预审法官不具备《公约》第6条第1款意义上的中立性。该案申诉人库伯因先前对其实施调查的预审法官成为之后庭审法官中的一员,并最终被判有罪,而提出其没有获得公正的对待。政府则一再强调,预审法官在正式庭审中并不发表意见,也不是法庭成员,仅仅是客观反映审前调查的情况;而且,预审法官并不负责指控,仅仅是客观收集对被指控者有利和不利的证据,并且独立履行各项职责参见:De Cubber v. Belgium[1984]ECHR ,9186/80,at[28].。欧洲人权法院没有接受政府的意见,而判决认为,预审法官权力广泛,包括对被指控者涉嫌的犯罪事实实施侦查,具有明显的纠问特征,而且与控方关系密切,很难不让被指控者对其中立性产生合理疑虑参见:De Cubber v .Belgium[1984]ECHR ,9186/80,at[29]-[30].。虽然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支持了申诉人的主张,但却显得非常隐晦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其没有理由去怀疑预审法官的中立性,只不过辩方会对其中立性产生疑虑。参见De Cubber v .Belgium[1984]ECHR ,9186/80,at[30].,而且没有对“中立性”拟定明确的客观标准。
事实上,欧洲各国的审前程序受诉讼模式的影响而区别较大。欧洲人权法院认为,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所有缔约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统一规范,因为对公正审判原则的遵循并不取决于具体的诉讼模式[6]120。对于在审前程序中询问证人,大陆法国家往往由负有侦查职能的司法官员负责,其不仅有权决定是否传唤证人,甚至还负责向证人传达辩方提出的问题。如法国预审法官的主要职责是实施必要的侦查行为,并做出是否将案件交付审判的决定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1条规定:预审法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一切他认为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的侦查行动。,其不仅享有独立的地位,还可采取一切有益于揭示事实真相的调查活动,包括传唤证人到场陈述,并可视情况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在场;德国的侦查法官虽不具有侦查权,但有权对检察官所申请采取的某些必要的侦查措施予以审查批准或者根据检察官的提请实施调查,故在认为必要时也可询问证人,甚至在原始证人缺席审判或者主张免证特权时,曾经询问过证人的侦查法官可以作为传闻证据的证人出庭[9];在瑞士,《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甚至直接规定被指控者在审前程序中对不利证人的询问应当在检察官的见证下进行参见《瑞士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转引自John D.Jackson, Sarah J. Summers.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Beyond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radition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347.。而对于英美法国家,审前的听证程序往往由相对中立的预审法官独任主持,控辩双方可以对证人进行提问。但需要指出的是,英国于《1996年刑事程序与侦查法》废止言词辩论式的预审程序后,预审法官决定将案件交付刑事法院审判之前不再听取任何口头证据[10]。所以,在符合传闻例外条件的前提下,未能到庭的证人于审前的陈述即便是向警察所做,也有可能符合对质询问权的要求。显然,无论是警察、检察官抑或预审法官,均非欧洲人权法院所认定的中立监督者。
(四)辩护律师介入的有限性
在遵循对抗制程序要求下,无论是在审前还是审判中,辩护律师在询问证人过程中的有效介入,无疑能够为被指控者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提供保障。欧洲人权委员会也认为,律师介入的时间越是提前,不仅能在程序的公正和公开有所缺失的审前程序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保障作用,而且基于诉讼早期阶段证人记忆相对清楚的原因,也更有可能发现或者提出新的证据线索参见:Can v.Austria [1984]ECHR,9300/81,at[50]-[55].。然而,欧洲人权法院对律师介入询问证人,特别是审前程序的介入却采取了相对保守的做法。
一是辩方律师在场权受限。虽然欧洲人权法院承认辩护律师在询问证人过程中在场的重要性,并且视之为实现对抗制的条件之一,但却并不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被指控者自己也有可能实现这一权利。在茨格洛诉意大利(Isgro v.Italy)一案中,申诉人茨格洛于审前程序中在预审法官的见证下对不利证人进行了对质询问,但辩护律师没有在场。在随后的正式庭审中,证人未能出庭,而法庭采纳了证人的庭前陈述并最终做出了有罪判决。申诉人以询问证人时辩护律师不在场侵犯其对质询问权为由提出申诉参见:Isgro v.Italy [1991]ECHR ,11339/85,at[36].。而欧洲人权法院却认为申诉人的理由不能成立,原因是:其一,申诉人在审前已经获得了机会去询问证人;其二,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在审前询问中同样未能在场。可见,欧洲人权法院并未按照对抗制要求来研判案件,反而是从平等武装的角度予以了回应,但无疑是进一步强调了被指控者本身对不利证人的对质询问已经能够满足公正审判的要求。
二是辩方律师直接询问权受限。直接性和言词性是对质询问权的基本特征,而在对抗制和平等武装原则的要求下,除了被指控者能够直接询问不利证人外,辩护律师毫无疑问也应享有这一权利。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辩护律师的这一权利却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在P.V.诉德国(P.V. v.Germany)一案中,欧洲人权委员会便认为,《公约》第6条第3款d项之规定并不要求所有案件中辩方都能够直接询问不利证人,被指控者及其辩护律师能够直接询问不利证人固然符合《公约》的要求,而将需要询问的问题通过法官向证人提出,同样不违反《公约》的规定[3]348。在之后的S.N.诉瑞典(S.N. v.Sweden)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重申了这一观点,即基于某些案件的特殊性质,比如性犯罪案件,《公约》第6条第3款d项并不要求所有案件的被指控者及其辩护人都必须能够直接询问不利证人参见:S.N. v.Sweden[2002]ECHR,34209/96,at[47].。需要指出的是,欧洲人权法院的态度实际上是默许了欧洲部分成员国的既有做法。除了上述案件外,瑞士的国内法规定得更为明确。根据瑞士《刑事诉讼法典》第147条的规定,在审前询问证人程序中,辩护律师虽然能够到场,但却无权直接询问不利证人,而只能将需要提问的内容交给主持询问程序的检察官,由后者向证人发问[3]347。
综上所述,欧洲人权法院并非如其对《公约》的一般性阐述那样,要求实现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必须是在对抗式的环境中,与不利证人进行面对面的对质。相反,在诉讼程序中的任一环节能为被指控者提供机会去询问不利证人,无论是否有中立监督者在场以及辩护律师是否参与,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便是“充分且恰当”的,并且符合公正审判的要求。换言之,《公约》的审判实践一定程度上对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进行了限缩。对此,笔者认为,原因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公约》的制定和执行虽然受英美法特别是英国法的影响较大,但欧洲人权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却不得不考虑欧洲各成员国的整体情况。事实上,欧洲各成员国因诉讼模式和法律传统的迥异,使得欧洲人权法院试图对所有欧洲国家的询问证人规则进行统一规范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因为证据的收集、质证与判定证据等活动的方式几乎在每个国家都有所不同。所以,做出适当的妥协,不仅能够使《公约》得以统一适用,而且还能有效提升欧洲各国对被指控者对质询问权的保障水平。
其二,处于公正审判权下位的对质询问权,虽然是《公约》赋予被指控者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权利,需要给予有效的保障,但欧洲人权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还必须兼顾其他利益。只不过因利益平衡所造成对被指控者对质询问权的限制应当被控制在合理的限度之内,且必须给予权利受限一方充分的权衡考虑和补救。
其三,就刑事案件而言,《公约》第6条的主要目的在于由一个有资格对“所有刑事指控”进行判定的“法庭”来进行公正的审判。事实上,《公约》文本也并未明确规范审前阶段应当如何进行。然而,在伊克尔诉德国(Eckle v.Genmany)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便指出,《公约》第6条第1款将被指控者享有公正审判权的时间起点限定为“受到刑事指控”。所谓“指控”是指,“由有权机构给予某人正式通知,宣称他已经犯罪;然而,‘指控’也有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表现为其他措施,只要这些措施实质性地影响到了犯罪嫌疑人的状况。”
参见:Eckle v.Germany [1983]ECHR,8130/78, at[73].显然,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公正审判权不仅适用于审判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对审判程序产生重要影响的审前程序,因为,“如果在审前阶段程序的重要方面已经出现不公正,那么仅有审判公正是不够的”参见:John Murray v. United Kingdom[1996]ECHR ,18731/98,at[29].。然而,欧洲人权法院似乎忽视了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在程序结构和诉讼功能上的巨大差异,而直接将在审判中形成的原则适用到审前阶段,而非为审前阶段制定专门的规则来确保被指控者所享有的权利,结果导致对质询问权在整体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缩。
三、对质询问权的底线保障——唯一或决定性规则
对质询问权虽然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缩,但这种限缩并不是没有边界的。正如欧洲人权法院所经常强调的那样,任何一项《公约》所明确界定的最低限度权利,对其限制必须是在合理的限度之内,而且不能有损被指控者获得公正审判。那么,这种限度如何确定?底线又在何处?为此,欧洲人权法院在一系列判例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了唯一或决定性规则(Rule of Sole or Decisive)。
欧洲人权法院将“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界定为,有罪判决不能基于具有唯一或起决定性作用的、且未经被指控者在刑事程序的任何阶段予以质证的传闻陈述而做出参见:Birutis v .lithuania[2002]ECHR ,47698/99, at[31].。也即,如果证人的庭外陈述对于证明指控的犯罪来说具有唯一或者决定性的作用,则证人必须出庭或者在审前程序中接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否则,其传闻陈述应予以排除。从一定程度上看,“唯一或决定性”规则似乎是《公约》第6条第3款d项规定的另一种表述,但其适用的范围却有所限制:即失去询问证人的机会仅仅只在该证据对有罪判决起主要或决定性作用时,才能构成对《公约》第6条的违反。
作为对被指控者对质询问权的进一步保障,“唯一或决定性”规则在安特波丁泽诉奥地利(Unterpertinger v. Austria)一案中便已有所提及参见:Unterpertinger v .Austria [1991]13E.H.R.R.175, at [9]-[32].,但首次有较为完整地表述其内容的,则是在道森诉荷兰(Doorson v. Netherlands)一案中。即有罪判决不能仅依据对案件事实而言是唯一的或决定性的,而又未能使被指控者在刑事程序的任一阶段进行过质证的证据而做出参见:Doorson v .Netherlands [1996]22E.H.R.R330, at[23]-[36].。但直到2002年布鲁特斯诉立陶宛(Birutis v.Lithuania)一案,“唯一或决定性”规则才被欧洲人权法院作为一项正式的禁止性规则而予以适用参见:Birutis v .lithuania[2002]ECHR ,47698/99, at[11]-[22].。
“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唯一或决定性”这一术语的最终确定也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欧洲人权法院的早期判例中,通常使用的表述是“唯一的证据”(参见:Asch v.Austria[1991]ECHR ,12398/86 , at[30].)或者“唯一性基础”(参见:Saidi v.France[1993]ECHR ,14647/89, at[44].),之后也曾单独使用过“决定性作用”(参见:Luca v.Italy[2001]ECHR ,33354/96 ,at[43].)的表述,而现在则一般将两者统合在一起。,为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定被指控者是否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去询问不利证人抑或刑事诉讼程序在整体上是否公正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唯一”和“决定性”的判定
唯一或决定性规则虽然是欧洲人权法院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发展出的一项重要规则,但却一直饱受争议。原因之一便是“唯一”和“决定性”的界定不明。英国法院在霍恩卡斯尔(R v .Horncastle and others)一案中提出质疑并认为,“唯一”看似易于把握,但随着程序的推进,对证据的取舍一直在发生变化,这无疑增加了认定“唯一”的难度参见:R v .Horncastle and others [2009]UKSC.14,at[69].;至于“决定性”,如果其含义就是“一旦缺乏该证据,那么做出无罪判决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有罪判决”参见:Al-Khawaja and Tahery v.United Kingdom [2009]49E.H.R.R.1 4th Section ,at[21].,那么所有的证据都符合条件,因为不具备“决定性”的证据往往会因其对定罪毫无关联而被排除
参见:R v .Horncastle and others [2009]UKSC.14,at[69].。对此,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对“唯一”判断并不存在困难;至于“决定性”,并非限于对有罪指控更具证明力,也并非仅指使判处有罪的可能性大于判处无罪,而是对案件的最终结果起到关键和重要作用参见:Al-Khawaja and Tahery v.United Kingdom [2012]54E.H.R.R.23GC, at[131].。
笔者认为,“唯一”与“决定性”就一般意义而言分别是从证据的量以及证明力两个方面所进行的客观描述,但两者无疑具有一种包容的关系。因为,当不利证人的陈述或证言是“唯一”的指控证据时,其证明力对于最终的有罪判决而言无疑也是“决定性”的。所以,对“唯一或决定性”进行准确把握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决定性”。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来看,“决定性”至少表现为以下两个要求:一是证明的直接性。“决定性”证据必须是直接证据,其存在能够使所揭示的证据事实与所要证明的案件事实之间建立直接的逻辑联系,从而增大有罪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如果缺少“决定性”的证据,做出无罪判决的概率将远远大于有罪判决。二是缺乏其他独立来源证据的印证。所谓独立来源是指“决定性”证据赖以形成的信息载体与任何其他证据不存在重合与交叉。正是基于上述两个标准,欧洲人权法院在判断证人陈述是否为“决定性”证据时通常会从两个方面入手,即一方面对证据本身的证明力予以考量,如性侵案中的被害人陈述或者目击案发过程的证人陈述;另一方面则是将全案的证据予以排列,逐一进行分析,依次辨析证据来源是否独立以及能否形成印证。
(2)唯一或者决定性规则的反向制约
欧洲人权法院适用《公约》第6条第3款d项用于判断被指控者是否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去询问不利证人的方式,被不少学者认为太过自由放任(laissez-faire)[3]348,以至于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对于《公约》确保对质询问权得以实现的几乎所有公正要素,包括询问方式、询问时机、中立者在场以及律师帮助等,都有弹性适用的空间,欧洲人权法院似乎并不愿意对此予以严格限定。然而,一旦证人陈述成为“唯一”的指控证据,并对最终的有罪判决形成“决定性”影响时,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结果则会发生逆转,原因便在于,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的适用使得“公正”标准趋于明确,而其也成为保障对质询问权的底线性规则。
1.限制对证人利益的平衡考量。欧洲人权法院虽然基于证人利益保护的原因而允许匿名作证,但需要严格审查以确保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而这一范围的限度却以匿名证人的庭外陈述是否为“决定性”证据而有所不同,即当证人陈述为“决定性”证据时,匿名证人应当接受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在克欧克诉荷兰(K.O.K v.Netherlands)一案中,证人知道被指控者持有枪支,因此申请匿名作证并得到国内法院的许可。但是被指控者认为其没有采取任何手段威胁或恐吓证人,且未能对证人进行对质询问,法院使用该匿名证人的陈述认定其有罪侵犯了其公正审判权,遂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欧洲人权法院认可了证人申请匿名作证的理由,更为关键的是,本案中匿名证人的证言对被指控者的有罪判决而言并非“决定性”的,故被指控者因证人匿名作证而导致对其对质询问权的限制处于一种可以接受的程度(a lesser degree)参见:KOK v.Netherlands[2000]ECHR ,43149/98,at[31].,法院使用该匿名证人的证言并未违反《公约》第6条第3款d项之规定。而因同样的争议提交欧洲人权法院裁判的威瑟诉荷兰(Visser v.Netherlands)一案,欧洲人权法院则认为,采取匿名方式作证的证人的庭外陈述对于有罪判决而言是“决定性”证据,而被指控者又未能对该证人进行对质询问,故无须再去考量是否还有其他因素能够对被指控者的权利限制予以补救,而直接认定荷兰法院违反了《公约》的对质询问权条款参见:Visser v.Netherlands[2002]ECHR,26668/95, at[51].。
2.科以官方确保证人到庭的严格义务。一旦证人陈述成为“决定性”指控证据,被指控者是否有机会对证人进行对质询问,将成为欧洲人权法院判定该案是否有违《公约》第6条第3款d项的主要标准。所以,“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的适用强化了各成员国确保证人到庭的义务”[3]350。这一变化在麦尔德和沃特兰诉芬兰(Mild and Virtanen v. Finland)一案中得到了一定的体现。申诉人麦尔德及其同伙被控分别伙同M和R实施盗窃。M和R因认罪被先予判刑,两人在侦查阶段分别指证麦尔德及另外一名同案人是多宗盗窃案的主谋。在对两名被告人的庭审中,M和R均未出庭,而是宣读了两人在侦查阶段的书面陈述。国内一审法院认为他们在确保证人到庭的问题上已经尽到了合理努力:一是为了让证人出庭多次延迟庭审,但均未奏效;二是证人M曾在发给法院的传真中明确表示不愿出庭作证,而且明知国内法律未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的权力参见:Mild and Virtanen v. Finland,[2005]ECHR,39481/98 and 40227/98,at[42].。但欧洲人权法院仍然认为国内法院未能履行促使证人到庭的义务,因为“证人虽已明确表示不出庭,但法院不能因此推定证人一定不会出庭”Mild and Virtanen v. Finland,[2005]ECHR,39481/98 and 40227/98,at[43].。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国内法院尚未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查明与证人能否出庭相关的所有事实,即便对难以预期的事实也不能进行偏向性过于明显的推断。而被申诉国芬兰有关这一方面的立法也被欧洲人权法院视为不适当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芬兰的国内法并无确保证人到庭接受被告人询问的条款,所以这方面的立法是不适当(inadequate)的。参见:Mild and Virtanen v. Finland,[2005]ECHR,39481/98 and 40227/98,at[46].,最终该案被判违反《公约》规定。表面上看,欧洲人权法院在该案中认定官方未能履行确保证人到庭的义务,但实际上已经将义务的履行程度与证人陈述在认定有罪中的作用紧密相连。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末尾明确指出:“证人陈述对案件的认定至关重要,以至于上诉法院对其余证据的分析一定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些证人陈述所展开。所以,国内法院确保证人接受对质询问的努力尚未达到合理的程度。”
3.强调辩护律师在场帮助的必要性。从大量的判例来看,欧洲人权法院并不愿意对辩护律师在询问证人过程中的作用给予过多的强调,其一方面认为律师对被指控者询问不利证人的帮助也可以由法官甚至检察官来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基于让律师全面介入庭前程序对各成员国而言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6]189。然而,当证人陈述对有罪事实的证明作用处于“决定性”地位时,欧洲人权法院则会改变态度,而将律师的在场帮助视为维护公正审判权的前提条件之一。在上文提到的茨格洛诉意大利(Isgro v.Italy)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虽然驳回了被指控者关于辩护律师未参与到询问证人程序有违《公约》对质询问权条款的申诉,但却在裁判理由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意大利)地方法院和上诉法院尽其所能也未能让证人出庭,但有罪裁决并不是完全基于证人陈述这一‘唯一性’证据而做出,因为有罪判决的做出还采纳了其他证据,故判决的公正性不存在争议。”参见:Isgro v.Italy [1991]ECHR 11339/85,at[35].尽管欧洲人权法院没有直接指明应当保障辩护律师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证人进行对质询问的权利,但实质上已经将证人陈述的证明力强弱作为辩护律师是否应当在场询问的重要考量因素。即“如果证据对被指控者的有罪判决而言是决定性的,欧洲人权法院则会坚持辩护律师必须在场。否则,必将违反《公约》第6条的规定。”[3]348
四、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公正”审判标准的重新界定
作为《公约》明确规定的最低限度的公正审判权利,对质询问权无疑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公正”审判的内涵。然而,欧洲人权法院涉及对质询问权的判例似乎矛盾重重。首先,在绝大多数判例中,欧洲人权法院均强调证据的采信和证明力评判属于国内法院的职责,本院仅负责审查对待证据的方式,以判定刑事诉讼程序在整体上是否公正;然而,唯一或决定性规则适用的前提不仅要对证据的证明力做出评判,还要对判决结果的准确性予以认定。因此,欧洲人权法院似乎难以自圆其说。其次,在部分相类似的判例中,欧洲人权法院对判决理由的阐述无疑表明了这样一种态度,即当证人陈述对有罪判决而言并非是决定性的,那么对被指控者对质询问权的限制则不会造成实质性影响,甚至辩方没有机会对不利证人进行对质询问也不存在审判不公的问题;而一旦证人陈述是“决定性”的,同样的限制将会侵犯被指控者的公正审判权,或者至少产生潜在的不利。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保障标准上的差异,甚至在判断《公约》第6条第3款d项是否得到遵循时,是应当首先评价“唯一或决定性”的证据是否存在,还是判断被指控者是否获得了“充分且恰当”的询问机会在先,都成为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最后,欧洲人权法院始终秉持一种统一的“公正”观,而无视审前和审判之间的结构差异以及对抗制和审问制之间的模式区别,通常有意回避案件中已经发现的违背《公约》的情形,并且拒绝评价和明确适当的做法参见:Hanif v .Unite Kingdom[2012]55E.H.R.R.16 at[154].,似乎只愿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表明一种概括性观点。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欧洲人权法院正面临着逐步削弱其所强调的,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应当是“充分且恰当”这一观点的风险[11]。
如上所述,作为欧洲人权法院在适用《公约》第6条第3款d项过程中发展出来并频繁援引的唯一或决定性规则,似乎让程序“公正”变成了一个不甚明确或者难以界定的概念。但笔者认为,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欧洲人权法院所秉持的 “公正”审判标准。
(一)公正审判的实现没有静态的评价标准,而是动态的利益平衡结果
被指控者的公正审判权被《公约》视为最低限度的权利。所谓“最低限度”,就在于“不论什么背景或者公共利益牵涉于刑事审判之中,都不能以任何方式对公正审判权予以限制、妥协和束缚”参见:Brown[2003]1A.C.681 at 694(Lord Bingham).。然而,这却并未阻止欧洲人权法院为适应个案的需要而对被指控者对质询问权的适用边界进行的不断调整,即只要被指控者权利的本质得以适当的维护,对这一最低限度权利的适当限制亦非不可。通过利益平衡实现的“公正”,在欧洲人权法院来看,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个案中的多元利益应当实现基本的平衡。正如欧洲人权法院在道森案(Doorson v.Netherlands)中表述的那样,“被害人、证人的合法利益同样应当受到诉讼程序的保障而不能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所以,公正审判原则同样要求所有的案件必须实现被指控者利益与需要作证的证人和被害人利益之间的平衡。”
参见:Doorson v .Netherlands[1996]22 E.H.R.R,330,at[70].而实际上,欧洲人权法院的责任是要使得整个诉讼程序的推进对所有诉讼参与人,包括社会公众都是公正的。
二是应当明确各种利益因素在“公正”概念范畴内的序位,从而建立一种整体性的评价体系。对于《公约》所明确规定的对质询问权而言,被指控者的利益仍应处于核心地位,对其限制必须遵循最大必要性原则,即限制必须合理适度,且应给予权利受限方充分的救济和弥补。
三是设置利益平衡的底线。即在“公正”底线之下不再进行平衡,因为平衡将会有损被指控者的公正审判权。所以,当证人证言是定罪的唯一或者决定性证据时,如果被告人在审前或审判阶段没有机会询问他,则其庭前陈述必须被排除,而不再考虑证人不出庭是否有正当理由。
(二)公正审判的实现并非发现真实的担保条件,而是一项内在因素
根据欧洲人权法院一贯所持的观点,《公约》的对质询问权条款所规制的对象并非是判决结果,而是整个诉讼程序是否公正。然而,大量的判例却表明,“唯一或决定性”标准才是判定当庭质证必要性的前提和基础。在高萨诉波兰(Gossa v.Poland)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虽然在判决书中长篇累牍地分析了官方是否尽到了合理努力以确保证人到庭,但最终确定该案并未违反《公约》的理由却是被指控者的有罪判决并非依据“唯一或决定性”的证据而做出参见:Gossa v .Poland[2007]ECHR,47986/99, at[63].。那么,为何欧洲人权法院对“公正”标准的判断转化成了对证据可靠性的分析呢?
英国的菲利普(Phillips)大法官曾在霍恩卡斯尔(R v.Horncastle and others)一案的审理中对唯一或决定性规则提出质疑,即“唯一或决定性规则制造了一个矛盾,越是具有说服力(cogent)的证据越不能依赖(而需要通过对质询问)。”
参见:R v.Horncastle [2009] UKSC 14, at [91].虽然这一质疑遭到了欧洲人权法院的驳斥,但其内在的逻辑却不无道理,那就是当证人陈述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作用越强,检验其可靠性的必要就越大,也就越需要证人出庭接受对质询问。这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求所有做出证言性陈述的证人必须接受对质询问以检验证据可靠性的方式如出一辙。所以,唯一或决定性规则的适用,使得欧洲人权法院不再将公正审判视为实体真实的外在保障,而是将其作为促进发现真实和实现精准裁判的内在因素,即程序公正先于实体真实。
(三)公正审判的实现关键在于必要程序的保障,还是实质机会的获取
在判定被指控者是否获得“充分且恰当”的机会去询问不利证人时,欧洲人权法院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根据其对《公约》第6条第1款以及第3款d项的阐述,当被指控者对不利证人的询问能够保证平等武装原则的贯彻以及以对抗式模式的展开,那么这种机会就是“充分且恰当”的。然而,实际情况确乎如此吗?
公开、口头、平等武装甚至是中立裁判者在场这些对抗式的程序设置就一定能够实现对质询问权保障的实质化吗?
当所有程序设置符合欧洲人权法院的要求,证人却因遗忘而无法当庭回答辩方提问或者在庭上始终保持沉默,从而使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难以对证人证言进行正常质证时,对质询问的效果必然大打折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能认为被告人获得了实质的机会呢?事实上,此种情形在欧洲人权法院以及欧洲各成员国法院并不鲜见。瑞士苏黎世最高法院(Zurich Court of Cassation)在审理一系列相关案件的过程中便明确指出,对质询问权的保障并非仅仅要求对质听证程序能够正常推进,更需要被指控者拥有实质的机会去探知不利证人在对质询问中的正常反应[3]356。在其中一个案件中,一名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在庭前做出了指控性的陈述,但庭审时却以担心受到报复而拒绝复述庭前陈述的内容并始终保持沉默。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并未受到不合理限制,但最高法院却认为,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并未受到充分保障,被告人理应给予有效的机会去询问不利证人,从而能够对指控性的证言进行质疑;否则,被告人将难以通过对质发现证言中的矛盾以及观察证人回应质疑时的正常反应参见:Kass Nr.2003/014S ,para..4.b.。与瑞士一样,部分欧洲国家的法院也将对质询问的要求确定为辩方不仅有机会询问不利证人,而且能够对证言的实质部分进行质疑参见:Kass Nr.2003/014(judgment of the Court of Cassation of the Canton of Zurich, Switzerland).。正如欧洲人权法院在艾提可诉意大利(Artico v.Italy)一案中所表述的那样:《公约》对所有权利的保障必须是可行而有效的,而非理论和虚幻的参见:Artico v.Italy[1980]ECHR,6694/74,at[33].。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一系列类似的案件参见:F.K. v.Austria[1990]ECHR,16925/90; Bayer v.Austria[1990]ECHR,13866/88; Peltonen v.Finland[1995]ECHR,27323/95; Vilhunen v.Finland[1999]ECHR,30509/96; Hopia v.Finland[1999]ECHR,30632/96. 在F.K诉奥地利(FK v.Austria)一案中,申诉人提出因诉讼程序拖延太久,使得证人在庭上无法记起案发当时的情况,以致其无法对证人进行实质上的对质询问,而法院最终采纳证人的庭前陈述违反了《公约》的对质询问权条款。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该案中被告人并不是没有机会对证人进行对质询问,而且也难以证明证人在庭上保持沉默就会对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构成不合理的限制。同样,在佩尔顿诉芬兰(Peltonen v.Finland)一案中,对于证人在庭上保持沉默以及辩护律师不得不放弃继续追问的情况,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仍未侵犯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虽然证人在庭上始终保持沉默使得任何提问都归于无效,但辩方并未处于相对于控方的劣势,平等武装原则能够予以保障,故无法认定有违被指控者基于《公约》第6条第1款以及第3款d项所获得的对质询问权。需要指出的是,佩尔顿案中证人陈述,甚至一度被欧洲人权法院认定为“唯一或决定性”的证据。在欧洲人权法院看来,却并未被视为对《公约》对质询问权条款的违背。就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和实践来看,其对公正审判的理解更加倾向于实现对官方权力的限制,而非辩方能够像控方一样对不利证人进行询问。然而毫无疑问是,《公约》第6条第3款d项所明确的对质询问权必须是被指控者有机会对不利证人进行有效的询问和质疑。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权法院的态度是否会有所改变,目前尚无法得出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要达到公正审判所要求的“充分且恰当”的标准,仅仅为询问提供充分的程序性保障显然是不够的。
五、对我国完善对质询问规则的启示
包括《公约》在内的大部分国际性条约以及多数法治国家都将对质询问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赋予受到刑事指控的人,并以此作为准确裁判以及被指控者获得公正审判的必要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 条虽然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长期的司法实践却是证人普遍不出庭,即使是重特大案件的审判中也少有证人出庭作证,以至于“对证人证言进行当庭质证”的规定几乎总是沦为一纸空文。欧洲人权法院关于对质询问权的实践以及公正审判标准的界定,无疑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一)赋予被指控者要求证人出庭并接受对质询问的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法》仅明确了“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虽然规定了证人出庭的法定条件,但仍将决定证人是否出庭的裁量权赋予法院行使。立法对实践的推动效果并不明显,原因之一就在于对不利证人进行对质询问还未能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切实有效的诉讼权利。事实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质询问权不仅仅是公正审判的基本要求,也是为了能够通过控辩双方对证人的当庭询问以审查判断证言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增强裁判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如果被告人明确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却不能保证证人出庭,而采纳证人的庭前陈述作为定案的依据,则不仅会增加事实误判的风险,而且也会导致庭审证据调查程序的“虚化”[10]481。所以,应当将询问证人作为被指控者的基本诉讼权利,如果证人无正当理由不能出庭作证,法院应当通过排除其庭前陈述予以救济。
(二)合理确定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范围
保障被指控者的对质询问权并非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证人一律出庭,而是需要确定合理的范围。欧洲人权法院将应当出庭的证人限定为证人陈述对判决结果起决定性证明作用的范围之内,无疑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对此,我国一方面应当重新界定证人概念,即以证据的实际功能为标准,将狭义上的证人以及被害人、鉴定人、共犯、侦查人员等凡是能够作证证明被指控者有罪的人都纳入其中;另一方面还应当确立关键证人必须出庭的底线要求。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我国关键证人标准的界定主要会考虑案件是否重大复杂、证人所证事实是否确有争议、证言是否影响定罪量刑以及控辩双方是否要求证人出庭等几个因素,即能够兼顾事实查明和权利保障的两个方面,特别是被告人不认罪且与证人陈述形成“一对一”的情形。当然,将应当出庭的证人范围局限于重要证人,能够确保大量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得以简化快速处理,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应对有证人出庭的案件,即简化简单多数和优化复杂少数的目标,实现效率和公正的统一[12]。
(三)科以控方以及法院确保证人出庭的义务
在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证人不出庭,原因不仅在于证人对自身义务的逃避,更在于控方以及法院基于证人翻证担忧以及驾驭庭审难度的增大而不愿证人出庭。为了避免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流于形式,必须科以控方和法院确保证人出庭以及控方就不能到庭的原因予以严格证明的义务。对此,至少应从四个方面予以规范:一是明确控方应尽合理努力确保重要证人出庭,同时就已采取的保障措施向法庭予以充分说明;二是明确控方对重要证人确实不能到庭承担证明责任,且应达到优势证明的标准;三是法庭认为控方未尽合理努力确保重要证人到庭,或者认为控方证明重要证人不能到庭尚未达到优势证明的标准时,应直接排除证人的庭外陈述;四是二审法院发现一审法院应当排除而没有排除证人庭前陈述的情形时,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27条第(三)项的规定,以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四)合理设置庭前证据保全程序
虽然法庭才是对质询问的最佳场所,但受限于诉讼条件以及案件多样性的实情,欧洲人权法院将庭前询问作为庭上询问的有益补充。除此之外,庭前询问程序的设置对于发现真实以及提高诉讼效率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庭前询问必须以程序公正作为保障,否则不但不能缓解证人不出庭的困难,反而会陷入程序滥用的境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犯罪嫌疑人在庭前有权询问证人,实际上,目前也不具备设置庭前询问的条件,因为整个审前程序并未呈现出司法化的运行模式,没有诸如法治国家的预审法官,而检察官本身作为公诉人也具有明显的“当事人性”,难以承担作为“庭前询问”的主体角色。笔者认为,从我国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看,应当设置控辩双方同时在场的审前证据保全程序。首先,证据保全程序可以使控辩双方特别是辩方通过该程序询问证人,当场质疑证人的庭外陈述,从而增设一条有效的取证和质证渠道;其次,证据保全程序相对于庭审程序而言,在程序设置上更为灵活,又处于审前阶段,能够有效应对证人无法出庭的难题;最后,证据保全程序由专门负责庭前事务的法官主持,控辩双方在场,能够解决取证和质证的合法性和可信性问题,通过证据保全程序所录取的证人证言,在证人因正当理由无法到庭时完全可以作为控诉证据使用,从而有效避免证人庭外陈述的滥用。
参考文献:
[1] P.Wall.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n Criminal Case[M] .Springfield:Charles C.Thomas,1965:9.
[2] 米尔吉·R·安达马斯卡.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制度[M].吴宏耀,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
[3 ] John D.Jackson and Sarah J. Summers.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Criminal Evidence:Beyond th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Tradition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332-333.
[4] 龙宗智.论刑事对质制度及其改革完善[J].法学,2008(5):13.
[5] 魏晓娜.刑事正当程序原理[M].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3.
[6] 萨拉·J·萨默斯.公正审判——欧洲刑事诉讼传统与欧洲人权法院[M].朱奎彬,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171.
[7] 张吉喜.论证人匿名作证制度[J].比较法研究,2014(6):117.
[8] Marcello Daniele.Testimony through a Live Link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ight to Confront Witnesses[J].Criminal Law Review,2014(6):190.
[9] 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43.
[10] 孙长永.探索正当程序——比较刑事诉讼法专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78.
[11] L.G.Loucaides.Question of Fair Trial under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J]. H.R.L.R,2003 (3) :27,30-34.
[12]李本森.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3(3):87.
本文责任编辑:周玉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