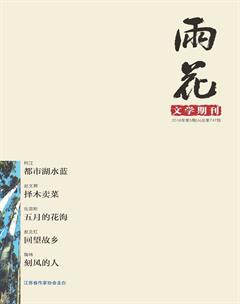歌曲·爱情
陆建华
永不枯竭的“一条大河”
拍摄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是一支经典的歌,也是一支奇妙的歌。
这支歌,自打它1956年第一次唱响那天起,在长达近60年的漫长岁月中,什么时候人们唱起来都是激情澎湃,泪光盈盈,成了歌颂祖国母亲的传唱最多的歌曲之一。这样的歌当然是经典。
这支歌承担着歌唱祖国的庄严神圣的主题,正式歌名是《我的祖国》,但歌中象征祖国的艺术形象却是连名字都没有的“一条大河”!此正是这支歌奇妙无比的地方。有资料记载:当这支歌的词作者乔羽,应电影导演沙蒙的邀请把歌词写好之后,沙蒙问他:“你的这一条大河是指的长江吧?”乔羽回答说:“是。”沙蒙说:“好极了,我没猜错。那么,既然是写长江,为什么不写万里长江波浪宽或者长江万里波浪宽,那样不是更有气势吗?”乔羽答道:“长江的确是中国最大的一条江,居住在这个流域的人口也很多,但和全国人口相比,仍然是少数。用‘一条大河就不同了,无论你出身在何时何地,家门口几乎都会有一条河,即使是一条很小的河流,在幼小者的心中也是一条大河,而且这条河上的一切都与你息息相关,无论将来你到了哪里,想起它来一切都如在眼前。”
乔羽的解释不仅让沙蒙折服,也让我们再次明确一个创作真谛,在创作重大题材的文艺作品时,对籍籍无名的“一条大河”的深情吟颂,其艺术感染力并不一定就逊于赞美人们过于熟悉的黄河长江。多年以来,文艺创作中的标语口号式的不良创作倾向,给予我们很大的困扰。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一提到主旋律作品的创作,首先总是想到“高八度”,接着便是宏大的意象,火热的情感,华美的词句,高昂的旋律,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到达预定的目标,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
仍以歌曲为例,新时期以来,以歌颂祖国、赞美家乡为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但真正产生广泛影响、受到人们由衷喜爱、如同《我的祖国》那样久唱不衰的,仍是那些创作者殚精竭虑有着精巧艺术构思、并且无一例外饱含真情实感的佳作,例如彭丽媛演唱的《父老乡亲》,例如腾格尔演唱的《天堂》。我自小在苏北里下河水乡长大,老家离《父老乡亲》中歌唱的山东、《天堂》中赞美的蒙古大草原都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在他们的歌声中得到共鸣。听彭丽媛饱含深情的叙述:“我生在一个小山村,那里有我的父老乡亲”,一直潜藏在我心灵深处的乡愁、乡恋马上就被激活了,我会自然地觉得,她唱的也是我的父老乡亲,因为他们同样“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至于腾格尔唱的《天堂》,我对他把家乡比成天堂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美好无比的比喻,这支歌才得以跻身经典行列。每次听腾格尔唱《天堂》,我总先是醉心于他一开始的浅唱低吟:“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原, 奔驰的骏马,洁白的羊群,还有你姑娘”,全是朴实无比的草原素描,但他唱得那样深情,一个大胡子的蒙古族男人仿佛少女一样妩媚;而在他把家乡之美一一列举之后,突然神情一变,刚才还在的妩媚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近于撕心裂肺的狂歌:“这是我的家,我的家,我的天堂!”那一刻,我真的被他对家乡的深爱感动得泪水涟涟……
听李谷一评点两首经典歌曲
这两首歌同一主题,都是歌颂祖国。
一首是乔羽词、刘炽曲、郭兰英唱红的《我的祖国》,诞生于1955年;另一首是张藜词、秦咏诚曲、李谷一唱红的《我和我的祖国》,诞生于1984年。乍看之下,这两首现在都已成为当代久唱不衰的经典歌曲,好像除了词曲作者和演唱者不同,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不仅主题相同,甚至连歌名也相似。但歌唱家李谷一却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说:“《我的祖国》只有一个主体,就是祖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和我的祖国》是两个主体,强调了我们每个人对祖国的贡献,‘我个人和祖国的关系。把自己手上的事做好,就是对祖国的一种爱。”
作为歌唱家的李谷一,这番话不但朴实、坦诚,更有难得的精辟。她敏锐地发现在《我和我的祖国》歌曲中,个体的“我”醒目地以“主体”身份出现,并且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水乳交融般和谐自然。这不止是歌词创作上的一种突破,更显示出时代的进步。很长一个时期,“我”被看成孤立的个体,甚至视为集体的对立面,以至于本来堂堂正正的“我”,竟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心虚胆怯起来。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不然,它理直气壮地大声宣告:“我与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淌出一首赞歌!”正是这种以祖国为自豪的神圣感情,再没有人敢怀疑歌中“我”的真诚,也没有人敢剥夺“我”对祖国的爱,因为,“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漩涡!”
李谷一已经说得很精辟了,但我仍想补充两点。第一,无论是《我的祖国》还是《我和我的祖国》,这两首歌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炽热的爱国情怀。爱国爱家忧国忧民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形成了千百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不变的主题,那就是视祖国如生命,什么时候都把国家利益置于第一位。从春秋战国时期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南宋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再到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到当代的歌曲《我的祖国》与《我和我的祖国》,都是一脉相承。或许还可以深一步说,我国知识分子对祖国的爱是忠贞不渝、虽九死而不悔的。不必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屈原因亡国之痛而毅然跳入汨罗江,《我和我的祖国》词作者张藜曾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到了1984年改革开放之年,目睹祖国春回大地,心潮澎湃,激情难忍,很快写下这首献给祖国的深情的歌,我们由此能触摸到他那颗无限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
第二,颂扬祖国是一个永恒的题材,歌唱祖国是每一个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不但要常写、多写,更要努力写出新意,寻求突破。设想一下,创作者如果没有思想情感和表达情感的艺术手段的富于创造性的追求,那些以爱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岂不长久停滞在同一个水平层次上?在这方面,无论是乔羽在《我的祖国》中独辟蹊径地以人们熟悉的“一条大河”作为祖国的象征,还是张藜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把“我”作为主体与祖国联系在一起,都为我们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
深情拥抱生活的章世和
不久前,章世和携他刚在南京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收有他新世纪以来写下的19首主创歌曲选辑的《让我抱抱你》登门看我。坐在我面前的章世和还是我十多年前刚认识时的样子,在他眯细着眼睛的白皙清净的脸上,依然浮现着让人看了亲切谦和的笑容,但此刻,我却好像第一次认识他,真的对他有刮目相看之感。
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把诗歌视为与散文、小说并列的文学样式之一。其实,只要稍微追根溯源便会知道,诗与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且,歌的历史要比诗的历史长得多。《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时至今天,诗者能谱曲写歌的不多,善谱曲写歌者能写诗的也比较少,而世和却一手写歌词,一手谱曲谱,在诗与歌的和谐结合道路上奋力前行,且取得让人瞩目的成绩,仅此一点,也值得我们肯定与赞扬。
世和创作歌曲的历史并不长。他自称:“本人没有音乐天赋,但是,受军营文化和音乐文化的熏陶,我对音乐逐渐产生了兴趣。”这些话不完全是自谦,很大程度上却是道出了实情。2001年,他参与筹备海军指挥学院院庆50周年晚会,需要一个具有部队生活气息的女声表演唱,他翻出十年前就写下的赞颂话务兵的诗作,经过一番呕心沥血的推敲,终于创作出他生平的第一首歌《潇洒话务兵》,不仅保证了整个晚会的圆满与成功,自己也从此走上歌曲创作之路。
《潇洒话务兵》在世和的创作中不是孤例,他的许多歌曲差不多都经历了相似的创作过程,这些源于生活、不乏真情的歌曲在群众中产生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也让他多次获得从省到国家级的奖项。从苏北乡村走出的章世和,在部队生活18年,当过炊事员,通信兵,指导员,部队院校教员,转业后一直在地方宣传文化部门工作至今,如今却在歌曲创作方面取得不俗的成绩,我们只要认真翻阅他写的歌词,聆听他谱写的那一首首歌曲,再参看他随着唱片附着的介绍每一首歌创作过程的小册子,不但可以了解到歌曲背后的人与事,品味到生活当中的情和义,更能体会到世和在业余歌曲创作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两条弥足珍贵的创作经验,一为刻苦,二为情真。因为刻苦,他才能终于敲开音乐之门且登堂入室;而情真,则让他的作品充盈着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唤起人们的共鸣。他的《潇洒话务兵》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当年在某部电话台任指导员的生活。终日面对100多名十八九岁的女孩子,世和不但工作上指导他们,还兄长般关心她们的生活。每逢这些女孩子中有人出公差,世和说他就会“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感觉度日如年”。《我的好兄长》是一首悼念战友的歌。那一天,正开着车去上班的世和,突然接到这位战友病逝的噩耗,他心痛如绞,“立即把车子靠路边停下,呆坐在车上想了好大一会儿”,几天后含泪写出这首感人的歌。
章世和说:“歌曲创作虽然是艰难的,却让我充实、快乐。”他选择《让我抱抱你》作为自己歌曲专辑的书名,不只表达了他对相濡以沫妻子的爱,更显示了他在歌曲创作的道路上永远拥抱生活的真情与决心。
金果临两句歌词跻身经典之后
大多数人可能会对金果临这名字感到陌生,但只需进一步了解到他就是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的歌词作者,原先的陌生感肯定会迅速消失,那轻松活泼、童趣十足的熟悉旋律便会随之在耳边响起,其耳熟能详的歌词,也会脱口而出:“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1969年11月29日那一天,才13岁、正在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读书的金果临,面对当时英语课本中不知看过多少遍的两句话:l love peking. l love Tiananmen(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突然来了灵感,将本来的两句话,合成了一个七字句:我爱北京天安门。有了这七个字的开头,第二句水到渠成般接踵而至:天安门上太阳升。那一年的上海正处于“文革”狂澜之中,作为学校里的墙报委员的金果临,经常绘制心目中的天安门城楼光芒万丈的形象,这样,第三、第四句歌词也随口吟出:“太阳升起金光照,金光照的全球红。”四句写成后,金果临将“金光照的全球红”定为全诗的标题。在这之前,不乏写作才能的金果临已经在上海的少儿刊物上发表过两件作品,这次,他将自己的新作,投向一份名叫《红小兵》的杂志,投稿前,他忽然觉得原来的题目不理想,改成《我爱北京天安门》。稿件很快被编辑部采用,发表时后两句被编者改成:“太阳光辉照万里,祖国山河处处春。”不久,金果临的表姐金月苓看到了表弟这首歌词,这位自幼爱好音乐创作的女孩为这四句诗谱上曲,也投向《红小兵》杂志,同样很快发表。事情到这里还没有完,1972年4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特刊,向全国推荐10首歌曲,其中便有《我爱北京天安门》,为了符合当时宣传的需要,歌词的最后两句改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至此,这首儿童歌曲算是最终定稿。
我写这篇短文,并不是因为这首经典的儿童歌曲创作过程的传奇性,引起我注意并深思很久的是,多年以后,不少人建议金氏姐弟充分利用《我爱北京天安门》创作成功及其深远影响的有利条件,再度合作。对此,金月苓颇为赞同,她一再鼓动弟弟写词,但金果临始终不为所动。他说:“我的笔早就放下来了,文化上没有这个底气了,时代也不一样了,写出来未必受欢迎了……”
金果临无疑是聪明的。当年,上海数以百万计的学生、老师,面对英文课本的“我爱北京,我爱天安门”熟视无睹,唯有13岁的他将两句合成七个字“我爱北京天安门”!更为难得的是金果临的冷静与明智。他明白,这首广为传唱的儿童经典歌曲的歌词,真正属于他创作的只有两句;而此歌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固然有个人的因素,更由于无意中适应了特定年代的特别的要求。这样的创作机遇可遇而不可求,一旦时过境迁,再无复制同样成功的可能。当此之时,见好就收,便成了最佳的选择。
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成双……
中央电视台一套大型公益寻人节目、由倪萍主持的《等着我》,每周二夜十点半后播出。开播至今收视率节节攀升,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观众,到时候就打着呵欠守候在电视机旁,不看完没法安心睡觉。去年国庆节期间,从一号到三号,《等着我》接连三天从原来深夜播出,特地安排到中午一点后黄金时段播出,一跃成为中央电视台庆祝国庆65周年的重点节目。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所谓金杯银杯不抵群众的口碑,这些至理名言在《等着我》这一栏目上又一次得到有力的印证。
且看十月二号的《等着我》,倪萍帮着找的是些什么人—
第一位是青岛年轻的女教师寻找她十年前曾经教过的韩国留学生;第二位是来自长沙的一名“90后”女大学生,寻找她不久前在放假回家的火车上与一位偶然相遇的、也是放假回家的男生;第三位是一位大连的女孩,她与小姨在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遇到一位让她心动的男青年,让她回家后的几个月一直念念不忘。
这是一场感人的寻爱之旅。三位女性面对全国成千上万的电视观众,毫无畏惧地落落大方地大声说出她们对爱的追求。且不说在千百年来奉行“非礼勿视、非礼勿言”的封建传统的旧中国、在视爱为罪过的“文革”时期,都是无法想象的事,就连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之初,已经冲决了“左”的禁锢的人们虽然已不再顾忌谈情说爱,但那声音却是温柔而纤弱的,无论如何不会像这三位女性勇敢而坦诚。在叙述其当年与意中人邂逅相识过程时,她们是那样坦然;在责备自己当初未能把握住机遇,以至于让爱与自己失之交臂时,她们是那样率真。不妨说,正是在这些揭示自身情感深处波澜的细微处,我们从她们精神层面的隐秘角落,清晰地听到改革开放走向纵深的时代的足音。
遗憾的是,三位女性朝思暮想苦心寻找的意中人,虽然都一一找到,但有情人并未能终成眷属,因为他们都已经结婚生子,组建了家庭。观众感到惋惜的同时,却也看到更为难得一见的真情流露:这三位女孩明白结果后没有妒忌和恨,失望的泪水还在她们的脸上真实地流淌着,她们却及时而大方地给对方送上真诚的祝福,依然是那样坦诚而率真!当此之时,我突然想起在中央电视台同一频道著名栏目《今日说法》里经常出现的残酷画面,一些因爱生仇的犯罪者,或是将硫酸泼到如鲜花娇艳般的姑娘脸上,或是丧心病狂地将对方杀害……当然,他们最终都难逃法网,受到法律的严惩。两相对比,这些犯罪者是恶魔,那三位勇敢登上《等着我》舞台寻找真爱的姑娘是真正的天使!
一千多年前的苏东坡就感叹过:“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千百年来,在爱情舞台上,既反复上演着好事成真白头偕老的甜蜜和幸福,也多次演绎了失之交臂难成眷属的惆怅和遗恨。我们需要《今日说法》保卫神圣的爱,也需要《等着我》用真善美的甘露去滋润千千万万在寻爱的路上艰苦跋涉的年轻人的心。
“彻夜无眠爱的路太长,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如果今生不能与你结成双,来世化蝶依偎你身旁!”请记住藏族女歌手降央卓玛深情的歌唱!
速成的爱情很难甜美
“现在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倪萍的话音刚落,走上一位北京女孩。她说,自己到《等着我》栏目来,是想请工作人员帮她找到不辞而别的新婚丈夫。女孩说,她在网上认识一个男孩,山东人,在北京打工,长相酷似某歌星,很帅,立刻就爱上了他。女孩是独生女,家境很好,父母全听她的。第二天她就主动与男孩见面,七天后就结婚。但两人蜜月没有度完就开始争吵,最主要的是那男孩受不了女孩唯我独尊骄横霸道的作风,一忍再忍之后,选择了愤然出走,已经两个多月了,音讯全无……
倪萍听明白了,“哦”了一声。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同样听明白了,也“哦”了一声。两个“哦”的内涵一样吗?我无法问倪萍。我“哦”,是因为又一次看到速成的爱情很难甜美。尽管如此,在我近年来看到的网络爱情的若干事例中,这位北京女孩的故事的结局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了。在大量法制电视节目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男女网上邂逅相识,然后匆忙开房间,或干脆结婚,再然后,就不妙了,分手算好的,也就是破财失身罢了,最可怕的是女孩被抢、被蹂躏甚至被害,充满血腥,让人痛心……
自进入网络时代后,一切都加速了,现实生活也随之变得一日千里,日新月异,这一切当然是好事。但爱情也跟着加速,这就让人不知说什么好了。或许我的看法太保守,我总觉得,爱情这事急不得,尤其不能速成。如同播下种子不可能立刻结果,男女互慕生情后,需要双方花费时间共同去呵护培育,这才可能结出甜美的爱情之果。不错,中国自古就有“一见钟情”之说,但成功的几率似乎不高,由于它没有给社会造成太大的危害,所以也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今天以速成为显著特征的网络爱情不同,它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理了。
绝大多数的网络爱情之所以不甜美甚至危机四伏,是因为这种爱多半是男女邂逅相识于虚拟的世界里,回到现实生活中后,本应双方互作进一步的深入了解,但,统统省略掉,就匆匆忙忙草率结合了。说得尖刻一点,这种爱只是性的冲动,而不是情到深处时的真爱的结晶。再深入一点想,网络爱情与一夜暴富有某种相同之处,它们都是当今社会浮躁甚至是暴戾之气的反映。近日偶然在由《新周刊》主编的《2013语录》一书(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中看到作家李洱说的一段话:“传统文学作品中,我们要经过很多很多的回廊,才能到达潘金莲的卧室,要经过很多儿女情长的铺垫,才能看到黛玉葬花的那一幕。但现在我们非常直接。电影界曾归纳过十个字:进门捅刀子,上床脱裤子……”李洱的话,或许偏激了些,但不无道理,且发人深思。
走笔至此,想起刀郎翻唱的一首老情歌《草原之夜》:“美丽的夜色多沉静,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突发奇想,如果那时就有微信、微博、短信,不是就没有这个有情没法传的“可惜”了吗?再转念一想,还是等一等邮递员为好,果真当时就有传情于一瞬的网络,且不说这样的爱情能否甜美,至少我们会立马失去一首让人缠绵悱恻百唱不厌的老情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