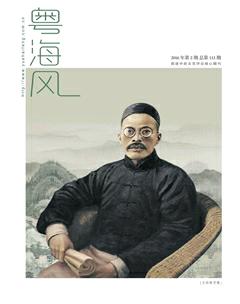铜钵盂:盘错于正史与传说中的乡村中国
曾令存
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为大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历史的轮廓。……所以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9)
党争是最可怕的。不是吗?你们革命,主张暴力,主张武装斗争,流血的是谁?是民众,是兵勇!他们为谁流血?为皇上,为孙中山?还是为他们自己?你说说看!斗争、打仗、流血。死的是民众和官兵,他们之间有仇吗?连谁是谁都不认识,不知道,就杀死对方,互相残杀,为什么?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一次战争就死了几千万人。何为?
——郭小东:《铜钵盂》(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
一 《铜钵盂》与家族叙事文学
《铜钵盂》在郭小东创作中显得有些另类。作为知青一代的他,在这部作品中不再沉湎于“中国知青部落”,而把目光投向了潮汕平原一个叫铜钵盂的村落,通过一个家族(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另一个家族)的百年沉浮,从一个侧面再现了20世纪中国的风云际遇。从作品“题叙”与“后记”中,读者不难看出“仁记巷”与“光德里”和20世纪中国百年时局的关系在维系作者与潮汕故乡情感中的不可替代性。因此,把《铜钵盂》的创作看作是郭小东乡愁的自我缓解,一次心魂的自我安妥与疗养也未尝不可。
家族叙事是古今中外文学中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创作母题。与西方文学不同,在中国文学,这个原型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与重血缘的文化传统有关,另一方面还与严重依赖土地的农耕社会分不开。在中国文学史上,自《红楼梦》之后,作家们对家族故事的书写,并非都是“三代之治”式的牧歌与赞歌,而常常烙印着大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痕迹,弥漫着一层拂不去的挽歌式的悲凉与凄美。20世纪中国文学伊始,在启蒙的感召下,“家族”即被涂抹上了一层“世纪原罪”的色彩,成为五四一代作家们控诉与批判的对象。他们笔下的人物几乎都视家族/家庭为必须冲破的牢笼,挣脱的枷锁,子君那“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呐喊,声音尽管有些空虚,却曾成为时代青年的共同宣言。“离家/出家”被五四时期作家们想象为包治社会与人生各种痼疾的灵丹妙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整个民族都因战乱而颠沛流离在旷野上的抗战年月才得以改变:“回家/归家”才逐渐代替了当年的“离家/出家”,成为这一时期包括《京华烟云》《四世同堂》《寒夜》《财主底儿女们》等小说以及中国诗人们的渴求,“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家作为空间形象,相对于陌生、危险、动荡、广漠、孤立无助世界,它狭小却亲切,昏暗却温暖,平庸却安全,它荫庇童年的生长,维系血缘的亲情,繁衍延续的生命,传递历史的记忆与讲述。”[1]“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平安。”[2]然而寻求“安稳”谈何容易!在1949年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提倡“向组织交心”的1950年代,直至“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横行的文化大革命,家族/家庭再度成为罪恶的渊薮,家与国成为矛盾冲突的对立体,这在以《伤痕》为代表的新时期早期文学中曾有过让人揪心的描写:为了政治/加入共青团,王晓华毅然与母亲/家庭断绝关系。“她必须按照心内心外的声音,批判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彻底和她划清阶级界限。她需要立刻即离开她,越远越快越好。”只有到了世纪末的八九十年代,经过近一个世纪的离乱与翻覆,在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与家族不可抗拒地日渐消逝与式微的陵夷末世,以《白鹿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才开始从黄仁宇所说的“大历史”观出发,理性地去审视/反思绵延了几千年中国的家族问题,并不再简单地以是/非、善/恶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评判来讲述中国家族的故事。作家们试图在讲述家族故事的同时,让读者与自己一起来思考这个家族/民族的前世今生,重现那些被正史遮蔽乃至湮没的民间历史文化与乡村道德人伦,展现出一种不同于却未必逊于皇朝正史的民间家国情怀。
《铜钵盂》尽管带有演义的性质,其中内容也常常是正史与野史互通相溶,但作为一部以家族为叙事原点的小说,对其意义的把握,显然很难绕开解析家族叙事作品必须面对的一些关键词,大至世家情结、家族伦理、历史沉浮与国家兴亡,小至妯娌琐事、父子反目、兄弟情仇与主仆恋情,乃至于民间命师、流浪艺人和江湖神秘大侠等三教九流的芸芸众生。甚至于叙事模式与情节的设计,作为一部家族叙事文学作品,《铜钵盂》也显得“有史可稽”:从家族→民系(区域)→民族(国家),由个体命运→朝代兴衰,等等。
不过仅从家族叙事文学的基本层面去把握《铜钵盂》的意义是不够的。或者说,《铜钵盂》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有关家族兴衰与历史沉浮的常态性话题,同时还有由明清以来潮人仰赖为生的侨批银信引带出来的悲欢人生与家国情怀,那种不同于子曰诗云,“一种似乎与政治有关,又无关”,在正史中被遮蔽乃至湮没的民间道德理想与伦理契约;由瞽师/盲妹(漂泊流浪的民间艺人)吹拉弹唱的以劝善抑恶为内容的潮州歌册展现的醒世/警世良言,以及小说对以命师相术与堪舆为代表的神秘超人力量的渲染。正是这些,使得《铜钵盂》区别于其他的家族叙事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盘错于正史与传说中的乡村中国,成为一个关乎潮汕民系的物质与精神的独特文本。
二 百年时局中的铜钵盂(一):“仁记巷”
《铜钵盂》重点讲述的“仁记巷”郭氏家族以及与之息息相关的“光德里”马氏家族,是传说中的潮汕二虎。郭小东借重铜钵盂,由都市反观乡村,在环视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同时,释放自己生命深处从童年开始郁积下来的家族记忆,书写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乃至人与神(神秘力量)之间的关系。在他笔下,“仁记巷”与“光德里”无疑是小说故事展开的重要场所。但另一方面,它们又并不是简单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一种象征与符号,隐藏着郭、马两大家族的秘密。久远厚重的文史底蕴,使得这千年古厝成为了寄寓作者思想感情的重要载体。
对《铜钵盂》家族叙事文学性质的大致审度,是我们读解这部作品内蕴的必要前提,比如小说所记述的“仁记巷”与“光德里”和20世纪中国动荡时势的关系。毋须置疑,这是小说最值得关注的内容,也是小说中最亮丽的风景之一。在这一脉线上,我们看到了作为正史的铜钵盂,看到了作者通过铜钵盂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文学想象与重构。不难想象,如果把这部分的内容拿掉,那么小说关于家族故事讲述的分量将受到极大的淡化。可以这么说,穿越“仁记巷”与“光德里”的时间与空间隧道,是横在我们读解《铜钵盂》意义面前的第一道槛。
“潮汕厝,皇宫起。”被淹没在“故宫”林立的潮汕大地、毗邻练江的“仁记巷”与“光德里”,用作者的话说,曾经都是历史上的“阀阅仕族”:“仁记巷”郭氏家族始祖汾阳王郭子仪,原是唐代三朝元老。郭氏十三世祖郭浩创基铜钵盂,到了郭仁卿这一代,已成为潮汕一带远近闻名的鸦片掮客的“客头”,富可敌国。“光德里”马氏家族始祖,则是宋朝在这里落草的马银青大夫。“仁记巷”完工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纵深几百米,两边紧凑排列着八栋有着三进天井、前后花园及地库、栓后伙巷的“驷马拖车”建筑。为建筑这八座厝,郭仁卿当年从上海运回了足足两个小火轮的银元。而完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光德里”,传说耗费了从泰国、上海由五条火轮运装的银两,由六条小巷交错隔成五座“下山虎”构成,居中祠堂“马氏宗祠”由颜之推手书。尽管千百年离乱的世道已将其中无数久远的故事消解消淡得微不足道,然而其中“显赫的几世,钟鼎贵胄的文史渊源”,还是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翻开《铜钵盂》,读者可以看到历史对这“潮汕二虎”的再一次改写,是新旧政权更迭的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不过与以往不同,这次改写残酷而暴力,充满血腥,而且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当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自然是“仁记巷”。如同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共和国初期土改的大叙事作品所描写的那样,1949至1950年的岁末年初,“解放”了的铜钵盂迎来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在“斗地主,分田地”的中国式革命中,“仁记巷”郭家祠堂大夫堂一夜间被清空,挂上了“铜钵盂农民协会”的招牌,驻扎进了土改工作队。“喧天的锣鼓和遍地的红旗,让‘大夫堂原本的体面全无,尊严尽失。大夫堂神桌香案上的祖宗牌位被清扫到天井里,一把火烧了。墙上悬挂的字画、精美却内容腐朽的木雕,都投进了大火中。”[3]覆巢之下无完卵。更为惊心动魄的还是翻身作主的民众对郭氏家族人施行的肉体与灵魂的革命。铜钵盂郭氏家族族长、“伟大的太平天国志士,中国同盟会会员”,116岁的郭向笙,被戴上写有用红笔打叉的“恶霸地主郭向笙”的一米多长的高尖纸帽,由村中民兵半是拖拉半是挟持着游街示众之后,“当晚就倒毙在天井里”,“据说是咬舌而死。”紧接着的另一个晚上,“仁记巷”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旧中国杰出的银行家、大慈善家”,1930年代的沪上潮商首富,曾于1926年与其叔父郭子彬捐巨款兴建复旦大学中国第一所心理学院“子彬楼”,1935年捐资30万龙银作为浙江大学办学经费,在潮汕解放前夕与马灿汉合作为国军460师筹集军饷50万龙银策反起义,并郑重地交代儿孙“共产党一到”,无条件将郭家几家钱庄、十几幢房产如数献出的郭信臣,无法忍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羞辱,最终用曾经为他生下15个儿子的妻子连淑发用过的一条白腰带,把自己一米九二的身躯吊死在从太祖郭节母廖太夫人传下来、不足一米五却已有150年历史的眠床上。然而悲剧并没有就此结束。1966年,24岁即断然出家庵堂做尼姑、不问世事的郭豫恭之妻郑惠照,被民兵谴送回“仁记巷”,押进后库一间堆放杂物的8平方米小屋里,和郭氏另一位女性住在一起,直至6年后离世。更富于讽刺意味的是,1973年,当年铜钵盂土改队副队长、面对批斗自己老祖太爷郭向笙、爷爷郭信臣、父亲郭豫恭却无可奈何的“仁记巷”继承人郭文雄,这个1930年代曾决然放弃繁华大上海、疏离同样显赫的马家千金去投奔延安、转战大南山,去受苦打游击的“仁记巷”长孙郭文雄,“被迫害致死,匆匆被送去火葬场”,其五男一女,只有四儿子为他送终,其余的均远在海南等地上山下乡……
“那年那天黄昏,郭氏家族上百口人,从仁记巷八座厝无数间房屋里,被赶到这个门楼前的花园里,什么东西都不能带。人们一字儿排开,搜完身后,列队走出‘仁记巷,然后任其流浪。那是己丑年年底,再过一天,便是庚寅年了。”(第301页)沧海桑田,多年后,读者仍能够从“汾阳世家”郭氏家族那个叫“四叔”的后人摸着抹彩填金、雕镂着宣统三年的字画石刻的“仁记巷”门楼时看似漫不经心的回忆中,想象到这一门阀世族在“革命成功以后”几十年间斯文扫地、家破人亡的惨烈场面。
然而时光倒流50年,正史记载中的“仁记巷”,却不乏壮烈辉煌的一面,此中尚且不论流传于铜钵盂民间有关郭氏列祖与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种种奇谈,仅观1896年秋万木草堂之一幕,即可充分感受到郭氏先祖的万丈豪情。为支持康、梁的变法维新,郭仁卿一掷十万金,把父亲从南洋几经水客批脚水炉辗转汇来建造“仁记巷”的侨批放在梁启超讲学的桌面上,其“国家残破,何家之有?”的肺腑之言,震撼了康、梁等在场的人们,以至30年后在沪上的康、梁与郭仁卿之子郭信臣论起此事,仍赞赏不已。而郭仁卿在这一年(1926)“为国家大义所动”,将半生经营积蓄烟桥茶山罂粟付之一矩的壮举,其果断、胆识与气魄,再次让康、梁感慨万端。退一步说,即便在前面检点“仁记巷”1949年后斯文扫地的历史中,我们亦可感受到其中壮烈与辉煌的一面。
三 百年时局中的铜钵盂(二):“光德里”
《铜钵盂》借助郭、马两大家族人、事的穿针引线,重现从19世纪末变法维新开始至20世纪末后工业时代中国社会的百年时局,小说对其中历史事件的涉及有分有合,但大致还是各有所重。如铜钵盂与变法维新康、梁一脉及沪上文化名人的关系,主要倚重“仁记巷”郭氏宗族,而有关铜钵盂与辛亥革命开始的国民革命的关系,则主要通过“光德里”马氏宗族。相比较之下,作者对“光德里”与中国历史关系的处理,要相对集中一些,除了钱庄批局,主要是马家长孙马灿汉与现代中国革命的一生这一线索,不似“仁记巷”,还有烟桥茶山鸦片、郭大伟郭文雄兄弟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等枝节。“丁未起事,‘光德里就是起事的大本营之一。孙中山通过光德里在海外筹款,光德里在海外的几间批局,全是革命党的联络站和钱库。南来北往的交通员,也大多经过‘光德里,或落脚,或避难。……1898年的百日维新,‘光德里也为康梁筹过钱款。民国建元,‘光德里出了一个县长,二个黄埔教官,三个省议员,四个县党部主任。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光德里出了二个国军中将,四个少将,中下级军官无数;共产党方面,从义勇军、新四军到八路军,各级将领,也不在少数。田中央村从清末变法、丁未起义,到辛亥革命,始终是个火药桶,军火库,革命党的根据地。潮汕地区第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也发生在田中央村。在这些历史大义中,‘光德里都是革命的堡。”(第176页)潮汕解放前夕,马灿汉奉周恩来之命以地下党的身份回来筹款策反国军460师却不慎落入地方游击队手里、被关在让他们洗劫而成监牢的“光德里”时的回忆,颇能够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马氏家族从19世纪末开始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与20世纪许多家族叙事文学所描写的那样,《铜钵盂》告诉读者,生在皇纲解纽、礼崩乐坏的陵迟乱世,1901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来、让“光德里”马氏宗族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马灿汉,并没有选择“学而优则仕”,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传统人生道路,而走上了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之路,未及20岁时即成为丁未黄冈起事的的主要谋事者之一。小说开篇即以极富诗意的笔致直奔主题,描写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一个秋日,一身白衣骑一袭红马的马灿汉,在丁未黄冈起事失败后潜回“光德里”筹饷。“酒色红马,从地平线上缓缓而来,像一簇光。长长的古驿道,空旷冷寂,晚秋的凉风掀起白衣骑者的风衣,白色风衣在风中展开,如盛开的白牡丹,在驿道上飘动了很久。”(第2页)马灿汉后来参加黄埔新军,任职国民政府,在武汉参与打响“中国第一枪”,成为辛亥革命的“有功臣子”。1920年代,已是国军中人的马灿汉,回来铜钵盂兴女学,代表国民政府主持“大中女子学堂”开学典礼,力倡男女平等;淮海战役结束之时,奉周恩来之命以地下党的身份回来筹款策反,成功动员李汝名的国军460师易帜起义……
但同样吊诡的是,马灿汉,连同“光德里”,在“革命成功之后”,不明不白地成为了另一场革命的祭品、冤魂。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种“公平”:一河之隔的“光德里”与“仁记巷”,一夜之间几可谓“殊途同归”,时间与空间的界线在这里已被彻底抹平。与作者写到距离丁未黄冈起事32年后的又一个秋天,回来筹款策反460师却被地方游击队关押的马灿汉从昏厥中醒来,“发现关着自己的牢房竟是‘光德里老叔公的书房时,他顿觉得震惊!感觉到革命几十年竟然革到自己头上的滋味,竟然用自己的手,洗劫了这个传承了上千年的马氏家族。从宋朝马银青大夫开基的马氏家族,一夜之间被扫地出门,而‘光德里成为监牢之地。”(第268页)与三十多年前描写“白衣骑者”的诗意笔致比较,让我们感受得更充分的是那种悖论性的黑色幽默。1949年以国军少将身份潜回田中央村“光德里”筹款策反的义举,以及后来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后来都成了清算马灿汉的罪行”。“尽管后来460师有一个团的兵力,就在田中央村举行缴械仪式,在‘光德里交枪易帜,但‘光德里的主人,并没有因此而洗去罪责。据说盐碱地撤离‘光德里时,牺牲了两个游击队员。这两个游击队员的家属,后来成了控诉马灿汉,定罪马灿汉的证人。”(第235页)1951年1月,马灿汉以“反动军官”罪名被枪决,“死在自己人手里”,直至1987年才平反。文革时期,新中国政府给马灿汉当年从自家批局,叔叔马文荣等批局筹得10万龙银军饷颁发的荣誉证书,被红卫兵作为“四旧”一举烧毁。“理由是这10万银元是剥削阶级剥削所得的黑金。不追究剥削责任就是宽大政策了,哪来的荣誉可言!”1999年,“光德里”在掌门人马家老太马郑氏去世后,“日渐荒芜,其中的马氏家祠已经坍塌了屋顶,两旁的驷马拖车也已不堪风吹雨打”,1901年为庆祝马灿汉在美国获得学位而建造的“硕士第”,如今是一家生产文胸的工厂,“终日织机轰鸣,棉絮灰尘纷飞……”
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认为,对人类来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苏联解体,这“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1),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他指出,接连不断的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历史学家们认识20世纪设置了许多障碍。“进行评价已不是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弄懂那些对于我们来讲几乎不能理解的事情。”[4]这其实也是作为小说家的郭小东在创作《铜钵盂》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并试图通过“仁记巷”和“光德里”,重现百年中国的兴衰沉浮,以及裹挟在这历史潮流中的人物的悲欢离合。[5]
四 侨批/歌册与“民间的铜钵盂”
“民间的铜钵盂”是本文自创的一个概念,意在用来阐释《铜钵盂》作为演义小说的内涵。关于“演义”一词,明杨尔在《东西两晋演义·序》曾作过这样的解释:“一代肇兴,必有一代之史,而有信史,有野史,好事者藂取而演之,以通俗谕人,名曰演义。”简言之,作为一种小说体式,“演义”小说中兼有史传与传说的成分。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文体学意义上,“演义”并不简单是一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内容,具有参与文本意义构造的功能。对于《铜钵盂》“侨批局演义”的解读,本文前面主要还是偏重于史传——信史/正史角度,重点分析“仁记巷”和“光德里”与百年中国时局的关系。在这一部分里,本文将侧重从野史/传说的层面切入《铜钵盂》,对铜钵盂作一次“民间”层面的解析,目的在于延展我们认识与了解铜钵盂的视阈,完成我们对铜钵盂的想象,包括铜钵盂人们的生存方式、精神世界与道德人伦,等等。其实,作为一个民系(潮汕)读本的《铜钵盂》,野史/传说于铜钵盂的重要性,并不轻于现代国家/民族之于铜钵盂的意义。从效果上看,郭小东显然是在最大限度地调动民间资源,以一种通俗谕人的方式讲述铜钵盂的“真人伪事”或“伪人真事”,以“尽可能重拾家族的文明史线索”,并把控讲述这一沉重题材的张力,追求一种“有距离的悲剧”的审美效果,以免破坏读者的阅读感受。如果不过分苛求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把《铜钵盂》用“民间”、“演义”的形式来讲述一个古老家族与现代国家/民族建构关系的种种探索与尝试,看作是作者对同类题材作品的艺术超越。
类似野史/传说这样的内容,在小说文本中几乎俯拾即是,如风水先生太清道人有关天地人的神秘论说,传说中的神偷燕子尾,流传乡间的“叫魂”妖术,关于烟桥茶山鸦片的生生灭灭,丁未黄冈起事领袖林达的生死行踪,清廷对革命党、诗乞詹廷敬的凌迟示众与祝允明《箜篌引》书帖的莫名去向,潮汕民间停柩待葬与出殡的风俗,批脚走南闯北的“走水”人生,等等。本文重点考察的,是对推动小说情节发展、在烘托作品氛围与人物情性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侨批银信与瞽师歌册。这如今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侨批与歌册,尽管千百年来一直流传(流行)于粤东潮汕民间,甚至一度成为支撑、滋养潮人精神的重要资源,然而它们在国朝正史中似乎却鲜有记载。
然而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了侨批与歌册,《铜钵盂》将是怎样的黯然失色单调乏味。
历史上,亦信亦银、银信合一的侨批,曾经是维系漂洋过海另谋生路、包括客家与潮汕两大民系在内的粤东先民在异国他乡联络家乡亲朋的一条重要纽带。在潮汕,“水客,鸦片掮客,批脚……无数闯海者冒险家的故事,随着潮州歌册的唱和,在千百年的民间教化中,成为潮汕人求生的向导。”“潮人仰赖此批款为生者,几占全人口十之四、五,新祠夏屋更十之八、九。”(《题叙》)在邮政交通还没有普及民众权利的年代,俗称“走水”(送批)的水客与批脚应运而生。当然,应运而生的,还有正如在小说中所写的遍布城乡的琳琅批局——兑换批银的钱庄。[6]在作品中,作者一方面申明大义,将侨批与百年中国风云际遇关联起来,赋予历史上这种粤东民间社会的“中间物”现代国家/民族意义,从大处领略到了与近代中国的风云际遇。——这在有关侨批的文学叙述史上,《铜钵盂》大概是第一次。“仁记巷”和“光德里”与近代以降中国“大事记”的关系,几乎都与侨批/批银/批局/水客相关联,这在本文前面的内容中已有所述及:1896年郭仁卿为支持康、梁维新变革在万木草堂的壮举,丁未黄冈起事中十万批银与少年批脚的传说,马至诚批局与黄冈起事烈士抚恤款项的筹措,烟桥茶山郭仁卿给林达价值12000银元的批封,潮汕解放前夕马灿汉策反460师所筹措的军饷与“光德里”的批局,……
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将侨批放回民间社会的活水中进行还原,让读者看到已经进入历史博物馆的侨批曾经具有的生命情怀,包括在此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信义社会与伦理契约,以及与此相关人的精神境界与道德情操,行事方式,等等。这其实也是读者最感兴趣的。一封侨批就是一个悲欢离合故事一部长篇小说,“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辛酸史”。在近代的潮汕,正是那些从海外源源不断辗转回来的侨批,让后人从小处感受到了这个民系的侠义古风,那种不同于子曰诗云的民间道德理想与伦理契约。对此,作者在小说的“题叙”与“后记”中有颇多精彩的评论。
这种遥远信托形成的依赖,虽无血缘,却胜于血缘的承诺。自15世纪以来,除了海盗的劫掠,水客批脚尽管自身生活艰难,银钱拮据,虽过手千万,但侵吞批款或丢失侨批的事极少发生,鲜有记载,而为寻错批主人而苦苦找觅的屡见不绝。(《题叙》)
以乡谊、诚信、口诺等精神性保约,化合而行的邮政交通,是侨批最丰富最人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结晶。它成为潮汕这座城邦之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保证。它的现代性,皆因其对古老淳朴乡土风俗的守成。(《题叙》)
重要的不在财富本身,而在于对财富的态度。在关于侨批史浩繁资料及文本记录中,至今尚未见到侵吞或冒认侨批的事。而其高度的虔诚与诚信,成为了侨批史上,最为生动和庄严的品格。(《后记》)
……
围绕侨批银信,在小说中所描写的批脚群像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刻画了马伯良这一形象,并通过他来表达自己对潮汕民系这一古老邮政符号的文化思考与伦理考量。小说第十二章写马伯良曾经无数次地触摸一封光绪二十二年(1906)从新加坡寄出、却始终无法找到收批人的的侨批。“这份批封在马伯良心中,已经读过了无数遍,他甚至闭上眼睛,都能想象出这46个亲友的模样。”马伯良通过这个批封,想象到类似“光德里”一般的庞大家族,以及那半个世纪乡村的人情世故。第十三章,作者再一次写到马伯良在所有死批、错批中读得最多,一封“愚婿郑盛添”寄给“岳母大人”的批银。每次读到批银中的那些无微不至的字眼,马伯良都“忍不住嚎啕大哭”。马伯良的嚎啕大哭,在读者心中唤起的,已不仅仅是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种民间道德人伦。马伯良最后的离世,喻示了一个时代,一种久远的文化的消逝。在小说后记中,作者写到了自己对马伯良这类批脚的文化思考与道德评判。“在我的人物中,凸现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欲望在那些生活于旧时代,崇信旧文明,却也恪守并建设着新道德与新伦理的人物身上。”“为了一件死批错批,一件没有地址的批封银信,而终其一生的信守与寻找的精神。”
除了侨批,《铜钵盂》对民间资源所作的另一充分调动,是对几百年来流行于潮汕民间的歌册的巧妙运用。潮州歌册是流行于潮汕民间的一种说唱艺术,以潮汕方言表演,以潮汕地区的戏曲、歌谣为基础,吸收外地弹词、木鱼书等唱本的题材、结构而形成,它积淀了潮汕民系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铜钵盂》借助瞽师/盲妹吟唱的歌册,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烘托人物情感世界,创造一种讲述的氛围,同时也展示了浓厚的地方风情。“打起包袱过暹罗,赚有钱银多少寄,好返唐山娶老婆……”忧伤的二胡弦声,悠远而幽怨。小说开篇即以瞽师的吟唱,“把乡愁与无奈唱得嘹亮,唱得衷情满怀”,也为整部作品定下了一个关乎乡愁与乡情的基调。在此后的情节中,作者适时地插入这家喻户晓的民间歌谣,次第将故事向前推进。“有福之人感动天,纵有祸难仙救伊,千辛万苦受流落,苦尽甘来得团圆。十本歌文做一排,悲欢离合唱人知,善人终须有结尾,恶者到底受磨折。”(第299页)
在小说的最后,作者再次通过即将弃世的郭信臣,描写瞽师吟唱潮州歌册的悲凄:“瞽师唱腔,似经千山万水而来,那凄惨悲切的唱声,深入骨髓。”(第299页)
《铜钵盂》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无意中藉此给我们画龙点睛地勾勒出了千百年来盘踞于岭南,但又有别于广府与客家的另一个重要民系——潮汕。在岭南文学世系中,人们常常会把欧阳山的《三家巷》与广府民系、程贤章的《围龙》与客家民系关联在一起,视之为这两大民系的代表性叙事文学。把《铜钵盂》作为潮汕民系的代表性叙事文学,现在也许有些为时尚早。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有关潮汕民系的叙事文学作品中,《铜钵盂》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借助一个家族以讲述一个民系,进而再现一个民族的百年历史,《铜钵盂》于潮汕(民系),与其说是一个巧合与机缘,还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从《三家巷》到《铜钵盂》,可以说是岭南民系的一次文学再造。
注释
[1]黄子平:《命运三重奏:〈家〉与“家”与“家中人”》,《读书》1991年第12期。
[2]张爱玲:《我看苏青》。
[3]郭小东:《铜钵盂》,羊城晚报出版社,2016,第296页。本文后面所引作品原文均出自此版本,故不再注释,只在引文后面注明页码。
[4](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前言和致谢》,马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5]郭小东在小说“后记”中即提到由于历史久远及过于庞大的家族等原因,“对于家族的历史,从来就缺失一种史的连缀和准确的描述”,因此小说采取了传记小说的通常方法,“真人伪事,或伪人真事,其动机与目的全在尽可能重拾家族的文明史线索,努力寻找可能已然无法确凿的史实,努力接近那个时代的情感及其表述方式。”
[6]关于这方面情况,可参考作者在《题叙》中提供的数字:光绪25年(1899)汕头银庄达60多家,下辖海内外分号775家,国内各县投递局20多处;在水客最多的19世纪,仅在汕头,专门递送侨批的水客有800人之多,香港有200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