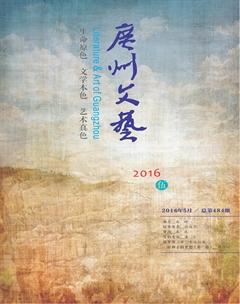一粒种子的梦想(外一篇)
一
不仅她自己,她的父母、老师和同学都认为她是一粒颇具潜力的种子。她梦想这粒种子能觅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在那里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鸟儿在枝头跳跃,树上结满殷实的果实。因为有了这棵树的存在,在不久的将来,那里将变成一座绚烂的花园。
为了追寻她的梦想,那个师范学院毕业的女孩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她要成为“孩子王”,去投入人类最美好的教育事业。可是,现实就是现实,搭载种子的降落伞仅在几秒钟后便改变了航向。那一年,她成了一名警察。
那年的深秋,在入警培训前的那个夜晚,她辗转反侧,整夜未眠。“警察”这个硬朗的名词,变成了活生生的“举起手枪、挡住匕首、追捕抢劫犯、制服杀人犯”等动词短语,电影屏幕中一幕幕足智多谋、虎虎生威的画面更是令她激动万分、难以入睡。而她,一个瘦弱腼腆、书生气十足的女孩子,实在想不出能在警营里做些什么。
第一天到派出所报到,她好奇而紧张。然而,这里和想象中的窗明几净相去甚远,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十几个男人或女人,三四个人一撮,在走廊里或蹲或站,在等待着。几个男人大口地吸着烟,头凑在一起,叽叽咕咕地小声商量着什么,间或有人咳出一口浓痰,吐在丢满烟头的地上,用脚掌来回地搓几下。还不时有人透过门缝向外勤室内探头探脑。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在她背后响起。一个灰头土脸的壮汉被两个警察反扭着胳膊,其中一个警察身上也沾满了灰土,脸上有两缕血痕。显然,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小戏剧。派出所走廊里的气氛有些神秘,让她感到莫名的紧张。
挂着外勤室门牌的那个屋子很小,五六张桌子、七八把椅子便把空间塞满,出来或进去的人不得不侧起身子走。一名中年男子蹲在角落里啃着面包,手腕被铐在暖气管上。电话铃声响起,一名披着警服、趿拉着鞋子的老警从值班室内歪歪斜斜地出来。他迅速地将堆在电话机上的卷宗整理了一下,将电话接起,电话那端传来急促而焦急的声音,老警在本子上快速地做着记录。隔壁副所长办公室紧闭着房门,不时从里面传来几句高声的问话。
教导员领着这个女大学生向民警们逐一介绍,他们放下手中的工作和她打着招呼。那个接电话的老警冲她疲惫地咧了咧嘴,他的眼睛红红的,似乎一夜未睡。
二
种子静静地飘落在这片土地上。耳边是呼啸的西北风,它枕着洁白的雪花,等待春的到来。
她开始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每天骑着自行车,早早地来到单位,为三位所领导的办公室拖地,擦桌子,烧好水,灌满铁皮印花大暖壶。有时还会帮着外勤民警打扫值班室。更多的时候,她会将自己的办公室收拾得很干净整洁,换上挺括的警服,静静地坐在桌前等待陆续而来的群众。
她工作的地方在内勤室。两张办公桌、一排档案柜是内勤室的全部家当。那个办公室只有一扇小小的木窗,光线暗淡,屋里显得有些清冷。
她喜欢静静地一个人看书,或是写日记,累了便透过小窗向外瞭望。经常,满窗的霜花阻碍了她远眺的视线,却让她发现了近处的神奇。霜花变幻莫测,景色万千,有春的浪漫、夏的繁锦、秋的殷实和冬的晶莹。清晨,笔直的白桦树影婆娑有致,繁密的椰树林随风荡漾,清秀俊逸的竹子亭亭玉立。上午,太阳升起,霜花渐渐消融;下午,阳光移走,霜花再次慢慢爬上来,纤柔的水草、飘摇的海藻、怒放的牡丹、绽放的菊花……有时那霜花像玲珑的叶子,丝丝脉络错落有致;有时那霜花像丰满的羽翼,徐徐张开又慢慢收拢。
每当望着这些窗花的时候,她的眼睛亮了起来。她无数次地想起了她上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梦一样的美好时光。这满窗的霜花多像她梦中的那座花园。但更多的时候,她相信着,窗花融尽后,春天来了,她的梦就真的会升发、结果了。
其实,她梦中的花儿正在开放。他们大清早便徘徊在内勤室的门前,等待着她早点上班,把一件件重要的事情交给她去做。她从他们办理的业务中大概了解到他们的家事。他们家有一个小生命诞生了,来她这里申报出生;他们家最近办了一件丧事,老人没了,来注销户口;他们家娶媳妇了,嫁姑娘了,买新房了,考上大学了,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他们喜气洋洋地来她这里办理迁移,有的还塞给她几块喜糖;他们来领取身份证时,她有时会打趣地说:“恭喜你领到一份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她从来没有这样觉得,她的存在会有这样的意义……
她尊重他们,就像对待亲戚一样。他们也尊重她,叫她“同志”或是“姑娘”。他们到派出所一般都很拘谨,就像她第一次踏进派出所一样,用手指梳理几下被风刮乱的头发,扑一扑身上的灰尘,跺一跺脚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将他们用纸袋仔细包裹的喜悦或是悲伤一层又一层地打开,再紧张地盯着自己的指尖,生怕出现什么差错。
她的指尖在键盘上飞快准确地敲打,她知道她敲打出的一个个字符代表什么。她将办理完毕的证件郑重地递还给他们,他们多数会感激地对她说:“谢谢!谢谢!”她舒了一口气,虽然她忙碌了整整一个上午,没顾得喝一口水,上一次厕所,但是她很充实,她又为面前的这些素不相识的人完成了一件他们甚至他们家族的大事。
三
冬天就快要过去了,这粒种子苏醒了。它看到冬雪笑花了脸,春风在一寸一寸地向城市靠近。
种子依然在这个窗口生长着。透过这个窗口,她看到了一幕又一幕人间悲剧。她看到遭遇抢劫的妇女被扎成重伤,鲜血淋漓的现场;她看到面貌忠良的老汉强奸邻家幼女带血的床单;她看到一奶同胞的兄弟因争夺家产打得头破血流仍然还在扭斗的画面;她看到从离异家庭出走、参与盗窃的少年叛逆的眼神;她看到派出所领导终日不得舒展的眉头和民警匆忙而急促的身影……这些画面一次又一次撞击着种子稚嫩而单纯的心灵。有时,那些画面会潜入她的梦中,滴血的尖刀、缠满绷带的脑壳、刺耳的尖叫……电话铃响了,她在梦中挣扎着醒来。
地上积了一层薄薄的轻雪,早春深夜的寒风似乎要钻进骨髓。派出所民警抓获了一个组织卖淫的团伙。五六个卖淫女垂头丧气地靠墙站着,等待她对她们进行搜查。
她在屋里踱了几圈,迟疑着。这是她第一次参与办案,也是第一次接触卖淫女,她不知道该从哪一个开始,从哪里下手。看着这群妇女,她眼前浮现出莫泊桑笔下那个又矮又圆、肥得要滴出油来却让男人趋之若鹜的妓女“羊脂球”的影子。而她们,除了一两个稍显年轻外,其余的都是中年妇女,头发枯干,脸色腊黄,满脸斑点。有的还没来得及穿件外衣,干憋的乳房吊在透明的睡衣里面,若隐若现。一个年纪大些、身材臃肿的女人斜着眼睛偷瞄着她,一副久经沙场、满不在乎的样子。
她戴上手套,向她们靠近。
最后一个被检查的女人瑟缩在墙角,一直用手指抠着墙皮。种子拿起她的身份证,诧异地看着她,还不到十八岁!这粒种子忽然想起自己的十八岁,花样年华的许多片段浮现在眼前:老师的谆谆教导,同学们开怀的笑声,母亲清晨蹑手蹑脚做饭的背影,下晚自习时父亲在胡同口望眼欲穿的眼神……
那个女人低着头喃喃地对种子说:“我是被强迫的……”她脱下羽绒服,内衣斑斑点点,已经分辨不出是白是灰。这个女人清秀俊美的脸庞仿佛已是被霜打的花瓣,枯萎而暗淡。她用手抹了一下斜刘海,黑白分明的眼中滚落两大滴泪水。她用蹩脚的普通话对种子说:“阿姐,我想我妈……我要回家……”她苍白的嘴唇因啜泣而微微颤抖着,她单薄的肩膀突起一层青紫的鸡皮疙瘩。种子给女孩重新披上衣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离开那个窗口许多年以后,她还无法忘记那一天的场面,常常会想起那个被拐骗的卖淫女孩的眼神。那是一粒不幸而卑微的种子,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开花结果?
四
一根细小的根须触到了春天的心跳,种子嗅到了万物复苏的芳香。派出所门前那几颗老榆树吐出新芽儿,麻雀在窗前跳来跳去,蓬松着春天的羽毛。她仰视着老榆树,努力地抽出稚嫩的新叶,一片、两片、三片……
穿上那身深蓝色的警服,她行走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那一年的春天,她离开了工作六年之久的派出所,被调到了分局机关,成为一名公安纪检干部。
她依然像在窗口一样接待来访者。但这些人进来后,个个理直气壮,个个满怀委曲,把一腔怒火向她发来。她给他们倒一杯开水,微笑着倾听;她不在意他们在她面前高声喊叫,有时还和他们一同落泪。
她渐渐学会了与被投诉的兄弟谈心,常常喜欢用“幸好”两个字向他们表述。“幸好,老百姓理解你,原谅了你……”“幸好,你只是触犯了警务纪律,没有触犯法律……”“幸好,你及时改正了错误,一切都不晚,还来得及……”“幸好,你还没有走得太远……”那一刻,她觉得她已经是一位老师,虽然有时也替这些兄弟伤心惋惜,但是,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她有时也觉得是一件幸福荣耀的事情。
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中有的人一意孤行,走得太快、太远,再也回不来了。
她听到一个兄弟的传闻。这位警察兄弟经常和被打击对象纠集在一起,还染上了毒瘾。她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变成那个样子,更希望那只是一个谣传。她找出入警培训结业时拍的照片,站在最后一排高高瘦瘦的是他。他眯着眼睛笑着,笑容阳光而率真。
——直到那一天,她在她的部门看到了他,她再也坐不住了。
她想和他打个招呼,可是她发现他已经认不出她了。他变得又黑又瘦,胳膊像两根竹竿。他显然许久没有理发和刮胡须了,头发蓬乱,满脸胡茬。他疲惫地蜷缩在椅子里,双手无力地从扶手上垂下。他的眼睛失去了当年的神采,像即将熄灭的烛火。他的神情飘忽不定,游离到遥远的地方。他听不到对方的问话,似乎还沉浸在某个情景中回不过神来。当他听到“开除”两个字时,他将眼神慢慢地收回,仿佛时光被重拾回来。他仍旧一言不发,撑起身子,呆呆地挪动脚步,向外走去。
她跟在他的身后,望着他,他醉酒般摇晃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转角处,她的心受到了重重的一击,她仿佛看到一具走失灵魂的躯壳。
种子第一次感到无奈和伤心,就像一阵风吹来,她在风中摇摆着,无望地看着远方。
种子已经长成一棵小树,她像那些大树一样:秋天,摇落一树绿叶;春天,用贮藏了一冬的力量去抽枝吐叶,为粉墨重彩的春天添上一抹动人的绿色。
这一年,她调转到市公安局纪委。这里有更广袤的土地,更肥沃的土壤,是她另外的一个起点。这里更需要深谙文字的人,需要有人总结经验来指导基层,需要有人撰写信息,展示基层工作成果,她承担了那份工作,从此与文字结缘。
她在这里收获了一份安静、一份从容、一份内在精神世界的宝藏。如果说之前她处在一个喧闹的世界,那么现在她是在一个安静的世外桃源。
一位作家说:“不管世界多么热闹,热闹永远只占据世界的一小部分,热闹之外的世界无边无际,那里有我的位置,一个安静的位置。”是的,她找到了一个安静的位置。她在安静中工作,安静中读书,安静中写作,安静中思考。在静谧的白昼,她想起她的战友们用血和汗打赢的一场场战役,想起他们晨昏颠倒的警营生活,想起他们的妻儿心疼的报怨,想起被害人家属企盼的眼神,还有犯错老警悔恨的泪水……这是她的宝石,她把这些经历凝在笔端,透过她的文章,让世人去了解,去感叹。
窗外,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万物安静地接受大自然的安排。在安静中,仿佛时光放慢了脚步。
安静,如同徐徐绽放的花蕾,沉香而雅致,如同秋水中的凝眸,深情而多情,如同天幕中的星辰,深邃而幽远。在那份难得的安静中,她驰骋在思想的草原,插上了想象的翅膀,奔跑,飞翔。
然而,她既不能奔跑,也不能飞翔。她是一棵树,根要深深地扎在泥土,树冠要伸展在天空。她要做一棵常青的树、深沉的树、思想的树、文学的树。葱茏的叶子是她的心路历程,她希望勤劳的鸟儿能衔去编织温暖幸福的小窝。
一转眼间,十八个春秋过去了,种子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春风吹过,她轻轻地摇动树枝,洁白的花瓣雨随风飘落。
哦,一树芬芳,梦想花开。
等风吹来
不怕冷风吹。就在这里,在丁香树下,等你归……
淡妆。米白色滚着荷叶绿边儿的棉麻旗袍裙,平底绣花鞋。一个笔记本,一支笔。对的,就是这种感觉。在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一座幽静朴素的院子里,这样的妆容和那里极为般配。
平底鞋轻轻走过木质地板,静静地,悄无声息。奶黄色的灯光,柔软,朦胧,照亮了巨大的玻璃展柜,沉睡百年的旧时光,在眼前慢慢浮起,游动。
一帧帧照片,一本本老书,一张张旧报,一份份书稿,在百年的长堤中拍打,冲刷,饱经了日晒和风霜,被镀上了岁月的苍桑。
先生,就在我的面前了。
我立在一幅照片前,久久凝视。
那一年,先生28岁,刚刚从日本留学回国。
那时的先生身着洋装,系着领带,雪白的衬衫将他衬托得俊朗洒脱。可是,他的眼神却稍显疲惫,略带一丝忧虑地看着前方,仿佛要将那个无奈的时代看穿,看透。
先生是个孝子。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奉母之命,回到浙江绍兴老家,与大他三岁的乡下女人朱安拜堂成亲。
我无法不寻找她,走遍整个展厅,搜寻朱安——先生原配的踪迹。在众多的展品中,我仅在一张照片中觅到了她的容貌。
长脸,宽额,塌鼻,阔嘴,她相貌平平,身材矮小且目不识丁。
这样的女子,怎入得了先生之眼?
可是,先生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面前,选择了服从。
用先生的话来讲:“在女性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四天后,先生便离开新婚的妻子,东渡日本继续留学深造。
归国后,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教育事业中,极少回家。
而朱安一直独守空房,陪伴着先生的母亲,孤独地生活,直至终老。
试问世间情为何物?先生的回答是:“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然而,那一年,在先生沉寂的情感世界里,却绽放了一朵洁白的莲花。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那个小他十八岁的新式女子许广平,敲开了先生紧闭的心扉,与他结为终身伴侣。
在先生与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的全家福照片中,先生目视前方,没有微笑,神情中却透出安详、幸福。
秋日的天空旷远、幽蓝,北京城少有的晴朗。
午后的阳光温暖、慵懒,微风裹挟着淡淡的月季花香。银杏树缀满了一串串果实,叶片被秋风钩上了金边儿。
从展厅到先生的故居,几步之遥,我依旧轻轻移动脚步。
一只肥胖的花猫在树荫下酣睡,毛绒绒的肚子随着呼吸有节奏地一起一伏。
小小的四合院里,黛墙红窗。先生亲手植下的两棵白丁香树,在九十年的风雨中,依旧枝繁叶荗,旁逸斜出。
轻风抚来,树影筛落一地细碎的斑驳。绿叶微伏,指尖轻叩红漆木格窗门。
风来了,吹过丁香树,穿过窗棂。窗台上,一朵火红的石榴花悄然飘落。
朱安做了一个梦,忽然醒了。她掀起薄被,披上衣服,穿上鞋子,一颠一颠地踱到院中。
透过窗子,她朝婆婆的房间望了望,婆婆还在午睡,发出均匀的鼾声。
她拿起一根木棍,朝搭在树枝上晾晒的棉被轻轻地敲打着,微尘随风四散。
她将几床棉被叠放整齐,码在柜子里,又捧出先生的棉袍子。
棉袍子九成新,新里儿,新面儿,新棉花,是她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可惜先生只穿了几次,刚到春天便脱下它走了。
朱安用粗糙的手掌抚平皱褶。她发现衣襟很显眼的地方烧了一个小洞,她赶忙拿起针线缝起来。
别看她模样不俊,没文化,可做起针线活来却是十里八村的好手。
当初,媒人就是相中了她的巧手和一对“金莲”,凭着三寸之舌将婆婆游说心动,才嫁进了周氏府内。
她咬断手中的棉线,将目光移到自己的小脚上。脚骨卷曲变形,尖如棕子。
这对曾经引以为荣的小脚,却是先生最为鄙夷的,他从未掀起被角看过一眼,更别说碰它一碰。
她轻轻地叹息一声,从床下拉出一只竹箱,里面藏着几双先生的布鞋,双双簇新。两双单,三双棉,底儿都是她一针一针纳出来的。
“南方的冬天阴冷潮湿,北平的天气多好……”她向窗外望了望,决计不离开这里半步。她想不出,走出这个遮风避雨的四合院,哪里还有她栖身之处?
她拿起鸡毛掸子,抚去先生书柜和书桌上的灰尘。笔在,墨在,纸在,砚在,书在,书上的方块字方方正正,藤椅也在,只是那桌前光影轻摇,先生已经许久未归。
起风了,丁香树叶沙沙地摇起,几片黄叶纷飞飘落。墙边一棵枣树枝头结满红枣,噼啪落地几粒。
朱安掂起小脚,将绳子上晒干的衣衫摘下。忽然,她听到门环叩响,急忙颠着小脚小跑着去开门。
门前空空荡荡。只有一阵疾风吹过。
她站在门口,手扶门框,翘起小脚向胡同口张望。
风,吹乱了她花白的头发。她肥阔的裤脚鼓胀起来,犹如她满满的心事和漫长的等待。
等风吹来,风吹来的是先生与许广平的绵绵情话。
等风吹来,风吹来的是后人的声声叹息。
……
一阵微风吹来,一粒红枣落在那只猫咪的身上。它伸了一个懒腰,眯着金黄色的眼睛。我向它招手,它便踩着款款的猫步靠近我,在我腿边蹭来蹭去。
阳光渐渐西斜,先生故居的灰色屋檐上,几根野草抽出了毛茸茸的穗子,微微点头,聊着它们经年不变的话题。
仰视那棵参天的枣树。稠密的枣子将枝条压低,缀弯,可它们仍旧顽强地向着空中,向着四面八方,向着下一个春天生长,向着岁月深处伸展……
责任编辑 梁智强
韩秀媛:全国公安文联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