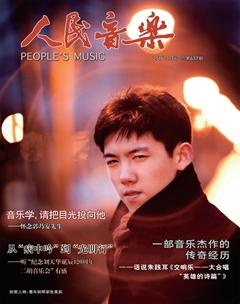对音乐家口述资料采录的迫切性及相关问题
过2015年度的系列采访与汇编,本人于今年年初终于结束了对音乐史学家冯文慈(1926—2015)口述资料的整理。{1}这项看似简单的工作实际涉及到了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与采访、记录、汇编直接相关的知识问题、技术问题已随着课题的进行而同步查阅、咨询并予解决,所涉及的更深层次的相关话题拟于此简要论述。
一、对音乐家采录的价值与紧迫性
本人所完成的“访谈录”虽然是针对冯文慈先生的个人采访,但其学术意涵实则指向所有“冯文慈们”——共和国成立前后所培养、成长起来的一代音乐家。这代人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音乐界的骨干或曰“脊梁”,他们更有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这代人中的多数,曾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与苦难,完整参与了20世纪中期因新政权诞生而需的音乐文化的创建、复建;在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的艺术造诣与积累又影响甚或主导了世纪之交音乐领域的大发展。如今,这代音乐家已因岁月的销蚀、身体的衰弱,逐步在告别现时乐苑、学界。客观地讲,这个群体无疑就是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音乐艺术体系构建的化身,是一笔难于重现的沉甸甸的艺术财富。
犹如本人对冯文慈先生人生历程、艺术历程的理解——见证过京城多所艺术教育、科研机构近七十年的发展,接触了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不止一代众多音乐家的音容笑貌;而在本人从事对他的采录课题之时,他已然89周岁的高龄,长期病患的折磨使他的身体虚弱不堪;更加令人唏嘘的是,在采录阶段的工作结束一周后冯先生即发烧住院,与病魔抗争二十多天后与世长辞。此情此况,典型性地印证了这项专题采录工作所具有的价值及刻不容缓的“抢救”意味。但回顾中国现代历史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社会环境、人文理念以及传媒技术程度,使得这批在当时处于盛年的音乐家的艺术成就、艺术理想、人文思考、历史足迹难以得到合式而充分的记录与“书写”;80年代之后随着上述客观情形的改善,这批音乐家又多因高龄、体衰从岗位离退休,逐步淡出了公众视野。因此,对于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发展历史、音乐艺术的演化,对于音乐家个人的艺术历程来说,及时搜集、记录、研究、保存这批“一手”的“活态”资料,应该成为当下音乐界、音乐学术界十分重要的一项使命。
当然也不能否认,近些年来社会对于老一代音乐家的关注、关爱有了很大改善,对这个群落包括民间音乐家相关资料直至口述资料的搜集、整理已有所重视。不少院校、机构在富有成就音乐家80岁高龄之后的重要日子多举办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借以回顾、总结、表彰、弘扬老一代音乐家的艺术成就和贡献;一些院校还组织了诸如艺术家档案式的资料搜集、刊印,以期逐步建立起规范的艺术家“档案库”;部分研究者开始以老一代音乐家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专题性质的个案研究。所有这些举措或学术构想,都说明这些饱经风霜音乐家们所具有的艺术价值、学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价值正在得到世人的愈加高度的注目。但怎奈岁月无情,经历了20世纪波澜壮阔文化变迁与音乐发展的老一代音乐家的现状非如闲庭信步那般从容——粗略回首2015年至2016年初的音乐界,像冯文慈这样所历所感丰富且匆匆别离我们的音乐领域的方家马革顺、黄晓同、周大风、洛地、郭乃安、于润洋、金湘、阎肃、周小燕……这些均已耄耋甚至百岁高龄的音乐家的驾鹤西行,似乎已使得这种“抢救”工作的紧迫感骤升。
以自己的亲历来说,中央音乐学院曾于前些年(约2013年)启动了“老艺术家档案”搜集、整理的院内科研项目,鼓励音乐学系在读的本科生、硕士生在导师的辅助下对本院已故或健在艺术家进行档案资料的搜集。本人曾率先“认领”了蓝玉崧、金文达两位已故先生的档案搜集任务。其中,张绎如同学(2009级本科生)经过半年多的翻查各类资料、人物访谈与阅读学习,除了完成指定的人物大事记、艺术年表、资料搜集归类之外,尚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两万多字的学士学位论文《蓝玉崧先生及其在教育教学领域的贡献》(此文在2014年11月份结束的中国音乐史学会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中获得“学士组”二等奖),文章的精选章节刊登于学院的学报。{2}张茜同学(2010级本科生)随后接受了对于音乐史学家金文达的档案整理,历时一年半的辛劳,除了完成课题必须的资料搜集、归类,亦完成了约三万字的学位论文《金文达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领域的贡献》,而她先期所撰写的文章《〈仁智要录·春莺啭〉的中国音乐遗存——兼谈金文达的“日本雅乐”研究及其他》则获得院内举办的“王森基金论文评选”(2014年度)的三等奖,再获第八届全国高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学士组”二等奖。音乐学系内其他多位老师指导一批同学先后完成了十多位艺术家的档案搜集与初步研究。但是,即使由这种规模化的资料搜集行动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难掩广泛的全国性的“抢救”乏力的尴尬;况且,以在学的学生群体为主的资料搜集能够达到怎样的学术成效,也是值得观察与再思考的。
二、谁来采录?采录什么?如何采录?
重视并加快搜集、整理、研究、保存老一代音乐家艺术资料(含口述、音像、文本、图片、实物等)的工作,不应该只是个别音乐学术研究者、甚至只是更小范围的从事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研究者的“分内事”,这种仅仅期待有限专业人员介入的心理“预想”将使工作更加被动而缓慢。那么,这样一项带有抢救性质的紧迫工作由何人来完成呢?——应该在音乐界各个机构的支持与襄助之下,由音乐界内外所有怀揣艺术梦想并富有科研探求意识的人群共同而为。
这样的表述并非在提倡“全民科研”。我们仅以单纯的采访者和被访者两方参与者的角度来看:采访者专业身份的不同,所关注事项的范围与深度就有所不同,而不同专业背景的采访者将会有不同的探求话题和采访收获;被访者虽然是固定的人群(音乐家),但作为艺术、思想、见闻积累丰富的老一代音乐家群体来说,他们将会因跟随采访者的不同引导,“迸发”出不同的火花。尤其对于当今从事表演艺术及创作领域的从业者、从学者来说,常常受困于科研的压力,不少人士为科研的选题而愁眉不展。但同样在于这些领域,许多艺术积累丰厚的老一代音乐家本身就是一项可以多维度、多层次展开的研究课题;对于与之专业相近的中青年音乐家群体来说,选取这样的“研究对象”无疑是多利之举。
在记录手段、传播交流方式日益多样化、便捷化的当代社会,开展音乐家口述资料的采录工作不再是传统的现场录音加文字速记,采录的方式与手段可以采取多样化的方式进行,融录音、录像、拍照、文字记录等种种形式于一体,还可以通过电话、网络视频等形式做远程的采访。
对于采录的内容,则完全可以根据采录者的科研构想、传播需求或者课题要求,与被访的音乐家相协调。以音乐艺术、音乐学术的专业特点来说,应该主要体现在艺术理念、音乐技法、人才培养观念及方法、所历所感的艺术事象、个人生平等方面。从近些年各类机构与个人所完成的具有口述资料性质的成果形态来看,基本无出其类。
需要指出的是,口述资料的采录与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项具有相当学术、技术难度的系统工作,采访者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资质和学术积累,且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前期准备;音乐界工于此域的人士提出,对于口述资料的采录来说,采录者所持有的音乐观和音乐文化认识论,最终将决定这些口述资料的内容取向,可见采录者的重要地位。{3}对于受访者来说,则因多数年事已高,不宜频繁接受各种形式的访谈、采录。因此,有计划、有准备、科学化、系统性的采录工作就显得异常重要。而这种富有规划的采录行为的实施,则需要结合老一代音乐家所长期从事的各专业领域内现有专家群体的力量,将之与各专业方向自己的艺术发展、规律探寻、历史研究、人物建档相结合、相统一;假如由各专业机构或专业协会做出统一的宏观规划与组织协调,无疑将会使采录、整理工作更具秩序与条理。总之,站在更高的认识平台切实重视并加快对于这代音乐家的学术“抢救”,应该被音乐界、学术界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三、关于“口述史”与“口述资料”
由以上的话题,不能不牵出“口述史”的相关问题。“口述史”的概念及其事项呈现于中国音乐学术界是相对晚近的事情。{4}但今日音乐界“口述史”所欲反映的学术内涵、所欲实现的学术目的,则在中国历史学领域久已有之且久已实践之,甚至可称其始终伴随着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演进。先秦时期史官的记事以及由此而成书的早期史著,无不具有“口述史”的背影。只不过恰如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因时代的不同、治史观念与目的的不同,对“口述”资料采集、应用的方法也会不同,但作为基本的入史形式与原则——口述、采录、纪实则是相通的。因此,对于今日学术领域让人感到学科新起而躁动的西方“口述史”(Oral history)理论,应该多些审慎的思考。
以笔者愚见,仅就当下“口述史”“口述史学”之说,我们应该首先站在历史学的基本立场上做出一些审视:第一,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学的基本治学方法是什么?第二,假如“口述史”成立,历史学又是什么、又该如何类分?
对于第一项设问,无论以怎样的观念来认识,对“历史学”内涵中的主观性体现都是无法摆脱的,即“历史学”是因历史学家治史行为的融入而写就的文本。这种由人的主观行为的参与而著成的关于过往历史的文本,必然借助种种方法的应用而达成,即必据今之所谓史学“方法”。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还是西方的历史学,历代的史家无不费尽心机为笔下的著述而探寻合式的方法,是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目的,“口述”材料的应用就是中西史学界自始至终在应用的基本的治史方法。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广博考据文献且“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就是在大量借助对文本材料考据的基础上又融入了实地考察与“口述资料”采录的方法,这些早已成为史学界治史的楷模。这种对于史料(当然包含口述资料)的广泛搜集、考订、应用,也成为历史学科研究的基本治学方法。
第二项设问中的“口述史”问题,是西方学术界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传统的史学观得以颠覆的产物。“研究领域的扩大带来了研究方法的改变,旧史学囿于官方文献的传统方法再也不能为新史学提供足够的史料,这样,史学家们不得不借助社会科学和其他学科方法来还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图景,于是口述方法同计量方法、系统比较方法、心理分析方法一起受到了重视和应用”。{5}由此,“口述史”便首先在美国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与传播。这种发展势头也蔓延到了具有古老史学传统的中国。那么,作为历史记载形式(文献、实物、口述)之一的口述资料(即“口述史料”),能否舍弃其他史料形式而单独成史?自身尚需广泛借助文本资料及治学方法且以文本形式体现的“口述资料”若可称“史”,历史学又是什么?历史的其他记载形式及历史学的诸多研究方法又该如何称谓?
其实,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交往中,源自于西学的学术流派或学科方法纷繁多样,中国的学者和学子也在拼命汲取着营养,问题是真正应该汲取的是什么?汲取到何种程度?自己应该做出些什么?对于此等困扰中国学界的“老话题”,长期旅居海外的周勤如先生曾通过对安波这位从延安土窑洞走出的“音乐工作者”在半个多世纪之前所著成果分析之后指出:“安波在音乐学方面的超前意识并不亚于后来的西方民族音乐学大师”,“他懂得了道理,就立即起而行之,能找到纷乱头绪的关键,并迅速建立起适于特定研究对象的逻辑体系”,“当代音乐理论家……如果时至今日,仍不能像安波那样脚踏实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或者干脆主张全盘西化、根除传统,前途就实在堪忧。如是,高喊再多的‘乐教复兴、‘登昆仑之巅吹黄钟大吕也恐怕是南辕北辙”{6}。此言可谓振聋发聩,也极具警示与思考价值。
就当前音乐界的“口述史”理论来说,如何既注重“书写人民的历史”、注重微观历史的书写,又能继承传统史学、中国史学的丰富宝藏,使当代学问家所著的成果体现出“优势互补”,如此方显出当代中国音乐理论家继往开来的国际化视野的纯熟融合。
{1} 该课题自2015年1月开始筹划、前期准备,4月初开始实地采录,7月初采录结束进入后期汇编、整理,2016年1月份完成24万字的《音乐学人冯文慈访谈录》书稿并交付出版机构。此书稿将由中国音乐学院科研成果项目资助,于2016年春夏之际出版。
{2} 张绎如《蓝玉崧先生在专业音乐教育领域的贡献》,《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
{3} 单建鑫《论音乐口述史的概念、性质与方法》,《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
{4} 对此问题,臧艺兵、单建鑫等曾有较为全面的介绍和完整的归纳,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详见臧艺兵《口述史与音乐史:中国音乐史写作的一个新视角》(《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单建鑫《论音乐口述史的概念、性质与方法》(《音乐研究》2015年第4期);2014年9月24—25日,由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全国首届音乐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数十位学者围绕此域问题也曾展开专题研讨;还有一批中青年学者结合“口述史”的理念和方法,面向民族民间音乐、现当代音乐已展开了一定的课题实践。
{5} 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特点及对我们的启发》,《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6} 作者于2015年12月19日在中国音乐学院主办的“纪念安波诞辰一百周年暨中国民族音乐教育体系建设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后修改定稿;详见周勤如《自觉·自为·自信——从三个实例看安波的创造精神》,《音乐研究》2016年第2期。
陈荃有 博士,中央音乐学院编审,石河子大学“绿洲学者”,《音乐研究》副主编
(责任编辑 金兆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