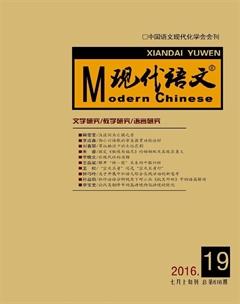从“大中国主义”到“文学国度的子民”
摘 要:由于出身眷村,眷村在朱天文小说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题材。从最终描写和谐融洽、充满温情的眷村生活,抒发将中华民国作为“永生恋人”的赤子之情,到渴望逃离眷村的梦魇,投入大都市的怀抱之后顿感困境重重,再到在全球化的背景里讨论物与人的关系,朱天文的眷村小说始终探讨着族群的身份认同议题。
关键词:眷村小说 朱天文 身份认同
眷村是国民政府迁台时为安置军人及军眷所建设的简陋房舍。作为眷村第二代,眷村小说是朱天文早期创作的重要分流,虽数量不多且均为短篇小说,但其《子夜歌》(1982)《伊甸不在》(1982)《小毕的故事》(1983)《童年往事》(1985)《世纪末的华丽》(1990)等作品可以说是眷村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青年时期的朱天文与其妹朱天心等一干同仁创办《三三集刊》及三三书坊,早期创作深受胡兰成影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礼乐充满了一种浪漫诗意的憧憬和怀想。大中国的传统文学观与身为眷村族群的大中国意识相互作用,使得朱天文早期创作既豪情满怀,又细腻旖旎。在收入散文集《淡江记》的《我梦海棠》中,朱天文感慨:“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是只向中华民族的江山华年私语,他才是我千古怀想不尽的恋人。”在《之子于归》中更是深情喟叹:“那三月桃霞十月枫火的海棠叶,是我们永生的恋人——哪一天,哪一天啊,才是民国的洞房花烛夜?”
《子夜歌》作为朱天文“三三”时期的眷村小说创作,也充溢着绮旎细致、温情绵绵的意蕴。小说篇名取自乐府标题,展现出一幅古典田园牧歌的美好景致,正与主人公童稚视角所看到的风雅静谧的眷村生活相和。然而从深层意义上来看,篇名的古典隐喻与作品的内容并无实质性的联系。与《子夜歌》一同被收入《传说》小说集的其他作品,如《青青子衿》《扶桑一枝》《春风吹又生》《腊梅三弄》等皆用篇名营造了一种可以独立于小说内容之外的古典唯美风格。毫无疑问,朱天文是在借助题目的古典隐喻来抒发她的大中国情怀,以及明确她传承传统的文化身份。
从内容上看,朱天文早期的眷村小说仍不脱家长里短、试图再现眷村图景的模式。《子夜歌》写丁家上校退役做起了生意,红门紧关,很少与外人来往;杜妈妈家有七个孩子,穿同样衣服浩浩荡荡如同七仙女;小金父母不合,她常孤身在家,金妈妈与人偷情,在菜市场被人打,后来在眷村晚会上浓妆艳抹登场高歌,引得村民纷纷侧目;还有“我”家,妈妈在家织毛衣或者做小天使补贴家用,“我”和姐姐去小金家串门,跟小哥哥看金色的青蛙,家人晚上一起吃西瓜,点点滴滴全是温情暖意。再有《叙前尘》以朱天文的父亲朱西宁与母亲刘慕沙为原型,讲述外省军人与本省女子的爱情奇缘。《这一天》则写父亲的战友们齐聚一家、欢聚一堂的场面,展现了父亲与生死之交们之间的浓浓情谊。
《小毕的故事》虽创作于同一时期,但与上述小说在主题上呈现出较大的转变。虽背景仍旧设置在眷村,但朱天文将关注焦点由眷村第一代转移到了眷村第二代身上。以此为起点,朱天文的眷村小说逐渐开始关注眷村第二代在成长中面临的叛逆与逃离、苦痛和迷惘。小毕就是这样一个桀骜不驯的眷村少年,他是母亲在工厂打工时与已婚的领班的私生子,为更好地照顾他,母亲嫁给了外省军人毕伯伯。他从儿时便调皮捣蛋,进入国中学抽烟,跟人打架,和不良少年纠缠不清。国三时偷了毕伯伯为他准备的学费去交朋友,被毕伯伯打时叫道“你不是我爸爸你打我”,母亲失望难堪至极开煤气自杀。此时的小毕才幡然醒悟,考入军校,以“中华民国空军中尉军官”的身份重获新生。从这个结尾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出朱天文纯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及爱国情操。
创作稍晚于《小毕的故事》的《伊甸不在》虽同样聚焦于眷村少年的成长,但朱天文全心全意将中华民国作为永生恋人的想法渐渐退去。省籍矛盾初见端倪,而朱天文也已度过天真烂漫的少女期,开始关注严肃的政治议题,像《子夜歌》《扶桑一枝》此类借助文化上的大中国主义来消解本省人对眷村族群身份质疑的做法已经失效。此时的朱天文开始像《世纪末的华丽》中的甄素兰一样,在身份的变换中质疑自我。
甄素兰生活在父亲拈花惹草、母亲疯癫痴狂、姐妹感情淡漠的家庭。她痛恨破落的村落,渴望逃离不幸的家庭,却悲观地发觉,“没有用,是她母亲的永远还是她的,连这个家,这个村子,连甄大民,烧成了灰,化做了烟,还是她的”。这或许也是朱天文的心声,当自己动辄被贴上眷村第二代等同眷村第一代、等同国民党外来政权以及既得利益阶级的标签时,当所写的眷村经验被认为是不属于本土经验,而不符合乡土文学论战的标准时,朱天文便是这样地愤慨作答。十几年眷村生活深入骨髓,烧成灰、化为烟,仍流淌在血液之中,她并不能逃脱。
终于以演艺明星“甄梨”的身份走出眷村,甄素兰离开家庭,开始了新的生活。当出演的影视剧红透半边天时,她又具备了另外一重身份——影视剧中她饰演的角色“戚双红”。虽然甄素兰想借助“甄梨”和“戚双红”来脱离封闭的眷村,然而她想与外界“没有边界”,想彻底融入本省的生活却是无法达成的心愿。离开眷村之后的生活,甄素兰却感觉“总总不切身”。尤其当她看到她的情夫——已婚的乔樵全家笑颜合照时,一直以来的情感寄托垮台,她开始怀念眷村的日子。“她想起从前眷村的日子,很多很多,不一定是快乐甜蜜的,可是都是自己的。再坏,再不快,悲伤的眼泪流下来都是自己的。”[1]绝望虚无之下,甄素兰悄无声息地走上了割腕自杀的道路。朱天文以“甄素兰”“甄梨”“戚双红”作为小节名,将整篇小说看似清晰地切分成三个部分,然而游移在多种身份之间的甄素兰却在这种变换中渐渐迷失了自我,陷入莫名的恐慌和虚无中。对她而言“伊甸”究竟在何处呢?是曾迫切想逃离却切身属于自己的眷村生活?还是期望中与外界融为一体的都市生活呢?不管“伊甸”意义为何,曾经的,或是期望中的,都再也不存在了。
相较甄素兰的恐慌虚无,朱天文在《伊甸不在》三年后创作的《童年往事》中展现了眷村第二代开始脚踏实地地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开辟自己的新天地。绰号为阿哈咕的何孝炎回首童年往事,厮杀打斗、结交地痞、留校查看、双亲病逝、外出求学,一幕幕过往如梦如幻,让他不由感慨,“不知什么样的因缘,将他风从云,影随形,花树自开水自流,将他推化到今天”[2]。他们的长辈不曾想到“在这个最南方的土地上死去了,他们的下一代亦将在这里逐渐生根长成”[3]。 “生根”这个词意味着朱天文切实让笔下的人物扎根到了脚下的土地上,而不再抱着浪漫的绮思活在飘忽虚无里。值得注意的是,《小毕的故事》以小毕考取空军抹平其放浪形骸的曾经,遵循的依旧是“哥哥爸爸真伟大”“当兵杀共匪”的逻辑,到了《童年往事》,朱天文的政治认同有了相当大的转变。在《童年往事》中,当收音机广播副总统陈诚的丧礼时,阿哈咕正在士官俱乐部玩撞球,被士官要求肃静时推开老士官,并与玩伴们逃出房子,还捡来砖头将玻璃窗打破。在这一叛逆的行为背后,朱天文对国民政府反攻神话及台湾当时政治体制的批判隐隐可见。
朱天文创作于80年代末的《世纪末的华丽》可以说是《伊甸不在》的升级版,模特米亚与影星甄素兰同出身眷村,一个拥有情人老段,一个拥有情人乔樵,其对生活的虚无飘渺感也是如此相像。但不同的是,朱天文在《世纪末的华丽》中将故事重心由主人公眷村的成长背景转移到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在营造堪称颠覆性的都市景观的同时,也使得米亚的心境在与眷村的联系之外上升到人类普遍化的高度。
《世纪末的华丽》小说情节性不强,雪纺、乔其纱、绉绸、金葱、纱丽等布料,冰白、透青、纤绿、虾红、鲑红、亚麻黄、蓍草黄等色调,薄荷药草、白兰洗衣粉、刮胡水和烟、肉桂与姜、乳香等气味,印度风、中性化、洛可可风、复古风、未来风等时尚潮流组建起了米亚的整个世界。香气刺激嗅觉,嗅觉激发记忆,记忆联系潮流,米亚用感官直觉感知世界的方式构成了整篇小说的逻辑。朱天文颠覆性地大量堆积色彩、布料、香味等符号,使得小说主体内容空洞无物,正是借助这种方式,她将现代人对符号、对物品品牌而非实体本身的过度追求——亦即商品拜物教展现得淋漓尽致。
80年代末,解严之后的台湾社会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商业化、都市化的泛流侵袭着人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先进与落后并存于同一空间,时空仿佛被压缩,凸显出荒谬与虚幻之感。生活于其中的年轻人一方面“人生在世须尽欢”,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另一方面在不受控制高速发展的社会中,又恐惧眼前的欢乐时光转瞬即逝。正如王德威所说,“欢乐在正式开场之前其实就已经结束,任何期望都只是一种变调的怀旧甚或对怀旧的奢望。深不可测的绝望和无法满足的欲望竟是一体两面。台北在末世忧郁和及时行乐思想刺激下,染上了世纪末综合征。”[4]《世纪末的华丽》写的正是这样一群以醉生梦死逃避现实、放逐自我的年轻人。他们耽溺于午夜狂舞,车开上阳明山,在草地上尽情狂欢。这种表面洒脱飒爽的行为,其实背后暗含着对现实的惶然和对未来的不安。米亚却略有不同,她以自己的嗅觉、视觉记忆活在感官的经验里,以此来反抗理性与制度建立起来的世界。朱天文在小说结尾写道:“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建。”以怀旧、记忆、感官来抵抗理性与制度,这或许是朱天文拒绝掺入政治、拒绝身份表态(是心系中国还是台湾)的一种表达。
值得一提的是,《世纪末的华丽》虽被视为眷村小说,然而主人公米亚的眷村身份不再被凸显。朱天文文笔犀利地写道,“这才是她的乡土。台北米兰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结成的城市邦联,她生活之中,习其礼俗,游其艺技,润其风华,成其大器。”在商业化、都市化、全球化愈演愈烈之下,被米亚视为乡土的并不是贫屋陋舍的眷村,而是相差无几的大都市邦联。家国的畛域在不断地扩张,无限外扩之后几乎虚化不存,而生活于全球化浪潮之中的个人主体性也被不断地消解,在丧失自由与创造力的同时,被异化为相差无几的“个体”。个人的独特性消失了,族群之间的差异以及所谓的身份认同便成为一个伪命题。直到发表于1994年的《荒人手记》,朱天文借用同志的边缘化身份来隐喻自我,“我终于了悟,过去我渴望能亲履之地,那魂萦梦牵的所在,根本,根本就没有实际存在过。那不可企求之地,从来就只活于文字之中的啊。”于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天文彻底排斥了地理、历史、政治、族群等因素,作别眷村的童年往事,作别眷村族群,将自己看作是文学国度的子民,此后便专注地在这片国度上开疆拓土。
综上所述,朱天文早期眷村小说《子夜歌》《扶桑一枝》《叙前尘》《这一天》等多描写眷村里林林总总的邻居、和谐美满的自家生活、父亲与战友的浓情厚谊。以《小毕的故事》为起点,在《童年往事》《带我去吧,月光》《尼罗河女儿》《世纪末的华丽》等小说中,朱天文聚焦于眷村第二代的成长主题。这些眷村少年或已经扎根于台湾的土壤,或仍旧无法融入眷村外的生活从而质疑身份、迷失自我。由于省籍矛盾初见端倪,政治格局也在悄然变化,在这一阶段的创作中,朱天文不再用古典诗意的标题及风雅韵致的语言来表现对大中国主义的文化观的拥护,也渐渐退去将中华民国作为永生恋人的浪漫绮思,转而开始批判国民政府的反攻神话及政治体制。解严之后,朱天文将眷村小说的背景外扩至现代大都市,或者以商业化消解个人的独特性,以世界性消解族群议题,或者自称“文学国度的子民”,在文学中构建乌托邦,以此拒斥地理、历史、政治、族群等因素,同时也为自己的身份认同创作主题画上了一个句点。
注释:
[1]朱天文:《炎夏之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2]朱天文:《炎夏之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3]朱天文:《炎夏之都》,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3页。
(张文婷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