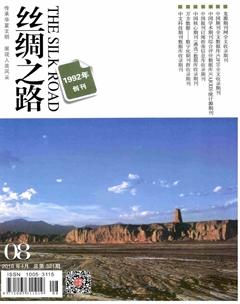老庄思想与中国现代陶艺
袁炯
[摘要]大而空的人文思想不足以支撑起中国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最需要的是一种具体的人文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之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游离于传统与当代艺术之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在帮助解决现代人的思想困惑和指导中国现代陶瓷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能够提供重要的参考思想。如老庄思想以自然为美,在言、象、意的认识取舍上为中国当代陶艺创作提供独特的审美视角。在庄子看来,天地万物本为一体,传统与现代也本为一体,当代人与其在现代陶瓷艺术中困惑挣扎,做无病呻吟,不如学庄子“乘物以游心”。
陕键词]老庄思想;中国现代陶艺;传统与现代;自然美得意忘象
[中图分类号]J3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6)8-0050-03
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步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直到上世纪末中国现代陶艺仍普遍追随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由于对中国现代陶艺这个新生事物缺乏深入和系统的了解,以至于当时各大院校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现代陶艺作品,不仅令人啼笑皆非,某些恶搞行为更加重了人们对所谓的现代陶艺的质疑。其实现代陶艺并不神秘,它是陶瓷艺术在经历了传统陶瓷艺术高峰之后出现的一个崭新的阶段。相对于传统陶瓷艺术的审美法则,它的现代性表现在对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尊重,从而使当代陶瓷艺术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生命力。虽然相对于传统陶瓷艺术,现代陶艺在审美与价值观上有着颠覆性的区别,但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哲学思想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也为两千多年后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因此对中国古代传统陶艺语言的追溯和对中国现代陶艺语言的探索并不矛盾,对中国当代陶艺语言的时代表现更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层挖掘。
事实上道家的老庄思想博大精深,其思想体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哲学和智慧而存在,还是一种为古人广泛接受的艺术审美思想。历史上,被誉为“汝窑为魁”的汝窑瓷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传统陶瓷艺术的最高成就和最为正统的汉民族士人的艺术审美,便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结出的硕果。道家思想以“道”作为至高存在,充满了朴素的自然主义情怀,它让人快乐地享受当下,物我两忘。庄子说:“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一种朴素的以自然为美、注重内心修炼的审美情怀。正是汲取了这种超拔而灵秀的思想,才有了宋瓷的沉静、含蓄、内敛、典雅的审美高度,同时也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陶瓷艺术高峰。当然,当代陶瓷艺术无需再刻意重复宋人的老路,宋瓷的文化高度也只是对老庄思想冰山一角的理解和诠释,当代人理所当然应该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更多的与现代陶瓷艺术理念相契合的思想交集。
之所以认为老庄思想为两千多年后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预留了足够的空间,需要我们对道家文化中的老庄思想进行较全面的了解。我们会惊奇地发现,道家文化中的老庄思想与现代陶艺中的艺术思想理念有着惊人的暗合,在很多方面完全能与两千多年后现代人的审美理念产生共鸣。道家思想对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启示超过了老庄文化对人类其他方面的影响,而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发展其实非常需要道家文化作为它的指导思想。
老庄思想以“道”为至高存在,展现宇宙视野,并努力论证道的内存性。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这个“大美”,在庄子看来应该是尊自然为美。道的内存性决定了天、地、人乃至万物的运作都离不开这个“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道,既然自然美符合“道”,那么人为地设置美的法则和条条框框则有违于“道”。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也说:“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于外饰。”意思是说我们追求的道,就是返璞归真,我们追求的理不用任何装饰。这与老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既然这种“见索抱朴”的美早已在中国文化中深入人心,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艺术形式中,那么在现代陶艺创作中我们是否更应该能够容忍泥性在高温中的自然展现,釉在窑火中的恣意放纵,烟熏火燎中产生的窑变甚至脱釉、气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共同作用成就了陶瓷艺术的魅力,传统陶瓷艺术更关注釉色(即金)的表现潜力,现代陶艺更侧重土(代表智慧)、火(代表激情)、木(代表灵气)的艺术表现潜力。传统陶瓷艺术审美是相对单一的,而现代陶瓷艺术审美是多元和综合的。
老庄思想模糊了美与丑、高与下、善与恶、难与易的界限,指出了它们的相对性,这事实上为现代陶艺拓宽、发现美的新元素提供了理论依据。老庄思想并不刻意去直视、深究事物的美丑,而是侧重从宏观上探讨人类社会的立身之道(包括了治国、处世、养生等思想),而这种世界观恰恰是古往今来艺术审美的人文基础。庄子笔下描写了许多如支离疏、叔山无趾、申徒嘉、王骀等奇形怪状的人士,他们或形态佝偻,或残肢断臂,在社会中绝对属于被忽视的群体。但是庄子笔下,他们善良、勤劳、乐观、豁达,且生存往往具有常人不具备的优势。庄子笔下的人物看似违背常理,实则正是道家思想睿智的独特所在。老子曾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故有无相生,难易想成……”可见在老子看来,美与丑、善与恶实为逻辑关系,双方皆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如果其中一方不存在了,另一方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老子看来,所谓的美与丑实质上是人为的赋予,受到社会、宗教、民族、地域诸多强制,其实质存在严重的思想偏见。这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文明人从生到死都摆脱不了奴隶的偏见”思想暗合。在唐代陶瓷领域南青北白的对峙格局中,陆羽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若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则茶色绿,邢不若越三也。”在今天看来,茶圣陆羽对青瓷和白瓷的褒贬恐怕也有许多的偏私和牵强,这种偏私和牵强正是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哀叹的原因所在。总的来说,老子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体现的所谓“美”,并不彰显于事物的外相,而是存在于人的精神与自然生命和谐共融的逍遥之中。很显然,如果说道家思想中有“美”这个概念,那么这种“美”是藏起来的,是站在“得”的对立面。在道家看来,物质的东西甚至自身肉体成为寻求这种境界的“大患”。而这种精神境界正是当代中国现代陶艺家所缺乏的。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去一味表现特定的主题,或者为了美而表现美,为了某个庸俗实用目的来表现,皆不符合老庄思想中“知忘是非,心之适也”的无功利思想。所谓“情动于衷则形于言”,现代陶瓷艺术创作应该是有感而发。
老庄思想充满了朴素的自然主义情怀,对具体的“器”给予了应有的肯定和尊重。相对于儒家强调的所谓“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老子把“形而下”的“器”上升到了一个哲学的高度,并且还详细描写了两千多年前陶的制作过程。老子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从这里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最原始的陶具在练泥与成型上与21世纪的现代陶艺区别之大。相比传统陶艺,现代陶艺追求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更注重对材料个性与潜能的自然表现和挖掘,这正是对庄子“莫之为而常自然”在艺术表现中的最好诠释。
老庄思想为两千多年后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方法论。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无穷”,这些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问题、观察事物的独特视角。现代艺术从模仿自然一路走来,从视艺术为双重欺骗到视艺术为复杂形式,再到视艺术为符号,到视艺术为观念或视艺术为境界……从古希腊到近代东西方,美的不断嬗变也提醒我们,现代陶瓷艺术是一种开放的艺术,它的生命力正是它的开放性所在,它的艺术生命不应该仅仅属于当代人,也应该涵盖过去和未来,不应该只属于西方人,而是属于全人类。现代陶艺不应去简单地追求所谓的完全形式,应该重新审视烧成过程中由于不为人所控所留下的所谓缺陷、遗憾,把更多的念想留给一个远离当代世俗价值观的世界;不应该去尝试过多地去干预作品在窑火中变化,应该允许更多的鬼斧神工在不为人所控的自然窑火中雕琢而出。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自然能够生产出更多整齐划一的陶瓷产品,但是不应该成为现代陶瓷艺术的人文终结,更不应把现代陶瓷艺术引进封闭的死胡同。留一片空白给神奇的大自然,给躁动的情感,给干燥或湿润的灵魂,留一片忐忑童真的心灵与炙热的火焰在千年的古窑中共舞。现代陶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陶瓷艺术不能丢失浓厚的人文思想,不能淡忘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沉淀。虽然现代科技与现代陶瓷艺术不矛盾,但是人文思想才应该真正成为现代陶瓷艺术生存的“氧气”。不能批量生产不是现代陶艺的不足,恰恰是现代陶艺坚持人文思想的重要方式。保存一份人类应有的敬畏给神奇的大自然,也是我们从事陶瓷艺术创作者应有的品质。
现代陶艺的创作对艺术作品的思想酝酿应该越单纯越好,这倒是很需要庄周梦蝶那种“与天徒”的境界。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思想越是远离急功近利越能在作品中超凡脱俗,人类的贪婪、偏私、浮躁和一切不切实际的欲望,都需要艺术工作者在每天的悟道中逐一摒除。“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不厌其烦地强调内心修习的重要性。事实上,现代陶瓷艺术已承载了现代人太多的思想包袱,它承受了现代人对当代社会物欲横流的困惑、无奈、痛苦和彷徨……这是否就是庄子笔下的“顺而不一,安而不顺”的渐趋思想堕落的状态呢。人类无止境情感泛滥,用老庄思想看来会加重对观者的思想困扰,老子说:“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庄子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现代陶艺不应该作为承载太多当代人思想挣扎痕迹的角斗场,语言应消融于形式,形式应消融于意境。庄子一生都在感叹“吾安能得一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几百年后南北朝王弼的“得象忘言”,“得意而忘象”,更像是在与高处不胜寒的庄周对话。王弼认为:“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可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可以存意,得意而忘象。”意思是说无不能自明,必须通过天地万物才能了解,也就是“意以象尽”、“寻象以观意”的意思。而所以能以象观意,那是因为“有生于无”,“象生于意”。因此,从“以无为本”的理论讲,必须得出“忘象得意”的结论,也必须运用“忘象以求其意”的方法去把握无。从感官之知到意象之知再到圣人体无之知,这就是推崇老庄思想的中国魏晋玄学的独特审美观点。魏晋南北朝的宗炳更是最早将老庄思想应用于中国山水画,其“澄怀味象”思想的提出,也是主张人们在审美过程中摒除杂念,超功利和保持虚静空明思想。这种思想对现代陶艺创作也是适用的。如何在最大程度把握对象的最大特征的同时,将对象次要部分尽可能地舍弃,牢牢把握住对象的精神实质,将对象从生活中的形象上升到艺术的层次、文化上的高度。
老庄思想总的来说是一种舍的艺术,繁琐的堆砌、面面俱到、思想僵化是站在这种思想的对立面。现代陶瓷艺术作品需要如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说的“无我之境”,即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无我之境”倒是很像道家思想中“淡然独与神明居”的精神,王国维先生看得很清楚,大而空的人文精神仍不足以支撑中国当代艺术,中国现代艺术需要的是一种具体的人文精神作为艺术思想指导,王国维先生倡导的境界美正是深得道家思想精髓的无我之境。
中国陶瓷艺术走过了漫长而辉煌的道路,近代中国陶瓷艺术的落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缺乏相关的理论指导和缺乏对该领域的艺术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中国士人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因为军阀的复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导致了中国近代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分割,以至于当时许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看不到国家的未来而意志消沉。今天的中国当然不存在对本土文化认知的问题,但却存在对传统文化漠视的症结。其实所谓的传统与现代并非遥远得割裂开来,所谓“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人为地加大现代陶艺与传统陶艺的对立更不可取,两千多年前的庄子都能慧眼看穿宇宙时空,今人反倒失去了这种睿智,天地万物本为一体,传统与现代也本为一体,看不破它,只会注定要作茧自缚。与其在现代陶瓷艺术中挣扎、困惑,做无病呻吟,不如学庄子“乘物以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