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岁月忆往
延安整风:“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整风分两个层次
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了。整风,我是从头到尾都参加了的,但那只是一般中下级干部和学员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当时以至后来很长时间,都不知道延安整风分两个层次。其实决定中国命运的,主要的还是上层整风。
现在看来,对于延安整风的两个层次,大概可以作这样的归纳:上层整风是进行路线斗争,反对两个宗派;普遍整风是改造思想,反奸审干。
上层整风,党史上已经正式定为:开始于1941年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我们参加的普遍整风,只能从1942年4月3日中宣部作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关于开展整风和毛主席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 (即第一个“四三”决定) 算起。
张闻天找我谈话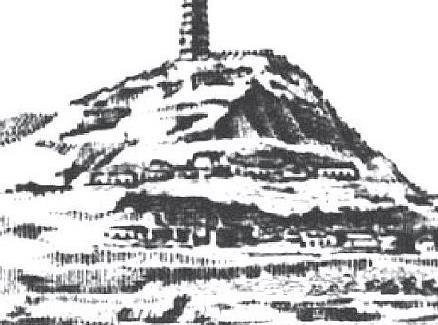
当然,在正式开始整风前还是有些先兆的,表现在1941年的延安生活已出现很大变化,盛行于1938—1939年的许多活动,像以前那种遍地歌声和经常的集会游行、纪念会、联欢会、大报告、上大课、上下一同逛街等,逐渐减少甚至消失了。有些现象,如等级制、保密制、警卫制、宣传教育的管理等,却明显加强了,开始不断改革学校和在职干部教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找我谈了一次话。
大概是1941年四五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期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从我们住的清凉山东边的黑龙沟到杨家岭,甩开大步,大约也得走一个小时。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接见,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方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很快就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也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
那时的等级制还不十分严格,上下的生活待遇也悬殊不大,再加上他们自己的严于律己和不开后门,所以他们吃的小灶和我吃的大灶悬殊并不太大。他们有两个炒青菜,也没肉,油水并不多。我们只有一种大锅菜,都是煮熟的,没油水。主食,我们完全是小米饭。他们却每人有四个约老秤半两的小馒头,小米饭管饱。刘英挺热情地说:“你们平时吃不上馒头,今天这几个馒头都归你,我们吃小米饭。”甭提这几个小馒头对我的诱惑力了。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气地给吃了个精光,但连个半饱都谈不上,又不好意思再吃小米饭,就只好起身告辞,打道回府了。后来我跟张闻天工作了十多年, “文化大革命”以后又和刘英来往了二十多年,还多次提到那次谈话。对我来说,谈话的详细内容是大半忘了,但那几个小馒头却始终牢记在心。
从杨家岭回来,大家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我叙述后,他们也和我一样搞不清是什么意思。直到近几年我改行学习党史,才领悟到这是张闻天要紧跟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整风期间所写的 《反省笔记》上讲,大约从1940年起,毛泽东就老是批评他主管的宣传教育工作,包括经过毛泽东看过和书记处通过的有关干部教育的文件。可见,张闻天找我谈话时说的,已经流露出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意思。不过说老实话,我的感觉还是太迟钝,不但当时,就是事后也没把这次谈话和很快就开始的整风运动联系起来。
学习整风文件
普遍整风是从学文件开始的。中宣部的《四三决定》 规定了十八个文件 (后来陆续增加到二十七件,正式定了个名字叫 《整风文献》),包括毛主席的整风报告、几个讲话和 《反对自由主义》等文章,康生的两次报告,中央的几个决定,斯大林的十八条 (《联共党史》 结束语六条,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以及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要大家学习讨论、写笔记,还要考试。按照延安机关学校的统一部署,我们单位也改为半天学俄文,半天整风。
学了一阵文件后,按规定就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了。头一段主要是给领导提意见,每天开会,还出墙报,也可以给上面写信。这阵时间,当领导干部的感到紧张,我们这些学员们却显得轻松。例如俄文队队长曹慕岳 (解放后改名曹慕尧,在沈阳军区工作),听大家提意见和本人检查就开了一个星期的全队大会,他自己也承认有好几个晚上没睡着觉。不过这种矛头向上、批评领导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就转向各人联系自己的实际,按 《四三决定》 的要求,“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这样一来,形势又倒转了过来,群众 (一般知识分子干部) 开始紧张,领导干部显得轻松了。特别是进入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领导上抛出一批思想斗争的重点和审查历史的对象,使这些人感到巨大压力,既要在会上接受大家 (主要是积极分子) 的批评和回答没完没了的问题,还得不断写出书面的检查交代。其余的人,也是既要准备自己的反省,开会时还得向重点对象进行批判和提出质疑。这样一搞,没有多久就走向全面紧张,俄文学习完全停止,集中力量搞整风了。所以毛主席说,1942年是基本上停止工作搞整风的“整风年”。
批判王实味
学习文件搞了没几个月,就开始批判王实味了。
1942年三月间,王实味写的 《野百合花》 分两期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当时大家看了以后,从内容到形式 (文字技巧) 都非常佩服,对后来一些人发表的批评文章还颇不以为然。就在报上不断发表批评王实味的文章的那一阵,延安各机关学校发下来 《野百合花》 让大家讨论。一开始,我们这些学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地同意王实味的观点。因为我们并不了解,中央是把 《野百合花》 当作反面教材发给大家看的。我们一个班发一份,给大家念,念完让大家讨论。讨论时,大家说,对呀!写得挺好的呀!写的都是真的呀!而且普遍认为,革命队伍里确实有缺点,提出来是有好处的。要是提出来就批评,以后谁有了意见还敢提?革命队伍不就成了死水一潭吗?大家讲得兴高采烈,振振有词。不料没过几天,领导上就动员批判了。
大家一时转不过弯来,开会没人发言。经过领导再三动员和积极分子带头,形势才扭转过来,大家才批判王实味和检讨自己的思想了。后来才知道,批判王实味是毛主席的统一部署。看了 《野百合花》 以后,毛泽东发表了意见: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解放日报》 怎么能登这个东西!立即打电话,让他们检讨!这下子才开始组织批判 《野百合花》了。我们这些人当时虽然不摸底,但是一看 《解放日报》 不断在大力批判《野百合花》,就再不敢表示同意它了。不管你有没有意见,也得跟着批。
那时的批判,有的是真的,也有的是假的,是为了表示划清界限,还有半真半假的。随着运动的深入,往往是弄假成真,大家的思想还真转变过来了。
其实,不光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延安的大知识分子像丁玲呀等等,比我们转变得还快,不到一个月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对王实味的口诛笔伐,上纲上得更高。据说只有一个萧军坚持不同意见,竟然放弃吃公粮,到农村当了两年老百姓,自食其力地种地。
我们学校的整顿三风,除开头几个月学文件,提意见,还谈点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转入批判王实味,就只有检查思想、追究历史、交代问题了,整风运动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抢救运动。从各机关学校的情况看,大概都同我们一样,1942年七八月后,就不再搞什么整风,而是大搞抢救了。
抢救运动:一时被迫承认自己是“复兴社”成员何时开始
批判王实味实际上就是抢救的开始。因为把王实味弄来弄去,很快就弄成了托派、特务。王实味和托派的关系,本来是他自己早已向组织部交代了的。后来一批判,和这联系起来,他就成了托派,于是全延安就声讨托派王实味。根据那时的逻辑,托派、汉奸、特务是三位一体的,王实味也很快升级为“国民党探子”。
王实味被打成托派后,还抓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反党小集团。紧接着,彭真又在中央党校抓到了“特务”吴奚如,还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抓“特务”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也发出了要发现坏人(托派、日特、国特),拯救好人的号召。随后他又在西北局高干会和康生一起批评一些单位领导麻木不仁,对抓坏人重视不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哪个单位还敢怠慢?于是遍地开花,到处抓起特务来了。各单位领导看到人家抓出坏人,心想咱们这儿怎么能没有呢?经过互相听汇报和交流经验,一些单位还有点比着来,好像抓的坏人越多成绩就越大。
抢救运动逐渐搞起来了,时间大约在1942年秋天和冬天,各单位的进度不完全相同。我们学校就是在天气还没变凉的时候,从追查历史发展到抢救的。我印象特深的是,围攻和抢救我的时候,天气既不热也不冷。当我实在瞌睡得不行答应考虑考虑,一时得到允许回窑洞睡觉时,炕上没行李,只铺着草,我就是没脱衣服在铺着的草中睡了一大觉的。而且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住的还是在黑龙沟的老窑洞。
联系实际、追查历史,怎么个追查法呢?各单位的情况大体一样,就是每个人轮着来,交代自己的历史,好像是搞人人过关。其实不然。一般都先安排一批重点对象,而且很快就卡壳了。一个人的历史也可能一个月也搞不完,因为问题会越交代越多。有些问题还有点道理,多数问题毫无道理,本人也根本说不清楚,真是“秀才遇见兵”。一开始还有人在那里吹自己的经历呢,说自己很早就参加救亡运动了,吹着吹着,就吹出破绽了,正好让人家抓住小辫子。许多人并不想吹,但在翻来覆去的追问中,自己也会前后矛盾,甚至越说越糊涂。我们有个同学叫高中一 (后改名高亚天,翻译过西蒙诺夫的 《祖国炊烟》),参加革命前在北平大同中学上过学。运动一开始,他就被当作重点对象抛出来了。学校领导组织大家追查他的历史,说问题的要害就在北平上学这段。当时我还没出问题,也被布置了任务。那时我们的同学中没有几个到过北平,更不用说上学了。所以光一个大同中学就搞了好多天,问来答去,还是一盆糨糊。多年以后,问答的内容都忘了,但当时那种尴尬场面和大同中学这个校名却印象特深,忘记不了。正巧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外交部工作,大同中学就在旁边,我的儿子还在那儿上过学。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抓高中一上大同中学的问题。
我来自西安,还算见过一点世面。但有的人比我还土,竟弄出这样的笑话,问审查对象是怎样来的延安。回答说是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乘火车。提问的人立即插问:你是经过什么关系坐上火车的?那国民党的火车能随便坐吗?真是弄得大家哭笑不得。说话的人认为,火车是国民党的,参加革命的人不能坐。这说明他不但没坐过火车,也没见过火车。
其实,当时延安没见过火车的干部特别是老红军,还有的是。我在抗大的原队长曾世保,是四方面军的。他就给我们讲过:他们在从鄂豫皖向四川转移时,要晚上穿过平汉线。由于从来就没见过铁路,所以在急行军中大家也要弯下腰去摸一摸。结果大为失望。原来以为铁路是在地上铺上厚铁板才叫铁路,没想到只摸着了两根铁杠,那火车怎么能在上面走呢?
当时抛出的重点和怀疑对象,多是历史比较复杂一些,特别是在旧社会做过事情的,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被敌人逮捕和关押过的,以及平时吊儿郎当、爱讲怪话、表现不好的,等等。确定对象后,就由领导给分工,找几个积极分子,再搭配几个普通学员,去“帮助”一个重点对象,日夜鏖战,直到被围攻者“坦白交代”。如果坦白得“好”,又表现积极,还可成为积极分子,去“帮助”别人,并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例如我们的同学兼区队长何匡,交代就比较早。当抢救对象越来越多,积极分子越来越少的时候,他就又吃开了,不但恢复了区队长职务,还去抢救别人呢,也“帮助”过我。解放后,何匡在编译局翻译 《资本论》 等马列著作,后来任 《人民日报》 理论部主任。我们还常有来往。
我被“抢救”
由于我小小年纪就到了延安,本来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所以一开始还被看成积极分子,跟着人家瞎嚷嚷了几天。但是,没多久,我就被“抢救”了,一上来就遭遇了“车轮战术”,弄得我蒙头转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
我为什么被抢救呢?估计是,我从家乡带出来的那两个比我小一岁的同学之一,叫史宗棠的供出了我。另一个同学叫陈克让,当时他已经上前线,后来在前线牺牲了。为什么我怀疑是史宗棠供出我的呢?因为经过几天的僵持后,学校政治处主任叶和玉找我谈话,他说:人家比你小都坦白了,你自己还装迷糊?我听后一想,那一定是史宗棠了。我们是一起被国民党抓住和关押的。他大概是顶不住,自己坦白了,还拉扯到我的身上。这只是当时估计,直到现在也不能肯定。后来我也再没见到过史宗棠,也许是冤枉了他。
对我的抢救,一开始还算客气。他们总是说:你再好好想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了以后,一切都照旧,不会对你怎么样,还是自己的同志,只是上了国民党的当嘛;国民党这个坏东西,罪过在他们身上;你一个年轻人,辨别能力不强,跟着人家做了什么坏事也不要紧,只要说出来就好,就是自己人了;你现在在沟那边,我们一拉你就过来了,要不然,你还在沟那边。他们讲得甜言蜜语,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那些假坦白的积极分子,看架势,好像已经从国民党方面站到共产党方面来了。别人还在被抢救着,他们已经没事了,但在抢救别人时并不太积极,显得理不直、气不壮,多少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比如何匡吧,他也来抢救我,把我叫到山坡上,坐在那儿,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坐上一两个钟头。最后,他说:还是放明白一点儿吧!这样,他也完成任务了,我也算被劝说了。但是两年后一甄别,他又说起真话来了,说他一开始就不相信何方那么个小鬼会是特务!
在抢救我的头几天,我还坚持和他们讲道理,软硬两套都不吃。因此,他们一个星期里就根本不让我睡觉,白天晚上都劝说审问。那时候,连煤油灯都点不起,印象中皓月当空,六七个人围着我,翻来覆去地跟我说:你老实一点,等等。有唱红脸的,有唱黑脸的。有的人还“讲道理”,总而言之是让你不得安宁。你在那儿低着头,不说话也可以,不理也行。有时候人家提问题,需要你解答,你就答复一下。瞌睡得不行了,也回答不清楚了。
僵持了一个星期,人老不睡觉不行呀,我招架不住了。我说:我坦白。他们说:好,那你就好好想一想,明天把交待写出来。我一下子高兴了,回去就睡了一大觉。第二天,他们去抢救别人了,让我写材料。交代什么呢?想来想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我说,我忠心耿耿干革命,怎么是特务呢?在信中,我一方面表明自己不是特务,是他们搞错了人;另一方面还批评这种抢救的办法不对,恳求毛主席派人来了解情况,加以干预。
人家总是催:你写的材料写好了没有?我说:我写得慢,有些情况还得慢慢想。这样,我又可以多睡几天。他们在那儿抢救别人,我变成旁观者了。但不能总当旁观者吧,人家还在催我写交代。于是,我就把我写的东西交上去了。交上去,一看,原来是告状信。这可坏了!第二次抢救开始了。这样一来,他们的态度不像以前了,更不“友好”了,开始骂人。一个女同学把一口痰吐到了我的脸上。那简直窝囊死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恶心。
大概又有一个星期左右,这期间我被围攻得更厉害了。这个推你一下,那个推你一下;你才打个瞌睡,他就把你推醒,让你恼火得不行,又不敢和人家干仗。这里边有的人是已经坦白了的,也有的是还没有惹到他头上。又熬了这么一大阵后,我也“想开了”,既然上次上书毛主席都不理会,一定是被学校领导扣压了,自己已没有别的出路,就坦白吧。于是我对抢救的人们说,这次我决心坦白,他们表示欢迎,但怕再上当,怕我又写信,所以就常来检查。可我呢,确确实实又写信去了,前面写得含含糊糊。他来检查,也看不清楚。那时候也挺乱的,到底谁检查谁,谁管谁,他们不太明确。我究竟是归谁管,我也不知道,所以实际上没人管。我在信中写的内容有些还是申诉。领导和积极分子们看了当然不承认我是坦白交代,于是又折腾起来了。
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那时,我有个同学,算是女朋友吧,但关系不深,来往时间不长,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只是我们互相有点好感,认为是朋友。那时候我在学习等各方面都表现得比较好,又给大家作时事报告,那个女同学对我挺佩服,愿意接近,非常友好。我也很喜欢她。这时连她也来抢救我了,还暗地里塞给我一个纸条,说是只要我坦白交代,朋友还是朋友。本来我一被抢救,就意识到这个朋友关系不可能再继续了。等她一来抢救,我就完全灰心了。“朋友还是朋友”,只是劝我坦白的抢救辞令罢了。所以我当时在填的一阙 《菩萨蛮》 里,还记得最后两句是:“挥泪向云英,表心待来生。”
提起填词,倒要多说几句。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而且好高骛远,不知天高地厚,进抗大后就开始学着作诗填词了,还不懂基本格律,就已写成了一小本诗集,上引两句也抄在这个本子里。后来抢救运动越来越紧,大约是1943年夏天,就开始搜查和收缴个人的东西了。我们当时的支部书记,在没收我的东西中也包括有这个小本诗集。但是他看不懂,问我这写的是些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他。另外,他们怕我自杀,连我的一把小刀也给没收了。特别是我的几本日记,没收后不发还我,使我极为恼火。当年,我在西安被扣留的一些事都记了日记。我很早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不管每天有多么忙。到延安以后,也是把学习、劳动都记了日记。这些东西没收后再也没归还我。我一怒之下,做了两个大改变。一是从抢救以后,再也不记日记。但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总得做点工作笔记。不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这些工作笔记,包括东北地方工作和外交部时的工作笔记,又被抄走了,也是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返。二是再也不学写诗填词了,所以“文革”初期外交部没收我的东西中就少了这一项,积极分子们批斗我时只能在我抄写的旧诗词中做文章,而找不到我有什么“反诗”了。
当我决定坦白交代时,却不知道要坦白什么?真费脑筋呀。当时人家具体地问过我,有时候也提示,比如你究竟是“复兴”还是“CC”?这两个组织是怎么回事,我并不知道,到现在也还是不清楚。但是不知怎么搞的,当时想来想去,竟然觉得“复兴”比“CC”强一点儿, “CC”大概更坏,因此我就承认是“复兴”了。这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也真复杂,除了CC、“复兴”以外,还有什么军统、中统、蓝衣社、三青团等一大堆,随你挑。我挑了个“复兴”,但怎么能说清楚呢?由于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自己也搞不清这些特务组织,所以只要你承认是某个组织的特务就行,他们并不深究。即使有人问到,你只推说人家没讲这些,也就蒙混过关了。严重的是紧接着就要追查组织关系,这是最难办的了。抢救的问:是谁介绍你参加的?或者你的领导是谁?这个问题更费劲。我想,我决不能陷害朋友和熟人。但是你不说,又不行。于是我想来想去,认为白区大概不会搞抢救,就说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一个人。那时候,我还记得他的名字,现在已经忘了。在办事处是他给我办的手续。我就说,是他介绍我参加复兴社的。我说,他介绍我时,没对我说复兴社是怎么回事。究竟加入了以后干什么事情,他说以后再通知我。就这样,算是马马虎虎过关了。过了关以后,我回去越想越不对头。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事情呢?不但害了自己还害了别人!精神上的压力比坦白前还厉害。所以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坚决推翻了。但不是说推翻就能推翻的,也得写材料!再叫我写材料的时候,我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复兴社,我完全是因为自私自利、个人主义,为了自己睡觉,为了过关,瞎胡编了一气,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同志。这个决心一下,再怎么折腾,我也决不再承认了。所以我从那次坦白中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后来反而长期成为“死顽固”的抢救对象。
这样僵持了一年多,一会儿紧,逼你交代问题,劝你坦白;一会儿松,又不检查了,叫你去劳动。不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实行三人同行制。平时不准随便离开学校,出去劳动的时候,开荒种地是集体行动,掏茅坑抬粪,也要“好坏”搭配,三个人一起。我推翻原来的交代以后就一直在那儿挂着。紧的时候,硬着头皮顶住;轻的时候,我就找一些闲书看。例如抬粪的时候,我就带本 《红楼梦》,有空就看,没空就背。这些倒没人管,也还有点小自由。因为戴上了特务的帽子,所以也没人敢理我。我感到很孤立,就用死记硬背一些古典诗词来自我消遣。后来,女朋友和一个高级军官结了婚,我也无动于衷。
到了1943年7月的时候,兴起了一阵声势更大的抢救运动,规模已经超出我们学校的范围,参加校外的坦白大会了,还到中央大礼堂看过几次示范。有一次,军委系统在王家坪的桃园开坦白大会,我们俄文学校属军委系统,当然要参加了。大会由大家叫他参座的叶剑英主持。他做动员,号召失足的人坦白。我们校长曾涌泉在那儿领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主席台两边设有“光荣席”,桌上摆着香烟茶水,看来很简单。其实这香烟在延安可是个稀罕的东西。这以前,听报告或开大会时,有些人总是抢着坐在前面一排,为的是拣点儿烟头。例如像毛主席等吸烟的中央领导,他们虽然够节约的,但总会剩点烟屁股扔到地下,这时坐在前排的人就可偷偷用脚把那烟头勾过来,拾起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回来就和几个烟友一人抽一口。但是“光荣席”上的香烟吸引力并不大,许多人被积极分子连拖带拉就是不上去。人们也来拉我,我也坚决抗拒。直到前些时候 (2003年),我的老同学蓝曼还开玩笑,那次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何方抱着一棵小桃树,怎么也不松手。有一批人上去了,不晓得有多少人,我也看不清。他们被拉上去,坐到了光荣席上。即使你没有坦白,坐在那儿,大家一看,也会以为你坦白过了。一坦白,就算“光荣”了,还可以抽一支烟。但是我坚决不上光荣席,抱着小桃树死不撒手。让他们嚷嚷去,嚷嚷完了总得散会。
这样时紧时松地抢救搞了一年多,被抢救的人占了一半以上,其中大多数都做了坦白交代。
甄别前后
1944年开春,延安的机关学校先后停止轰轰烈烈的抢救,开始搞甄别了。这个甄别大概搞了一年多,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还没完全结束,有些人例如成钢、王里等人的“五人反党集团”,蒋南翔的“反对中央九条方针”,是一直到胡耀邦平反冤错假案,才给做了结论的。在这一年多里面,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一个一个地搞平反。
我的问题应该说并不复杂,但也是过了几个月,差不多是半年以后才再找我谈话,亮底。大意是说,你不是政治问题,抢救你的原因是由于你有自由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意识等等。我一听就是瞎编的,当然不干。我说自由主义怎么能变成政治问题,你们不是批自由主义,是当特务抢救的呀!他们 (政治处主任、组织干事等) 解释说,那是非常时期,国民党要打进来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容易混淆了。我说,你们当时可是说有人供我,人家比我年轻都坦白了,现在又扯到思想意识问题,明明是给你们找借口,不但不承认搞错了,还要给我留尾巴,我是绝对不同意的。结果谈了好几次,互相都没说服,我就拒绝在结论上签字,另写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交了上去。直到现在,这个没本人签字的结论还放在我的干部档案袋里。
按照毛主席的说法,1942年是整风年,1943年是审干 (实即抢救) 年,那1944年就是甄别年了。不过这甄别只是少数人的事。至于大家呢,上半年除一些政治学习外主要就是劳动生产;对多数人来说,重点已转为俄文学习。学专业,大家是欢迎的,也显得很积极。但整个空气仍然沉闷,生活也活跃不起来,还是有点万马齐喑。不久,没想到日本宣布投降了。大家这才欢腾起来,到处烧篝火、敲洗脸盆,又唱又跳,热闹了好几天,然后就分头准备,盼望着尽快离开延安了。
告别延安:急于离去, “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轻装上路
日本投降后,延安从上到下都有点人心惶惶,原来那种正常生活一下被打乱了。人们在兴高采烈、欢庆抗战胜利的同时,就是急切地等待着组织上宣布自己到哪儿去,什么时候走。我们学校几乎没人想到自己还会留在延安。所以那些天,课也不上了,生产劳动也不搞了,还不断杀猪会餐,学员的活动几乎没人管了。大家都各自收拾行李,处理一切带不走的个人所有书籍和被褥等用具,尽量筹措一点可归个人支配的路费。我的马列书籍不少,也保存完好,但只能当废纸卖,一斤卖不到一毛钱。我虽然不再记日记了,但学习笔记本还是很多,也都一起当废纸卖了。比较值钱的是我从西安带来已经用了七八年的被褥和几件破旧衣服,因为延安长期遭受封锁,这些东西显得紧缺。买的人都是闻风而来的老百姓。那些天,南门外新市场的人也陡然增多,一堆一堆地在讨价还价。我们这些同学过去都没有卖过东西,更不会讨价还价。特别是老百姓伸出手来,要和你袖口对袖口用手指头在袖子里讲价钱,这就抓瞎了,根本无法对付。和我一起去卖东西的同班同学阎明智 (阎宝航的长子,阎明复的哥哥),人家一问价钱,他脸先红了,竟答不出一句话来。所以头两次,我们都是把东西扛去,放在地上,半天卖不出去就又扛了回来。不过最后我要处理的东西还是贱价卖掉了。那时公家规定,凡离开边区的人,可以将边币换成银元,所以我也换成了五块大洋。
就在这忙忙碌碌处理东西的过程中,也就是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一个星期,外语学校开全体教职学员大会,宣布第一批去东北工作的人员名单,由俄文系和英文系合组成一个工作队,共二三十人,分两个班,其中就有我的名字。8月28日上午,毛泽东一行乘飞机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下午,中央就在八路军大礼堂开会欢送去东北的干部。会议由朱总司令主持。他先讲了毛主席去重庆的事,说有许多同志担心毛主席的安全,这是中央一再考虑过的,以防万一,中央已决定在毛主席回到延安以前由少奇同志代理主席。接着就请刘少奇作指示。刘少奇的讲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我和你们一样,对东北的情况并不了解,谈不上什么指示,一切靠你们自己去闯,闯关东。他的意思总的说来,就是东北关系重大,一定要拿到我们手里。会后第四天我们就整队出发了。没有统一的制服,各人只背一个简单的行李,如几件准备御寒的衣服和日常生活用品如水壶、搪瓷缸之类。一同出发的有多少队,我不清楚,只知几十个队编成一个干部团,团长是张秀山。
9月2日一早,太阳刚出来,我们外语学校二三十人的东北干部队,就在队长刘端祥率领下集合出发了。全校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东关飞机场为我们送行,都说是我们先走一步,他们随后就会赶来。许多人还表现出羡慕的意思,特别是那些被抢救后甄别结论还没下来的人。这第一批出发的人,都是年纪比较轻、历史简单的人。我虽然还不满二十三岁,但已算老气一点的人了。加上当过助教和常作报告,所以大家就推举我向送行的人作告别讲话。现在我已记不起当时讲了些什么。当何理良等同学说要我保重时,我的回答是“没打算活过二十五岁”。这句话的印象特深,后来还和包括何理良在内的一些老同学谈起。
就在这个简单的仪式后,我就甩开大步、头也不回地向东走去,明显地表现出有点情绪,这是送行的人也看得出来的。这一去就是半个世纪,直到1997年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去参观了一趟壶口、延安、黄帝陵。
这就是我对延安岁月的回顾,也算是对延安的历史告别。
(选自《从延安一路走来:何方自述》/何方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