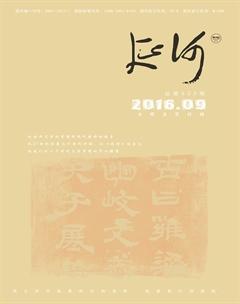醒目的铜钥匙
你会俄语吗?不会。中国驻白俄罗斯使馆的一秘忧虑地看了我一眼,那你怎么和他们的作家交流呢?我愣了一下,他们应该会有同声翻译吧!我说。
虽然是代表中国作家来参加明斯克国际书展“时代与作家”文学活动,可是在酒店现场,没看到任何人,没问清楚任何问题,没拿到任何有关会议活动的文字,但我还是很笃定。关于作家的事情就是这样,于混乱不堪中自会有一些独特趣味。
酒店在给我房门钥匙时,还挂着一个黄铜制作的钥匙扣,我感觉它没有一斤也有半斤,拿在手里,像拿了一个锚,更像一个沉甸甸的目标,出门去哪里回来都有了方向感。
第二天,我耐心在酒店的大堂等待组织来找我,果然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女孩走过来用英文问:你是不是中国作家。我说是。她说,你在这里等着,我会带你走。
我们还等到了一个意大利的女作家和俄罗斯的男作家,一起上车。汽车把我们拉到了昨天我已经来布展过的明斯克会展中心,这个建筑很像一个四角翘起的飞碟。
进到会展中心,在存放大衣的地方,会议工作人员用英语向我说更多的事情,但很明显,她说英语也有些吃力。
这时那位满头白发的俄罗斯大叔在后面慢吞吞的用中文说:你们想说什么?
我们两个同时回头看他,他竟然会说中文,他说是小时候在海参崴跟着一个俄国老师学的,虽然过去了五十几年,现在看见我,很多词汇又想起来了。
等交代完工作,那位俄罗斯大叔说,你别担心了,我会告诉你,所有的工作安排,吃饭时间,我会去你的展台找你啊!
坐在展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对翻译玛莎说,我需要买一双高跟鞋,玛莎说:什么?我说,我需要买一双高跟鞋……
我们立刻起身去展馆对面的一个大商场,买了一双,马上穿上之后回到展馆。刚刚坐在椅子上,明斯克首都电视台就过来采访了。
记者问我,你对明斯克什么印象?我说:我在北京时,买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来看,一直从机场看到这里。比起书里的惨痛感受,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安静、清冽还有一些优美。
但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军队摧毁了白俄罗斯境内619座村庄,切尔诺贝利灾变则让该国失去485座村庄和居住地,其中的70座永远埋在了地下。战争时,每四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个死亡,今天,每五个白俄罗斯人就有一个住在受辐射污染的地区,总数为210万人,其中70万是儿童。
我觉得,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会比白俄罗斯人离死亡更近,他们的这种刻骨感受,会让他们对生命的本质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解,和任何人都不同。
采访结束后,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美丽的女记者在拍照过程中紧紧挽着我的胳膊,这在我与外国朋友的交往中很罕见:因为这样陌生的人却在身体上很亲密……
我想,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拉近了我们精神上的距离?我问玛莎:“我在北京时以为到白俄罗斯会见到阿列克谢耶维奇?”玛莎说:“她不在明斯克,她也不承认自己是白俄罗斯人,因为她说她是出生在乌克兰。而且,她和政府的关系也不好,尽管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5种语言,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白俄罗斯,官方一度禁止出版她的书,被选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删除了。”
中国展台的对面是书展的休息室,有一堵透明的玻璃墙。早上到的时候,房间墙壁上挂着两个作家的巨幅海报:阿列克谢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到中午时,工作人员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海报摘下来了。这时,俄罗斯大叔匆匆过来找我,说我们该回去吃午饭了。回酒店吃饭的路上,我知道这位俄罗斯作家名为瑞雅,写作的内容也和中国人有关,是哈尔滨人在莫斯科的生活的故事。午餐时,一位拉脱维亚的男作家和我们坐在一起,瑞雅能够回忆起来的汉语词汇越来越多。包括一些很晦涩的单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