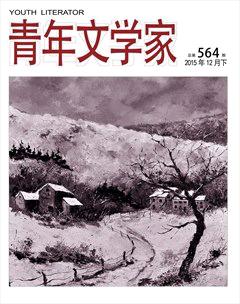解读《蛙》中“姑姑”形象
摘 要:作家莫言的长篇小说《蛙》,成功地运用了书信、小说、戏剧等跨文体写作的艺术手法,以新中国近60年来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成功塑造了姑姑、陈眉等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其中,姑姑的人生呈现出叛神者的典型轨迹,恰当地折射出莫言小说创作语言的丰富和乡土风情的醇厚,引发出更多读者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感悟到莫言小说所具备的独特艺术魅力。
关键词:《蛙》;姑姑;典型性
作者简介:王伟,女,1990年7月出生,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2014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02
《蛙》是作家莫言所著的一部反映中国当代乡村计划生育史的经典现实主义力作, 成功地运用了书信、小说、戏剧等跨文体写作的艺术手法,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描述了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平凡而传奇的人生经历,以此映照出国家在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过程中所走过的艰辛而复杂的历程。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审美性。
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说,《蛙》是因人物而产生灵感和激情,也是把塑造人物、展示人物命运作为最根本的追求。[1]换句话说,人物形象既是小说的起点,也是终点。因此,准确理解并掌握小说的灵魂人物,是解读小说的关键。下边本文仅从姑姑这个女性人物出发来展开叙述。
姑姑一生动荡不安、毁誉参半。其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解读:“送子观音” [2]时期、“夺命瘟神” [3]时期、“自我救赎”时期,简言之就是“人性”[4]、“魔性” [5]、“神性” [6]三个阶段。
1、送子观音时期
1950年代是姑姑行医生涯的黄金阶段。此时她扮演的是一位受当地乡村产妇敬爱与信赖的“送子观音”形象。她以启蒙者的角色推行新法接生,以精湛的接生技术取代“老娘婆”的野蛮、蒙昧的接生术。[7]姑姑泼辣的性格与干练的接生手法得到了乡间产妇的高度评价,如《蛙》中,我的母亲和成分不好的陈鼻母亲艾莲被姑姑接生后,自发地成为其新法接生“生意”的义务宣传员,她们常对人说:“姑姑的手是内热外凉,像丝绸一样的、宝玉样的凉。只要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减去了七分。”[8]此阶段姑姑性格开朗、为人果敢,对生命充满热爱,拥有为人所羡慕的爱情。她自认根正苗红,是英雄的后代、烈士的女儿。这一阶段姑姑整个的形象在自我与他人的视野中是完美的,她为自己的出身倍感自豪,这也是她五十年行医历程中最辉煌会光彩的黄金阶段。
2、夺命瘟神时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中国,作为“送子观音”的姑姑因与“叛逃者”王小倜的一段情史受到牵连,被打成右派。姑姑将出身看得很重,甚至为了证明清白、发泄愤怒而写下血书,切腕自杀未遂。如果说王小倜叛逃事件是使得姑姑性情大变的催化剂,那么计划生育则是使得她从“送子观音”到“杀人恶魔”角色转变的关键点。经历过暴风雨般痛苦经历冲洗后,她在落实计划生育的工作中表现出了强烈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变得心硬如铁、手腕强硬。如姑姑等欲抓捕张拳老婆堕胎时写到:“你看看,她浮得多好呀,她把游击队员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用上了呀![9]此时的姑姑已不复为人,而变成现代性计划生育庞大冷酷的机器中的一个冷酷、坚硬的红色革命螺丝钉。为了对党表示忠诚,她把自己的身心完全地投入到工作中,摇身一变转身成为了人见人憎的“夺命瘟神”,为了工作她遗忘爱情、搁置亲情,将大好青春韶华全部奉献给了党给了被人民大众所唾弃诅咒的计划生育政策。[10]为了坚决的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不顾及亲情、甚至连临近分娩期的孕妇都不放过。
从执法角度上讲,小说中姑姑的这种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工作态度确实无可挑剔,令人钦佩;从国家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成效上来看,她确实在控制人口数量、解决国家人口压力上为党为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来讲,她一味的坚决执行控制人口增长的死命令,未从产妇实际情况出发,最终导致王仁美、王胆、耿秀莲等产妇的死亡这一事实却无论如何都应当受到强烈的谴责与批判。面对人们对她的诟病,她无所畏惧,对自己“闯下的祸”未曾有过道德上的反思与忏悔,甚至理直气壮地以“我不怕做恶人,总要有人做恶人。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即使真有地狱我也不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11]“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都要被中国人压扁了。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的贡献!” [12]作为自我反驳的论点。这一点虽然很妥帖地体现出她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和坚决捍卫的立场,也同样展现出了一颗曾经被打击的伤痕累累的心在政治化极强的时代进行自我掩护的方式。
从送子观音到夺命瘟神角色的转化实际上是在国家政策和传统民间观念的强烈冲突中形成的。在这两种观念的夹缝中,姑姑既是政策的坚决执行者,同时也是无辜的受害者,是冲突的焦点所在,这也正是姑姑人生悲剧性的体现。这种行为在造成了他人的痛苦的同时也酿成了自己的悲剧。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中所言:“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 [13]可以很好的佐证这一点。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政治色彩极度敏感的时期,姑姑如此做人做事也可以算作是明哲保身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有效的方式。
3、自我救赎时期
当历史的浪潮缓缓退去,狂暴躁乱逐渐消隐 [14],年老的姑姑作为一个退休者,远离了喧嚣忙碌的职场,开始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思、忏悔。退休那天晚上,姑姑醉酒后被青蛙撕扯衣服,在一片片蛙声叫嚷中她感到了害怕。蛙是高密东北乡的图腾,但姑姑为什么那么惧怕蛙声?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是蛙声类似于婴儿的啼哭,这声音魂牵梦萦般缠绕姑姑耳际让她产生畏惧与忏悔;二是因为“蛙”的读音同于“娃”,成片的蛙声像极了被姑姑亲手打掉的若干婴儿的啼哭声,这让姑姑心惊胆战;三是当年亲眼见到蛙被解剖后裸露的大腿像极了孕妇的大腿,这份场景让姑姑感受到自己当初毫不留情地给孕妇堕胎的“罪孽”。
姑姑晚年的忏悔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实意的悔悟,她经常自我反省,也试图用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服自己,甚至让丈夫塑造泥娃娃来供奉,以期获得内心的解脱、灵魂的救赎,但终究无济于事。如果仅从个人心灵忏悔的角度去解读它,就会发现此时的姑姑演绎的是一个绝佳的“自我救赎”角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姑姑没有坚守自己的人生信条,最终既造成了陈眉失子的悲剧,也使得袁腮等不法分子逍遥自在,这种行为不仅不能使自己真正解脱,而且在助纣为虐的同时使得自己陷入更加难堪的境地,因此也不可能寻得真正的自我救赎之路 。“姑姑以赎罪的方式酝酿了更深的罪恶,以阻止悲剧的方式制造了更大的悲剧。” [15]“姑姑的双手,既带着芳香又充满血腥”。救人与杀人、活菩萨与活阎王、天使与无常,同时寄予姑姑一人身上,造成了性格的极端反差与人格的内在分裂。[16]
综上,姑姑耐人寻味的一生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转变,于“人性”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生命伟大的悲悯情怀,于“魔性”中我们见证了她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偏执,于“神性”中我们发掘了母性复苏的征兆。这三个阶段并非绝对割裂开来,她的人性、魔性、神性总是相互依存、相互映射。归根结底,姑姑的传奇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在寻找心灵寄托、寻找坚定信仰的过程,信仰的转变导致了其行为的变异,形成了其人、神、魔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形象。从姑姑这位极具特色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出发,引发出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影响,这也正是莫言写姑姑这一形象的立场所在,姑姑这一人物是三层复杂因子的完美结合。在这个人物身上本身并没有所谓对与错的纠葛与判断,作者在对其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可谓爱恨交织、诅咒与崇敬同在。这就是莫言从民间叙述视角展现的那个复杂而有内涵的女性传奇人物——姑姑。我们可以通过对姑姑这个人物形象典型性的认知,体味到莫言创作的独特艺术魅力和民间乡土风情的淳厚,感知到社会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一面,从而引发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
注释:
[1]张英.莫言.姑姑的故事现在可以写了.南方周末,2010(2).1页.
[3]张灵.《蛙》中的姑姑和她的一厘米的自主权.新文学评论,2013.51页.54页.
[2][14] 杨扬.莫言作品解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22页.224页.226页.277页.
[4][5][6][7] 张彦.蛙、娃、娲-论莫言《蛙》中姑姑形象转变的三个阶段.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3(2).48页.48页.48页.44页.
[8][9][10][11][12] 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20页.109页.222页.223页.151页.
[13]陈永国. 本雅明文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07页.
[15]梁振华.虚拟的真实与真实的虚幻-莫言《蛙》阅读札记.中国图书评论,2010.93-94页.
[16]孟庆树.莫言《蛙》三题.艺术广角,201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