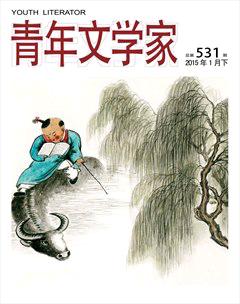最遥远的距离
夏天弈
倘若只论物理学,最遥远的距离当然只存在于我们头顶上的那个星空中。
地球只是那闪烁苍穹中的沧海一粟;而人之于社会,亦如社会的惊涛波澜中的一滴。
生与死的距离,已非时间或空间单位之所能及。正如战国时期的“大九州”学说一样,那样地似真又幻,看似存在却又似缥缈。
然而,我以为,最遥远的距离,无关乎古今,无关乎生死。
距离,这个词在某种意义上本就应是人类行为社会化的产物,本就隶属于唯心论的一部分,是任何宏观和微观世界所不能及的。
距离,源自于人的内心。
当俞伯牙遇钟子期时,两人没有过多的对话,只是一种心灵的感知。一个是楚庭重臣,一个是山野樵夫,但某一种力量却将这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人聚在了一起。那一刻,天地之间,万物都没有距离。
然而故人一去不复还,高山流水不复。此后,伯牙纵是身处闹市,能感到的恐怕也只有孤独。
社会学家说,人是群居动物。
而又有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属于或包含自己的小团体。可是,这只不过说明一个人已开始融入社会,至于他与他人之间的隔阂有多厚,鸿沟有多深,不得而知。
所以我说,最遥远的距离,在于你我比邻,却无灵犀。
每每奏响乐章,都会忆起当年笑与泪。曲至伤心处,已无心再继续。因为我指类下的那串音符,是空虚的,是虚妄的,是没有血肉的,是死的,因为它们不出自于内心,只出于指尖,也更不知往谁的心里去。
高山流水,知音难觅。芸芸众生皆近在眼前,可怎么看却又远在天边。
我知道,那是遥远的距离,彼岸与此间的渡河,使我无法企及。我们变得无心与他人真正地沟通,变得与他人格格不入,越来越自私,越来越遮蔽美好的德行,而展露残暴自利的天性。
曾几何时遇故人,不久前的是挚友,彼时互吐心思,互视若知己。而此时相遇已成冷遇,似白水之于黄油,永远溶不到一起。见面千言却又无声,眼前的故人好似隔了千山万水。转身又常见于路,擦肩而过,又向各自的利益奔去。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过人的天性,他说,“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帮助,但是如果仅仅依靠仁慈,那将是徒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密认为,道德是与此对立的,他还说,“社会……不能维系于那些总是想损害和伤害他人的人。”确实,一面,人不会贴近地走到一起,融入共同的一片心田中;另一面,他们永远会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甚至相互打压。
面前的今天,不知又是多少年前的昨日?
假如说“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我爱你”是最遥远的距离,那么我说,最遥远的距离莫过当年知己站在面前,而对方已不再知道自己的内心,灵犀不再。我虽然感觉到斯人的到来,但即便有言出口也已话不投机半句嫌多。迷失,迷失在漫漫人流中。
我不知我,我不知你,你我互不相知,这假若是陌生人也便罢了,但当当年的朋友也是如此时,便觉得这个冷漠的世界的可怕了。摘取一颗海上星,陪我终夜不孤寂。
只是那缠扰孤岛的雪雨,飘飘洒洒谁来停?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因而当人自己感到被抛弃时,才会有最远的距离的慨叹。也只有这时,人才会真正地去反思自己,反思人生,反思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日出迟暮,一瓢江湖我沉浮。
又岁荣枯,可你从不在灯火阑珊处。
独留一人赏花,花开又谢。灯花摇曳,摇曳后就随风飘远。
最远的距离,非是宇间与宙合,非是生死隔冥河,而是心灵相阻隔。无数个我们身居同城,可再近的距离也抵不过心灵的间距漫长。倘若人与人之间无法跨过那心灵的界线,二者也就永远无法相知,因此靠得再近也觉得两人之间仿佛隔了一世。
最遥远的抵不过心灵,
最漫长的莫过于心路,
最痛苦的非关乎生死,
最贴近的也可为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