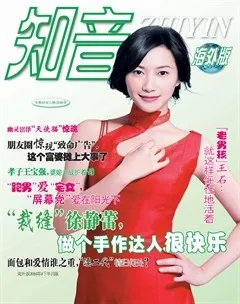“歌手”张信哲,捡来的破烂价值一个亿
在整个华语歌坛里,能够担得起“情歌王子”这个头衔的,只有台湾歌手张信哲一个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顶着高烧参加《我是歌手》,一首状态不佳的《信仰》却能获得当场第一的好成绩。粉丝们的青春里,都住着这位专唱情歌的王子,然而对于张信哲本人来说,除却音乐,他还有另外一份精神食粮,那就是——古董。他的古董收藏生涯,甚至长过他当歌手的日子,在成为歌手之前,他首先是个大隐隐于市的收藏家。
收藏“破烂”,是金子总会发光
古董收藏,对于幼年时的张信哲来说,是个触不可及的词语,因为那时候的他有个更接地气的外号“捡破烂儿的”。小伙伴们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张信哲只要看见老物件,就会往家带,一块木制的旧窗花,一枚缺角的老硬币,更别说正在拆迁的旧房子,几乎就是一个天然的宝库,是张信哲最钟爱的童年游乐场。
这个不同寻常的爱好,说来也是有缘由的。张信哲出生在台湾著名的古城西罗,遍地可见的木制老建筑,每到台风天就会吱吱呀呀作响,风刮过屋顶时发出浑厚的中音,吹倒门口的铁皮桶是尖锐的高音,挂在窗口的风铃好似奏起了悦耳的和弦……大自然亲自奏响了一首交响曲,张信哲用耳朵捕捉着各种音节,每当听到新鲜的声音时,他只要找过去,就一定能有所发现。雨过天晴后,就更是寻宝的好时机了:吹落的瓦片上有好看的花纹,收着;捡到的木头上好像刻着一句铭文,收着;装满雨水的破瓷盘看上去很有年代感,也收着……每每看到这样的张信哲,小伙伴们都聚在一起喊他的外号,“捡破—烂—儿—的—”即便受到这样的待遇,张信哲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每次回家,当木匠的爷爷都会亲自检验孙子的眼光:“这块木头不错”“这个工艺有点马虎,不及上次那块”,有了家人的支持,张信哲也攒起了收藏路上的第一个心得:不怕人说,大胆去找。
收藏的爱好伴随着张信哲度过了整个青春期。1987年,他通过歌唱比赛崭露头角,并签约巨石唱片公司,成了一名歌手。对于出生在音乐世家的张信哲来说,唱歌从来都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当第一张专辑进入宣传阶段的时候,制作人却来找他商量一件事:“阿哲,咱们能不能不露脸?”张信哲有点蒙,在他的印象里,哪有打歌不露脸的,这样歌迷们怎么认识你呢?他不死心地一再追问,终于得到了答案:原来张信哲虽然嗓音条件好,但是在公司高层看来,他的长相不是主流帅哥的模样,所以采取了保守的电台打歌模式。
被人嫌弃了长相,张信哲很受伤,他带着试听专辑回了家,门一开,久未谋面的爷爷就坐在客厅里等他,身边还放着一个蓝白条纹袋。爷爷神秘地揭开袋子,里面端正地摆放着一张酸枝木矮凳,熔岩巧克力般细腻的纹理让张信哲看得挪不开眼,独有的酸香气经过时间的洗礼,也变得十分柔和,最讨人喜欢的细节还是凳腿,敦实的圆形设计使得整张凳子多了一份灵气。看到张信哲对它爱不释手,爷爷却报出了它的身价:一分钱也不要。原来,爷爷去工厂帮人修东西,看见它泡在废仓库里,日晒雨淋的,就拿回家,仔细整修了一番,才发现是个好家伙。
“阿哲啊,你收了这么多东西,应该知道,找好家伙要耐得住性子,是金子它总会发光,谁都盖不了。”爷爷一边说,一边拍了拍张信哲装专辑的背包。张信哲这才恍然反应过来,原来爷爷听说了他的苦恼,专门带着一件藏品来开导他的。看着眼前的矮凳,张信哲默默点了点头:自己就跟它一样,不经历一些风雨,怎么遇得到识货的慧眼呢?
张信哲同意了公司的宣传方案,全副心思都放在了新专辑的制作上,然而这时候好消息却传来了——全台湾的歌迷都被《谎言》这张专辑打动,他们想知道张信哲是谁,长什么样,以至于广播台的热线电话每天都被打爆。这时候,张信哲心里终于落下了一个声音: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而他,已经做到了。
随性收藏,读懂藏品的心
首张专辑就打开了市场后,张信哲又凭借专辑《心事》正式走红两岸,《爱如潮水》成了大街小巷循环播放的金曲,随后《信仰》、《白月光》、《从开始到现在》等歌曲的出现,巩固了他“情歌王子”的地位。
名气越来越大,收入水涨船高,张信哲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收藏版图:年幼时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只好上街“捡破烂”,现在经济独立了,他兴致满满地想要一展身手。这时候,老家传来消息:外曾祖母过世了。
外曾祖母年过百岁驾鹤西去,也算是喜丧,张妈妈在帮忙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有几件颜色鲜亮的旧时长衣,图案精致,纹理清晰,想到曾祖母生活的时代还是晚清,说不定这些衣服还是古董,征得家人的同意,她重新给收了起来。而当张信哲赶回家的时候,一进门就看到了这几件色彩鲜亮,做工考究的衣服,凭着多年的收藏经验,他知道这正是极富价值的织绣,而且宝蓝、天青色正是宣统年间的流行色调,整件衣服的身型偏窄,正是清朝晚期受到了西方审美的影响而经过改良的版型。
最了不得的是,除了这两件长衣,还有一个荷包和一双金莲鞋,这两件东西让张信哲想起幼年时,外曾祖母总是腰上别着这个荷包,走到哪都自带着一股幽香,虽然是三寸金莲的小脚,但是每次见到自己来做客,都晃悠悠地小跑着迎接。这几件充满了回忆的物件让张信哲痛上心头,他默默决定,要把这些属于外曾祖母的过去,一一保管好。
意外地有了第一批织绣收藏品,这也调动起了张信哲的兴趣,做过大量的功课后,他才知道,《红楼梦》里让宝钗感叹“鲜亮的活计”的就是织绣,然而,古玩市场上几乎寻觅不到织绣的影子,于是张信哲开始紧盯国外的拍卖行,很快一双西藏喇嘛跳神舞的织绣鞋被他看中,他立刻通过朋友出价买了回来,可是等到半个月后收到实物时才傻了眼,草纳的鞋底已经散架,鞋面的织绣部分已经被小虫咬伤,好端端的一双鞋,就因为运输时的保存条件不过关而毁了。
这时候,张信哲找到熟识的古玩老板一打听,才明白原来织绣的保管工艺很讲究,因为绣制品本来就很娇嫩,空气太湿容易烂,空气太干又会变脆变薄易折断,除此之外,对光的要求也很高,由于传统织绣制品用的是植物、矿物染料,传统的定色技术遇光容易褪色或者发黄,得知了这些门道后,张信哲赶紧托人打造了一个超大樟木箱,把家里挂着的织绣取下来收到箱子里,这样既能防虫又避开了光照,充分延长了织绣的保存时间。吃一堑长一智,这下张信哲终于摸到了门道:收藏不能高调,要随着藏品的性子走。
然而织绣在整个收藏圈都很冷门,张信哲收藏路其实走得也很孤独。但这也给了他更多机会跟藏品谈心,每件藏品的背后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故事:出生的年代、历史的背景、原主人的故事,甚至是选色、工艺的妙处,都让张信哲着迷,为此他还恶补了很多历史知识,为的就是能够更好地估算出藏品的价值。
爱收藏的张信哲很快在圈里也出了名。2001年刘德凯邀请他和周迅出演电影《烟雨红颜》,为了更好地还原电影里的民国范儿,道具组准备了不少老物件,但张信哲一进组,就发现打火机的样式太新潮,男士外衣的款式也偏西化,可眼看着开机的日子越来越近,服装和道具一时间也找不到替换的物品。张信哲立刻赶回家,拿出了外公穿过的外套,和淘来的打火机、烟盒,有了阿哲的把关,导演也格外放心,电影拍到后半段,道具和服装两个部门经常拿着清单请张信哲过目,只有他点头说OK,他们才敢放心去置办。
但这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比如每次看宫廷剧,张信哲都会变成“挑刺哥”,服装不过关,道具太随便。就连好评连连的《甄嬛传》也让张信哲看得很跳戏,因为在他看来,生活在雍正年代的人物,穿的却都是同治年间的服装,女演员头上戴的钿子,也是道光年间才有的,就算皇帝穿对了龙袍,可衣服上绣的龙又不是雍正年间的。这些疏漏看得他患上了强迫症,最终只好强迫自己关掉电视,去弹首曲子换换心情。
收藏人生,教人断舍离
2016年6月,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展览现场,举办了一场明清织绣服饰展。这是张信哲举办的第三次织绣展览,从策划到布置总共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展品中不仅有嘉庆皇帝穿过的龙袍,还有同治年代的“大阅甲”,这些价值不菲的藏品,最终都通过现场拍卖找到了新的归宿。
辛苦搜集来的藏品就这么卖了出去,张信哲也有自己的想法:“作为收藏家,‘收’其实是为了‘藏’。一开始收藏的时候,我的确有这种观念,也有想收藏一辈子的宝贝。但是藏品多了,就发现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一辈子留着的,这些收藏品有点像是我的课本,当你学完这一级要进到下一级的时候,这个课本就用不着了,它们就等着跟别人分享,或者等着学弟学妹来用。”对于藏品来说,每位拥有者都是过客,它们不会只属于一个人,所以在该分别的时候毅然断舍离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断淘洗藏品的同时,张信哲的收藏观也在不断更新,与其把藏品束于高阁,不如让它们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他从欧洲跳蚤市场淘来的顶灯,就挂在饭厅正中央,书房地面的鲜红地毯,是他从北京亲自背回去的,客房里的床是当年杜月笙姨太太的睡榻,配套的化妆镜也是战国时代的铜镜。这些老物件将张信哲的家打造成了一个天然博物馆,每次好友上门做客的时候,都会笑言:“阿哲,我要坐明朝的椅子,用上次那只乾隆时期的茶杯。”
收藏帮张信哲练出了达观的心态,这也直接影响着他在工作时的状态,近年来唱片行业愈发不景气,曾经的“情歌王子”也逐渐被人淡忘,但是张信哲却从没有停止过对音乐的追求,他放下姿态向乐坛新人学习,选秀出身的华晨宇被他视作偶像、网游改编的电视剧《古剑奇谭》邀请他唱主题曲也欣然应允,这些新人新物在张信哲看来,只要是能引起他兴趣的,他就愿意去尝试一把,因为他早就放下了过去的荣耀,没有被“情歌王子”的头衔禁锢,而是以“音乐人张信哲”的身份继续自己在乐坛的追求。
因此,参加《我是歌手》时,他没有打方便好用的“情怀牌”,每次都整出了新鲜的“幺蛾子”:带来亲自资助的少数民族儿童合唱团、挑战劲歌热舞、甚至连卖萌的颜文字表情都学上了,这样一个崭新的张信哲让不少00后粉丝大呼“可爱”,对此他又调皮地回复“阿哲总能超乎你想象。”
当大多数唱片公司为了开源节流,不再给歌手发唱片改由网络打歌的时候,张信哲却自掏腰包推出了黑胶唱片《歌时代》,这种任性的做法其实还有点“曲线救国”的意思。因为经费来源都是他拍卖古董的所得,家中有一千多件藏品,加起来价值共计一个亿,而为了自己的音乐追求,张信哲能够随时舍掉它们,在他看来,音乐才是他最无法割舍的一件藏品。
从当年在老镇街头执着“捡破烂”的男孩,到如今用收藏来实现音乐理想的男人,张信哲跟各个年代的古董谈了几十年的心,经过不断地淘洗,最终也找到了自己归属。他说将来自己这些精心的收藏,都会捐给博物馆,而他自己最钟意的珍宝——音乐,也势必会永远地被流行歌坛铭记。
编辑/贺长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