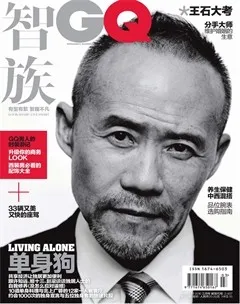赵梁 上山下山
穿长及脚踝的牦牛绒大氅,背柿子染的包,19年未剪过的长发飘在脑后,赵梁有一种不融于人群的气质。他知道自己特别,并致力于保护这一点——为了避免被人注目,他基本不坐地铁,实在没办法,就把头发藏进帽子,“要不然大家会觉得这是什么人?”
他很清楚自己是什么人。生活中百分之四十的时间他是卓有战就的舞蹈家,是中国第一个获得首届国际舞蹈比赛现代舞最高奖项“罗马奖”的人,刚二十出头的时候,就曾夺得国内专业舞蹈的各项大奖。最近几年,他连续创作了“东方灵欲三部曲”《警幻绝》《幻茶谜经》《双下山》等作品,令业内极为瞩目。
生活中另外百分之六十的时间,他一个人待着。没有人生角色,没有任何的身份隶属关系,只有自己。
为了更好地“待着”,他在北京附近的山上租了一栋300平米的平房。砖上刻着“1981年5月25号建成”,比他小了3岁。房子多年没人件了,很破败,赵梁重新刷了清漆,盖了厨房和厕所。堂屋地砖缺失了一大块,他涂上天蓝色的颜料,看上去好像地面上泼洒了一摊水。
他在看一本讲建筑的书,并考虑去学习古琴。闲时会打打坐。当卖菜的车开进村子里,拿着喇叭叫卖蔬菜,他就去买一点儿,再从山上拾些木柴烧。他是全村人议论的对象。大爷大妈经常用碗装着玉米茄子或者刀削面,门都不敲地进来看他,问,你穿的裤子为什么档那么低?像裙子一样。你是道士吗?不是。那怎么还不结婚?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不需要。
因为即使人与人之间简单的互动也令赵梁疲于应付。不管家庭还是伴侣,“她给你一个东西你要有反应的,你给她一个东西她也要回馈的。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需要你去花时间维护的,需要不停发生的。”
他过度敏感,家里不能放剪刀,看见尖锐的物品对着自己会很不舒服。“如果突然间有一个跟我一样、活的、一个会呼吸的生命体出现在我的房间里,我会觉得有压力。”他对我说。朋友来家做客,他能不留夜就不留。
于赵梁而言,这种对周围事物强大的感知能力,以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应该主要被用在艺术上,而不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日常生活。他12岁离家去学习舞蹈,19岁考取当时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并充分将自己感性的一面推至高峰。他会在下大雨的时候脱光了在操场上跳舞,或者把自己埋在跳远的沙坑里。一次户外的环境即兴创作,他跳了10分钟,“跳进去了”,开始吃土,“像个动物一样,就完全跟大地融在一起。”老师像抱着婴儿一样拍打他,好几个人压着他,他才慢慢恢复平静。
那是危险又近乎通灵的状态,他指着面前的杯子回忆,“好像我能够穿过这个杯子的感觉,好想叫。”
与万物通达的感觉,是赵梁创作的源泉。“我不是说靠某一种具体的方式而进入到创作的状态,我是靠这种打了引号的‘灵感’。那什么是‘灵感’呢?它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你不能够拿语言或者说拿标签去覆盖的感觉。”
他需要保持这种感觉,仿佛浑身布满了接收信息的天线,一个“你好、那个是谁谁谁”的社交场合,充斥着干扰自然信号的杂音。他会觉得自己太突兀,很难融进去。好像披头散发挤在下班高峰期的一号线地铁。
因此,混圈子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家在一起通常是喝酒、K歌,开心就唱一段跳一段,他试一两次就放弃了。“KTV我觉得是很妖魔的地方,”他说,“是人在宣泄的地方,喊,他们需要一个出口。”那里飘满了愤怒的、压抑的、自我膨胀的情绪,“我觉得很脏。”
24岁时,他放弃了去中央民族歌舞团当首席的机会,“那个东西拴不件我”。他渴望不被体制约束的自由,以及无法预知的、不受控制的人生。他开始一个人到处游历,去了云南、西藏,在30岁以前,去过三十多个国家。
在路上的新奇感,异国的陌生感,将熟悉生活中日渐懈怠的感官完全打开。他需要解决很多平日不假思索的问题,怎么找水喝,到哪里吃饭,路该怎么走。“你会有一种要去了解(的愿望),自然你的身体是张开的,你在捕捉很多东西。”身上的天线开始嗡嗡运转。“我觉得人就特别像个人。”
赵梁曾应瑞典国家剧院艺术总监之邀,旅居过瑞典两年。但他并不喜欢这个条件太过优越的地方,“像童话一样地在那儿待着”。他抗拒舒适的、单一的、稳定的东西,这些无法令他看到精神的丰富与层次。
他喜欢印度。有一年在印度过年,他在公交车上站了一夜到另一个地方,周身贴合着布满灰尘和汗液的人群。他到达目的地后洗了个澡,坐在瓦拉纳西的屋顶上看着朝阳下金灿灿的恒河,鸟在飞,印度音乐在吹,与昨夜的反差让他心中涌起巨大的幸福感。“你不吃苦的话我觉得你不会得到极乐。”
赵梁并非免于现实问题的困扰。他想创作,但苦于资金和资源的短缺;进入30岁以后,他发现结婚生子和房贷成为同辈追逐的主流,而这并非他的目标。父亲去世,死亡倏然成为生命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如何生活,又如何面对死亡?“是不是还要这么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地渫下去?因为我也会累的,而且我在那个点的时候有点儿玩累了。”
但是,“我的理想跟所有现实的东西完全是(反的),在现实里面我找不到我的空间,我的土壤。”
他开始自我怀疑,而这尤其令他惊惧,在他之前的人生经验里,从来没有过任何自疑。2012年,赵梁去西藏,和一位瑜伽士在雪山里待了二十多天。他们住在三百多年的木屋里,旁边就是悬崖。在静谧洁净的环境中,他感到身体又一次啪啪地打开。这次经历让他再度确认了自己的方向,去感知,去创作。“我觉得我赵梁一辈子就这样了,就一竿子到底,一定是这样的。”
赵梁在最近四年的时间里做了五部舞蹈作品,速度和质量令业内称奇。他处在创作的高峰期,之前十几年的积淀找到了出口,“像火山一样”。很多人告诉他,你赶紧做,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即便目前经费紧张,他也要把所有东西先做出来。
“我的作品就真的是我的老婆、孩子,啥都是。”他说。
现在,他的创作不再像当年在舞团的时候,常常进入感性到魔怔的状态,而是多了理性的层面。他试图锻炼出更强大的自我,来控制这两个维度的感知,以达到随时收放的能力。2012年,在《怪谈》首演后的会谈上,观众请他演“绿色”,他立即舞了一段,甩动过膝长发,沾上舞台上留下的片片羽毛,如春天的柳絮。
“什么样的一段舞是绿色的?”我问。
“我也不知道,你感觉是绿色的它就是绿色的了。”
赵梁并不善于描述细节,或者是不乐意。他不是作家式的创作者,迷恋叙述和自我剖析,他强调感知,并对自己的感知有坚定的信念。他的话语中常常出现抽象的词,这抽象本身是一种距离感。
“是不是任何一种颜色你都可以跳?”“应该吧。”
赵梁最近的作品是《双下山》,是由昆曲经典改编的舞蹈剧场。小尼姑色和空下山,色与小沙弥本无抛开枷锁,喜结良缘,空却疯癫了。如果前者代表着世俗的和谐,那么后者是极端的自我坚持。赵梁很难说哪个更接近自己,他把自己的两种意愿放大了,放在山上,给予它们肉身,它们就开始自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