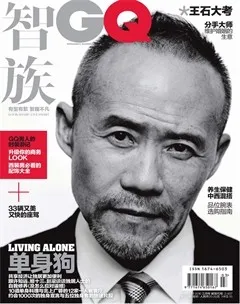熊小默:行走的盒子
在我的生命中,没有任何科技玩物能像Walkman那样让我神魂颠倒(甚至今天仍是)。这场青春期的膜拜之情恐怕不为我一人独享,一整代小朋友的手指都曾在索尼小铝盒的按钮上来回进退,读写记忆的磁道。摩挲着磨砂拉丝的外壳,穷究其自动搜曲的原理,享受着同学嫉恨的白眼,最后将它擦得干干净净放回皮套中——我们称之为幸福的—天。
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Walkman的重大意义:音乐曾经就像美景、西餐和春宫图一样,是不可以被移动着随意欣赏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如果你喜欢音乐,你必须跑到专门欣赏音乐的地方去,比方说音乐厅、俱乐部或者自家起居室。在1979年Walkman被发明之前,要是我打算在海滩上或者公园里嗨几下拍子,唯一能揣在口袋里的只有FM收音机,还得祈祷DJ千万别播徐小凤金曲回顾。
我很庆幸我出生在80年代,一个将“Walkman”收入牛津词典的节骨眼上。我曾经在狂风暴雨中听完了一整盘Enva:在春游的回程路上,和班长各一只耳塞分享了George Michael的“新”专辑《Older》(啊!此刻大型伤春悲秋!);我还用它录下了课间休息的一场幼稚谈话,几年后偶然翻出来时,竟还笑得花枝乱颤。在人生的随机安排中,听觉到达了不可预料的维度。
遥想这部精密、复杂、沉甸甸的小机器的诞生,来自三个日本人的全然不同的欲念:想在长途飞行中也能欣赏古典音乐的索尼工程师井深大,想掏空年轻人口袋的索尼总裁盛田昭夫,想要延长旧式录音带寿命的唱片收藏家大贺典雄——物质欲望和精神理想,毫不奇怪地盘旋在这件发明的头顶,如影随形。而我,便是为之魂不守舍的其中一员,前前后后我共买了11部Walkman,从最厚重廉价的基础款,再到由液晶显示遥控器操作的极高速自动选曲旗舰机,本身就是一段欲壑难填的历史。青春期的心心念念,让我至今尚能背得出这11部Walkman中大部分的型号名。
与大部分怀旧者不同,我并不是那种会被童年记忆蒙蔽判断的人,说句实话,磁带的音质糟透了。我很高兴iPod和MP3格式平地而起,将随身音乐推入了更清澈的21世纪。但靠着Walkman幸存甚至发财的音乐产业至今仍要记日本人一笔情,若不是无数盘九块八(常规磁带定价,另有部分是十三块八一盘)撑场,想要出头来唱歌给大家听的人会少很多。而我也惦记着自己的意外得益,雨衣里的Enva,以及一只耳的Georqe Mic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