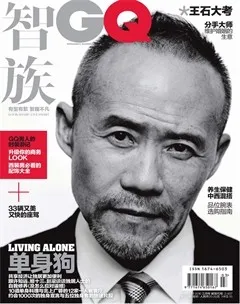编辑眼


时装周结束了,感触不多,倒是Zegna Couture的一场秀留了处反思,关于潮流走向何处,关于时装又是如何叫卖,先不管经济低迷是否会让时装秀乱了阵脚,走至如今一步,在大喊民主分享无成本的互联网年代,一场秀究竟要承载些什么,设计师的人格、市场的品性、圈内及圈外的互作用力又呈何种面貌,对,这是个问句。
Stefano Pilati的—场秀回答了这个问句:他把我们安置在了一个小剧院,没有故事与潮流作为噱头的老牌高级定制秀反而让我醒了神。哑副般的圆形灯光打在每一位模特身上,好莱坞黑白电影一样的气氛很是清醒。大家的目光跟随着模特的悠闲步伐移动,去欣赏他对细节与面料质感的追求,而不是掏出手机去拍那么两张吸人眼球的小伎俩。这是被大家遗忘的职业遭德,也是Pifati擅长的。刻画一件件柔美的外套是他的长项,一种理想化的老派与优雅,沉得住气的“自我陶醉”,这样的洒脱反而让当下聒噪的时装没有资格去较量。便是经典的力量,一种不需要喧哗却飘洒芬芳的魅力,也是当下困惑时代需要的节制声音。发布会结束后他对《智族GQ》坦白:“我展示一个系列向来很少用那些小诡计,它们会很干扰到服装的存在,这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为了几张社交网站的转发真的值得吗?”不知道是怎样的巧合,采访后没过多久,Zegna便官方发布Stefano Pilari离职的消息,我们的采访竟成了他在Zegna的绝唱,惊叹之余却觉合情合理,或许只愿老实做衣服的他真的还是未能适应当下的步调。
转过头来看自己的衣橱,虽然总是去购买季节性新衣,但其实放在前排的也就是那几件舍不得扔下的旧衣。它们有着明显的岁月痕迹,却也是我可以信手拈来的信赖衣物,因为它定义了我些许的生活貌相,虽然给予的并不再是那一刻带有冲动的心跳,但却是日久生情的老伙伴,说是一份情结未免太酸楚,可每当穿起的时候你依然会感激它的那份“合适”,经得起磨练与推敲,无论是车工还是剪裁,或是衣服上的某个细节,还有面料!对!懂衣服的人都懂得对好面料的珍重与感激,当然我也意识到这是变老的迹象,毕竟年轻的时代只需要顷刻的热恋,不求永恒。到现在都记得Tom Ford说过的那句话:“生活不改变,时装就不转变。”就是这么个道理,既然习惯了当下的生活方式就没有为衣橱更新换代的必要,也是当下浮躁时代需要的平和态度。不只是针对时装,而更多的则是人生。
我一直坚信,一个极端的昌盛便是另一个极端的崛起,这就是为何Maison Mmgiela和HM能共同存在的原因。前者诋毁消费文化,后者拥抱“时尚”二字,是很矛盾的时刻。但在时尚遍地绽放的今天却十分应景,整个产业飘动着奇陉的气氛,“Buy!Buy!Buy!”的宣扬性设计和你我衣橱里第一件大衣相比,却少了点儿毅然决然的态度。
两个废弃机场的不同命运
去年挺大一个遗憾就是未能在纽约TWA航站楼彻底谢幕前去朝拜,那是航空飞行辉煌时代的一座殿堂,而它要被改建成一个酒店了。好在,以后还有机会再见面。TWA跟泛美一样在飞行黄金年代都是美国主要的航空公司,它也是最先采用Hub制飞行计划的航空公司(spoke-hub distribution paradigm,说白了就是先把你运到某地再转运出去,所以你知道为啥有时你会在亚特兰大或明尼阿波利斯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转机了吧),而纽约的这个航站楼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使美国大陆人飞到欧洲大陆的启程地,所以美国建筑大师沙里宁(Eero Saarinen,1910-1961)赋予了它一双意欲翱翔的翅膀的形态。
无论外形还是内在,它的未来主义设计形式和感觉都高度统一,从街面走进中央大厅,你能从两三层楼高的流线型玻璃墙看到往来的飞机。TWA航站楼有当时多个创新:它率先安装了封闭式廊桥(沙里宁将它设计为三面白色,地上铺红地毯的戏剧性空间,赋予旅途启程结尾仪式感)、闭路电视、行李传送带等。看到TWA的各种细节如此和谐,你就能想到沙里宁所说:“永远在设计时考虑它之后更大的背景——一个椅子的房间,一个房间的一个屋,一屋的一所在环境,一个环境的城市设计。”
也正因为如此考虑,所以才有沙里宁为圣路易斯市设计的神来一笔:跨越半空的一条彩虹之门。这道高挑、充满想象力,仿佛飞来之物的“纪念碑”赋予了这个毫无特点的美国城市性格和生命。不过可惜的是,沙里宁没能看到TWA航站楼和纪念碑的落成。1961年,他死于脑科手术中。
说到废弃机场,就不得不提到Norman Foster老先生(北京首都机场T3设计者)眼中的“所有现代机场之母”的柏林Tempelhof。我第一次去这个已经废弃了的机场是夜里。记得当时北风呼啸中,突然一侧感觉有压倒性的气势:我一看就震惊了,一堵充满日耳曼雄性气质的“墙”绵延不断,排山倒海一样:因为车速快,你就会感到墙好像要压下来。这就是希特勒曾要求的“永恒”、“势不可挡”甚至“压倒性”的,能经得起“我们伟大信仰”考验的德意志未来首都的“世界机场”。
Tempelhof是注定要起飞的。早在1909年还没建机场之前,莱特就在这里试飞了全球首架量产飞机Model A,而因一战大幅刺激了飞机的发展,1926年,德国国家航空公司汉莎前身(Luft Hansa)也在Tempdhof第一次飞向天空。而转年到1927年,这里就已与柏林地铁相连。不过,不坐地铁也行,因为这是少有的机场建在城中心的例子,离柏林“王府井”只需骑车15分钟便到了。
可能命过硬,在整个柏林几乎被炸平的二战期间,Tempelhof甚至躲过了一劫。不过之后,它上演了分裂历史中的无数悲欢离合。2008年关停之后,它变成了柏林人民的大公园:民众在那儿放风筝和野餐。而当政府提出要重新规划机场旧址,甚至搞了个全民公投。你猜怎样?柏林人当然本能地投了反对票。不过历史演进,Tempelhof的命运也在不断改变,现在和将来的很多年,这里被规划成了难民营……
互联网没把我们逼疯的话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比环境变糟更可怕的是人类变蠢
在物质上面,我更相信《三体》的描述,未来没有那么糟糕,是个丰富、有序的世界。在很大范围上说,人类不会变得越来越蠢……这一点比“环境没有变糟”更加让人欣慰:很有可能,你可以住在干枯的河边,但你一定不愿意跟一群蠢货住在伊甸园里。
有趣和毒舌不再是媒体的政治正确
网络、平面,和刚刚开始的时候很不一样。我有点儿忘记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都在决意追求有趣。新闻不能严肃,要有趣。文章不能平淡,要有趣。选题不能太重,要有趣。图片不能随便找,要有趣。排版不能呆板,要有趣。“有趣的、好玩儿的”已经变成了媒体的“政治正确”,这种情况连续了几年,让我感到疲惫,反而想变成一个无聊的人。
人人都看书,不看就送去急救
即使通过科技手段,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到的所有资讯,最后能够被加载到视网膜上,但读书会作为一种类似“接种疫苗”般的存在。科技让获取信息变得决捷,但这并不代表信息会让你进入更加有效的思考,纸书则增强了这个功能——这一点即使在2015年之前的研究里也已经得到了证明。“你知不知道你不看书会影响整个人类的进化?!”希望你放弃读书的时候,会有医生对你说。
做自媒体的人可以有两种性格
不管是通过人造闪电把你劈一次,还是通过药物进行灵魂撕裂,希望干自媒体的人可以拥有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性格。互联网上的那个你再也不是表演出来的那个你,而是真实的你。就好像我在互联网上是真的精神有问题,但日常生活里就真的再正常不过(吧),没有谋面的人喜欢你变成神经病,但你周围的朋友必须跟一个正常的你在一起,这样两边可以互相不耽误。
虚拟网络规定社交配额
也就是说,如今你不得不维持微信朋友圈里800个联系人的生活,将成为教科书上的历史。“这种情况甚至衍生出了‘虚拟社会学’这一学科,涵盖心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却是一种圈养性的社会体系:人类第一次将近亲、合作者、谄媚者、性关系、陌生人等进行边界清晰的分组,但很快被法律禁止。”我们的后代将会在教科书上读到这样的描述。没什么好解释的,这段历史甚至像战争一样,残害着平民百姓的心灵。
评判人成功的标准不再是你奋斗的成果,而是你有没有时间回家吃饭
换句话说,无法掌控吃饭时间的人生会变得非常廉价。你见过很多厉害的人,他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不断用自己的业绩定义成功,但他们过得非常辛苦。“辛苦”在未来的价值体系里是一种被耻笑的状态,正常人无法想象,一个每天吃速食或者应酬的人凭什么说自己成功?所以“Slow food”会成为新中产阶级的门槛。
有的时候,阶级感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自我告白。当你有足够能力安排时间的时候,会把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留给读书和吃饭,这仅有的两种让你吸取生命养分的事。
人们可能会在波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范围内达成成功的统—标准:有没有可能推掉客户的饭局,有没有可能不为了赶时间吃公司楼下的快餐,而是坐在家里吃一顿没有人给你敬酒的晚饭。一顿饭吃得很慢很慢,吃到你妈或者你老婆都忍不住骂你:“吃那么久,一会儿谁洗碗啊?!”
呐,这就是你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