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旅游
“爸爸,您在‘荣誉公民之家’一定会得到很好的照顾。”比尔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
“敬老院”,有人认为这个称谓对老人不够尊敬,于是又想出了一个新名词——“荣誉公民之家”。“敬老院”也好,“荣誉公民之家”也罢,其实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本质上什么都没有变。我可不想和一群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住在一起,在相互打听诸如“你领多少退休金”之类的无聊问题中度过余生。当你刚刚把一扇小窗户推开一道缝隙,想通通风,换换气时,尖叫声、吼叫声比新鲜空气流通得还快,此起彼伏地传过来,“刮风了……”
我一直认为,我任何时候没给任何人添过任何麻烦。在还能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帮助儿子比尔,时常给他点钱。当他和他老婆搬到我这儿住的时候,我没有发过一句牢骚。想起来了,一次忘了关上冰箱的门,一次忘了放掉浴缸里的洗澡水,只做错过这两件事情。莫非错误很严重?只因为这两次错误,我就必须住进“荣誉公民之家”?!
比尔,住“荣誉公民之家”,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你这个古怪的家伙。古怪的人总是冒出古怪的想法,做出古怪的事情。唉……
打开衣柜,我在里面翻来翻去,想给自己找到一件合适的外衣。手指碰到一个光滑的拉手,我下意识地抓住它,往自己跟前拉了拉。挂衣架的横木因为干裂发出噼啪的声响。一只沉甸甸的箱子,连同一大堆衣服一起被拖了出来。这是父亲的箱子,水牛皮做的,牛皮表层因为加工独特而显得珍贵。这样的箱子现在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
忙碌一阵子后,我终于打开了箱子上的锁。我掀开箱盖,只见放游戏纸牌的皱皱巴巴的旧盒子、棒球和棒球手套……一个男孩子应该有的标准装备,一件不差、整整齐齐地码放在箱子里。丝丝快乐,淡淡忧伤,段段往事,我摩挲着孩提时的玩物,所有的情感一下子涌上心头。一个黑盒子里面保留着几张女孩子们的照片,照片是从什么地方剪下来的,上面没有一个字。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发现我的小秘密后,狠狠揍了我一顿。现在想起来,我还隐隐感觉身上好像有点疼。这是我的笔记本,里面有我写的诗,处女作……毫不自夸,当年的诗作还相当押韵呢。
笔记本掉在了地上,我弯腰去捡。衣柜门敞开着,我突然感到,一堆衣服后面,有一双眼睛透过缝隙,正偷偷地看着我。
贝拉!贝拉是我的机器人“阿姨”。
我小时候,机器人“阿姨”非常流行。有钱的或无闲的人把她们领回家,照看自己的小孩。贝拉是首批家庭机器人“阿姨”中的一员,对我们家来说,她是必需的奢侈品。其他小孩是在玩具世界里长大的,而我则是在机器人“阿姨”的呵护下长大的。贝拉是我的“阿姨”,也是我的玩具。贝拉奇特、长长的手臂足够摸到膝盖,我和她玩,像和猴子玩。
我出生不久,妈妈就病逝了。父亲面临的选择说起来非常简单:要么在家照看儿子,可是留在家里,钱从哪儿来;要么出去挣钱,保证家里有钱用。父亲选择了后者,从事三份工作。
他日日操劳,含辛茹苦把我培养成人。尽管我没在名校读过书,但最终没成为问题少年,更没有堕落成酒鬼。
可成年后我离开了家,外出打拼,没再回来,直到父亲去世。父亲用心收拾好我的东西,保留在箱子里。
我小心翼翼地把机器人“阿姨”从柜子里抱出来,放在地上。
贝拉双脚稳稳当当地站着。1米多点的身高,现在勉强到我的腰部,小时候,我以为她是巨人。贝拉的两个前臂粗一些,一只里面安装了罗盘,另一只里面安装了表。事实上,这些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我们经常玩疯了,忘记了时间,父亲不得不到处找我们。贝拉手上只有三根手指,看上去非常不靠谱,我还记得,贝拉怎么用另一只手弯曲铠甲来打赌。她的腿短短的,只有30厘米,但这样的长度才合理,否则,小孩子怎么追得上“阿姨”的脚步。
贝拉,我和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多快乐的时光!如果我的儿子像我一样,是在机器人“阿姨”照看下长大的,我现在也就只好住进“荣誉公民之家”。
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离婚后,伊丽莎白带走了儿子比尔,因为孩子的教育离不开妈妈。他们想到我,只是在需要钱的时候。我不知道前妻向儿子灌输了什么,这个小兔崽子断然拒绝见我。我敢打赌,这个恶婆娘一定插手了我养老的事情。
“喂,老伙伴……我们认识好久了,算是老熟人了。”我一边对贝拉说,一边兄弟般地拍了拍她的肩头。
“马蒂……”
我吓傻了。
“你是马蒂?真的是你吗?你在家?”
我惊呆了。
我不知道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机器人“阿姨”身上的电池到现在还有电,所以,贝拉通过这张老脸认出我,认出我是当年她照看的那个小男孩。
我,满脸的皱纹,眉头紧锁,眉毛杂乱。稀稀疏疏的灰白色头发偏向一边,梳理得还算整齐。松松垮垮的皮肤包裹着的脖子,一半塞进方格衬衫领子里面。针织套头外衣,尺码大几分,像只口袋套在我瘦削的身躯上。落有斑斑点点牙膏的便裤,在腰间用皮带卡子紧紧勒住。面对40年前的旧相识,如果是我,脱口而出“你是……”,未必做得到。
现在,许多人藐视机器人,因为机器人不是“互联网+”。
我在衣柜里又匆匆地乱翻了一阵子,找到充电器。当贝拉笨拙地随意摇摆脑袋时,我给她接通了电源。
输入新能量后,贝拉渐渐地活跃起来,“马蒂,我们一起玩吧!”
我舔了舔干裂结痂的嘴唇,“现在,不行。老伙伴,等一等。充一会儿电,我们再一起玩。”
贝拉高兴地挥舞着双手,“我们去旅游吧,马蒂?”
看着机器人打手势那有趣的样子,我蹲下身子。“旅游,我年纪大了,走不动了,贝拉。”看见机器人突然僵住了,一动不动,我急忙又说,“我们以后再去吧。”
机器人“阿姨”还没来得及难过,就进入了程序。
“你今天吃午饭了吗,马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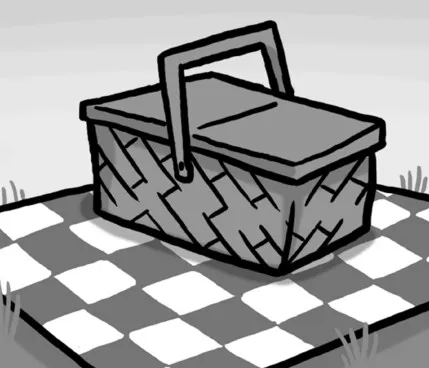
我缩起脖子。这带有几分责怪的腔调,暌违了。
“你今天吃午饭了吗?”这是机器人“阿姨”乔·尤金的经典名言,也是她最经常说的一句话。乔·尤金是我小时候家喻户晓的小明星,她成功地出演了几部喜剧片,赢得21世纪所有妈妈的心,妈妈们认为乔·尤金是她们孩子学习的好榜样。
“我们最好玩一会儿捉迷藏。贝拉,你逮我。”我建议说。
贝拉挥了挥拳头,表示同意,然后假装用双手蒙上眼睛,一、二、三地开始数数。
我走进卫生间,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我在自己家里吸烟,却常常惹恼儿媳。她喋喋不休,大发脾气。现在好了,无所谓了。
任何可怕的事情都不会再发生了,再也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相反,当发现父亲装满我小时候东西的皮箱,发现小时候看护我的“阿姨”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过去的日子。为什么这么激动?莫非我不想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家?
我在这个家里长大,家里的每一个细节,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木板地怎样吱呀作响,大风怎样穿过窗户缝隙吹进来,月光怎样照亮一个又一个窗口。
我的居室在二楼,楼梯右边。临窗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一台电脑,床铺依墙而放。走廊尽头是浴室,浴室和卫生间合为一室。这里才是我的安身之地。厨房在一楼,记得我常常在夜间“设宴”犒劳自己一番。厨房旁边是漆黑的小库房,那里,我能不去就不去,多一眼也不想看。后院是我和贝拉整天玩的地方。
为什么我要离开这里?
我倚靠到墙上,神经质地吐出烟雾,反复地问自己。
当贝拉说“马蒂,你在家?”时,她为什么如此惊讶?
吱呀,门开了。开门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找到你了!”贝拉说。
贝拉背后拖着电线。
“喂,接球!贝拉,接球!你怎么像根香肠,不堪一击。”我大声地喊叫着,把球抛出去。
贝拉,戴着棒球手套站着,笨手笨脚地试图接住球。显然,贝拉老了。几十年前的老机器,又长时间没有运转,显然,迟钝了。
“你太不厚道了,马蒂,用这么大的力气扔球,疯了。”贝拉任性地回答道。
“40年前,你就是这样和我说话。”我嘲笑她说。
贝拉从地上捡起球,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
“我们去旅游吧,好吗?”她出乎意料地问我,把球抛回来。
我恰好接到球,又把球抛回去。
“不,我们不去旅游,贝拉。”我喘息着答道,“我和你从来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为什么你突然想起了旅游?”
贝拉沉默不语,然后,捡起球,又把球抛过来。
“我们去旅游吧,马蒂,和我们一起去旅游……”
突然,我的后背上有一种令人难受的蚂蚁爬行的感觉,随后这种感觉遍及全身。我停顿了片刻,猛地向贝拉扑过去。
“和谁?和我们?我们是谁?”我急急地问道。
贝拉不说话,垂头丧气地低着头。看得出,她在犹豫说还是不说。
“和谁?和我们?我们到底是谁?”我几乎吼叫起来,重复地追问着这个问题。
贝拉还在犹豫。
“贝拉!你想和谁去旅游?”我有意拖长声音问,像是央求她。
贝拉猛然抬起头,两眼放出了令人生畏的光。
“和你,和爸爸。”
我用手握着球,手指关节咯吱咯吱地响。
在离开家之前,我和父亲大约每个月旅游一次。说是旅游,其实是郊游、野餐,从来没有在外面宿营过,每次大约也就四个小时。我们一大清早出发,爬爬山,在树林里坐一坐,狼吞虎咽地吃块三明治,大口地喝杯咖啡。我做每一件事情时,父亲从来都没有表现出兴趣,甚至索性一言不发,也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山里的空气寒冷却也新鲜,里面散发出三明治奶酪和咖啡的芳香,我们带来的味道。其实在这样的时候,能够简简单单地坐在一起,也就足够了。
如果我们没有带她去旅游过,该死的贝拉又从哪里知道旅游的事情?
愤怒取代了慌张。
“你从哪里知道的?”我大声喝问道,“你怎么知道旅游的事情?”
“爸爸带我去过。”
“闭嘴!我是问你怎么知道的。”
“爸爸带我去过。”
我使出全身的力气举起球,向贝拉砸去。随着轰隆一声,贝拉应声倒在了地上。
“爸爸带我去旅游了,你这个大白痴!”贝拉委屈地喊道。
随后她又什么话也不说了。
有一个声音隐隐约约地传来,是父亲的声音……
我跪倒在地,向童年小伙伴的身边爬去……
球碰到了贝拉身上的一个按钮,她身上的屏幕亮了起来,开始播放视频记录。
“怎么了,贝拉,这里真的很高吗?”父亲问。
我看见了山,是我和父亲曾经去过的那座山。父亲,越发苍老,他端着一杯咖啡坐在一块较平的石头上。绿色麂皮绒夹克外衣的扣子紧紧扣着,一粒也不少,直到喉咙。寒风凛冽,毫不怜悯地吹动着他灰白的头发。绒裤裤脚扎进高帮旅游鞋里。
“马蒂和我们在一起吗?”父亲向贝拉身上的摄像头看了一眼。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多么想和你们在一起啊!
“好了,我们回家吧,好吗?”父亲说着,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房间里异常昏暗,沙发上躺着一个人,一床被子从下巴盖到脚。传来金属般的沉闷响声,我想,这是有人在咳嗽,不免心里怕得发慌。贝拉用三根手指的手端着一碗清汤,但是父亲只想翻翻身,继续躺着。
“爸爸,您应该吃点东西了。”贝拉说。
又是一阵吃力的咳嗽,这次父亲坐起来,接过那碗清汤。
“谢谢你,贝拉。”他感激地说。
我没有想到,父亲病得这么严重。
我收到公证人从邮局发来父亲病逝的消息,直接来到公墓。为什么他不给我打电话?为什么不让我回来看看他?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地问一问他近来怎么样?
贝拉可谓用心良苦,我终于明白了。我轻轻地爱抚着她的脑袋,她是我的真“兄弟”。
“老伙伴,和你比,你才是他的好‘儿子’。”我看着贝拉两只无神的眼睛,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没有机器人‘阿姨’,如果不是贝拉比自己的亲儿子还亲,住‘荣誉公民之家’,总比一个人孤独地死在家里好。比尔,算是白养你了。”
突然,贝拉的眼睛忧伤起来。
“什么是‘荣誉公民之家’,马蒂?”她问道。
我想了想,希望能够给她一个准确的定义,“像废品回收站,是没有用的人去的地方,贝拉。”
贝拉疑惑不解,但没有再问下去。
“我不想去那种地方,”她终于做出决定,“最好我们去旅游,马蒂!”
我擦了擦眼泪,笑了笑。
“好,去旅游。贝拉,我们一起去旅游。”
我身穿滑雪服,左手拿着滑雪板,右手领着贝拉三根手指的手,我要带贝拉去滑雪。因为贝拉,我不得不弯着身子。背上的行囊里装了一大壶咖啡和两块三明治。
如果比尔坚持认为,我时常会做出古怪的事情,最好住进“荣誉公民之家”的话,那么我以为,我不如和最好的朋友去旅游。不,不是最好的朋友,是最好的兄弟,哪怕是最后一次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