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与哲学相遇,是一生幸运
王立群
他没有读过大学,如今却是山东大学被学生尊重喜爱的师者;他研究哲学纯属“半路出家”,如今却成为山东大学哲学研究的旗帜性人物;他化玄妙为平常,变枯燥为生动,将哲学的运思轻松地传授给后来者;他已硕果累累,却总叹不甚满意,未有代表性成就,称自己一直在路上;他在哲学的世界里安家,以思考本身作为生存方式,在世俗看来或寂寥、贫困,或无聊,但在他的眼中,与哲学的相遇,是一生的幸运所在。他,就是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
半路出家,一点儿“传奇”的味道
10月底的济南突然降温,外面天气很冷,但何中华教授的小屋温暖如春。乍一跟他相见,你就会感受到他浑身上下所散发的儒雅气质。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谦逊地看着你,随时准备聆听你的想法,让你感觉跟他相见,能够把你心中所有有关哲学的问题与他探讨,而事实也的确如此。
山大一直人才辈出。今天,你随便抓住一名山大的学生,问他臧克家何许人也,他一定会给你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个传奇般的故事:上世纪30年代,时任山大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破格录取一个数学0分的考生,众所周知,这个考生的名字叫臧克家。那种浮现在山大学子脸上的骄傲,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晓,山大破格录取人才的传统,不仅限于学生,也存在于师者。
“我是半路出家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有点儿‘传奇的味道吧。”直到今天,何中华依然能清楚地记起30年前那个初春上午温暖和煦的阳光。山东省莒南县委宣传部的办公室里,一位素昧平生的陌生学者的到来改变了他的人生,那个人就是时任山东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周立昇。周立昇先生此行的目的明确,考察何中华,并表达将其调入山东大学工作的意向。
“因为事先未经联系,周先生一行的突然到访,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没有任何心理准备,所以深感十分意外。”何中华回忆说。这颇有乡野寻贤者劝其出山入世开创一番事业的故事在当代就这样真实地发生了。
或许,最让何中华意外的因素,不是周立昇先生的突然到访,而是自己的“出身”。“我没有读过大学,只是高中毕业而已。1978年高考落榜之后,在当地一家化肥厂就业,后来又换了几个单位,如供销社、县委宣传部。”是什么引起了周立昇先生的特别关注?“因为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爱好哲学,平时喜欢思考一些与哲学有关的问题。有了些想法,便诉诸笔端,遂写成文章,投给有关刊物,像《国内哲学动态》《哲学研究》等专业杂志。发表了几篇文章之后,在学术界有了一点儿影响,被山东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们发现了。”何中华的回忆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清楚,能够让一位一等学府的院系教授登门邀请,这需要怎样的“一点儿影响”?
1987年6月,在周立昇先生的努力下,何中华正式调任山东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何中华正式踏入学术圈,开启了一条与此前迥异的人生旅途。
“野路子”,哲学研究的“双刃剑”
从1987年正式进入山东大学至今,刚好30年的时间,30年中,何中华从一个“半路出家”的学者变成了颇具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并非科班出身的何中华曾笑谈自己的哲学研究是“野路子”,如此一来,其与正统哲学的学术研究自然存在不同。“首先要强调,正统的哲学研究应该是‘学院派风格,研究者需要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和较长时间的训练,有一套完备而严密的‘学科规训,或者说库恩所谓的‘范式。做出的成果,严谨而规范,或者说是合乎哲学的行业标准。”但是在他看来,这样的正统之路也存在其缺陷,“这就是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哲学变成了‘学院之事,越来越与研究者自身的生命和生存本身相脱节,沦为研究者的身外之物。而哲学本应该是切己的生命之学。”
“自学者的长处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的限制,思想更加自由而发散。”何中华表示,“记得钱钟书曾经调侃道,在学术上勇气来自无知。不过这句话也有几分真实。知道得太多,反而有可能窒息标新立异的冲动和能力。譬如,一个翻译家往往写不出自己的东西,因为他已经被所翻译的作品征服了。据说西方前卫派画家不敢进卢浮宫,因为当他了解了古典大师的作品后,就失去了打先锋的勇气。由此看来,‘无知也是一把‘双刃剑。也必须承认,自学者同样有着不可忽略的弱点以至于缺陷,最主要的在于他们缺乏系统完备的专业训练,基础不那么牢靠,知识面不够宽,知识结构往往有些畸形,思考问题的规范性较弱。真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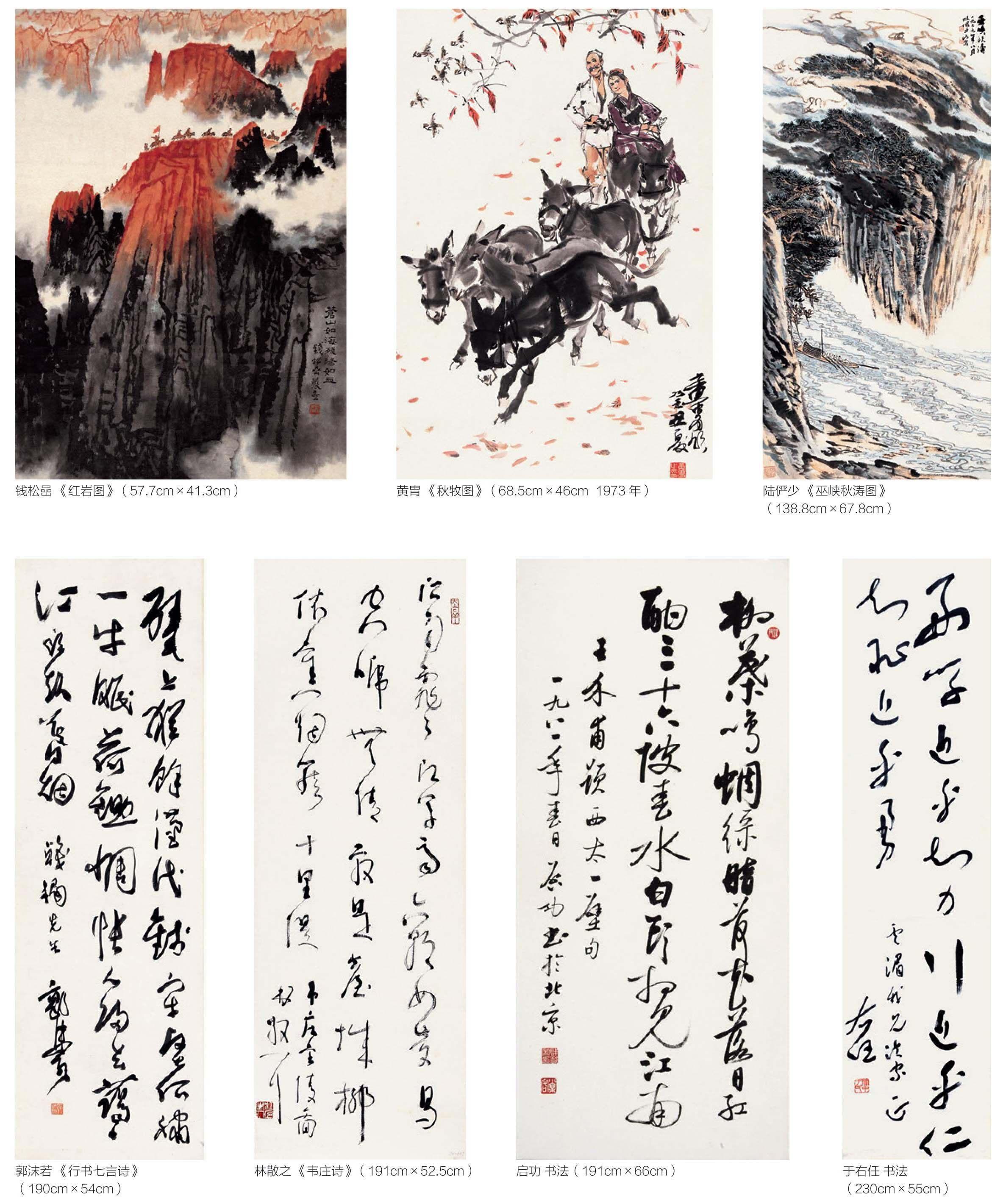
无论是“野路子”还是正统的“学科规训”,完全投入哲学怀抱的何中华是幸福的,当周立昇先生找到他时,“我突然意识到,有机会过一种沉思的生活,是埋在自己心底的一种虽隐蔽却又十分强烈的渴望。”之后的30年,他投入了一种自己喜爱的“沉思的生活”之中,“这样一种生活,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也许是寂寞的、贫困的,既无聊,也无用,因而不值得选择。但是,我对这种生活却有着一种执拗的渴求。与哲学的相遇,应该说是我这一生的幸运所在,也是自己在心灵上找到安心立命之所的皈依。所以,逗留在哲学中,在思想中‘安家,以思考本身作为生存的方式,对我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诗与哲学,生动却难以臻于完美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哲学是无聊的,这种成见,让哲学成为枯燥和神秘的代名词。但是,在很多山大的学子们看来,在何中华教授的课堂上,哲学是精彩的。有学生曾如此评价:“如果说魔术师是把平常的事物变得玄妙的话,那么何老师则是把玄妙的事物化为平常。”
在何中华看来,哲学本身就不是枯燥的,她是一种“像人的生命般鲜活的、富有灵性的智慧”。在教学中,何中华做过一些尝试,他喜欢由问题切入,不愿把哲学讲成高头讲章般的“学问”,而是注意从每个人切己的问题出发,诱导听众运用自己的心智去思考和处理这些问题。“哲学绝不是通过背诵答案而形成的知识堆砌,而是通过实际的思考而习得的运思能力。”何中华教授喜欢举例子,以例子来“说明”深刻的哲理,“可以诱导人们比较方便地进入哲学语境。”“当然,例子在哲学中并不是逻辑的,而是修辞的,也就是说它的功能不是‘证明,而是‘说明,这一点同实证科学不同。”何中华说,“譬如,要领会王弼所谓的‘物无妄然,必由其理,也就是存在者之所以能够‘是其所是,都是由于它有自身存在的理由。没有理由的东西是无法存在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制造一辆汽车,而不能够制造一台‘永动机?其差别就在这里。真理往往是朴素的,所谓‘大道至简。故弄玄虚大可不必,它不仅败坏了哲学的名声,而且也戕害了哲学同生活的联系。”
在何中华教授的世界里,哲学是如此多姿多彩,但是他的现实生活呢,似乎与哲学“换位”,变得稍微“单调而枯燥”了一些。2015年末,在回忆周立昇先生与自己的知遇的文章中,何中华曾说,好的哲学家就是好的诗人,好的诗人也是好的哲学家。那么何中华自己呢?“就我本人的性格来说,缺乏诗人的浪漫情怀,生活中也没有什么诗意。”在他看来,哲学与诗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相通的。“如果说,哲学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心灵的还乡;那么,诗则是在艺术层面上的寻找家园。因此,哲学与诗具有同构性。”“另外,哲学所把握的那个绝对之物,也只有借助于诗化的语言才能够被恰当地表征出来,它需要的不是指称,而是隐喻和象征。而这种表达方式,恰恰是诗歌所固有的最为典型的修辞手法。”
但是何中华教授的生活,“除了读书、思考、写作,除了本职工作,业余爱好几近为零。这也许是做哲学之所以难以臻于完美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难言满意,学术一直在路上
曾有人罗列过何中华教授的哲学研究成果: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提出建立哲学学体系的构想,并在元哲学领域进行了探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方面,提出由物质本体论为代表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向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的转变;对发展和现代化理论本身进行哲学反思,注重对“发展”和“现代化”范畴的形而上学前提的追问;对市场经济与道德及其关系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提出“互斥论”和“划界说”等等。诸多成果的取得,让何中华教授成为山东大学哲学学科的带头人之一;但是,对自己取得的所谓成果,何中华教授“并不感到多么满意,很难说有什么代表性的作品。因为我的哲学思考一直是在路上,在途中。”
在他自己看来,“比较有意思的,可能是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做了一点新的诠释。”“我是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实践作为本体范畴何以可能?我尝试着给出自己的一种可能的理由。在这个基础上,我进一步把实践同人的存在联系起来,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本身的最本真的建构方式,认为实践本体论只有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才是可能的。”何中华教授表示,“套用笛卡尔的那句名言‘我思故我在,马克思哲学可以说主张的是‘我实践故我在。”这方面已有的阶段性成果,大致体现在他的《重读马克思》和《历史地思》这两本著作当中。“当然,这个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中,远远没有完成。”
当下,何中华教授最为关注的依然是马克思哲学的重新解读,试图在今天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做出属于他自己的“有点儿新意的阐释。”“具体地讲,就是从现象学角度去领会马克思哲学及其内涵”,“马克思同康德的思想史联系,也需要深入挖掘。康德在知识论范围内提出的核心问题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语境中隐含着一个类似于康德式的问题,只是马克思把它作了根本的改造而已。“马克思的问题是‘超验规定的历史建构如何可能?但迄今为止,学界对此几乎未曾触及。”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也是何中华教授持续关注的问题。另外,他表示,“我还想亲近中国古典思想。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落叶归根。其实,一个人在思想上也没有办法逃避这个宿命。所以,我还想就中国古典思想的咀嚼和领会方面做出自己的一些努力,力求对此得出一些有意思的新的体认。”
显然,在自己最喜爱的领域里,何中华为自己预设的道路依然很长,这是幸福的跋涉的旅程,更是幸运的思考的旅程。
(未署名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