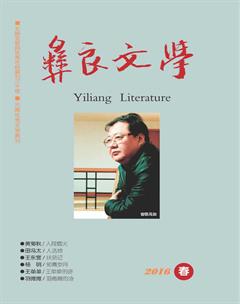铁柔的诗
铁柔
父亲笑了
记忆开始之初
他是集体农具厂的一名铁匠
每日,往胸中灌注铁水
在人世锻打骨头,皮肤黑红,发亮
农具厂倒闭后
他是一名水泥装卸工
汗水,以吨计;工钱
以毛计。一袋净重五十公斤的水泥
他从一楼,抱到九楼
像抱着自己尘埃未尽的骨灰
身子挣岔气后,重活做不了
他成了保洁公司的一名清洁员
哥几个,像空降兵
清洁发电厂烟囱
厂房外墙,和办公楼的玻璃
从未听他提起恐高,也从未
见他冲着地面上的我笑
我儿子出生那天
他请假,从高空下到产房外侯着
一阵啼哭,推出来,他的小孙子
这一次,他笑了
盯着襁褓中,还未睁眼的小脸笑
伸出干瘦有力的手,轻轻抚摸着笑
这偷渡而来的老天使
站在廊道五月十一日阳光充溢的窗口
特地为此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
抱儿子看落日
在老家,在阳宗海边
抱儿子看落日
让他看一看
太阳,到了最后
也是红的
照着这片苍茫的水域
清晨一样新鲜
我抱着我儿子
他就要满周岁
就要行走与表达
让他骑在我脖子上,像骑着
一根结实树杈
够着,看一看
落日沉下的山岗,是老家
漫无边际扩散着的坟场
人间的余热,仍在温暖死亡
我抓紧他的小手
像握住,那即将消逝的光芒
暮色涂抹群山
身体里的黑,愈加浓重
他被即将降临的夜吓哭了
他禁不住在我肩膀上撒尿
越来越远的哭声中
他指着点破一湖静赤的二三水鸟
咿呀不清地发声
我站着没动
想变成岸边一块古老的顽石
让他坐着一次看个够
在他进学堂之前
抽烟喝酒之前
失恋之前
在老家,那么多逝去之物
借助这仅剩的余光
向我传递微弱电流的激动和忧伤
我抱着他
如抱着我的祖父,曾祖父
抱着冬日田野的一丝热气和稻茬
我用笨拙的逗哄
让他在我怀抱里破涕为笑
抱着他,当落日完全坠下后
走在返家的路上,像抱着
这些年流落的一盏灯
像抱着自己,还童后的惊异,羞愧
冬日:下午三点半的阳光
抬起头,才发现阳光
去了街的那边。先前来人
还赞美一番的这棵文竹
不知不觉沉浸在阴影里
翠绿着,但不再欲滴
此刻,那边内衣店牌坊熠熠生辉
银行人满为患,梧桐整齐排列
巨大光瀑下,朝天空喷溅秃枝
像一把把赎罪的伞骨
汽车似绝尘而去,但静观
它们仍是鱼贯而行,奔赴时间驿站光的栅栏里,荡起
灰尘密密麻麻的鬼脸
——那边某个人也许我认识
像一棵被忘了在秋天收获的向日葵
阴冷办公室里,我不由自主转动
椅子的方位。她在阳光里攒动
辽阔而孤独
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怎么去爱
有一段时期我不知道怎么去爱
我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跑了
一个变节和强盗、背后有一个伤心男人的
故事
就是这样
我跟随我爱的女人来到
身后云南,抬眼就是四川的金沙江边
江水宽阔、缓慢,怎么流
仿佛都在原地打转
悲愤的落日一次次投入江面
一次次,想落荒而逃
就是这样
我跟随我爱的女人来当恩爱的乡村教师
恩爱没了,乡村教师一直在着
用湿枕捂着脸注视
命运的孽缘在门缝肚子里越来越大。就是这样:爱被调包了,操场上公然漫步
多少个暮色,蟋蟀不厌其烦练习我的叙事曲放眼皆巨岩、峭壁。睡觉的时候
常常梦见大地裸出山体的伤疤
我固执地认为,爱有一个结果
一个具体的事物
后来我常常冲着山谷啸叫
里面,的确传来了回声
我起的很早,爬上一块上好的岩石
对着蓝天唱 《向往神鹰》
后来,我爱上了金沙江
广阔山野,以及我的十三个小学生
——就是这样:每天我得以生活在童年的
岸边
陌生女人的哭声
已经半夜三更
为什么还要哭?
哭,有什么用?
别人都在睡觉
但她不这么想
她坚持哭,断断续续地哭
像一只蚌,呜呜,呜呜
在吞吐夜时光的流沙
她的哭声在这家酒店
打开了一个窟窿
她把我惊醒,抛入其中
细听命运无止境的惶恐和孤独
她把我惊醒,我也睡不着了
但又怕耽误明日的行程
我该怎么办?做点什么?
我没听到过哭声已经很长时间
我想到穿墙术。我想钻进那哭声
手持蜡烛,在她面前露出
一个陌生人不再陌生的心
我想,以我的笨拙和耐心
等墙凿通,天就亮了
我就能真切看到哭声的源头
——她古怪一笑:我整夜沉浸于哭
原来整夜,也有一个陌生男人
默不作声挖着隔音壁
我还以为根本不会有人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