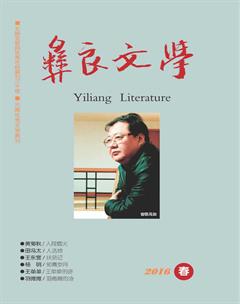向以鲜的诗
向以鲜
1970年的炸药
1970春天
聂家岩的香樟树打开巨伞
那真是无风的好日子
我偷走了一圈儿导火索
白云的棉线
缠绕住凶猛天性
让它在手掌中盘桓一会儿
像远山安静的暴风雪
然后以铅笔刀
划开闪电的断肠
空气中顿时弥漫硫磺
与木炭交织的呛鼻气味
收拾起满地黑色花蕊
沉于墨水空瓶底部
其上筑入一层
研细的干燥浮尘
当孩子气的危险装置
还未嵌进石缝之前
心中早已翻卷六月惊雷
我沉缅于想像中的日月失色
深恐转瞬即逝的爆炸
会毁掉邪恶的乐土
一只觊觎多时的松鼠
好奇地迫近观察夺命坚果
试验在惊惶中收场
除了轰鸣和烟雾
在枯树的上空停留
便是一道意外的伤口
1970年的炸药威力
一直刻于面壁之夜
玻璃碎片呼啸着
从我右眼角掠过
倘若在镜子前发呆
就能看见44年前的电光石火
正在缓慢地聚焦
谁也无法逆料
下一个春天下一次爆炸
会是什么样子
光明与黑暗合谋的炸药
从未停止化学反应
穿云箭
You are the bows from which your children
as living arrows are sent forth.
——Kahlil Gibran Children
差不多半个世纪前的夏夜
让人想痛哭一场的夜晚
那种苍白、万峰环绕的美好
那种贫穷的幸福感
是今天的孩子再也无法相遇的
烟霞山和覃家坝河
聂家岩的瓦舍、墓园和恐惧
一齐被母亲怀中的新月镀亮
父亲斜倚在陈旧的躺椅上
旁观着儿女们的游戏
我和小果神色庄重
俨然古代部落的猎手
眯眼虚拟着稍纵即逝的麂子
獐子或别的可疑动物
在水银乱泻的操场浮现
汗青弓紧绷麻绳弦
速度之外,最迷恋的
是那种弦外之音
晚风之中的弓弦振荡
比蜜蜂翅膀的高频轰鸣短暂
却微妙,更易激动幼稚的心灵
悲凉中蓄积力量
童年沙场,出征的旋律
从脏兮兮的小手弹射
当高梁箭杆掠过柳枝剪影
我们从父亲口中知道
世上还有一张神气十足的箭
曾为传说中三太子所侠盗
从陈塘关劲射天下
即使是高不可及的太阳
或隐居深渊的龙王
均为这支穿云箭之的
父亲娓娓道来的故事
虽然瞬间让我们手中的武器
变得羞涩又寒酸
却唤醒了沉睡的想像力
我和小果在睡梦中
踏着三太子的箭锋勇往直前第一次接近了苍穹
并试图领略无限的含义
父亲轻掸夏夜的尘埃和露水
母亲则躬身拾起散落地上
被随意抛弃的火烧竹制玩具
用衣襟细心包裹起来
像包裹一个弦月变化的秘密
于母亲而言,睡梦中的孩子
艰难拉扯成人的儿女们
才是她穿云痛心的箭
父亲的银卷尺
在錾花的老银表面
芝麻的黑点散布其间
如同星汉里的暗物质
以腐蚀的语言和恒河沙痕
与记忆达成默契
父亲与之形影不离
仿佛随时准备丈量
谷穗、麦芒的高度
或放学回家的孩子
山羊般跃过溪水的宽度
事实恰恰相反
卷曲的尺子很少展露容貌
从祖父传下来的小银盒
是父亲珍藏的一颗
不欲轻视于人的瑰宝
偶尔也会让儿女们握一握
当父亲郑重递出那团
亮如苍穹一隅的冬眠神物
我甚至能听到
沉睡的心脏在跳动
蛰伏在黑暗中心
并为数学或哲学问题所困绕
本是测量事物空间的工具
却成了时间的见证者
这的确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我不知道盘踞其中的
坚韧皮革如何测出
星光与睡梦之间的距离
如何测定鸟儿及蝴蝶
飞舞一世的长度
父亲心里似乎早有答案
所以很少抖开斑斓的身躯
银色阴影中,时光的野兽
隐约留下了线索
或许父亲一生
唯一测绘过的山川
是自己七十五年的苦厄
和最后要去的龙泉燃灯寺
在寂静的春天
打量尘封的银卷尺
仍然是我怀念的特殊方式
父亲,已退回到更小的银屋子
卷尺在握,万物皆有分寸
地主罗婆婆
最先引我好奇者
是罗婆婆的两枚金牙
那儿镶着上世纪六十年代
十分罕见的昂贵物质
即使浓烈的叶子烟
也无法使之变得晦暗
迫于反复纠缠与祈求
罗婆婆允许我伸出右手食指
小心触及标识身份的门牙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
接近不朽之物
在孩子的眼中
阁楼上的菩萨也是不朽的
菩萨与地主之间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
是统一的还是矛盾的
菩萨像地主一样美
地主比菩萨还要善
罗婆婆身上总是带着
某种神奇的力量
不仅源于她用熟读的
本草救过我的命
用阿司匹林、银针、苦菊花
各种充满幻想气质的偏方
阻挡农民的死亡
力量之源还在于
罗婆婆曾有位北大潘先生
被秘密枪杀的巴山才子
谈吐中也闪着金色光芒
这些事物汇聚起来
不断为乡村增加活下去的信念
如同聂家岩积雪
照亮吠声若豹的长夜
罗婆婆自己的力量
每天却在悄无声息地减少
她说:潘先生,久违了
在我离开聂家岩的
第一个春天,明月照积雪
罗婆婆终于化为涓滴
这将构成另外一种江河
比黄金更加壮丽,更加清澈
其溃防决堤的力量
也更加不可预知
核桃世界
——哈姆雷特:啊, 老天呀, 我可闭
于核桃壳内, 仍自以为是无疆限之王。
还是青涩的时候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大多数果实躲藏
于叶底。像喜鹊躲藏
于谜语或丛林
一颗、一簇、一树
好多丰收的歌谣啊
苦味的星辰缀满枝头
整个聂家岩的夏天都卷入
一场关于核桃的宗教
层层包裹:翡翠的袍
斑驳黄金支撑起
思想的穹窿
并以造化运行方式
无限接近玄学的丘陵
那儿白雪经年,泉水绕屋
世界突然恍惚起来
孩子与老人相互叠映
唉!核桃啊核桃
时光雕琢的崎岖珍宝
当我再次凝视
掌中油亮的阡陌之美
心中升起无限敬意
仿佛从另一个角度
重新审核自己
牛粪如烟
What did you do in the great World War Two?
You wont have to say
Well, I shoveled shit in Louisiana.
——George Smith Patton
在所有的动物粪便中
我唯一能接受的是牛粪
它不仅与传说中的黄金有关
更与低矮的房屋有关
有时候,还是治疗冻伤的良药
聂家岩的牛群三三两两
黄牛最英俊,常在松林间撒野
浓墨写意的水牛和孩子们欢叫着
点染外公守护的池塘
大地馈赠无所不具
牛粪裹着青草、尘土和麝香的气味
各种颜色的甲壳虫出入其间
那仿佛是另外一种独立存在
来自于反刍与回忆的世界
每一个腐朽角落都被太阳烤得透亮
这就不难解释牛粪之火
为何如此壮丽又暖心窝
值得思考者:一堆燃烧的光芒
常常来自于卑下之物
甚至是俯仰即拾的脏东西
犹记得和小伙伴的快乐游戏
当我们将手中余温未消的牛粪团
像酷毙了的巴顿将军一样
使劲儿摔到老墙上
牛的力量已转化为潜伏火星
只需一根瘦小的火柴
就足以点燃童年的落日孤烟
[注]外公鲜思喜的墓前池塘,是聂家岩的灌
溉蓄水塘,
也是夏日牛群与孩子们的天堂。
蚂蚁劫
近于虚无的遥远夏天
又大又黑的金刚战士们
举着剪裁得当的柳叶旗帜
向着落日堡垒飞逝
那片小小的沙化高地
雄关连着漫道,烽火照遍亭台
仿佛鏖战方休的埃及法老
眺望尼罗河颓废城池
更庞大的阴影及预感
来自于专心注视
天真烂漫的司芬克斯
突然焕发怪兽固有的残忍念头
酷暑中的秘戏巧妙又激烈
一方进退无方迂回有术
灵动的爪须如闪电
一方攻防恰到好处
在聂家岩小学的孤独球场边
儿童无端肢解一只
卑微又勇敢的动物
卑微得看不见一丝血迹
这情形并不罕见
并不比驾驶吉普猎杀曼德拉雄狮
或用高能武器击毁民航客机
多几分冷酷、少几分仁慈
棉花匠
迄今为止,我仍然以为
这是世上最接近虚空
最接近抒情本质的劳动
并非由于雪白,亦非源于
漫无边际的絮语
在云外,用巨大的弓弦弹奏
孤单又温柔的床第。弹落
聂家岩的归鸟、晚霞和聊斋
余音尚绕梁,异乡的
棉花匠,早已弹到了异乡
我一直渴望拥有这份工作
缭乱、动荡而赋有韵律
干净的花朵照亮寒夜
世事难料,梦想弹棉花的孩子
后来成了一位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