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极寒淘旧书
京城极寒淘旧书
Colum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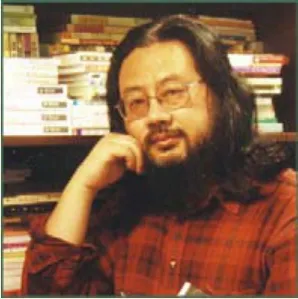
白壁斋,宏猷书房之谓也!
借《大武汉》一角,设书话专栏一,清茶一,书友三五,品茗谈书,岂不乐乎?开篇之时,东湖樱花正开,谨捧碧水书香,就教于读者诸君也!
新年伊始,又去北京讲课,正好撞上了三十年一遇的极寒。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六摄氏度,且寒风呼啸,地面上的塑料袋被风刮起,漫天飞舞。讲完课,正逢星期天。心里便痒痒,想去潘家园旧书地摊去淘旧书。家人听说,纷纷来电劝阻。有的朋友知道了,也说,你知道北京多冷吗?实际温度到了零下十九度,郊外大风吹得汽车直摇晃,街上人都站不住,哪里会有人在室外的极寒中摆地摊呢?除非是疯子。
但是朋友们不知道,我这个人,在坚持自己的审美主张上,还真的是个疯子,不动声色守望的疯子。搞艺术的,没有一点疯劲,还真是干脆回婆娘屋里烤火去。第二天一大早,退了房,带上了行李,冒着严寒,直奔潘家园。
天使晴了。太阳是出来了。但是室外真的好冷。用一句俗话说,真的冻得人生疼。前不久来的时候,潘家园门前的马路,水泄不通。现在,空荡荡的,行人稀少。潘家园内,也没有了昔日的人潮汹涌。大部分的店铺都关门了。但是,古玩跳蚤市场仍然摆满了地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跳蚤市场有阳光。虽然风大很冷,但是还坐得住。而背阴处的旧书地摊就不行了。不仅没有一丝太阳,而且,还是个风胡同,一走进去,就像走进了冰箱似的,浑身开始发抖。我来的时候,是上午的十点多钟,虽然没有过去那样拥挤的人流,但是,仍然有不怕死的人,在摆地摊,大声吆喝着:“哎,天冷啊!两块一本!随便挑哇!”
前来淘书的人。大多都是中老年人了。一个个缩着脖子,蹲在地上翻书。我遛了一圈,发现我想去的地摊,依然摆上了。那个经常卖民国旧书的大婶,笑盈盈地递给我一双手套,指着小马扎说,坐下挑吧。
我半个月前刚来过。她的地摊上,还是那些旧书。新鲜的不多。上次,我看中了一本曹禺先生的《蜕变》,她不肯单卖,说要买就整套的买。今天,她马上拿出一本品相好的《蜕变》,说是跟我留着的。她说她的先生,是个喜欢收藏旧书的。藏了一辈子的旧书,现在老了,有些旧书,就想出手了。难怪她卖出的书上,都有刘先生的收藏印呢。
在旧书地摊上待久了,两只手马上就冻僵了。脸颊上,还有耳朵,火辣辣地生疼。随即走到跳蚤市场旁的旧书大棚,那里有阳光,我想去看看上次相中的几本合订本的旧杂志。
果然,沙先生夫妇都在呢。他们的书摊上,摆的都是民国旧书刊。最近,可能从黑龙江进了一批书刊,上次的《人世间》,就是在他们书摊上买的。
沙先生一看见我,马上就拿出了《文坛》与《文丛》的合订本。两种杂志,都有创刊号。有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资料室的收藏印。天气太冷,手冻僵,都翻不开书了,便直接谈价钱。最后,分别以一千元和两千元成交。
《文坛》,1946年1月20日创刊于上海,月刊,大32开本。魏金枝主编,丁英编辑。上海联华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发行人陆守伦。这是一本短命的刊物,同年5月出版到第3期后,就停刊了。我淘到的这个合订本,恰好是三本,也就是说,《文坛》的创刊号与终刊号,全部在里面。这在我的收藏史上,还是第一次。
《文坛》的发行人,也就是老板陆守伦,是民国时期上海的广告、出版巨头。他创办过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小说月报》改办成传布新文艺的《文坛月报》。聘请作家魏金枝任主编。
魏金枝,浙江人,是著名的作家。1918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1920年开始写诗与散文,并参加文学团体晨光社,毕业后,一直任中小学教师。1926年,发表短篇小说《留下镇上的黄昏》。1928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七封书信的自传》,被鲁迅誉为"优秀之作"。后来,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编辑左联刊物《萌芽》月刊。后来接手主编《文坛》。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工作,担任过《上海文学》副主编和《收获》副主编,兼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
《文坛》的编辑丁英,则是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丁景唐。文革结束后,他为中国新文学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恢复深受国内外文化学术界关注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的影印工作,出版了四十余种太阳社、创造社和“左联”、“文总”等有重大历史价值而存世极少的文学期刊;二就是开始影印汇集了我国五四新文学精华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茅盾先生在1980年11月曾赠诗于他:“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
至于《文丛》,也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期刊,是巴金与靳以合作的结晶。1936年底,巴金和靳以合编的《文季月刊》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两人便开始筹划新的文学期刊。次年春天,第三本以“文”字打头的期刊《文丛》又创刊了。《文丛》的第一卷第一号于1937年3月15日出版于上海,靳以主编,由巴金任总编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总经售。
《文丛》出版了第1卷第5期后,抗战爆发。“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许多文学刊物不得不停刊,《文丛》也在其中。
1938年3月,巴金和靳以从上海经过香港到达广州后,开始积极恢复《文丛》。当年的5月20日,《文丛》第2卷第1期在广州出版,带着抗战的烽烟,重现在读者面前。扉页是丰子恺的“任重道远”漫画,刊期由月刊改为半月刊。靳以在“编者的话”里说:“从去年的七月到今天,有多少好男儿的血洒出来,为了国家,为了自己;我们不再像一只驯羊,等待别人的宰割,我们已经坚强地站起来,以打击来答复打击。”复刊号开始连载巴金的长篇《火》。而当时的中国,到处是战火。在战争环境中编辑刊物,真的好不容易。巴金先生《在轰炸中过的日子》一文中写道:“敌机去了以后,我们自然继续:工作。两个刊物的出版期又近了。稿子编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样送来就得赶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应当打电话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样。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册。我们应该把它们的大半数寄到各地去。于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连一个朋友的九岁孩子也要来帮一点小忙。”刊物的排印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印刷局不肯继续排印,以加价要挟,连已经打好纸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出版;至于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书,则因为那个印局的关门,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这些编务琐事,在烽火连天的抗战中,可能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了,但在今天,重新翻阅当年的《文丛》,不由得对巴金和靳以先生肃然起敬。他们就这样冒着危险坚持编辑《文丛》,一直到日军攻入广州的前夜,巴金才撤离。他除了带着简单的行李外,还有《文丛》的纸型。后来,辗转到桂林后,才将杂志印出来。在《写给读者》一文中,巴金写道:“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够摧残的。我们有着广大的丰腴的土地,到处都埋着种子,我们的文化将跟随着我们的人民和土地永远存在。正如唐诗所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文化也是烧不尽的。”
我淘到的,正是《文丛》的第一卷。也就是说,从创刊号,到第一卷第五期,全部都在,且品相良好。这也是非常难得的。
北京遭遇极寒。一个爱书的书痴,就这样在极寒的冬天,在旧书摊上淘到了心仪的旧书刊。回到住处,双手,脸颊,耳朵,全都冻红了,火辣辣地发烧。我想,那是因为我手中揣着一团团火的原因吧。




雪落三千院·玩物玩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