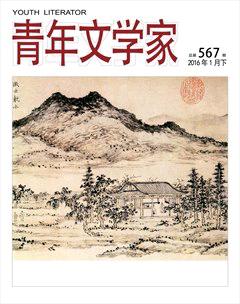浅论朦胧诗的论争
摘 要:20世纪70年代末,一个青年诗人群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他们的创作被加以“朦胧诗”的称号。诗人们对固有审美规范和批评原则的巨大冲击,形成了新时期诗坛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浪潮,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朦胧诗的崛起固然是新时期诗歌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而围绕朦胧诗所展开的论争,以及这场论争产生的影响,也许远超越了朦胧诗本身。
关键词:朦胧诗;诗人;论争
作者简介:文静,女,1982年生人,苗族,中央民族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贵州省中共黔东南州委党校讲师,《黔东南党校学刊》编辑,主要从事文学批评、民族文学及文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朦胧诗在当前各种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无疑取得了非常高的评价和地位,但在它作为新诗潮登上文坛的当时,走过的却是一条布满荆棘的许道路。朦胧诗在20世纪80年代初震惊文坛,作为一种艺术的变革,它则发端于70年代初或更早。食指(郭路生)1968年写下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诗篇,可看作朦胧诗的源头;北岛的创作也始于70年代初;60至70年代到白洋淀插队的芒克、多多等人形成朦胧诗群体的核心——“白洋淀诗群”;北京“地下沙龙”里徐浩渊、依群等人的诗作等许多所谓“朦胧诗”代表作已在地下以手抄、油印等方式传播。
1978年《今天》的诞生,使以白洋淀为中心的地下诗坛,以及与其风格相近的其他诗人得以集体亮相,也标志着地下诗坛对主流诗坛的挑战。而朦胧诗作为一股新诗潮在公开刊物上亮相是1979年。北岛的《回答》在中国最具权威的诗歌刊物《诗刊》上发表;紧接着舒婷的《致橡树》,《这也是一切》,《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顾城的《无名的小花》;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陆续在公开刊物上发表。青年诗人们的影响不断扩大,终于形成了气势磅礴的洪流不可遏止地席卷文坛。随之而来的,是文学界关于朦胧诗的评价越来越尖锐化、表面化。
1980年的8月,《诗刊》刊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作者认为当时“有少数作者大概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作者称:“这种诗体,也就姑且名之为‘朦胧体吧。” 朦胧诗的名称由此而来。诗人公刘1979年发表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提出青年诗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及表达方式问题,认为应加以理解并予以“引导”,这被看作朦胧诗论争的开端。1980年4月在广西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中,较为传统的批评家和诗人倾向于否定朦胧诗的创作,而以谢冕、孙绍振、徐振亚为代表的“崛起论”者则倾向于肯定朦胧诗的创作。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一开始就陷入一种口号、概念之争,并与许多非文学的因素纠缠不清。虽然大家都倾向于认为朦胧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主流诗歌截然不同,但肯定的一方将其等同于“含蓄”加以理解和推崇,而否定的一方则将其等同于“晦涩”加以贬斥。朦胧诗肯定论者认为朦胧诗是对传统美学观念的一种反叛,是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上一次积极的自我否定。孙绍振将朦胧诗所蕴含的这种反叛与否定精神概括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则认为以往那些“吹牛诗”、“僵死诗”、“瞒和骗的口号诗”将新诗艺术推向了不是变革就是死亡的极端,而朦胧诗正是新诗对自身的否定。但朦胧诗的否定论者则有不同意见。因为,自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始终处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严酷的内忧外患使得一切必须服从生存的需要,不断推进文学艺术的“革命化”,在“革命”的名义下,诗歌同其它文学形式一样,都被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一体化”改造并取得空前的成效,个性纷呈的自由创作已被荡涤殆尽。在文革结束前,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从内容到形式都高度一致的诗歌形式。朦胧诗的否定论者大都是“人民的文艺”的长期实践者 ,他们认为应该把文坛上出现的新事物拉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创作轨道之上。
朦胧诗论争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诗的懂与不懂;晦涩与含蓄的界限的问题。否定论者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朦胧诗让人读不懂。他们认为诗歌作品的目的是要让人欣赏。太浅显直白的诗虽未必是好诗,但让人看不懂的诗一定不是好诗。但朦胧诗的肯定论者却主张不应将懂与不懂当作评价诗歌好坏的标准,应当将诗的朦胧与晦涩区分开。懂与不懂有时不是诗歌本身造成的,而是读者对诗的感悟与理解造成的。同一首诗,有的人看来是晦涩难懂,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明白易懂,其中的界限是由读者不同的知识背景和欣赏水平造成的。诗歌有其自身的逻辑及特殊的表现方式, 对时间、语言的扭曲与陌生化是诗歌创作中的基本手法,若是一味纠缠于传统意义上的时间、语言规则,则可能抹煞了诗歌的艺术性和美感。从创作上来看,诗歌的懂与不懂大部分是由诗歌的“显”与“隐”这对矛盾带来的。过“显”,易流于粗浅;过“隐”,易流于晦涩。朦胧诗的肯定论者倾向于诗的“隐”,而否定论者则倾向于诗的“显”。反映到诗歌理念上, 即是肯定论者倾向于对自我的表现及提高, 否定论者倾向于服务大众和普及。肯定论者认为,虽然诗歌的创作与欣赏不是少数人的专利,但诗歌也不能彻底妥协于读者的理解能力和欣赏水平。
诗歌的欣赏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活动,因此诗歌的“隐”比诗歌的“显”更能激发读者的创造潜能。然而过犹不及,诗歌一旦走向朦胧的极端,就有可能变得晦涩,使阅读陷入僵局。其实这种现象在朦胧诗的创作中广泛存在, 就连朦胧诗的肯定论者也指出,某些诗沉迷于破碎形象的偶然拼凑、浅层次的象征和繁冗的装饰,空茫的意象充斥诗中,而使诗歌的可感性达于低点。可见,要求所有诗歌都浅白易懂固然不现实, 但若只以花哨之技法掩盖空虚之内容,以语言之晦涩营造故作深沉之假象,同样是愚蠢的。
什么是诗?诗与非诗的界限在哪里?是论争的又一个主要的问题。朦胧诗的否定论者认为,诗必须是反映时代精神、气势磅礴、精神豪迈、格调高亢的,否则就不能算正路和主流。尽管他们也承认,诗歌创作应多元化发展,但内心对不能纳入“人民的文学”的作品是排斥、看不惯的。他们眼中不存在绝对的自我,自我是与集体相伴生的。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如果不与社会主旋律保持一致,那就代表了一种政治危险性。所以他们很难想象与社会、政治脱离的诗歌创作,而朦胧诗中所渗透的怀疑、反叛的情绪和灰色的风格也是他们反感和难以接受的。
朦胧诗的论争中还涉及了诗歌创作的继承与发展问题。朦胧诗作者和肯定者们热衷于把自己塑造成文学发展史上的革命者,从而与前代诗人划清界限。其实,就诗歌的朦胧美而言,李金发、卞之琳、冯至、穆旦等创立的诗歌传统中早已有之。艾青甚至指责朦胧诗人一面抄袭他的作品,一面又要把他送进“火葬场”。也曾有人指出舒婷的《致橡树》与艾青的《树》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这种说法成立与否,我们都可以从侧面了解到, 那些所谓“革命性”的文学潮流,并非是无本之木。它是崭新的,因为它为读者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同时它又是旧的,因为它总不能摆脱与已有审美经验的联系。
虽然,朦胧诗的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最终各执一端,互不相让,最后使得这场全国性的论争草草收场,但这场影响广泛的论争,对我国文学界的意义却不可估量。尽管当时的中国文坛还不能完全摆脱以政治裁判取代学术争鸣的现象,尽管论争对一些诗歌关键性问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思考,但论争以朦胧诗现象为出发点,到整个诗歌理论,再到我国新诗发展方向的逐渐深化,使朦胧诗原本十分含糊的概念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也使以往很少触及或模糊不清的理论课题,如传统与现代,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朦胧与晦涩的关系等问题逐渐清晰。特别是一次艺术上大面积的平等对话,激活了诗坛的民主气氛,诗歌观念也得到了积极的反思与发展,为新时期诗歌的发展准备了坚强的理论后盾。在此次论争的过程中,朦胧诗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渐被更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不仅在诗歌创作中获得了合法地位,而且成为了80年代初我国诗歌创作的主潮流,可以说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而站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那场硝烟弥漫的论战,正如杨炼所说:“一切,不仅是启示”。
参考文献:
[1]张闳.《声音的诗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
[3]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J].诗刊,1980 .(8).
[4]钟文.《三年来新诗论争的省思》[J].成都大学学报,1982.(2).
[5]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J].诗刊,1981.(3).
[6]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J].当代文艺思潮,1983.(1).
[7]谢冕.《一个世纪的背影》[J].文艺争鸣,2007.(141).
[8]田志伟.《朦胧诗纵横谈》[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9]李新宇.《中国当代诗歌艺术演变史》[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