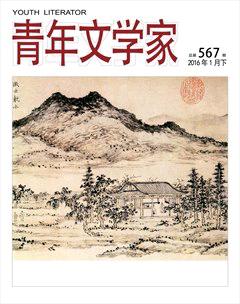关于“什么是诗”的一点思考
邵华
摘 要:诗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对什么是诗的探讨,需要从语言形式和艺术性两方面入手,而这两方面又是紧密联系的。要将诗与散文区别开来,不仅要把握诗在语言形式上的特点,也应注意它们在观念方式上的差异。
关键词:诗歌;语言;艺术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03-0-02
诗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什么是诗,却是历来争论不断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一切诗歌研究或诗歌史写作的基本问题,因为只有回答了这一问题才能确定其对象和范围。前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往往有一种本质主义倾向,即假定了诗有某种本质或者说“诗性”,因此试图给诗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以表达它的这种本质。但一种事物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却是值得怀疑的。当代哲学有一种反本质主义倾向,许多哲学家认为一类事物有许多彼此相似之处,但却没有什么本质,将某种特点作为本质实际上反映了研究者的某种特定的视角,而这种本质往往不能涵盖所有这类事物,总是会发现有例外现象。这种观点也可应用于诗学。古今中外,对诗的定义不胜枚举,但无论在外延和内涵上都难以令人满意。虽说下定义是困难的,但也是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寻求定义的过程不是看作去发现诗的本质,而是去寻找诗的某些显著的共同特点,虽然可能没有哪种特点是本质性的或者说是诗所独有的。这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什么是诗。
显而易见,诗首先可以看成是一门语言的艺术。强调诗歌是一门艺术,这又涉及到什么是艺术或艺术性这样的大问题。一般来说艺术不同于现实,它是从现实生活中选取材料,进行加工创造,从而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世界——艺术的世界——以传达人们的思想情感,引起人们的审美愉悦。艺术必然具有人为的造作性,哪怕看起来仿佛就是自然。另一方面,诗是以语言作为媒介或构成材料的,不同于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门类。语言不是外在的物质材料(如绘画所用的颜料、画布,雕塑所用的石头),而是精神性的意义或观念的直接表现形式。所以诗所呈现给我们的不是具体可感的声音、形状、颜色,而就是观念。可听的语音和可见的文字只是观念的指示。通过语言,客观的外在世界和主体的内心感受都转化为观念。可以说诗的内容和媒介都是精神性的,因而诗能不受感性媒介的限制,驰骋于无限的精神世界。
由于诗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我们可以从两种视角来考察诗的特点,一是从语言形式上,一是从艺术性上。当然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诗的艺术性是通过语言媒介体现出来的,因而有其独特性。诗的语言形式的特点直接决定了诗的艺术性特点。
语言的组织可以是有音韵的,可以是无音韵的。一般而言,诗歌属于有音韵的,散文属于无音韵的。中国古代就有“有韵为诗,无韵为文”的说法。诗歌讲究音韵,意味着它富于音乐性。在人类原始时代,诗、音乐、舞蹈是融为一体的。中文中的“诗”是“诗歌”的简称,歌谣可以说是诗的源头。最早的诗就是唱出来的,将歌谣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成了文学意义上的诗。无论是中国的《诗经》,还是西方的荷马史诗或印度的史诗皆是如此。
为了突出诗的音乐性,传统的诗歌创作讲究固定的音韵,如中国的律诗,西方的十四行诗。不过西方很早就有不那么讲究音韵的自由体诗,近代以来自由体诗逐渐成为主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新诗也力图突破传统诗词格律的束缚,自由地表达思想情感。自由体诗虽然没有规整的字数和韵律,但仍然是分行写的,而且相互之间起伏呼应,有一种低回往复的律动感,并非平铺直叙。可以说还是具有一种内在的节奏,能造成音乐效果。当然有些诗歌实验走向极端,完全不讲节奏,排斥音乐性,这些创作出来的诗也就不成其为诗,或者说是“假诗”,很难得到人们的欣赏。
为什么要诗采用这种具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当然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即诗意。我们经常有这样的经验,将一段诗翻译成散文,虽然意义还在,但诗意尽失。诗的字面意思也许很平常,但是用诗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有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情趣。这其实就是诗的音律造成的效果。“事理可以专从文字的意义上领会,情趣必从文字的声音上体验。诗的情趣是缠绵不尽、往而复返的,诗的音律也是如此。”[1]音和词的结合使得诗的表达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含蓄蕴藉、回味无穷。诗意不仅在于情趣,也在于超然的境界。由于诗的语言具有音乐性,它能够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世界引开,上升为一个更高的、理想的世界。甚至哪怕是悲惨的事件、丑陋的事物,用诗的语言来描述也可以起到美化的效果。“用美学术语来说,音律是一种制造‘距离的工具,把平凡粗陋的东西提高到理想世界。”[2]瑞士美学家布洛认为只有当主体与客体保持了一种无功利、非实用的“心理距离”时,才有可能产生美感。艺术作品之所以比现实事物更容易引起美感,就在于艺术作品的形式起到了制造心理距离的效果。诗歌的语言作为一种艺术化的语言正起到这种作用。
二十世纪俄国的形式主义者对于诗的语言问题有更系统、更科学的分析。他们认为散文语言是出于交流的实用目的,因而语言表现只是一种传达手段,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在诗歌语言中,实用目的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是居于次要的地位。诗歌语言具有独立的价值和它的特性有关。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给诗歌下了一个著名定义:“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语言”[3]。诗有权打破口语或散文的语言习惯,不遵守语法,颠倒语序,杜撰新词或化用古语。诗还有自己特有的辞藻,即在一般话语中不会使用的字词和比喻。由于诗歌语言打破语言的常规,我们对语言形式有了敏锐的感觉,并且会产生紧张感和感受的持续性,而对于散文化的语言,我们的接受往往是习惯化、自动化的。语言的自动化使我们对语言所表达的事物习以为常、熟视无睹。诗歌语言则造成陌生化的效果,使得事物呈现出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面目,从而使我们的感觉摆脱自动化,唤起了敏锐丰富的感受。
传统诗学强调诗歌语言体现了节约原则,即用精炼语言来表达丰富的内容。朱自清先生说“诗是精粹的语言。因为是‘精粹的,便比散文需要更多的思索,更多的吟味。”[4]语言的精粹化固然是诗歌经常表现出的特点,但是也应看到,有时诗歌中的用语不是精粹的,而是无意义的、重复的,主要就是为了造成诗歌的韵律节奏,获得某种音响效果。正是诗歌所追求的音乐性使得诗歌的形式变得复杂,它阻碍了语词和意义的直接结合,增加了感觉的难度从而使感觉得以强化,同时也延长了回味的时间。
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诗歌的语言形式的可感觉性,并进而将形式的可感觉性等同于艺术感。这种观点有点偏激,未考虑到艺术感所应有的精神内涵。但对形式的感觉确实构成了艺术感觉的重要环节。因为正是艺术形式让我们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使我们的精神有一种面对现实的超越感、自由感,这正是艺术感的实质。对于诗歌而言,诗歌的语言形式不同于日常交流的语言形式,它使得对象陌生化,使我们不是以实用的、功利的态度面对对象,而是超然地对其进行审美的观照。
这种关注诗歌的形式和审美特质的观点,会导致许多人批评它不重视诗的内容。内容有两个层次,一是诗所表现的对象——无论是客观的事物或行动还是主观的内心活动。二是通过此对象所展现的意义。根据一般的看法,诗的内容更重要,形式只是为内容服务的。不过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其实是题材,是外在于诗歌作品的东西。散文和诗可以有相同的题材,如描绘同样的对象,表达同样的思想主题,但效果大为不同。这说明题材在诗中居于次要的地位,关键是如何去表现它。诗的创作手法赋予了题材以诗的艺术形式,造成对题材的加工变形,题材通过变形而转化为艺术内容。诗的形式和内容构成了一个不可分的整体,内容总是形式表现出的内容,形式总是具体内容的形式。这种将题材转变为艺术内容的过程,就是造成现实世界的陌生化的过程。
传统文学理论一般将文学和散文相对待。散文可区分为两类,一是作为日常交流或信息传递之手段的应用性散文,一是作为文学的散文。后者与诗都属于语言艺术,因而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比如敏锐的感觉、丰富的想象、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这些诗歌常见的特点在散文作品中经常可以找到。它们之间最显著的区别还是在于诗歌语言具有音乐性,然而甚至音乐性在散文语言中也常有反映。如中国文学中铺陈扬厉的汉赋、对仗工整的骈文,都声律铿锵,极具音乐性。它们可以说是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一种文体。即使一般古文也不乏形式整齐、朗朗上口的语句。另一方面,一些诗虽然对仗工整、音韵和谐,但是仍如散文一般叙事说理抒情,让人感觉徒有诗的形式,如打油诗之类。到底如何去区分诗和散文,语言形式固然是一个重要方面,还要从诗和散文呈现观念的不同方式入手方能明了,在这方面黑格尔的观点值得借鉴。
黑格尔认为,散文意识最显著的特点是抽象的知性思维,即从相对的、有限的观点去认识事物及其联系,仅停留在事物的偶然状态和特殊规律的认识,而不能深入到事物的本质和整体的有机统一性,也不能达到事物的内在意义和外在表现的活的统一。相反,诗中所表现的繁多的现象贯穿着一种普遍的精神,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普遍的内容意蕴和形象的表现是未曾分裂的原始的统一体。因此诗有一种留恋细节的倾向,对细节的描绘就是在表现精神的意蕴和普遍联系。而散文意识将形象和意义割裂开来,形象只是作为认识意义的单纯手段。散文虽然也描写事物的外貌,但其目的不是在于唤起形象,而在于达到某种其他目的,如进行说服。因而在散文意识看来,诗的表现方式是走弯路的、多余的。总而言之,一般的意义和特殊表象能否达到有机的统一,是诗和散文在观念方式上的主要区别。
由于散文诉诸知性思维,它表达的意义是明确的、可理解的,而诗总是借助形象来表达意义,这种意义往往是模糊的、含混的,具有多重解释的可能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于诗要运用形象思维,它由此也摆脱了意义的束缚,使我们关注其具体的生动的形象。因此诗的意义不像散文那样是直截了当的,而是涵意无穷、值得回味,表现为一种“意蕴”。太直白的诗就不像诗,而像押韵的散文。中国传统的诗论强调作诗要含蓄蕴藉,最好能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如叶燮所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可不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5]。在这方面诗歌的音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所造成的音乐效果能帮助营造诗意氛围,使读者在字面意义外产生更多的感发和联想。黑格尔也强调,诗的语音因素能将严肃的内容冲谈或推远,使人摆脱其束缚,而上升到更高更优美的境界。“用音律的散文不能算是诗,只能算是韵文,正如用散文来创作诗,也只能产生一种带有诗意的散文。至于诗则绝对要有音节或韵,因为音节和韵是诗的原始的唯一的愉悦感官的芬芳气息,甚至比所谓的意象的富丽辞藻还要重要。”[6]
总而言之,诗歌是讲究音律的语言艺术。当代是一个诗歌泛滥的时代,但好诗又极少,文化空间中充斥着大量形形色色的假诗、冒牌诗、劣质诗。只有将音律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的诗,才是真正的诗。
注释:
[1]朱光潜.朱光潜全集(3)[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112.
[2]同上,第121页.
[3]王先霈、王又平主编.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17.
[4]朱自清.文艺常谈·经典常谈[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7.
[5]叶燮、沈德潜.原诗·说诗晬语.孙之梅、周芳批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35.
[6]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