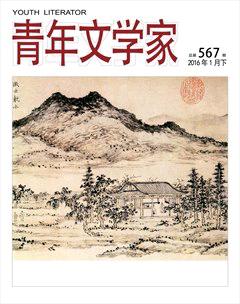火车见闻录
郭子宜
出发的前一天是大年初五,去售票厅排不上票,托站上的一个亲戚买初六的火车票。妈妈说买晚一些,十五十六才好——年还未跑,人倒跑了——我们去旅行。
早上五点钟的火车,照例四点钟就要起床往车站赶。天只挂着蒙蒙的亮光,马路上寂静空旷,临街地店铺和这城市一样都在睡着,在半黑暗中,只有高高的水泥杆上悬着一盏昏黄路灯,像隔绝了的一个小温暖世界,怎么看都是昏昏欲睡。
车站里面穿酱紫大衣的检票员来回走动,一张困倦的脸被灯光照着,似乎显得苍老。到检票的时候,排在最前面的两个女人因为持过期票被售票员扣了下来。有一个女人是乡下装扮,头上围着绿麻手巾,挎了一个花绿方格的包袱,脸上惊慌错愕的表情有些狡黠,张嘴喊着:“我的老天爷呀。”又和同行的另一个女人商量给站上哪一个认识的人物打电话,看能不能通融过去。
这火车是发到很远的地方,似乎本地只是一个小站,旅客们不敢耽搁,进了站台拼命提着箱子往火车奔,人人像难民逃命。接站的列车员挨着白铁壳子火车站,看不清脸,只有手里握着的绿光手电筒不停摇晃,就像乡下跳大神的神婆祷舞,看着有些诡异地骇然。临上车的时候左顾右盼,出发的喜悦心情已经像去购物。
旅客们一上完,火车就在晓雾里嘶啸着开出城市,车窗外面亮了很多,城市和人群是方才醒来的无神,一些灰黑的房子里朦胧亮着灯火。因为早起,坐了三站,也盹了三站,后来一下子涌上许多人,火车上热闹起来,方便面地气味在车厢里晃来晃去。
张爱玲女士说,中国人的出行似乎带有野餐性质。西方旅客就不同,他们素来不太担心旅途中的食物,乐观的仿佛路上哪一处都可以买到——难道是某种暗示性质地传承?从前三宝太监下西洋到古里,只是“刻石于兹,永昭万世”,访问了一番又回去。过了许久,却有个叫达伽马地葡萄牙人也到了古里,在人家的土地上插了标注,意思以后这里是殖民地了,仿佛在抢注专利。又有个南非的政治家讲:西方人来到我们面前时,手中拿着圣经,我们手中有黄金,后来时间久了,就变成他们手中有黄金,我们手中拿着圣经……中国人大抵有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甚深。
因为是野餐性质,每到一地都有一地的特产,煎饼、花生、大枣……停站的时候,挎着篮子的女人会上车叫卖。有一种山东的特产德州扒鸡是火车上售货员推着铁皮小车叫卖,从第一节车厢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一张肥嘟嘟地烧饼大脸上油气光亮,仿佛是扒鸡熏染过的。这火车厢人很多,然而她总有法子变魔术一样从人群中反复穿过,像个泥鳅一样,腻着人走。
火车走了一路,除了城市,外面大都是青黄的土地和一些高高的山丘,河流很少,几近干涸,终究看到一条大河,可能是冰封住了,落日的余辉下,散发出阵阵雾气,萦萦绕绕,茫茫的无边。几艘木头小船横七竖八放在岸边。远处是一个个青黛色的小山,山腰上一片片干枯的树林,有几间灰白低矮的房子星星点点散布其间,颇有一些油画的感觉,给这寒冷的增添了些诗情画意。
有一个天津女人,不知是哪站上来,查票的时候没有车票,她大抵有过许多经验,跟查票的先尾尾诉苦。那查票的是东北人,戴着六角边框眼镜,看起来就是一幅“悍然不可动”的样子,等她讲完了,只说如果不补票,下一站到站就要赶她下去。天津女人跟他磨了半天,终究还是补了一张站票。
下一站是个转站的地方,下的人多,她就找了座位坐好,但仍然悻悻地对旁边人讲,她上一年春运如何靠一张站台票混到家里:“喏,从西安到天津,好几千里都没事嘛。”她笑着讲,是那种偷到果子的开心。
坐火车,时间会充分显示它的冷峻和孤傲,它把本来疯跑的岁月,细细辗碎,像夜晚的风一样拂到你的面前。它让你不得不细数这些日子以来,你的孤独,你的忧虑,你的高兴,你的悲伤,还有你的未来。就像里尔克在《孤寂》里那样写道:“孤寂的雨下个不停/在深巷里/昏暗的黎明/当一无所获的身躯分离开来/失望的悲哀/各奔东西/当彼此仇恨的人们/不得不睡在一起/这时孤寂如同江河/铺盖大地。”
火车上的时间,是我们期待答案的过程,是拂晓的天光到来之前的黑暗,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各个阶层。他们有农民工、学生、白领、小商人、画家、作家、军人、自由职业者、身怀绝技的手艺人等等。他们中有的走南闯北,见识广博,还有的天资聪赋,料事如神,他们是生活中的某些代表。他们谈政治,谈时局的变化,谈中国和外国,谈文化和艺术,谈生意和职业,谈奇闻和经历,谈战争和犯罪。有时候你会听得哈哈一笑,有时候你竟觉得他们谈论的事情是你从未知道的,不由得生出民间果然藏龙卧虎之感。
突然想起鲁迅先生的话,人立起来之后,“沙聚之邦,转为人国”。人不立,国家再有钱、再强大,也是没用的,这个国很快就会覆灭。当我们去认真思考中国传统教育的精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精华,以及当前欧美、东亚等其他国家教育的精华时,会发现其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就是:“学以致用,学以成人”。
是啊,现在想起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的结尾所发出的一声最为沉痛愤懑的呼喊“救救孩子”似乎是惊醒了一个时代,开启了一个有关启蒙与教育的重大话题。
王安忆在她的小说《忧伤的年代》里写道:“我们经受着怎样的折磨啊!生长的尖锐的激素咬噬着我们,痛苦是无可明状的,不确定的,不明所以的。寻找突破口,也是盲目的。
在半睡半醒间想了许多,火车在一处站台停了很久,又到了吃饭时间,卖盒饭的推着铁皮小车叫卖,价格却贵得离谱。好在大多数人都带了食物,因为知道火车上太贵——这仿佛成了他们特权,理所应当比街上店铺里贵两倍的价钱。等到带的食物吃了七七八八,也到了下车时间——野餐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