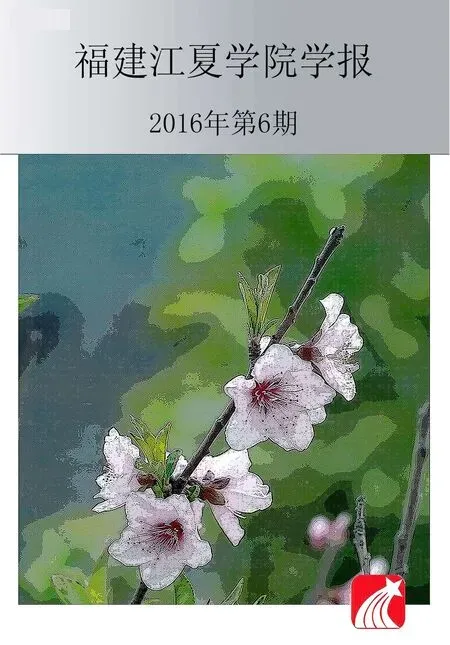试论中华民族复兴视角下历史记忆及现实意义
戴韶华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浙江杭州,310018)
社会·文化
试论中华民族复兴视角下历史记忆及现实意义
戴韶华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浙江杭州,310018)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直在为改变屈辱现实和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富强而努力。历史记忆围绕这个目标的实现为全民族的团结凝聚共识,提供精神动力。我们需要利用历史记忆中的优秀精神资源,克服现实中的思想偏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崛起需要古代传统文化的转化与革命传统的继承、创新,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社会共识,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坚实的思想价值基础。
历史记忆;民族复兴; 共识
历史记忆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种传承,同时也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这与西方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更强调的是主观性的认识,而对中国这样的未完成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客观性的历史积累则是为国家凝聚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的思想基础。对于历史记忆,既要看到其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偏向,特别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所造成的偏差,只有努力克服这种偏差带来的不良影响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更有利的精神支持。
一、历史记忆及其对中国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并且与文化的传承融合在一起。因此,当今仍然需要历史记忆在实现民族复兴中发挥其思想和价值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历史记忆在社会变化中的凝聚共识作用
“构成民族要素的历史因素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客观存在,保留在民族记忆之中(书传或口传),这就是所谓的民族的‘历史记忆’。”“建构民族历史记忆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护本民族道义上的利益和物质上的利益。”[1]因此,历史记忆的强化既是一种文明自觉的体现,从根本上来看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人的社会性。“因为在每个人的人性深处,埋藏着我们对最原始人群感情(同胞手足之情)的信赖与苛求。”[2]因此,历史记忆具有强大的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动力,也是一个国家合法性、政治稳定的思想基础。对于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历史发展中的辉煌业绩的记忆和颂扬是民族自尊、自信的来源,它会通过集体记忆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为“从先人那边,集体经验与个人的历史和起源紧密结合,这种把过去和未来串联起来的‘时间’定位,满足了个人某些最深沉、最迫切的需要。”[3]158从根本上说,政治的稳固和人心的慰藉最可靠、最亲切的精神资源来源于历史发展连续性基础上的探索和对社会变化的适应。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历史渊源有一个断裂和重新建构的转折,而中国文明的连续性使得历史始终处于政治、社会发展中“宗教”般的地位。朝代的变换、政府的变迁必须要利用传统文化、历史记忆作为政权稳固的基础,这其中也包含着优质的文明资源。“中国人拥有光辉的过去,并自认为自己的历史是最伟大的。”[3]183即使“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虽然不乏西方意识形态的色彩,但绝大部分的动力来源却是恢复古代中国的伟大”。“严格地说,中国人没有‘起源的传说’”,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与天地同时的”。[3]184尽管五四时期和上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的现状有过对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但那是为了救国而形成的“反传统的传统”,并不能动摇传统强大的社会基础以及对传统的美好回忆。我国目前对于历史的记忆总体上还是处于“民族主义史学”的范畴,“忠诚于民族主义,以本民族为中心,是民族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4]。这种历史观与我国的历史和发展实际密切相关,短时间内不会有很大的转变。
(二)历史记忆在时代变化中的主观建构作用
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对于历史事实的重现,更重要的是在于对历史事实的选择和解释,而选择、解释是根据现实的需要,为现实的国家利益、执政党的合法性服务的,因而也是主流价值、意识形态的体现。因此,这里需要对于历史事实进行“再脉络化”的重构,并结合现实进行新的解释。近代以来中国的发展路径可以概括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救亡压倒启蒙”说,顾颉刚放弃对中国古代文明神话传说和典籍的学术质疑,特别是其对“民族一体”“地域一元”等核心观点的质疑(当时被戴季陶斥为“动摇国本”[5]),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近代的历史记忆在于唤醒人们对于国家的感情和民族的认同,而这是在外在压力、冲突下的一种表现。在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记忆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历史屈辱和历史辉煌的张力,在中国解放和富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情绪和心理需要两者在相互关系的处理上不断成熟和理性。“历史通过人们的持续不断地与之对话,从曾经的经验教训中发现真理,进而既使历史成为当下人们追求自由的财富,又为当下的人们接着书写。正是在此意义上,一切曾经发生的又都是要经受持续不断地对话,并在对话中成为鲜活的历史。”[6]因此,历史记忆需要使人们对于历史的理性思考,对理想人格的培养。当然,更要注意防止历史记忆变成对历史仇恨的记忆,成为受害者的极端记忆,成为延续矛盾、冲突的焦点,影响着国家间的正常交往和国际秩序。因此,历史记忆更需要宽容和形成共识,否则历史的教训会有再次上演的可能。
所以,当今中国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历史记忆的延续和建构必须在传统和现代的联结方面适应现实的需要,因为历史记忆的选择以及其中的争论常常表达的是人们对现状的不满。从理论上讲,“历史认识之所以重要,首先体现他事关历史正义”[7]。因此,人们的历史观包含着对现有秩序的认同与否。对当下的中国来讲,不但需要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推进以及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的需要和信仰,同时还需要振奋民族精神,凝聚人心、增强民族自信。特别是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传统、建设成就和发展前景的继承、承认和自信。“要从根本上确立国家的权威和民族的信心,不仅要使人们认同国家的合法性,更主要应当依赖于人们对于这个国家的同一文明和共同伦理的认同,而认同的同一性基础,只能是超越个体生命、政治权力、地理区域的普遍性真理。”[8]这是我们当前思想认识、价值观念发展的方向。
(三)历史记忆在民族发展中的思想激励作用
“牢记历史,是人类共同的责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工程是为了使人类记忆更加完整,申报文件档案对于特定人类群体的精神价值尤其受到重视。”[9]因为传统的“决定性的标准是,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并且被代代相传”[10]。当今许多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的纪念日是通过强化人物、事件、仪式等来形成象征、符号、想象,并在时间上进行重点的强化,从而塑造历史的脉络,最终在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和日常语言表达中达成共识。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弥补当前社会中的价值迷失和传统文化缺失。同样,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在面对自然的严酷挑战和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争斗中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也蕴含民族发展最原始最有利当然也最有力的动力、智慧,这是一个民族在争取和维护其生存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经验,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品质,只有接续这些精神、文化特质,才能获得民族发展最根本的思想动力。
二、社会转型中的历史记忆与民族主义问题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11]每当民族国家遇到危机和社会转型时,总是从自身发展的历史传统中,从民族性的源头和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的斗争经验中吸取精神元素,并逐渐把这些元素与新的时代需要结合起来,不断延续民族精神中的最有生命力和最能表达民族性格的精华,从而使得民族国家的发展有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因此,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是有选择性的,是要根据现实的需要尤其是民族国家政治性的需要的。对历史记忆的选择和解释,决定着一个国家国内外的发展态势。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12]。
在历史转折时期总是伴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特别是在国家、民族危亡或转型时期更需要把全社会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凝聚和整合到维护、巩固国家独立、统一、富强的洪流中去。当前我国在历史记忆中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建国后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的断裂问题;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的问题;与周边国家的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与台湾、西藏的某些群体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与现实的关系方面的不同认识所影响到的国家统一问题;对于民族英雄的质疑、否定甚至污名化的问题等等。这表明“中华文化多维向心结构”[13]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14]共识的形成还需要克服许多困难。中国的爱国情绪常常表现为对外的一种反应,特别是把现实的国际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屈辱记忆,从而形成强烈的爱国热情。这种热情既是对内深化改革的动力,又是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的动力。中西之间不仅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较量,同时还有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因而,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是国家发展中非常关键的情绪和心理。
近代中国社会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不断转型,这种转型是文明的转型、体制的转型,也是民族精神总结提升的过程。历史记忆在这个过程中更突出地表现在要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发展重心等核心问题相适应,特别是历史教育、思想政治宣传教育、知识的“合法性”方面。因此,当今在经济基础不断夯实的基础上对历史记忆、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提炼和升华,这个过程包含多种逻辑、规律、趋向的萃取和转折,需要逐步深化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在新时期和中国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当下,需要重新梳理现代化、革命传统和传统文化的结合点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世界发展的结合点。如果历史记忆仍然一味地以自我为中心,特别是强化自身“受害者”的角色或者自身的优越性、独特性,停留在强弱对立的思想状态,那么就很容易在不同的群体、民族以及国家之间引发冲突。因此,“爱国主义转型的未来必将是没有民族主义化操作的爱国主义”,而这种剔除了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在历史教育、历史记忆中,才能够“将个人的无私转化为国家的利他主义”[15],从而实现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结合。
然而,历史的神圣性、使命感及其辉煌的过去,对任何民族来讲都是其自豪和自信的思想基础。对中国来讲,屈辱与辉煌的交织塑造了矛盾、敏感的复杂民族心理。而对这些屈辱记忆的选择和运用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和理论基础等方面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记忆有进行社会动员、凝聚民族精神和提供精神动力的积极一面,但是对于屈辱历史的记忆也要注意,这样的纪念常常把那种敌对的状态、观念、感情传递下去,使得民众的情绪变得不理性,这不但影响到国际关系的战略部署,同样也会在国内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美国学者杨(James Young)认为,犹太人有意识地将犹太大屠杀创造成一种全球性的对于苦难的文化记忆,而中国人则缺乏这样的视野与意识,我们没有一个宏观的文化关怀,只是将南京大屠杀当作自己民族的一种低层面的集体记忆。[16]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历史记忆来振奋民族精神,更需要记住历史教训以加强对屈辱历史的反省。但是,对于历史的灾难“有限‘宽恕’不是以受害者的名义给予施害者宽恕,而是‘宽恕’过去,让自己理性地面对过去的创伤和现在的责任。这种理性不是功利的态度,而是心智清明地管理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既在理智上切断对已逝事物过度的爱或恨,不让这爱或恨非理性地占据自己,也在情感和良知中保持对这爱或恨的恰当感知,以哀悼和纪念来恢复对自我和世界的正确认识”[17]。
这种思想上的决断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完成两个问题,既要形成自身的历史共识,增强国家认同,又要使这种思想能走向世界,带有普遍性的意义。形成这种成熟的认知和心理对于中国来讲必须要经过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协调。
三、历史记忆中的转变与对民族复兴的促进
中国近代以来对于西方世界认知的“刺激—反应”模式决定了历史记忆对中国来说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促进民族精神的发扬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自身发展中文明延续性以及政治发展所必须赖以依靠的资源。但是,无论是近代以来被迫走向现代化的转向还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主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都需要从整个思想观念、处事规则以及行为方式等方面逐步转变。而这种大的转变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思想、体制、行为方式等方面的转变和重构。而在这个过程中,从历史记忆来看,需要从思想观念、民族心理上逐步适应国家的转变和民族复兴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转变:
(一)历史记忆中的真实与建构
历史记忆的真实是后人探究历史的基本条件,也是在国内、国际形成思想共识的基础。同时,对于历史的解释、建构也是凝聚人心形成共识的途径。在当前条件下,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增强使得公民对于历史的认识和理解形成了广泛的社会需求,人们并不仅仅满足于课本和宣传的内容。同时,人们对历史的研究开始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实证研究的转变,也使得历史研究更加丰富具体。但是,这也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一定的偏向。“历史研究是历史资源利用的基础,只有弄清历史真相,充分尊重历史,我们才对得起历史,对得起英烈,才能杜绝历史虚无主义”。[18]因此,对于历史问题,更要用事实说话,形成公共的讨论空间,在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公共史学也是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一种表现。另外,历史的解释、建构本身也是历史记忆的一部分,如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救亡和民族复兴,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便是如此。直到今天,利用历史资源塑造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整体性、团结性而进行的建构仍在进行,其目的都是为了适应现实的需要。当前,这个工作必须要适应民族崛起的“软实力”建设,否则就不能解释自身的崛起及对世界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也不能真正形成自身的核心价值。
(二)中西之间在历史问题上理解的矛盾与处理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救亡图存的革命斗争,是被迫的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因此,中国的民族主义更强调的是民族自尊、自强、自信。目前我国的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民族主义从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功能上来看还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的错位,以及中西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上的不同,使得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激烈的民族主义思潮在当前显得非常突兀。其实,爱国主义这个“国家形态的民族主义”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它需要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必要性与激烈的民族主义之间进行平衡。中国政府在国际上提出“和谐世界”“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展现了其在这一方面的积极姿态。
(三)走出“民族主义史学”所影响的观念和情绪
历史记忆要逐步走出“民族主义史学”,走出民族耻辱的受害心理。这个问题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有待逐步突破的难点。理性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以包容、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我们未来实现强国梦的心理状态。然而,近百年来民族耻辱的痛苦记忆以及为增进民族团结、凝聚的精神动力而进行的相关教育,使得我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在外在刺激下很容易就引发历史耻辱记忆而产生激烈的民族情绪。这是受价值观念和教育内容等方面所影响的。但是,如果不能走出民族主义的特殊性所影响的观念和情绪,就不能真正的走向世界。当然,这也取决于存在问题争议的诸国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四)吸取前苏联的教训
历史记忆中所蕴含的问题关涉到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这也是近几年特别强调该问题重要性的原因。近些年出现了在历史记忆上的混乱,特别是在历史观和历史问题的认识、解释方面的混乱,也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前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19]。而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对历史问题的重视程度程度以及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来看,基本上都是在思想道德上对以往历史观念混乱引发的不良影响的纠正,并使其通过树立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形成共识、增强国家认同、树立民族自信。这是俄罗斯重新恢复大国形象的一部分。因此,对于历史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纠正必须上升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五)历史教育中的问题
历史记忆的积淀不断为民族精神增添新的内容,使得民族认同有共同根基,但如果历史被曲解、阉割或遗忘,那么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就可能扭曲和中断,从而影响这个民族的心智和人格。历史教育是延续文明传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培养青少年的公民意识,进行健康的人格教育,增强对历史的理性认识的能力的重要方式。但以往我们的历史教育中特别是近代史教育中具有浓厚的悲情意识,使得青少年不能通过自身的理性思辨来分析和认识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这样既失去学习的乐趣,也不能培养理性的爱国思想。因此,中国要走出“弱国心态”,同时又不能失去理性而膨胀出激烈的民族主义。
中华民族的凝聚、国家的权威、思想价值的统一是相互关联的一体。我们需要利用历史记忆中的优秀精神资源,克服现实中的思想偏颇,为全民族的团结凝聚共识,提供精神动力。而如果历史记忆及研究能够在以往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历史自觉、社会动员和共识方面更进一步,为当前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国际定位提供支持的话,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玉屏.新中国建立以来民族关系历史记忆建构的反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90(6):1-2.
[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424.
[3](美)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M].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8,183,184.
[4]罗新.民族主义史学是“幼儿园历史”,现在必须同它告别了[J/OL].(2015-08-05)[2016-01-20].http://www.thepaper. cn/newsDetail_forward_1360585_1.
[5]葛兆光.徘徊到纠结——顾颉刚关于“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解[J].书城,2015,(5):6.
[6]高兆明,洪峰.“哲学的历史”:事实与叙述、记忆、理解[J].探索与争鸣,2015,310(8):46.
[7]雷墨.中日和解绕不开历史这道坎[J].南风窗,2015,548(18):36.
[8]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79.
[9]钟声.历史记忆,就是要强化[N].人民日报,2014-06-12:(2).
[10](美)E.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导论,15.
[1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58.
[12](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M].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
[13]徐国宝.《格萨尔》与中华文化的多维向心结构[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少数民族文学系,2000:1.
[14]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序,13.
[15]潘亚玲.“9·11”后的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D].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7:212.
[16]燕海鸣.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J].中国图书评论,2009,217(3):13.
[17]刘文瑾.不可能的宽恕与有限的“宽恕”[J].读书,2014,427(10):40.
[18]吴楠.历史记忆是民族成长的重要条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0-8:(02).
[19]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20.
(责任编辑 赵珊珊)
Historical Memory and the Reality in the Sense of Perspective in the National Rejuvenation
DAI Shao-hua
(Zhejiang Police Vocational Academy,Hangzhou,310018,China)
In modern times,the Chinese goal is to change the reality of humiliation and struggle f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national prosperity,which requires historical memory around the nation to achieve this goal and provide the motive power for the unity and cohesion consensus.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we need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outstanding historical memory and spiritual resources to overcome the reality of ideological bias.In the new historical period,the rise of china needs to ancient traditions and the revolutionary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an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social consensus and integration inthe process,to lay a solid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value.
historical memory;national rejuvenation;consensus
D61
A
2095-2082(2016)06-0087-07
2016-12-01
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14NDJC15YBM)
戴韶华(1970—),男,山东冠县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公共基础部副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