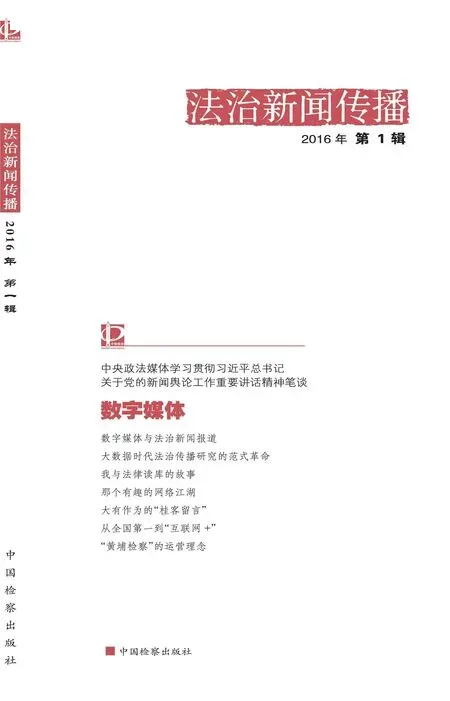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
■李艺
论大数据时代的隐私权
■李艺
大数据时代与隐私权问题的新发展
(一)大数据时代带来信息爆炸与隐私保护的尖锐矛盾
隐私权(Right to be let alone),作为权利谱系中的一项新生权利,是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而产生的。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直接催生了廉价商业报纸的诞生。以美国四大廉价报纸为例,这些报纸或宣称为读者谋利,旨在推动社会变革,以评论为重,如《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或宣称读者至上,以“读者兴趣”为试金石,以煽情吸引眼球,如《太阳报》。但既把报纸作为商品出售,就必然看重回报和利润。记者用“骇人听闻、华而不实、刺激人心和满不在乎的那种新闻阻塞普通人所依赖的新闻渠道,把人生的重大问题变成了廉价的闹剧,把新闻变成最适合报童大声叫卖的东西”。①《纽约先驱报》更是首创社交版面,把私人的聚会变为了读者眼皮底下公开的表演,开创消费隐私的先河。后来的波士顿报纸《星期六晚报》不仅用被认为是高度私人化和令人尴尬的细节报道了沃伦夫人在家中举办的一系列社交娱乐活动,还用头版头条报道沃伦夫妇女儿的婚礼。深受其苦的美国学者沃伦联合友人布兰代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发表《隐私权》,首倡隐私权,即每一个人都拥有决定“他的想法、情感和情绪在多大程度上传播给其他人”②的权利。
如果说报纸时代的隐私及隐私权还囿于技术的限制不能全面而深刻地侵蚀到人们生活的话,“2009年以来走红的‘大数据’概念则实现了对知识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变革”。“面对浩瀚无边的信息海洋,如果不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应对能力,我们就可能被信息淹死”。③“大数据”时代的特征是“巨量资料、浩瀚信息”。④无处不在的摄像头、窃听器、长焦镜头,cookies、黑客程序、木马病毒等实现了对计算机使用者网上行踪的监控和数据隐私的窃取。网络上一篇名为《清华男如何四十分钟锁定王珞丹地址》的文章,就充分揭示了作者如何百度上通过搜索王珞丹的博客和微博,并对其中的信息进行筛选,最终利用已知的公开信息寻找到想要的结果。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世界,任何人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对方的许多基本信息,数量远远超过希特勒通过恐怖政策获取其极权统治下的居民的信息量。⑤甚至有学者悲观地预言:“人们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隐私已经死亡”。⑥
(二)大数据时代带来隐私权的新发展
即使在隐私权极为发达的美国学术界,对隐私的定义也是五花八门。我国学者苏力先生将privacy译为“私隐”,理由在于“首先其是私才隐,而不是因其隐而私”。由此可见,“私”特指与公共事务无关的私人领域;“隐”则指某种不为人知晓或不为人所接触的事实状态。隐私权作为一种要求他人放任自己独处而不受打扰的权利,“在美国立法界和司法界,有两种较为常见的定义。一为‘个人信息控制权理论’,即个人对有关自己资讯的控制,强调‘个人信息’方面的隐私。一为‘独处权说’,强调个人对‘私人行为’和‘私人活动’的不受外界干预的自主决定权。”⑦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概念,如果以公认的美国学者沃伦和布兰代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律评论》第4期发表的《隐私权》明确提出算来,隐私权不过124年的历史。但随着科技、媒介、消费、权力的相互交融,隐私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隐私权又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概念。比如现在的隐私权就不仅仅存在于私人空间,公共空间的隐私权主张在司法实践中逐渐被提出并得到了承认。当隐私权从现实生活转移到虚拟生活中,网络隐私权作为隐私权的下位概念,成为隐私权的一种延伸时,陌生的网络虚拟空间由于其海量、隐匿、开放、互动等特点,也同时使得隐私权的主体、客体、属性及侵害后果都产生了一系列变化:
网络隐私权的主体范围扩大。目前占多数的传统隐私权认为自然人才是隐私权的唯一主体,然而由于网络世界的数据化与虚拟性,,在网络条件下“个体”的概念显然与现实中“个体”的概念有所区别。个体可能是自然人,也可能是自然人的组合群体、企业或社会团体。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带来了隐私客体的扩张。比如在前网络时代,个人的电话、住址、信箱、娶妻生子、家庭成员、患病情况等,公开或在熟人之间传播不会认为是对隐私权的侵犯。而在网络世界里,这些信息则被自动记录,转换为可能被整理利用的数据,成为商家推销产品、发布广告的来源,从而使当事人的私人生活被骚扰。导演冯小刚虽然身为公众人物,但却对自己的家庭住址被曝光极为恼怒,认为侵犯了自己的隐私。而原先不列入隐私范围的非自然人主体的独立空间、个体事务与个体信息都可能成为网络时代的隐私权的对象。
网络隐私权具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双重属性。理论上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同。在网络环境下,对作为隐私的个人信息的搜集、加工、处理、利用,使得隐私利益已不仅局限于人格尊严、公众形象,同时包括主体在经济上的获益。作为一种消极与积极并存的权利,网络隐私权不仅意味着消极地保护隐私、维护个体的精神尊严与安宁,还可以积极地保护隐私主体,比如隐私主体可通过处分和支配自己的隐私,将自己的隐私公开或出卖而获得财产利益(如曾红极一时的下半身写作、隐私写作就属此类)。或者,主体可能因为隐私权被侵犯而产生不良的经济利益影响也可依法寻求财产补偿。
侵害后果严重:在大数据时代,公民的个人信息一旦被以数据化形式储存,掌握在政府、非政府机构以及商业组织的数据库中,实际上就已经失去了对隐私的控制权,不仅私密性大大降低,而且一旦公开就不可能恢复原状。
维权困难:我国目前在隐私权侵权中采取了“谁主张,谁举证”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但从法律操作层面考虑,要求被害人证明人身权益(比如姓名权、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后果并非易事。而在司法实践中,如果国家机关、公益机构和各类法人侵犯公民隐私权时,由于无法证明隐私信息取得者的过错,公民隐私权往往得不到保护。比如医院对某单位在职职工做乙肝检测并将结果告诉用人单位,导致职工被要求辞职的情况,在目前的判例中,依旧以医院没有主观过错为由而不追究其隐私权侵权责任。
隐私权的中国式生长
(一)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起步较晚,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对隐私权保护与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同步进行,缺乏前期积累,情况复杂
在中国,“私”并不是一个好的词语,如自私、营私、阴私、窥私等,“私”意味着不能见人的各种秘密和行为。而“私生活”呢?在“父子君臣,家国一体”的宗族统治传承下,这种强调个人自由意识决定的权利生长尤为艰难。不仅中国传统社会素来没有保障隐私的传统,而且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起步较晚: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司法解释才改变了将隐私权放在名誉权名下保护的传统,实现了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2009年12月26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款明确将“隐私”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保护,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同时该法第22条又规定了侵害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的赔偿责任。第36条更是首次规定了网络侵权责任,对两类网络侵权行为主体即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侵犯民事权益包括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作出了规定。该条完全可以适用于对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如上所述,网络隐私权并不仅仅是传统隐私权简单的空间机械移动,二者有着颇大的区别,对隐私权与传统隐私权的同步保护只能是一种较粗放的保护方式。
(二)由于素养不足,民众以窥探和消费隐私的方式追求隐私权
伴随着中国媒介化、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兴起使得整个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原有的传播生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网络表达自由不仅拓展了公众维权途径,而且深化了公众维护基本权利的内涵。”⑧草根情结底色下萌发的权利意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规模介入生活。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已逐渐成为国人生活中越来越强烈的一项基本的权利诉求。然而意识觉醒,素养不足的现实却使得网络成为个人生产、消费和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重要领域,由此形成一个对权利既向往又排斥,既追求又阻碍的传播景观。
转型中国,利益诉求多元且庞杂。在“网络问政”“网络反腐”“网络倒逼”的名义下,对权利的无尽追求与对权力的无尽追问在网络上极易引发公众逾越隐私的边界。如网上盛传的“官员无隐私”一语,就极富鼓动性和偏颇性。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公职人员有必要对其财产收入、社会关系、生活经历、个人爱好等隐私加以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隐私权的完全丧失。作为受宪法保护的公民,公职人员同样具有人格尊严,其隐私权同样应受到必要的保护。
而以侵犯、消费别人隐私权利的方式来追求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更是屡见不鲜。
“2006年以后,人肉搜索逐渐成为网民惩恶扬善、挖掘隐私和施展暴力的工具,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人肉搜索无视法律规定,曝光他人隐私,进而恶语相加,甚至演变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成为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⑨
“雷政富事件”中对赵红霞私生活的曝光、“郭美美炫富”事件中对郭美美诸多私人信息的挖掘都超越了普通公众“知情权”的范畴,网友自发展开的“人肉搜索”对于隐私的探究和揭露已经明显带有“侦查”色彩。参考国外有关隐私权保护的条款,“未经公民许可,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调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之于众”“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之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都属于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我国《宪法》第38条已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怀疑、谴责超过必要界限,不仅违背禁止侵害公民人格权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文明社会摒弃“株连”陋制、尊重人权的道德关怀。
(三)现实中公权力对隐私权保障与侵害同在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1950年的《欧洲人权公约》8条第1款、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都明确规定隐私权为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我国于1971年加入联合国,并担任常任理事国,自动承担《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义务,于1998年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此,我国完全承认隐私权是公民基本人权之一,并在国际法层面上承担了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国际义务。隐私权的核心在保障主体与公共利益无涉的私人信息不为他人知晓,进而保障主体个人私生活的自由。然而我国司法保护中“礼主刑辅”,以道德教化为主导,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至上的运作模式依然在无形中损害着隐私权的保护。比如学生在学校接吻,可不可以出于教育的目的在校园网络上传播?当丈夫知道孩子并非亲生时,可不可以向单位同事广为宣传和向社会新闻媒体提供情况?基于犯罪预防、安全保障的目的,国家有关执法机关对特定场所或特定主体采取预防性监控措施秘密录音、监听、拍摄、搜查、取证等,有没有可能构成对他人私生活秘密隐私权的侵犯?
权利和权力历来是一对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关系。可以说,权力对权利既可以起到保障的作用,同时又可以轻易侵害到权利。没有权力提供组织与程序上的保障,制定相应的法律和规范,则权利无法实现;但每一种制定和规范又同时对权利的内涵进行了限定,这就可能在现实中构成对权利的侵害。大数据时代,私生活与公共事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私人领域到底包含哪些范围?其保护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些都给隐私权的保护提出了新问题。《警用摄像头成“偷窥眼”:个人隐私谁来保护?》《上海地铁乘客拥吻视频流传个人隐私受侵犯》等屡见不鲜的新闻就显示了公民隐私权在面对公权力被侵害时的脆弱性。
既给与又剥夺,既保障又侵害,在握有庞大资源和先进技术的政府手里诸多矛盾并存。比如,上海市政府对“群租”的整治举措就规定“一个房间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房屋应当以原规划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分门进出的客厅、厨房间、卫生间等均不得单独出租”等,就引发法学界和业界的强烈反应,认为“这些措施涉及到宪法隐私权在公民私生活自主决定权方面的保护。公民与谁合租,以何种方式合租,完全是公民个人的私人事务,受宪法隐私权的保护。国家除非出于更为重大的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否则不能对公民的私生活横加干涉。”⑩
综上所述,好奇与窥私、欲望与理性、审美与审丑并存不悖,隐私与公共、娱乐与政治、精英与粗鄙济济一堂,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及其急剧的社会转型,让大数据时代的隐私与隐私权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隐私权的保护
“作为一种扩张性权利,网络言论自由权往往通过抑制和损害其他权利作为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网络言论自由权需要受到限制。”輥輯訛基于私生活越来越多被卷入数据的洪潮,现代国家的管制与公民私生活发生越来越密切的关联,为保障隐私权的健康发展,有必要从立法和管理两方面入手:
(一)以宪法为根基,建立完善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
隐私权涉及的内容广泛,并不是单一的权利诉求,作为由众多内容组成的权利集合,内容也随着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呈现出其自身的扩张性特征。如同性恋和宗教信仰,过去曾受到公开的惩罚和规制,现在则基本上属于私人领域。婚内强奸、溺婴、虐童等以前认为是家庭事务,现在却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律的干预。要实现对隐私权的全面保护,确立宪法隐私权的地位,建立完善的隐私权法律保护体系势在必行。
虽然我国宪法并未直接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确立下来,但从宪法的条文规定中,完全可推导出宪法隐私权的存在。
我国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8条规定,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条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由此看出,这些对公民典型私领域的保护也正是隐私权保护的重点所在。作为基本人权之一,即使没有明确命名,但国家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
现在对隐私权的相关保护零散见于《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尚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系统的全面保护公民隐私权的立法体系。我国于2012年12月28日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并出台了《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对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信息管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和效力”,为保障和维护公民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限制国家权力扩大介入私人领域的扩张,明确规定宪法隐私权,通过宪法、民法典、刑法、诉讼法等法律的通力合作,通过建立起一个完善的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来科学界定隐私权的主体、内容与客体;合理界定隐私权与知情权、表达自由等权利之间的界限;规定侵害隐私权行为的种类及其构成要件;明确侵权救济与法律责任,对侵犯他人隐私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行为,还应做出刑事处罚的规定等等,从而充分发挥宪法、实体法、程序法甚至行政法规、政府规章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方面的合力。
(二)加强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培育公共领域的健康发展
在中国法制目前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监管与业界自律是一个良好的隐私权保护途径。
绝大多数网站为实现自己的商业目的,漠视客户个人的隐私权,利用cookies追踪用户的上网记录,收集访问者信息,非法收集、转售客户的信息给网络广告代理商和网络服务商。为保护网络隐私权,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扶持相关的产业,如:网络隐私投诉渠道、网络隐私权保护的中介机构、制作网络隐私权软件产业、第三方认证与评估组织等。另一方面有必要加强监督,督促网络整改,甚至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
同时网站也要出台自律规章或准则,加强对用户基本信息的保护,向用户保证不公开、透露用户的基本信息,不私自透露用户注册信息等。
(三)加强个人法律素养,净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
“大数据时代人类被绑架到一个无隐私的真空世界,未来也可能会爆发数据垄断危机,催生出形形色色的数据弱势群体,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工业污染——大数据污染。”輥輰訛网络世界一方面使得人们前所未有关注自己的个人空间,一方面也使得侵犯隐私变得更为容易。目前我国还没有推行网络实名制,这也使得曝光隐私、消费隐私和侵害隐私的行为在网络上更为泛滥,管理和处罚更有难度。2014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继续保持稳定增长。輥輱訛虽然网民众多,但自媒体使用者呈现低学历化、低年龄化,低收入化的特征。法治意识普遍较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成熟;知识结构有限等因素使得这样一个群体虽然有信息发布权,但很少会深思熟虑,也不会对道德、公义、社会利益等有着成熟的思考,极易造成对网络自由权的滥用,从而侵犯他人隐私。在中国社会转型、矛盾频发的背景下,网络发言不仅需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更需要明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所欲亦勿施于人”的道理,这都是培育尊重他人隐私观念的起点。对法律信仰的培育也许将是隐私权保护更长远且艰巨的任务。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注释:
①【美】迈克尔·埃默里等著,展江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第九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7页。
②Samuel D. Warren and Louis D. Brandeis,“The Right to Privacy”Harvard Law Review, Vol.4 No.5 (1890) .
③张涛甫:《大数据时代的出版困局及其突破》,《编辑学刊》2013年第2期。
④刘建明:《“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北京日报》2013年5月6日。目前对大数据还没有一个权威且统一的定义。本文赞同刘建明教授之见,即“大数据是巨量资料,浩瀚信息的另一种称呼”“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末盛行一时的信息爆炸的同义语”。
⑤【美】玛格丽特·安·艾尔文:《信息社会的隐私权保护》,陈雪娇、王继远译,《民商法论丛》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540页。
⑥MichaelRoomkin:" The death of Privacy? " , 52 Stanford Law Review 1461 (1999) 2000)
⑦刘水静:《也谈“亲亲相隐”的法律实质、法理依据及其人性论根基——兼评邓晓芒教授的〈儒家伦理新批判〉》,《学海》2012年第2期。
⑧林凌:《论依法引导网络舆论——兼论网络言论自由权保护》,《学海》2012年第2期。
⑨林凌:《网络暴力舆论传播原因及法律治理》,《当代传播》2011年第3期。
⑩屠振宇:《“群租”整治令与宪法隐私权》,《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1)林凌:《网络媒体立法初探》,《编辑学刊》2013年第2期。
(12)董小玉、温如慧:《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空间——众声喧哗的大数据》,《当代传播》2013年第6期。
(13)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3/ t20140305_4624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