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南方以南的彩色国度
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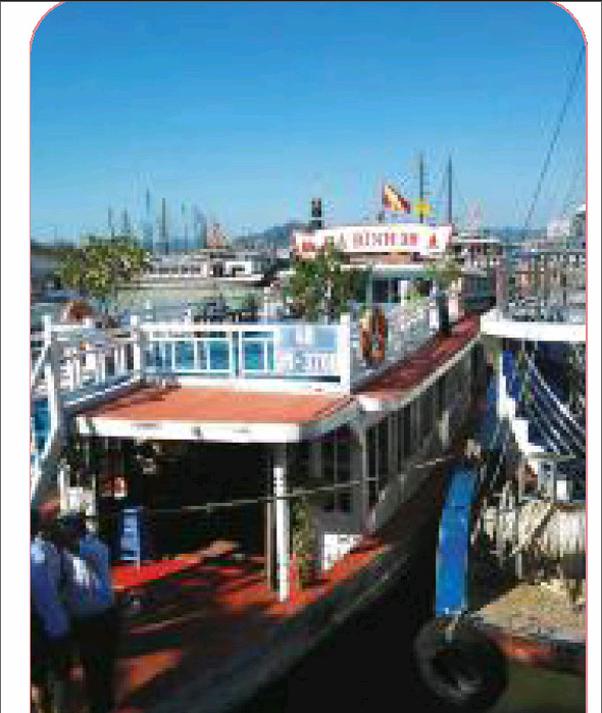

从南宁坐大巴去越南
越南是我、阳仔和猴儿东南亚穷游的第一站。初夏的一个早上,我们搭上从南宁到越南海防的车,目的地是下龙,那个被称作“海上桂林”的地方。
路上我一直好兴奋,听着《国境之南》,看窗外南国的树绿出一种磅礴的气势,远处的山绵延出形态各异的美,就好像每一座小山头都有一段故事。以前看楚留香的时候,读到香帅去找苏蓉蓉那段,那时想象中苏蓉蓉住的地方就应是在这样的山里。在友谊关出境时,边检用英语问我是否会讲英语,我竟然紧张得用法语回了他。他有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问“Et tu parles francais?”(法语:你会讲法语?)我回“Yes.”然后看他忍不住笑了,继续问道“where do you want to go?”我开心地答,“Hanoi.”
因为要在友谊关等很久的车,我只好在边境玩自拍又拍外面的蓝天青山,然后换好手机卡。河内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一个小时,看着时钟从12点回到11点,觉得好像是从上帝那里偷来一个小时。
去往海防的车上,我坐在车窗边看越南的乡下。窗外是好看的山和水田,这里的庄稼人戴着斗笠在田里做活儿,田边有很多两三层的房子,都是细窄的形状,墙面涂成彩色,有的人家还特意修出种植花草植物的小露台,感觉每一座彩色小房子都很漂亮。
司机告诉我们,应该在海阳换乘去下龙的车。我们在海阳下车后,原以为应该有个汽车站,不想竟只是个小镇的十字路口。站在那个小路口,阳光很晒,那一瞬间我特别真切地感到,我已经离开国内来到越南了。街上有人想给我们指路,却因为语言不通作罢。我们怕自己发音不准,便把“Ha Long”写在纸上,拦住一辆开往Hanoi的红色大巴,售票师傅从车上跳下来看了一眼纸,说了句“Ha Long,ok”,便开始帮我们提行李。在一个小路口找到了去下龙的路,这感觉好棒。
下龙很多人会讲不太流利的汉语,但通英语的人好少。这个城市看起来好像很旧,但因为建筑会涂成彩色,又有好看的雕花和露台,一眼看过去觉得很漂亮。旅馆房间也很旧,但桌子上插了一朵红玫瑰。越南人很穷,但好像活得很精致。
下龙:清亮温柔的海水有些美
第二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简直被下龙五颜六色的房子惊艳到了,原来它们在白天是这样的色彩斑斓。越南人会特意在每间屋子外建一个专门放花的小露台,露台上的花草也是五颜六色的,看过去觉得心情特别好。
我们坐taxi来到下龙湾,海边停着很多白色的船,通往甲板的楼梯上有欧式雕花,甲板上放着花花草草,还挂着好看的小彩旗。以前看“He is just not that into you”时,Rachel的男人有一艘类似这样的船,他因为不想和Rachel结婚,大吵一架后一直住在自己的船上。故事的最后,Rachel决定和他一辈子同居,去船上接他回家。男人在船上把Rachel抱起来转圈,回家后拿出了求婚戒指。不知是不是从那时起,爱上这种船,好想赚钱买艘船,可以在上面写字画画,或者做点小生意,闲了就开着它出海……
坐船游下龙湾的时候,觉得景色好美,阳仔说“它是世界七大自然奇迹之一”,猴儿说“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我趴在窗边往外看,想着不知道太真仙子是不是住在海那边的山里。
下船游溶洞时,一个妹子跑过来用很不熟练的汉语和我讲话,告诉我她是河内人,会讲一点点汉语,很想和我做朋友,旅途中遇到困难可以找她,还让她男朋友帮她和我们拍合影,真是个可爱的越南小妹。我们上岛进溶洞,各种彩色灯光把溶洞里形态诡异的石头照得很美。大家在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我觉得几千年前这里面应该住着一只妖精,溶洞沾了她的灵气和妖气,越发美得诡异神秘。
继续乘船游天堂岛的时候,我们遇到几个从西安来的阿姨。她们已经来东南亚自助游了一个月,几个阿姨不会讲英语也不会网上订票订住宿,就是真正地走到哪儿玩到哪儿。她们说都已经退休了有时间,就约着姐妹几个出来玩儿,用汉语和手语在东南亚自由行了一个月,玩得很开心。我听她们眉飞色舞地讲这一个月的经历,觉得她们很棒,都是有情怀有胆量又很可爱的阿姨。
天堂岛的海水很清,没带泳衣的我们也忍不住下海玩了好久,海水拍在身上温温的,让人舍不得离开。
晚上吃饭的时候,再次感叹越南人很穷却很精致。他们做菜舍不得放油和调料,却会把黄瓜切成波浪边缘的片状,直接放在炒饭上只为增加美感。
晚饭后我们又回到海边,夜里的海是深色的,抬头时觉得月亮格外明亮。我们就着月光赤脚走在夜晚的海边,深暗的波浪涌来时会有一种眩晕感,眼前的景色,壮阔又神秘。我突然想起初中时看《梦里花落知多少》,林岚跟着火柴和陆续晚上跑到上海的一个海边,坐在海边的石头上,火柴问林岚有什么感觉,林岚说忧愁。陆续一直不说话,看书时觉得“忧愁”这词用得矫情,现在自己站在夜晚的海里,突然就很想抱抱那天的林岚……
河内:喧嚣而沸腾的生活
早上从下龙出发到河内,路上看遍了越南乡下的风光。房子还是窄窄长长的,涂成斑斓的颜色,田间偶尔出现他们的陵墓,一般会建成红色的小房子,很是讲究。路况不好,车子一路颠簸着到了河内。
中午到河内后,我们找了家小店吃饭,老板娘只会讲越南话,我们只好用手语比划着告诉她我们要吃粉和春卷。在河内吃粉,是要自己把蔬菜和生粉放到一种有肉的汤里,有点像吃过桥米线的感觉。街上的房子还是很好看,越南城区没有多少高楼,据说这是为了保留城市原貌。很多房子都是老旧的感觉,但它们还是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露台上摆着好看的花儿,有的花儿甚至会垂下一层楼,好看得扎眼。下午以还剑湖为中心逛河内,我很喜欢那些写着汉字,贴着汉语对联的寺庙,它们静静地分布在热闹的河内古街上,当地人和游客都可以自由进入,但进寺庙礼佛前必须脱掉鞋子,以示尊敬和虔诚。很多寺庙里都有和尚在唱经,檀香的味道萦绕在经文里,让人忍不住想要跪下来,只为沾染安静虔诚的气息。
河内人很多,各种白皮肤蓝眼睛的人也夹杂在东方面孔里,让这个城市看起来更加热闹。摩托车大军奔流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大街上没有摩托车道和机动车道之分。可能是因为相较于摩托车,开汽车的人简直太少。越南人用帽子口罩长袖把自己全副武装,开着五颜六色的摩托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奔流而过,这是属于这个城市的独特风情。
我们选了一家湖边的咖啡厅,点了一杯奶昔。能坐在一个小咖啡厅里看看窗外的人,是我喜欢的接触一个城市的方式。相比于去旅游胜地扎堆,我更喜欢漫无目的的在一个城市游荡,夹在陌生的人群里感受它独特的气息。逛逛繁华的大街,也转一下冷僻的小巷。找看起来不错的馆子好好吃一顿,也去大排档和路边摊坐一坐。如此才能感受到属于这个城市的尘烟和风情。
晚上逛河内三十六古街,这里人声鼎沸。吆喝声里混杂着来自世界上各个地方的语言。越南妇女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水果,对每一个看起来像游客的人笑。她们大多不漂亮,即便是年轻的妹子,也都不太好看。可是看到她们笑,却无端地感到亲切。夜市上卖东西的阿姨和小媳妇们都不怎么会英语,我只好拿着计算器和她们还价,通常能还个几万越南盾。
我会记住这个城市的热闹喧哗,和她沸腾的生活。
胡志明:它曾经是西贡
去胡志明的前一个夜里,我重读了一遍杜拉斯的《情人》。不知道现在西贡的街头,是不是还如杜拉斯十五岁半时那样,充满了暧昧和忧伤的味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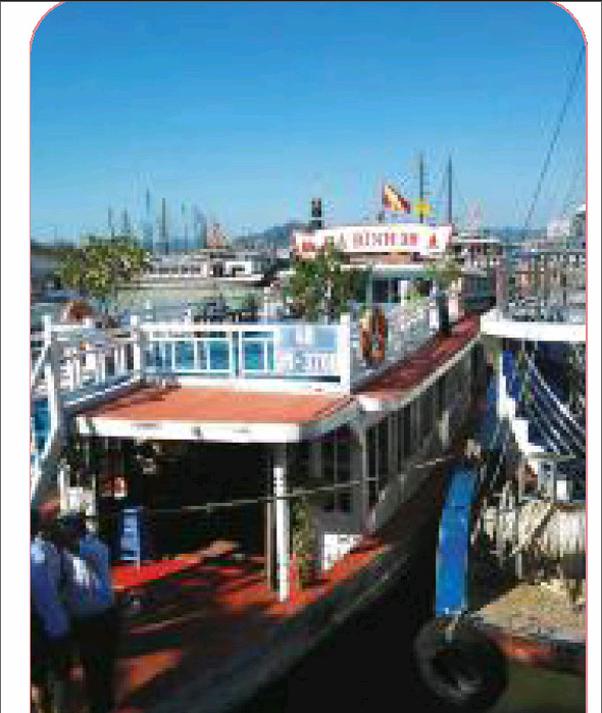
搭飞机去胡志明市时正值傍晚时分,天边有极美的晚霞。看到如此美丽霞光的那一刻,我好像突然更深刻地理解了“瑰丽”一词的含义。所谓瑰丽,原来应是如此无与伦比的美丽。我坐在窗边,看外面天蓝得透明,霞光映在湄公河上,把河水也染成温暖的红色。河上有船经过,荡在倒映着金色和红色的水波上,不知是去往什么地方。当年王勃看到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或许与眼前景光有几分相似。旅行最棒的时候,是眼前的景色与心中的文化积淀产生共鸣的那一刻。
第二天我去了一直心心念念的湄公河,湄公河河水是混浊的,就像杜拉斯写过的那样。河面很宽,天很辽阔,泥沙色的江水奔流而过,它们从澜沧江而来,去往南海。江水畔的岛上是一派热带风光,芭蕉和椰子树都有很大的叶子,植物生长的密度很大,叶子们层层叠叠地拢在一起,绿得浓郁又清凉。湄公河里飘着很多绿绿的植物,开始时我们还以为是昨晚的雨把树枝打在了河水里,可这些植物都长得一样,而且隐约还能看见根部,根茎不长,叶子是圆圆的。它们漂在宽广的江面上,像是随时都会被水浪冲走,但又热烈地生长着。忍不住去问了导游它的名字,导游告诉我它叫water-fern,原来就是睡莲,觉得湄公河真是美丽又神秘,混浊的江水下一定埋藏了很多往事,当然还有掉下去的睡莲叶和椰子果。
站在西贡湄公河口岸,想到《情人》里的杜拉斯,十五岁半的法国女孩在殖民地西贡的街头遇到她的中国情人,一个孱弱而文雅的中国男人。他很爱她,而她似乎并没有那么爱他,她内心阴郁晦暗,对爱欲享乐的渴望胜于对他的爱。很多年之后,中国情人去法国找她,杜拉斯从这个场景讲起她的故事。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意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
不知道十八岁的杜拉斯,在西贡湄公河口岸看到邮船外那个大概永不会再见到的爱人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二十四岁的我越来越深刻的觉得,男人还是喜欢看一张漂亮的脸……
最后一天,我们乘大巴离开胡志明去柬埔寨。我留恋着窗外的景色,它留下了法国殖民的痕迹,彩色房子和雕花菜品透着小资和精致的香味;它保存着中华附属国时期的遗迹,血脉里还有盛时华夏文化的影子;它也努力延续自己的文化传承。这一切和谐又美好地交融在如今这片土地上,在南方以南,喧闹而朝气蓬勃地生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