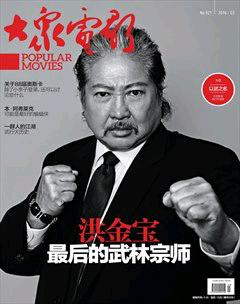毕赣爱人是永恒的故乡
毕赣是我专访的第四位金马最佳新导演奖获得者,前三位分别是以《寻龙诀》创下2015华语票房之最的乌尔善、以《爸妈不在家》爆冷获大奖的陈哲艺和演而优则导出《一个勺子》的陈建斌——金马向来以其善于发掘黑马和自成评判体系闻名,而出生于1989年的毕赣是历届新导演中最年轻的,是让同为80后、出生于1984年的陈哲艺也不得不赞叹的年轻。
他是我和很多人都不够了解的导演类型:来自贵州,非科班出身,没有国际背景,也不是影评人或有相关从业经历——换言之,他不在我们熟悉的任何一个套路里,正如他的电影《路边野餐》,诗意、潮湿、举重若轻地讲述了别离和生死。在金马之外,其还获得了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影片和洛迦诺电影节最佳新导演奖,前者在《电影手册》中形容其“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新魔幻现实主义,有时令人费解,却刻刻让人着迷”,后者的选片负责人马克·佩兰森则指出其“创造性地构建出一种诗意地进入自己故乡的途径”。
一位值得探究的新导演就此横空出世——就像电影《路边野餐》中引用的诗句所说,如同一道“柔和的闪电”,唤醒了台湾电影以及很多人的记忆。想要了解他,或许唯有通过观看他2016年3月即将于法国、4月即将于中国台湾率先上映的电影。
那日飘雪的清晨,我和他穿过大半个京城去补看这一场先有金马专访的电影。有些电影,适合一个人看;有些电影,身边若没有人陪伴,却好像很难看完。
不过,《路边野餐》哪种都不是。事实上,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归类的电影。在官方对外版本中,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贵州黔东南神秘潮湿的亚热带乡土,大雾弥漫的凯里县城诊所里,两个医生心事重重活得像幽灵。陈升为了母亲的遗愿,踏上火车寻找弟弟抛弃的孩子;而另一位孤独的老女人托他带一张照片、一件衬衫、一盒磁带给病重的旧情人。去镇远县城的路上,陈升来到一个叫荡麦的地方,那里的时间不是线性的,人们的生活相互补充和消解。他似乎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重新思索了自己的生活。
专访之前,我把以上这段文字看了三遍,最终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下面画了三个横杠,在采访中直接表达了我的不解。
“为什么要写那样一个……挺有诗意,但也挺绕的故事梗概?”
“没看懂?”是导演也是编剧的毕赣笑言,显然我不是这么说的第一人,“其实它的信息是很简单的,就是说他去找他的侄子,然后在过程当中……偏公路性质的这样一个电影。”
“它不是那种简单的线性叙事,当中还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用词……我不知道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对我来说,是很多很多很多个故事,每次我跟别人叙述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它是不一样的东西,它的本质就是去旅程的过程。”毕赣说,“有时候我觉得他是跟其他陌生的人相遇了,有时候我又会觉得他是跟那些人重逢。”
我被这个诗意的回答震得微微有点发愣——事实上那也是整个采访和后来看电影过程中不时会发生的事。毕赣否认自己是一个诗人,尽管他的诗作在网上用心一点还能搜得到,关于童年和小时候的电影院,“散场后凯里下了场大雨,比吃肉的白狗还急”——但我必须承认,他的影片有着难得的、真正的、浪漫成疾般的“诗意”——那是比被玩坏了的矫情文艺腔高级很多的东西,是从日复一日的生活里提炼而出、站得住脚又注目着远方的善意。看完电影后,我便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阅片无数的国际发行方小妞会对我说:“看完你会臣服于它的”,尽管我的回答是“我不会,我从来没有臣服于谁——只有认同或不认同的区别。”我对一个诗人的自传就像对一个网红的经历一样不感到丝毫兴趣,但就像和我一样品味刁钻的朋友、代表作有《蓝色大门》等的中国台湾著名导演和制片人徐小明所言,“《路边野餐》的表达是独特的,如今的时代,不匠气是很难得的。”
相对成熟的市场对《路边野餐》有更多的接纳和欣赏。签下了《路边野餐》台湾发行的前景娱乐有限公司负责人黄茂昌对我如此评价《路边野餐》:“有着超越文明的逻辑,里面的人物关系,父子、情人……是地域性的,但任何人也都是有迹可寻的。”
这与洛迦诺的评语不谋而合:在这部令人惊讶的长片处女作中,导演采取了一条最简单的实现道路——以一个40分钟的长镜头,混合了主角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事实上,因为资金和设备的限制,连毕赣都承认那完全不是一个制作意义上完美无缺的长镜头,但,陌生与粗糙,这并不影响它能带给人的感动——当你看到那个眉眼很有些像《苏州河》里的周迅的叫洋洋的女孩,镜头跟随在她的身后走在绿野间,她散开头发,披上蓝色的大衬衫,黄色的裙子随着她的脚步旋转、散开,左手腕上还飘着一根红布带——那是之后她要送给他的礼物,她说:“红布带给你绑上了,以后(摩托车)就不会老熄火了。”此时,她下到水边,上了船,嘴里喃喃地背诵着导游词,又买了风车……一个年轻美好的女孩,她去对岸,她总是要去对岸的,尽管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有理不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候——《路边野餐》不负责解决问题,而是提出。我自己在其中最喜欢的场景,是一个女孩为陈升洗头,她笑笑地说:“背着手的人是有罪的,因为老一辈的人说……都是前世绑着流放过来的。”她问从外面的世界来的陈升,“不知道蓝色的池子里有没有海豚”,陈升回答说“汞池是重金属,有剧毒”,然后他在关了灯后那一片暧昧迷蒙的黑暗里用手捂住了手电筒,指缝中透出红色的光,告诉她,“这就是海豚带给我的感觉”。
那不过是血管。我在这样的镜头里听到自己心底条件反射般的答案,在现实世界沉浸久了的人都会隐隐嘲笑这样的浪漫,但我脑海中浮现的场景却是儿时记忆里,午后放课空无一人的化学实验室,有个补课的小女孩盯着玻璃器皿里的蓝色液体——硫酸铜,那是一种鲜艳的、迷幻的、好像能致命的蓝色——后来她见过了很多文艺作品中的蓝色,吕克·贝松的《the big blue》,村上龙的《无限近似于透明的蓝》,但没有哪一种蓝,像那时的体验那样深刻,深刻到她想要以此祭奠出自己的一个故事。那个小女孩,是我。此时,以写别人的故事为职业的我想起了这一切,也想起了毕赣采访时所说的那句话。
“其实艺术电影最好理解,因为它不需要你去分析它,去感受就挺好的。”他说。
事实就是如此。与其说《路边野餐》带给我的是感同身受的感动,不如说是启示,用普希金的诗来说,带着“一种纯洁的、柔情的回忆”。在这个故事的结局里,毕赣的描述是“最终,陈升到了镇远,只是用望远镜远远地看了孩子,把老女人的信物给了她旧情人的儿子,一个人再次踏上火车——分不清这个世界是我的记忆,还是我是这世界的一个浮想。”电影的结尾里,是男人在火车的每一节车厢里画上钟表,“让她总能想起我”,女人女红才会用到的纽扣,却散落在钟表壳里——毕赣的《路边野餐》英文名叫作“Kaili Blues”,他把凯里变成了一个只有他能描摹出来的魔幻世界,他再次证明了动人和成功一样,都是没有模式的,唯有一点:就像我喜欢的《苏州河》和《迷失东京》一样,电影传递的是情绪、是一个梦,但它能且只能来源于创作者最熟悉的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路边野餐》奇迹般地几乎对每个牵扯其中的人都产生了影响,你很难说这是诗意,还是天意:得金马奖后不久,毕赣回到故乡凯里举办了婚礼;黄茂昌从台湾去到凯里参加了婚礼,同时发现影响毕赣电影美感顿悟的影片《导盲犬小Q》正是当年由自己发行,创造了日片在台上映记录,同时也是因为此片自己才有钱结成了婚;至于我,我在这个2月意料之外地往返故乡两次,在那里完成了大部分的新书书稿,在一次返乡途中收到了某个前任发来的生日礼物,那首自弹自唱和着吉他的歌曲让我想起了《心动》里浩君留给小柔的字条“这就是我曾经想你的日子,现在把它全都送给你”,而《路边野餐》中的那句“他就叫爱人,林爱人”则让我翻出了旧书中很久以前自己写的一段话:“我只想和我喜欢的人去看一部电影,希望他能让我想起在‘爱情一事上久别重逢的勇气……就让我们以相同的姿态依偎在电影院里,哪怕能触摸的东西,永远没有‘永远。”
都过去了,都实现了,周而复始——我在意故乡,因为那是梦开始的、最初的地方;我也不那么在意故乡,因为爱人就是永恒的故乡,这是我能想到的、对“对的爱情”的最高褒奖。毕赣说:“故乡对我们的概念已经改变了很多,它以前是一个地域,是一个空间,我得回去那个地方……但后来,故乡慢慢变成了图像,变成了时间,变成了其他的东西,就跟我的电影一样,故事也是被分散成各种东西。”对此,我不能同意更多了。
最本质的是普通普世的情感
你说过,电影相对文学来说可能是一种相对肤浅的表现形式。
它是具象的嘛,它比较具体,它只是一种很具象的幻觉体验,文学、音乐很多时候比较抽象嘛。
那怎么样把你比较偏好的这种文学语言转化成镜头语言呢?
会建立不同层次的文本让它们之间有一些互动。就是影像可以跟诗互动,然后很多时候,所谓的肤浅和高级,它不是那个比较的关系,比如说你拍一个镜头,你拍一个小孩在吃饭,它没有存在这些,好看就好看,美是很简单的东西。
有一些评论说你的这个电影是新魔幻主义,然后也有一些评论说你的电影没有任何的叙事的界限,但我想,应该每个人在成长的历史上都会有一些对自己影响比较深的导演或者电影吧?
我也有啊,像塔科夫斯基、侯孝贤都给过我很好的美学上面的引导。但是拍电影这个东西你要自己去拍,你要自己去落实,因为电影是骗不了人的。你要盯着它看,它是一分一秒在播的,你有任何的不好都会被别人看到,所以只有我们自己去拍的时候才会做各种处理,各种办法,前辈的很多电影只是给我们一个引导。
有没有什么在你成长当中比较多反复看的电影?
有,像《再见南国》,还有《潜行者》,我是反复看,像塔科夫斯基的电影我是反复看,反复看是为了欣赏他,不是为了获得他什么。
所以你觉得找到自己的这种电影美学的风格很重要吗?
就去拍就好了,我觉得也没有故意去寻找一种风格。其实我最本质的东西是一个很普通、很朴质的情感,那个东西是我想表达的,关于“爱”也好,关于“分别”也好,那是很简单的东西。然后至于怎么样用我的语言,用我的电影语言去诉说这个简单的事情,可能就会考虑到……但我不会一开始就考虑一个风格,我会设计出一个很好玩的概念,然后在这个概念里面去完成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朴质的东西。
比如说,在你的电影当中,你是怎么样找到一些好玩的概念,或者是和别人不一样风格的东西去阐述那个朴实的东西的?
比如说我之前拍那个短片叫《金刚经》,但我拍完以后我也不太懂这个《金刚经》写什么,我就去翻来看那三句话,“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然后看到这三句话就觉得我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我表述不出来,我到现在也表述不出来,我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我就想能够表达一下,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时间观念,其实我也是这么考虑时间问题的,然后就用电影去处理它——那个主角去到那个地方碰见了他以前的爱人,碰见长大了的他的亲人共同存在于一个旅程里面,我觉得看我的电影就可以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但是看完了又不知道了,就是这样。
你的这个处女作长片是由短片发展过来的吗?
不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建立一个地方,短片只是它的一个厨房,《路边野餐》可能是它的门,新项目《地球最后的夜晚》可能是它的客厅,重要的是整个地方——因为我是学电视的嘛,所以一般一拍就特别像电视剧。
电影这件事情不是学出来的
现在新导演的这种成长路径和以前有一些不同吗,你觉得?
因为我没有在圈子里面,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
你所谓的不在圈子里面指的是?
因为我是在贵州生活,我没有跟很多专业的人合作或者认识,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没办法去梳理它。
如果说没有特别学过电影这件事情,那么这个片子是怎么拍出来的?
学电影不一定是去电影学院,去哪个学校学个三年,读个研究生就学会了电影。
那么你的成长路径是?
在学校读书,读书的时候我老师很支持我,然后就拍短片。我也没接过那种商业的,我除了自己玩,还有自己解决生计以外,我也没有做过工业的东西,但是我对工业是有诉求的,我希望我的电影有一个工业标准,有一个工业的气质在里面。之前拍了一个长的很实验的作品,然后又到了这一部,到下一部……我没办法梳理这个坐标,反正我就是一个一个拍,比较好。
当然我觉得你已经算是获得了某种成功吧,这个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包括最佳新导演奖,你自己意外吗?
不意外呀。
(笑)这真的是年轻导演才会给出的回答。
没有,因为很多影展会跟我们要片,然后洛迦诺当时的选片人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讲述他是怎么来阅读我的电影的……但是评不评奖,这个有时候我觉得它是运气。
你觉得要怎么区分艺术电影和别的电影类型?
文艺电影它就是类型片嘛,它只是带有点文艺气质的商业片,它的商品属性会更强一些。艺术电影它就是一种很别致的体验。
甚至我都觉得可能艺术电影比一般的文艺电影更难让人理解,但可能带来的感动会更大一些。
其实艺术电影最好理解,因为它不需要你去分析它,去感受就挺好的。因为该分析的我们都做完了,观众只需要去体验它就好了。
——解读影片《路边野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