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除贫困 须补足社会发展欠账
赵福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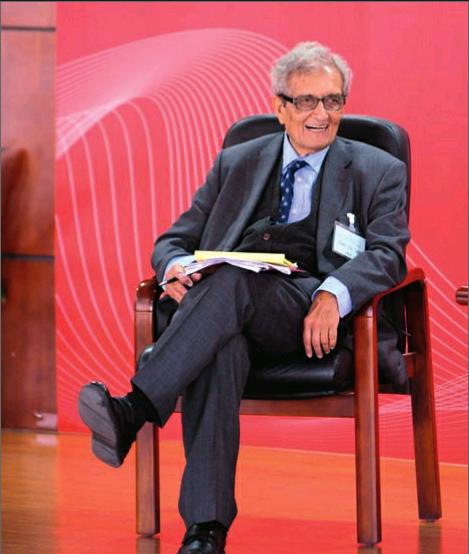
那是1943年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尚未独立的印度孟加拉的大城市达卡,十岁的男孩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正在自家前院里踢足球。
一个穆斯林男人蹒跚着走进来,虚弱地喊着:“救命……救救我……”男人肚子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血流不止。
“我大声哭喊,叫来了家里的大人,把他送到医院。”阿玛蒂亚·森回忆道。
当时印度正值宗教冲突与孟加拉大饥荒,虽然那个男人的妻子一再告诫他不要去动乱的地方,但是家人已经没有任何吃的,他不得不到印度教徒居住区寻找工作,最终丧命。
森于1933年出生在印度孟加拉邦圣蒂尼克坦小镇,与诗人泰戈尔是同乡。“阿玛蒂亚”便是泰戈尔为他起的名字,意为“永生”,泰戈尔说:“这是一个大好的名字。我可以看出这孩子将长成一个杰出的人。”森的外祖父是泰戈尔的助手,曾随同访问中国。
多年以后,森仍不断回忆起那个垂死的男人最后的遗言:“孩子们……他们好饿……”,他常常思考,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压力让这个男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推动了他至今的研究。
阿玛蒂亚·森的学术研究涉及经济学、道德哲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而且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对全球遭受苦难的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注,森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都是技术型的,但他更关心最广大人们的实际发展。老实说,只有印度会不断诞生这种悲天悯人、大智大慧的伟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王邦维教授说。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了时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阿玛蒂亚·森,授奖公告指出:“从社会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困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他运用经济和哲学相结合的工具,重新使用道德尺度来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
由于森始终保留印度国籍,以便参与国内事务,他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
经济增长不能只是少数人受益
“我们生活在前所未有的丰裕中,但这个世界仍广泛存在着营养不良与饥荒。人们通常含蓄地表示,我们无法做什么来改变这种极端悲惨的状况。”
在多次饥荒中,森都观察到:那些贫苦的农民、工人成千上万地活活饿死,那些地主和商人却在大发横财;严重饥荒时期,甚至有的饥荒地区还在出口粮食。
森发现,没有一次大饥荒真的是因为粮食短缺。饥荒是人们获取食物的权利不平等造成的,底层群体连果腹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即使最贫穷的国家,只要政府措施得当,也能度过难关。
相反,如果受难者没有地方发出他们的声音,就可能饿殍遍野。“事实是显著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言论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森的“福利指数”是对人的福利的本质更准确的把握。
以往衡量一国福利的指数就是人均国民收入一项。森指出,福利的本质不是收入,而是“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人的生活可被看作多方面的生活质量的集合。收入和一定的营养、寿命、交通、社会保障、环境、社会参与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核心是达致某个生活水平的机会和能力。
森进一步指出,“贫困不只是收入低下,而是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可行能力”的提出,为人类发展学说奠定了哲学基础。目前人类发展理论被众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用于测算社会进步,比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森批评那些狭隘的发展观,包括发展就是GDP增长、收入提高、工业化、技术进步等。
“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都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当代世界还远没有为众多甚至大多数的人们提供初步的自由,比如免受饥饿、贫困、本可避免的疾病、性别歧视,有适当的衣服、住所等。发展就需要消除这些剥夺。”
森认为,经济增长与可行能力的扩展是互相促进的,人类自由和可行能力的扩展是目的,GDP增长等都是手段。增长创造的资源可用于发展教育、医疗、营养和满足更自由的人类生活的其他需求。可行能力的扩展使得生产的加速成为可能,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有赖于此。“经济增长只是更宏大、宏大得多的人类目标的一小部分。”
对于印度的高增长成就,森也指出另一面:虽然特权阶层得到了好处,但是更多的人过着被剥夺和不稳定的生活,他们本不应如此。他们的生活条件并非完全没有改善,但是大多数人的改善非常缓慢,甚至几乎没有。
2012年,半个印度曾突遭大停电。整个国家理所当然对行政的低效率感到愤怒。但是,遭遇停电的6亿人中有2亿人从没用过电的事实却没有得到讨论。同样在这年,一起令人发指的轮奸案激起了公愤,针对女性的暴力终于成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但是激起抗议的原因是,受害者是一名医学院大学生。在遭到践踏的贱民女性中,类似暴行常年存在,却没有得到主流媒体关注或激起强烈抗议。
森因此认为,虽然在民主治理、世俗统一、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印度当今的荣耀是极度不确定的。
阿玛蒂亚·森教授对中国的发展一直保持关注,1983年以来,他多次到访中国,并从事中印比较研究。其观点对中国亦有重要借鉴意义。
印度无法超越中国
记者:您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增长近几年持续放缓?
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长期保持着非常快的发展速度,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没有先例的。在1995年,中国GDP约占世界的2%,而现在已经占世界的1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比重。事实上,中国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其增长速度自然会有所变化,我们不可能指望中国一直以那样的速度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不算什么大的问题。
记者:有预测,印度的人口尤其劳动力将会超越中国,而这会带给印度巨大的优势。
森:印度人口能否超过中国,我也不确定。因为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印度的生育率也在下降,而且人们往往低估了其下降的程度和趋势。
尽管中国的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仍存在差距,但其教育普及还是比印度均匀得多。印度一半地区的教育开支十分有限,而另一半地区则并非如此。印度有一半邦的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但是另一半则远高于世代更替水平。
我认为,在这样分化的印度,这种人口增长并不会使印度受益。我也不相信一定有所谓的人口红利,因为人口太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就业难等等。
在我看来,如果印度能够向中国学习,更广泛地发展教育,印度就可以从人口增长中受益。这是印度下一步需要重点做的。
记者:未来几十年,印度经济增长会不会赶超中国?
森:不会的,印度无法超越中国。因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不如中国那么稳健,目前印度国内对其经济发展有些担忧。
不管在欧洲、美国还是日本,经济增长的最基础要素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健康的劳动力。但是印度还有大量的未受教育的、羸弱的劳动力。印度需要改变这种现状,却一直没有凝聚起足够的改革动力。目前,印度国内的担忧还在不断增加。
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印度经济存在很大的缺陷。以商品生产为例,中国人可迅速制造出各种商品,印度人却无法做到。印度主要制造三种商品:信息技术和制药产业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非一般劳动力,虽然手机行业两种劳动力都有。这意味着它们不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和中国能够生产两万种商品的能力相比较,印度生产三种商品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
从长远看,印度经济增长确实前景黯淡,除非印度认识到,需要同时发挥社会的作用。中国的成功就在于,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而不仅仅依靠经济增长。
不过,印度并没有把二者很好结合,虽然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同时还有比较低的教育普及率、卫生条件、高失业率等等,印度人对此似乎比较沉默。
印度政府的总体思维似乎是,只要人们富有了,“自然而然”就会有教育和健康的改善。但这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先例的。
不认为有“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随着增长放缓和一些矛盾风险的显现,有担忧中国可能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森:首先,我不认为有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么一个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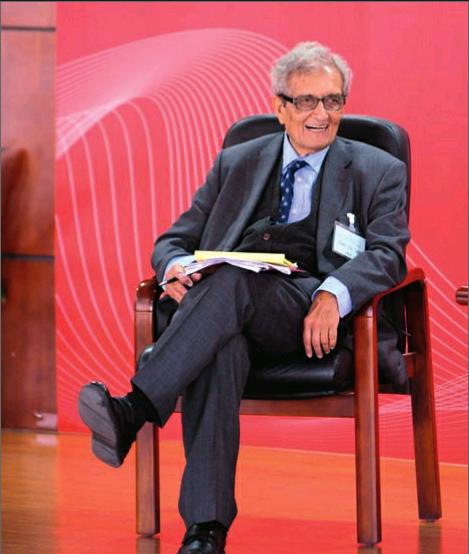
刚才已经提到,中国近20年的增长是非常快速的。我们也不能单纯以历史上的超高速来说未来增长会有瓶颈,当然现在中国的增长速度变得比较温和,但这只是相对的放缓,而且居民收入增长还是非常快速的。我从1983年开始,基本上每几年都会来中国,我发现中国发展的趋势在其他国家是没有先例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未来的增长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关键是中国如何对经济进行调整,包括财税调整,以提供适宜的激励机制,而且消费率还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最后,我想说,可能是我所知有限,我真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什么。当年也有人说到“经济腾飞”,但“腾飞”具体指什么,你也不知道,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
为什么中国经济放缓了?有人就说,因为我们遇到了中等收入陷阱。好像这样一个概念就把所有问题都交代清楚了。实际上,我们需要充分地研究和讨论,才可能把原因都说清楚。
记者:您对中国当前的发展有何建议?
森:这是一个重大课题,经济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该议题既可在细节上详述,也可从根本上加以探讨。我主要讨论它的基础方面。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增长都得益于对教育的重视。中国的成就很好地诠释了普及教育的威力,它几乎可以生产所有商品,这种能力就源于人人都获得基础教育。
在我看来,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将公社制度转变为个人责任制,以及1990年代的工业革命,教育普及都是它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今天,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加强。
教育也在改变中国的社会风貌,让中国人更加具有知识和素养。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得以传承。
有时候,这些变化没有被归因于教育。教育的巨大成就甚至在中国国内也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低估教育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知道,一提到中国的教育议题,就会有许多异议和抱怨。但从根本上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同样的速度达到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所取得的教育成就。
当然,中国需要认识到,它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比如,关于教育普及在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中所发挥的作用,就尚未得到广泛认可。人们常以为先有独生子女政策,后有总和生育率降低。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后的十年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8下降到1.5。其实,早在独生子女政策实施前的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从5下降到2.8,这主要受到女性接受教育及就业提升的影响。毛泽东很早就提出,要提高全社会的受教育水平,要实现男女平等。
要把经济成长转化为社会进步
记者:中国的哪些问题是您特别关注的?
森:中国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婴儿出生性别比失衡。
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提升,每个行业都可以看到女性开始挑大梁,这在其他国家也是很少见的。但是,在生育过程中,中国人依然有很强的重男轻女的倾向。
从全球来看,人类自然生育的男性是多于女性的,这是一个自然现象。30年前,我就在考察这一问题,男婴与女婴大概是105:100的自然比例(反之约为95%)。
德国、英国、美国等大致都是94%-96%这样的男女出生性别比例。同处东亚的韩国也曾经历过出生男婴显著高于女婴的阶段,但是近年韩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例也达到105:100左右。
在印度,一些地区的女性婴儿占男性婴儿的比例是92%,该比例接近欧洲的水平;但是在北部克什米尔地区,在班加尔等邦,这一比例就要低得多,甚至比中国还要低一些。
所以,为什么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跟印度最落后地区的比例更接近呢?为什么中国女性的家庭决策权更强了,却没有提升女婴的比例?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在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当地新生儿性别比也是比不上欧洲的。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文化因素,说明大家还是重男轻女,会有选择性堕胎。
记者:您长期致力于人类发展问题的研究,在此方面对中国有何观察?
森: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把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取得了两方面长足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如何进一步补足社会发展。
比如,我们有很多数据可以做中国与泰国的比较。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7岁,泰国人是78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都是11‰;孕产妇死亡率,中国是21.7/10万,泰国是11.4/10万。
为什么在很多社会指标上中国的表现不如泰国呢?
所以,中国必须思考如何把经济成长转化为社会方面的进步,如何把经济中的各要素充分调动起来,超越它的邻国。
从全球看,我们同样必须改变人类发展的既有模式,必须更加重视社会发展。
我和我的一位同事正在进行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像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能够按照旧有模式迅速发展的话,40年后才会达到埃及的水平。这是比较具有讽刺意味的,我们并不是要讽刺埃及,而是说40年的辛勤工作也只能换来收效甚微。
总之,必须把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