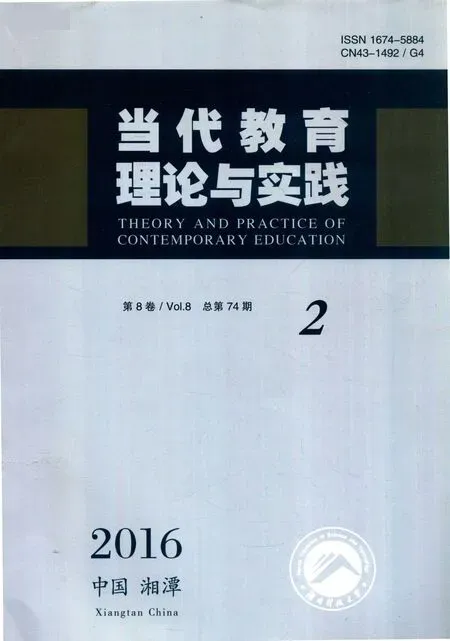高校师生的认同焦虑与身份重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刘勇
(三亚学院 外国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高校师生的认同焦虑与身份重构
——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
刘勇
(三亚学院 外国语学院,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新信息技术的发展,引起了高校师生之间一种普遍的身份焦虑。新信息技术“娱乐”化教育,与后现代碎片化、平面化的内容合谋,模糊了传统师生之间的界限,对传统教师和学生身份予以了祛魅。在对传统师生身份祛魅的同时,也为新的师生关系重构提供了契机。重建媒介意识,把教与学放到一个去等级化的新语境中进行互动,不失为一条重构新型“老师—学生”共同体的道路。
关键词:高等教育;身份认同;媒介环境学
以尼尔·波兹曼为代表的第二代媒介环境学认为,新技术正由“被人们控制”转变为“控制人们”。过去基于“传道授业解惑”的师生身份,正受到新技术所带来的“愉悦”的冲击,引起了高校师生之间一种普遍的身份焦虑。针对高等教育的这种危机,从政府到学界,或者从政策层面、或者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层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从传播学和文化研究来探讨高校师生身份危机的却为数不多。当代媒介环境的急剧变化,深刻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校师生亦然。透过媒介环境学,可以审视弥漫在高校师生中的身份焦虑,对当下高校“师生共同体”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合理的诊断,并为新型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选择。
1新信息技术时代高校师生的认同焦虑
波兹曼不无悲观地预言,“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电视可能会逐渐终结教师的职业生涯,因为学校是印刷机的发明,它的兴衰有赖于印刷词语享有的地位。四百年来,教师一直是印刷术创造的知识垄断的组成部分,他们正在目击这种知识垄断的解体”[1]。正是有别于印刷术的新科学技术和传播手段在当代高等教育中的应用和发展,波兹曼的这一观点正在得到印证。因而,对于作为印刷机发明的学校以及基于印刷术创造知识垄断的教师而言,这无疑是巨大的冲击。
在其媒介三部曲之一的《娱乐至死》中,波兹曼勾勒了西方所经历的三次教育危机,第一次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第二次是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给欧洲带来的巨变;第三次则是正发生在20世纪末以来的美国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的发明。波兹曼所说的西方第三次教育危机,正在迅速波及全球,而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中,中国的教育同样面临着此种危机。
走进当下的高校课堂,会发现一些令人沮丧的现象。学生不愿意走进教室听课,尤其不愿意听那些偏理论性以及思政教育类的课程,而是选择复制老师的教学课件;学生不喜欢上课严肃、考勤严格的老师,而是对上课随性、放松考勤和考核的老师给予较高的评教反馈。新技术的出现,一度被视为课堂讲授的救命稻草,能够用来唤醒教室里昏昏欲睡的学生。然而,新技术与教育的“联姻”,使得技术的“愉悦”功能得以加强,教育则在有形的声光影中被削弱。现代信息技术增强了愉悦性,却推动了无深度,因而课堂充斥了花哨的课件和影像资料,技术也成了迎合学生口味的手段。虽然这种基于新的电子信息技术的课堂模式充满了愉悦,却也使得知识变成了不假思索的影像灌输。波兹曼敏锐地指出,“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这种新型教育有三个典型特征,不能有前提条件,不能令人困惑,应该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2]。
让人身心愉悦的“娱乐”教育,何来“焦虑”一说?事实上,娱乐化的教育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教育的认知,尤其是高等学校在这股技术潮流中身先士卒,致使师生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产生了怀疑,引起了焦虑。传统讲授的课堂教学模式,随着新技术的发展,陡然变成了“娱乐场”。老师讲授的内容,学生们发现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互联网上获取。由于缺乏理论的学习和反思训练,学生的思考能力进一步弱化,学习无意义论在学生之间蔓延。有深度需要阐释的知识,既不受学生欢迎,也不讨老师喜欢,因为新技术拒绝精细繁琐的长篇论证和阐释。同时,社会对于高校学生的期望与现实情况的落差,导致社会对于高校毕业生的认可度逐年下降。高校师生自我身份认同焦虑与社会认可度下降的互动,更加剧了教师自身的身份焦虑。

2新信息技术时代高校师生身份的祛魅
后现代文化呈现出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文化突破了原有特定的范围,其疆界迅速扩张,几乎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它失去了神圣性,完全被大众化,变成了人人可以享受的日常消费。这种后现代文化变成了一种无深度、平面化的文化,取消了一切等级,而等级的取消则是对过去高等教育神圣面孔的祛魅。第二代媒介环境学认为,新信息技术带给人们一个“信仰危机”,电子媒体肆无忌惮地揭示文化秘密,从而对成人的权威和儿童好奇构成了严重的挑战。而曾经因为专业性而具有神秘性和纵深感的高等教育及其教师,其权威性正逐步瓦解。一方面,传统的教师身份随着印刷术的衰落遭到了挑战;另一方面,新信息技术的主导权却没有掌握在教师手中。尽管教师并没有放弃对新信息技术的利用,然而,在“技术垄断文化”的背景下,整个教育界试图依赖新信息技术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危机,似乎在缘木求鱼。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科技高度发展的信息社会,人类知识领域空前扩张,深刻影响乃至规范着人类的心理倾向和行为模式。科技的成就使一切事物丧失了神圣性。波兹曼在其《童年的消逝》一书中,从考察电报的发明开始,一直考察到新信息技术,详尽论证了“儿童”身份被解构的过程。新信息技术使得知识的来源多样化以及知识获取的零难度,最终导致了以“权威”为内核的“儿童—成人”共同体的解体,而“学生—老师”共同体的命运也是殊途同归。
波兹曼认为“任何一个群体都是针对不在这个群体里的人的‘阴谋’,因为‘局外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无法获得‘局内人’所拥有的信息”[3]。依言之,教育者即是学习者的“阴谋”,作为经过严格系统学术训练的高级知识分子,把自己所专的领域,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传授给学生,这是教育者存在的充分理由。然而波兹曼警告道,在这样一个公开的信息世界里,成人已不能再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了。新信息技术极大地扩大了知识的传播以及传授和学习的手段,信息的公开使得大量知识的获取变得唾手可得,在互联网上,人们可以轻易地聆听讲座和观看讲解,甚至可以进入同步学习与讨论的“慕课”中,这大大削弱了传统课堂教学的作用,蒙在教育者身上神秘的专业面纱被揭开。
除了知识获取途径的转变,信息时代在提供知识的同时,还提供了“娱乐”。“由印刷术的发明而兴起的以文字为主宰的‘文字说明时代’(Age of Exposition),虽然赋予成人与众不同的头脑,但是这个时代已接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叙事时代’(Age of Narration),如果要表达的更准确,更形象化,应该说是‘娱乐时代’(Age of show Business)”[3]。这与后现代文化不谋而合,知识无需阐释,只需要在平面化的背景下“秀”出来即可,知识后面复杂的运算、推理、论证都不是重点。而这一切,都是以电视的发明为开始,作为视觉形象的电视,摒弃了语言来表达内容,阐述被叙述所代替,从而使得电视产生了用之不竭的娱乐能力。曾经,学生获得知识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需要坐进枯燥乏味的课堂,耐心听取老师的阐释;可是现在,学生只要通过电视等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无须坐在教室备受煎熬,何乐而不为?尽管波兹曼讨论的是电视,而作为电视后续发展的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其传播的便捷性更是比电视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兹曼不无叹气地预言,伴随着信息的广泛传播和获取渠道的多样化,以及信息整理方式的变更,作为知识源泉的学校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主要意义。波兹曼在20世纪90年代作出了预言,而目前,这种预言正在逐渐变成事实。同时,这种影响并不是单向度针对教育者,对于学生来说,也正面临着身份的尴尬和焦虑。既然知识的获得如此容易,获得的过程如此娱乐化,那进入高等教育机构的意义又何在?于是,师生身份在同一个过程中一同被祛魅。波兹曼认为,“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将可能危及文化的发展。而这种教育已经以一种产业的方式迅速发展,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不再是这个产业的管理者,电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摇身变成了主角。
依照波兹曼的观点,我们目前正处于技术垄断文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技术不是依赖,而是屈从于技术带给我们的“愉悦”。在上个世纪末,波兹曼就已观察到如下现象:“在技术垄断条件下,我们改进青年教育的方式是改进所谓的‘学习技术’。目前,人们认为有必要把电脑引进课堂,正如当年人们认为有必要把闭路电视和电影引进课堂一样。”[1]之所以引进电脑,是因为这样会使得教学更加富有效率和有趣。事实上,现在完全印证了这样的观察,从老师到学生,在教与学的互动中,被动地屈从于计算机技术带给大家的轻松感觉。比如我们需要用最简单直观的课件讲解知识甚至进行逻辑分析,用动画吸引学生的关注,学生也不再习惯进行课堂笔记,转而依赖于教学课件,这种现象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愈加明显。
如果新信息技术客观上对师生身份进行了祛魅的话,那么主动拥抱并屈从于新信息技术,则最终瓦解了师生身份。在新信息技术时代,教师似乎已没有了存在的意义,因为教师在课堂上引述的知识,学生可以毫无门槛地从互联网上获取;而学生事实上已从“天之骄子”变成了“知识民工”,原因同样在于,任何人都能通过电子技术获取知识。于是我们比较悲观地认为:新信息技术只给师生指明了获取知识的手段,同时利用其带给师生的愉悦使得师生们忘记了教学的最终目的,而师生们正是因为沉浸在这种愉悦之中瓦解了自身的身份。
3媒介环境学视域下高校师生的身份重构
波兹曼对这一文化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悲观,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简直无法逾越,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办法,同时也许也根本不存在解决的办法。然而,即使希望渺茫甚或没有希望,我们依然要努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解铃还须系铃人,亦如波兹曼所说,希望渺茫的方法是“我们的学校”——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笔者以为,重建师生的媒介意识,消除对于媒介的神秘感,改造师生关系的存在基础,才能最终找到一条走出这一困境的道路。事实上,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书末提到,教育家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已产生某种媒介意识,但是这种媒介意识往往集中在怎样用计算机控制教育,而不是用教育控制计算机。我们发现,这种媒介意识的关注点出现了偏差,所以重建媒介意识,转变对计算机与教育之间关系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波兹曼指出,抵抗技术垄断,教育依然是最主要的途径。在笔者看来,由于教育目前同样被技术垄断,因而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的自救。重建媒介意识的第一步应该明白,现代世俗教育的问题在于我们忘记了学校最重要的贡献是给学生的学习提供连贯的意识,培养特定的宗旨、意义和相互关联的意识。然而一种“没有献身精神,没有观点”的在市场上出售技能的技术专家理想,却成了技术时代的教育目标,本应该作为我们教育手段之一的新信息技术,却成为当下的教育目标。
所以,我们最终要站在将教育视为一种“出世性教育”的角度来运用新信息技术,“这样的教育强调历史知识、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有素的语言技能、广博的人文和宗教知识,强调人类事业的一以贯之。对于技术垄断那种反历史的、信息饱和的、热爱技术性质的教育而言,这种教育无疑是极好的矫治剂。”[1]这个过程对于师生来说,也许更加痛苦,因为我们是在后现代这种碎片化、平面化、断裂性的语境中试图重拾也许是最高级别的教育宗旨,但是我们只能毅然前行。
4结语
综上所述,解决的出路依然在于学校本身,而最关键的因素无疑是师生。当下,高等学校的师生需要全面更新媒介意识,认识到传播媒介在解构师生身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此基础上,自觉调适师生关系的定位,重构师生关系。事实上,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试图提出如下观点:在后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新信息技术的广泛传播和运用,对教师和学生身份的祛魅,造成了彼此身份的焦虑和解构;然而在这种祛魅和解构中,也为师生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契机。因为祛魅往往带来威权的解散,使得教与学放到一个去等级化的新语境中进行互动:对于教师来说,打破了传统的关于教师的刻板印象,无须用一种负罪感来维持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化形象,从而能够以一种普通职业心态来进行传道授业解惑;对于学生来说,也脱下了“天之骄子”的外衣,无须用一种无法捉摸的使命感将自己塑造成一种英雄,从而能够以平和的心态来发展自己的能力,选择以后的道路,使得教育脱离技术的羁绊,回归人本身。
参考文献:
[1] 尼尔·波斯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责任校对王小飞)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6)02-0165-04
作者简介:刘勇(1986 - ),男,湖南湘潭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文化研究和汉语国际教育。
收稿日期:20150906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