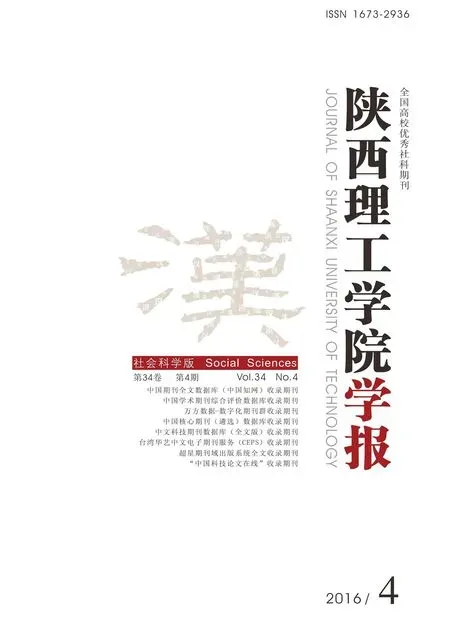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文化意蕴与地域文化阐释
徐 渊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金庸小说《笑傲江湖》的文化意蕴与地域文化阐释
徐 渊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植根于中国隐士文化,以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为价值追求的“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金庸在试图揭示中国三千年政治生态时所要充分肯定的,并主要通过源自“广陵散”的“笑傲江湖曲”的杜撰以及围绕“笑傲江湖曲”而发生的刘正风与曲洋的知音故事、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故事的描写,特别是通过令狐冲形象的刻画塑造,使之得以宣扬。从地域文化角度看,金庸将最能体现“笑傲江湖”精神内涵的令狐冲形象设计为华山派人物,应是金庸充分考虑华山丰厚的道教文化内涵以及其“形”似“剑”的地理特征后的自觉而合理的选择。令狐冲形象因之具有比较鲜明的华山特色。
金庸小说; 《笑傲江湖》; 文化意蕴; 地域文化; 阐释
《笑傲江湖》是金庸后期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始于1967年,完成于1969年。其内容主要描述了江湖门派之间的权力争斗以及主人公华山派首徒令狐冲身陷其中的无奈、挣扎与超越。“笑傲江湖”一语既是小说作品名,亦是作品中的乐曲名。作为乐曲,“笑傲江湖”是实指,指“笑傲江湖曲”,分琴谱和箫谱;作为小说作品名,“笑傲江湖”是虚指,它是对作品所宣扬的人生价值与追求的高度概括。无论是作为乐曲名还是作为小说作品名,“笑傲江湖”都蕴含着丰厚的文化意蕴。同时,金庸将最能体现“笑傲江湖”精神内涵的代表人物令狐冲设计为华山人物,应该不是随意而为,而是金庸在充分考虑了华山自然特征与文化内涵以后做出的自觉选择。
一
“笑傲江湖”作为乐曲,在小说中为曲洋和刘正风“两个既通音律,又精内功之人,志趣相投,修为相若,一同创制”[1]232。此曲虽集二人数年之功,是“二人毕生心血之所寄”,却并非二人完全原创,如刘正风所说,“这《笑傲江湖曲》中间的一大段琴曲,是曲大哥依据晋人嵇康的《广陵散》而改编的。”[1]233可见《笑傲江湖曲》与《广陵散》关系密切。不过,嵇康也不是《广陵散》的原创者。《广陵散》又名《广陵止息》,其作者、年代、内容等说法不一,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它是流行于古代广陵地区的民间琴曲,至少在汉代就已出现,其旋律激昂慷慨,充满强烈的戈矛杀伐之声。嵇康音乐造诣极高,因酷爱此曲而常加演奏,对此曲应有一定的加工改造,直至慷慨赴死前还曾演奏。嵇康虽不是《广陵散》的原创者,但《广陵散》却因嵇康而名闻天下。金庸在《笑傲江湖》中也认为《广陵散》非嵇康所创,借曲洋之口说:“嵇康临刑时抚琴一曲,的确很有气度,但他说‘《广陵散》从此绝矣’,这句话却未免把后世之人都看得小了。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晋时人,此曲就算西晋之后失传,难道在西晋之前也没有了吗?”并让曲洋“去挖掘西汉、东汉两朝皇帝和大臣的坟墓,一连掘二十九座古墓,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到了《广陵散》的曲谱”[1]233。问题的关键当然不在《广陵散》是否是嵇康所原创,而在于《广陵散》的内在精神以及它与《笑傲江湖曲》的联系。按蔡邕在《琴操》中的记述,《广陵散》的曲情表现的是“聂政刺韩王”:聂政父为韩王铸剑延期而被杀,聂政自毁容颜入深山苦练琴艺,后假扮琴师入宫,杀韩王后而自杀身亡[2]。不过,这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并不相同。《史记》中记述的是:韩国大臣严遂与韩相韩傀有仇隙,花重金请聂政刺杀韩傀。聂政感其礼遇,入邑都杀韩傀,后自毁颜面而自杀身死[3]2217-2220。依蔡邕说,《广陵散》中的聂政故事表现的是聂政反抗暴政、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按司马迁说,聂政事迹表现的是聂政“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尽管两说并不相同,但既然都与聂政有关,因此不仅聂政的故事在后世广为传颂,而且赋予其中的反抗暴政、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也为后世所敬仰。嵇康乃三国曹魏时期奇才,“竹林七贤”代表人物,“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宁可逃身山林,在洛阳城外做自由自在的打铁匠,也不愿与司马昭政权合作。“竹林七贤”中唯有他一人能够坚守自我意志。甚至当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举荐他入朝为官时,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以明心志。“这篇人生宣言式的长文痛痛快快陈述了他不愿做官的原因,可谓有自知之明。不管嵇康怎样解说,在司马昭看来无非是声明不跟他合作,宣布与山巨源绝交就是宣布与司马昭集团绝交。而且越说自己清高,就越是显示官吏的庸俗卑污,无异于讽刺司马昭集团,祸根就埋藏在这篇《绝交书》中。”[4]106这种与司马昭政权不合作的态度,使其终因为好友吕安仗义执言而涉吕安案被司马昭政权借机杀害。嵇康蔑视权贵,主张摆脱束缚,要求回归自然、释放人性本真。他临刑前从容弹奏一生酷爱的琴曲《广陵散》,不仅使他得以抒发蔑视强权的情怀,显现出傲然独立的伟大人格,而且使《广陵散》从此与嵇康紧密相联系,并赋予《广陵散》蔑视权贵、追求个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内涵而成为千古绝唱。而在《笑傲江湖》中,刘正风和曲洋本属于正、邪两大阵营,但由于二人都精于且醉心于音律,厌倦江湖权力纷争,于是以乐相知、相交,成为知音。二人所以能创制“笑傲江湖曲”并分琴谱和箫谱,是因为二人一长于琴,一擅于箫,而且“志趣相投,修为相若”。面对嵩山派威逼、众叛亲离危局,刘正风宁死不屈,曲洋冒死施救。后二人因均受重伤,合奏一曲“笑傲江湖曲”而亡。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设计此二人并叙述他们的故事,一方面,通过他们的故事直接诠释士为知己者死、不畏强权、追求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的精神;另一方面,让他们创制“笑傲江湖曲”并宣称改编自《广陵散》,且比较详细地告知令狐冲有关嵇康和《广陵散》的故事,既明确昭示了《广陵散》的文化精神,又直接确立了“笑傲江湖曲”的旋律基调和境界品格。所以,一曲“笑傲江湖曲”,与其说是金庸在《笑傲江湖》中的虚构,不如说是《广陵散》这曲千古绝唱在《笑傲江湖》中的唱响。而无论是“笑傲江湖曲”还是《广陵散》,都是对反抗暴政、蔑视强权、追求个性自由与人格独立的文化精神的宣扬。
二
“笑傲江湖曲”与令狐冲和任盈盈的爱情也有密切关系。首先,“笑傲江湖曲”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相识的线索。令狐冲受曲、刘二人临终相托,承担起传承《笑傲江湖曲》的重任。不想在洛阳被众人疑为“辟邪剑谱”,为辨真伪,至东城绿竹翁处。适逢偶然在此逗留的任盈盈,她以箫吹出“笑傲江湖曲”的神妙,使令狐冲得还清白。令狐冲心慕其技,更感其关怀,不仅将“笑傲江湖曲”相赠,而且将自己的遭际、冤屈包括对岳灵珊的恋情和盘托出。任盈盈深感令狐冲的至情至性而不禁情愫暗生。之后故事皆因此而起。所以,没有《笑傲江湖曲》就没有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相识。
其次,“笑傲江湖曲”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象征。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并非同步共生。任盈盈倾心令狐冲始于二人洛阳东城绿竹翁处相识之时,为令狐冲痴恋岳灵珊的深情、痛苦打动,可谓一见钟情。令狐冲对于任盈盈,最初则如书中“三战”一章中所说:
他和盈盈初遇,一直当她是个年老婆婆,心中对她有七分尊敬,三分感激;其后见她举手杀人,指挥群豪,尊敬之中不免搀杂了几分惧怕,直至得知她对自己颇有情意,这几分厌憎之心才渐渐淡了,及后得悉她为自己舍身少林,那更是深深感激。然而感激之意虽深,却并无亲近之念,只盼能报答她的恩情;听到任我行说自己是他女婿,心底竟然颇感为难。这时见到她的丽色,只觉和她相去极远极远。[1]966-977
直到从少林寺下山于洞中养伤之时,令狐冲才第一次向任盈盈表明心迹:“自今而后,我要死心塌地地对你好”,并发誓说:“我若是哄你,叫我天打雷劈,不得好死。”[1]986如果说此时令狐冲对任盈盈的爱还主要是出于感激,也尚存隔阂,并不时受到对岳灵珊感情的困扰,那么在之后,随着相互陪伴、相知加深以及多次历经生死,这种爱才逐渐纯粹、深厚起来。令狐冲对任盈盈的爱情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浅至深而两情相悦的艰难转变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正是令狐冲于抚琴之道由陌生而娴熟,内力修为不断加深,并最终能与任盈盈琴箫合奏“笑傲江湖曲”的过程。“笑傲江湖曲”分琴曲和箫曲,非修为相当、志趣相投、心意相通的两个人不能合奏或不能尽得其妙。此中关节在“授谱”一章中由曲洋说出:“今后纵然世上再有曲洋,不见得又有刘正风,有刘正风,不见得又有曲洋。就算又有曲洋、刘正风一般的人物,二人又未必生于同时,相遇相交,要两个既精音律,又精内功之人,志趣相投,修为相若,一同创制此曲,实是千难万难了。”[1]232所不同的是,“笑傲江湖曲”在曲、刘二人表现的是朋友间的“志趣相投”,在令狐冲和任盈盈则表现的是情人间的相知相爱。因此,当二人终于“曲谐”而合奏“笑傲江湖曲”时,正是二人于杭州西湖梅庄喜结良缘之际。所以说,琴箫合奏的“笑傲江湖曲”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爱情的象征。
再次,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充分体现了“笑傲江湖曲”的精神内涵。令狐冲是华山派首徒,任盈盈是日月神教圣姑,分属“正”、“邪”两大阵营,他们之间横亘着小说中所设立的正邪之间相互仇视、相互争斗而绝难相容的巨大鸿沟。于令狐冲而言,从与任盈盈相识相交开始就遭到师门及各方“正”派人士的强烈反对,甚至因此被逐出华山派。令狐冲对被逐出师门尽管痛苦至极,也时常引以为耻,但当得知任盈盈为己而身陷少林寺,感念其情义,遂率领江湖群豪浩浩荡荡前往营救;当路遇武当冲虚道长并劝自己“少侠如此人品武功,岂无名门淑女为配?何必抛舍不下这个魔教妖女,以致坏了声名,自毁前程?”还说“你若依我所劝,老朽与少林方丈一同拍胸口担保,叫你重回华山派中”[1]919之时,却坚定地表白“晚辈若不能将任小姐救出少林寺,枉自为人。”[1]919-920而在少林寺与岳不群比剑时,当岳不群在剑法中暗示令狐冲“弃邪归正,浪子回头,便可重入华山门下”,并得娶岳灵珊为妻时,令狐冲于瞬间喜悦之后想的是:“盈盈甘心为我而死,我竟可舍之不顾,天下负心薄幸之人,还有更比得上我令狐冲吗?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负了盈盈对我的情意。”[1]980-981在此,令狐冲抵御住了来自师门和位高望重人物的重压和利诱,做出了重情义而轻声名甚至无视声名的选择。另一方面,明知接受任我行日月神教副教主一职的邀约必然促成自己与任盈盈婚事,而拒绝则必将导致婚事的破灭,仍然选择不接受副教主的职位,同时向任我行请求将任盈盈许配自己为妻;面对任我行不传授疗救“吸星大法”治伤之法的威胁以及杀光恒山派所有人的恐吓,令狐冲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并向任盈盈表达在华山朝阳峰上“拜堂成亲”的愿望。尽管令狐冲在做出这一选择时有过犹豫,但最终在两难选择中选择了蔑视权力、不畏强权而追求简单、纯粹的爱情。相对于令狐冲,尽管因少女的羞涩与矜持而使任盈盈对爱情的追求不像令狐冲那么直露狂放,也没有在令狐冲提出于朝阳峰上拜堂成亲时表示同意,但不计日月神教圣姑身份而钟情于华山无名小辈且身负重伤的令狐冲并守护身旁,为换得“易筋经”救令狐冲而甘愿困居少林寺,不顾危险乔装打扮在嵩山相助令狐冲,虽没有答应令狐冲在朝阳峰上的请求却表明绝不独活的态度,放弃日月神教教主之位而与令狐冲“曲谐”于杭州西湖等等,昭彰了任盈盈无视正邪、无所谓权力地位、不计个人生死而只服从本心的爱情追求。正如金庸所说:“她对江湖豪士有生杀大权,却宁可在洛阳隐居陋巷,琴箫自娱。她生命中只重视个人的自由,个性的舒展。唯一重要的只是爱情。这个姑娘非常怕羞腼腆,但在爱情中,她是主动者。”[5]1440在正邪之争、权力之争异常激烈而残酷的江湖,令狐冲和任盈盈却尽可能保有独立人格,坚持个性自由,超越正邪、权力之争,冲破各种阻力和障碍,两情相悦并终成眷属,无论是过程还是结果,都足以“笑傲”江湖,正体现了“笑傲江湖曲”的精神内涵,或者说,“笑傲江湖曲”的精神内涵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爱情故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三
“笑傲江湖”作为小说作品名,高度概括了金庸借此书所要肯定和宣扬的价值观。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自承:“这部小说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会是这样。”[5]1440因此,本书表面上是纯粹而精彩的武侠传奇故事,实则是对中国三千年政治生活的深刻揭示。书中江湖各派与日月神教的正邪之争、五岳剑派内部的并派之争、日月神教内部的夺权之争、华山派内部的气剑之争等,其实都是权力之争。书中的大多数人物或主动或被动地身陷其中,或为称霸江湖而不择手段,或为保有现实利益而处心积虑,或为获取一定地位而韬光养晦,或为求得生存而虚与委蛇,无所不用其极,无人能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激烈而残酷的政治权力争斗,使众多人物为之疯狂、为之变态、为之扭曲、为之压抑、为之牺牲。《笑傲江湖》确然称得上“是一部更加纯粹的政治历史或历史政治的寓言”[6]250,对中国三千多年的政治文化进行了非常深刻的揭示。不过,在中国三千多年的政治生活中,参与其中的人并不完全都是争夺权力之人。金庸的基本判断是:“政治上大多数时期是坏人当权,于是不断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进行改革;另有一种人对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当权派同流合污,他们的抉择是退出斗争漩涡,独善其身。所以一向有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5]1439如果说当权派、造反派、改革派主要是权力争夺之人,那么隐士则与权力争夺无关。熟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金庸的判断没有错。隐士在中国古代出现很早,尧舜时代即有不受帝位而逃到箕山隐居的许由和同样不受帝位而在树上筑巢而居的巢父,商末则有著名的叔齐、伯夷,及至儒、道学说产生,思想兴盛,并渐成文化主流,历朝历代的隐士更是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因为道家主张无为、无名、无功,追求超然物外、齐物逍遥,儒家强调“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以无论是信奉道家思想还是崇尚儒家思想,抑或儒道合流、兼而有之,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思想支持或理论依据。可以说,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是隐士文化得以产生并不断丰厚的直接而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而所谓“隐士”,“隐”的必须是“士”,也就是有一定文化、才学、能力以及较高知名度的人。“士”所以要“隐”,是为了保全个体尊严,追求个性自由、人格独立。由于“士”在中国古代多与政治生活相关联,因此“隐士”与现实政治社会也具有不可分割的深刻联系。金庸“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自然会关注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士。更为重要的是,金庸认为,“那些热衷于权力的人,受到心中权力欲的驱策,身不由己,去做许许多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其实都是很可怜的”[5]1441。而对于隐士,金庸则认为,“隐士对社会并无积极意义,然而他们的行为和争权夺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种范例”[5]1439。不难看出,金庸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也因此,金庸在小说中通过刻画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等人物,生动、深刻地描绘残酷而血腥的权力斗争的同时,也塑造了刘正风、曲洋、令狐冲、任盈盈、风清扬以及梅庄四友等隐士形象,其中尤以男主人公令狐冲为典型。
隐士在类别上大体可分两种,即天生的隐士和后天的隐士。前者是因为向往自由人生而自觉自愿地选择隐居并由衷感到快乐;后者则是因为理想、抱负限于现实阻力不能实现,为了保全人格独立而无奈选择隐居。《笑傲江湖》中,如果说刘正风、曲洋、任盈盈、风清扬等人曾经热衷于权力追逐而最终厌倦,并试图退出斗争漩涡而意欲独善其身,因而是属于后天的隐士,那么令狐冲则是天生的隐士,如金庸所说: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对权力没有兴趣”[5]1440。金庸显然更推崇后者,不仅将令狐冲设计为小说的主人公,而且在小说中以多种方式和手段如他人评价、心理透视、人剑合一、行动显示、结局安排等丰满生动地刻画了令狐冲无正邪之辨、无权力之欲、无规范之束、光明磊落而任性随意、放浪无羁而自由独立的这一天生隐士形象。
何谓“笑傲江湖”?金庸说:“‘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笑傲江湖”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蔑视权力、不受束缚,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不过,金庸也深知,“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5]1441。因此,意欲逃避权力斗争的刘正风、曲洋和梅庄四友最终仍然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令狐冲多数时候也只能被裹挟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挣扎。一方面,令狐冲不自觉地参加了岳不群的权力斗争行动,尤其是因机缘巧合而获得“笑傲江湖”曲谱,习得“独孤剑法”、“吸星大法”后,更是自觉不自觉地卷入权力斗争,如助任我行夺权、执掌恒山派、帮岳不群夺得五岳剑派盟主之位、为保恒山派而与日月神教抗衡等;另一方面,令狐冲也是权力斗争的受害者,如为击退欲夺华山掌门之位的成不忧而受伤并致此后多难,被岳不群栽赃陷害蒙受不白之冤成为华山派弃徒,失去刻骨铭心的初恋之爱等。但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伤重、失爱还是蒙冤、遭弃,无论是威胁恐吓还是生死考验,无论是权力迫害还是权力诱惑,令狐冲都是权力斗争的超越者,始终不改初衷地追求“自由自在”。令狐冲之所以没有遭受刘正风、曲洋以及梅庄四友一样的结局,并最终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退隐”,独善其身于西湖梅庄,最重要的原因是,金庸在小说描绘的江湖情境中让令狐冲从风清扬处获传“独孤剑法”。因为掌握、融通了“独孤剑法”,令狐冲不仅得以一再在险境中求生,在危局中自保,而且能够抗衡、挫败江湖众多一流高手,从籍籍无名之辈而最终名满天下,从人人不屑的华山弃徒成为各方势力争相争取的对象。更重要的是,令狐冲因此拥有了江湖话语权,拥有了能够蔑视强权、坚守人格独立、追求个性解放、保持自由自在而不被倾轧的能力,从而使其“笑傲江湖”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金庸尽管深知“退隐”的不易,深知“笑傲江湖”的艰难,也因此描绘了追求“笑傲江湖”者的种种努力与抗争、无奈与牺牲,但并不愿让人格独立、个性自由这一终极价值追求被毁灭。因此,当令狐冲凭借象征着“隐士之剑”的“独孤剑法”叱咤江湖、与象征着“权力之剑”的“辟邪剑法”相对抗并最终在生存上、精神上、人格上真正能够“笑傲江湖”时,不仅使习惯于看到武侠小说的主人公最终一定会获得成功的读者产生巨大的愉悦感、满足感,而且使金庸对“笑傲江湖”精神价值的肯定表现得更饱满,也更充满希望,同时使传统隐士文化所内涵的人格独立、个性自由价值观得到更充分地彰显和宣扬。
四
无论“笑傲江湖”作为乐曲名还是小说作品名,无论“笑傲江湖”是刘正风与曲洋的内心向往还是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爱情象征,或是主人公令狐冲的人生追求及最终现实,其“自由自在”这一既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隐士文化又完全符合于人类终极价值追求的核心精神内涵正是金庸所要极力高扬的。金庸之于“自由”的宣扬当然不只是在《笑傲江湖》这部小说之中,正如徐岱所说:“金庸小说将趣味美学推进到了一个形而上的高度,借艺术的游戏性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激情:呼唤自由。所谓‘侠士道’也就是摆脱名缰利锁之道,和超越荣誉与权力之道。这种声音主要借助于金庸世界中的那些人物性格来体现,贯通在整个金庸小说的那种‘游戏精神’之中。”[7]423但《笑傲江湖》可以说是金庸最自觉地以表现“自由”为主题的作品,令狐冲应该说是最能充分体现“笑傲江湖”之“自由”精神内涵的人物形象。
毋庸置疑,金庸塑造的令狐冲形象具有典型性,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高扬隐士文化以及“自由”的价值的,而与地域无涉。不过,若从地域文化角度看,金庸将令狐冲这一形象设计为华山人物,倒也不是完全随意、盲目的安排,而应是金庸在充分考虑华山文化与自然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的自觉选择。对此,尽管没有金庸的任何明确说明作依据,但这样的判断并非没有道理。
首先,令狐冲形象的精神内涵与华山文化内涵相一致。华山文化虽然内涵丰富,但其主要内涵是道教文化。道教的核心信仰是神仙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修道”而“羽化”为长生不死、逍遥自在的神仙。而要“修道”,就要摒弃各种现世欲望,恪守生命本真,避居“洞天”之地潜心修行,最终得“道”升天。道教所说的“洞天”之地,即地上的仙山,山中有洞室可通于上天。道教共有十大洞天和三十六小洞天,囊括中国名山胜地无数。华山奇险而风景秀丽,正是“修道”的“洞天”之地,而且是“第四洞天”。因此,北魏新天师道创始人寇谦之、五代末宋初陈抟都曾在此修行,金元时期的郝大通、元代的贺志真更是开创了作为道教派别而存在的华山派,以致道教在华山兴盛,“修道”之人趋之若鹜,华山之上现存道观、遗迹无数。与道教神仙信仰相适应,各种得“道”成仙的故事也被道教典籍所记载、传诵,而其中,在华山之上遇仙、成仙或仙居的故事不少。如传为汉代刘向所作的《列仙传》中记述的众多仙人中有许多如赤斧、毛女玉姜等都是在华山遇仙、成仙的[8];东晋葛洪在《神仙传·卷二·卫叔卿》中说,汉武帝时,中山人卫叔卿服用云母而成仙,在华山“绝岩之下”与洪崖先生、许由、巢父等仙人“博戏于石上。紫云蔚蔚于其上,白玉为床,又有数仙童执幢节,立其后”[9]。最初源自于民间的道教所以能迅速发展,与其神仙信仰密不可分,“神仙世界跟现实的污浊和丑陋形成了鲜明对比,它寄托了美好的理想,也得到了各阶层人民的欢迎”[10]294。而无论是避居“洞天”之地的潜心修行还是得“道”升天后的逍遥自在,都是与现实世界的隔离,超脱于各种现实束缚之上,得保生命意志之自由。对于华山的道教文化内涵以及神仙传说,以金庸知识之广博,应该是清楚的,这也正是金庸小说华山派人物所以多隐士的重要原因所在。将追求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天生隐士形象令狐冲设计为华山人物,以华山文化为深刻背景,以令狐冲形象为生动显示,让令狐冲形象与“华山”相得益彰,自然也是金庸在充分考虑华山文化内涵以后的刻意选择。追求“自由自在”的令狐冲因之成为华山隐士群体的代表人物,具有鲜明的华山特色。当然,隐士不是道士。说令狐冲形象的精神内涵与华山道教文化内涵相一致,主要是就保持生命本真、追求个体独立与自由而言。正如陈墨归纳包括令狐冲在内的一些金庸小说人物为“道之侠”类型时所说:“道之侠中多‘隐士’。这些人的‘出世’并不等于是‘出家’——若是出家就等于做了道士。……他们不想白白地牺牲自己,而是要保全自己。保全自己的真性情,至情至性,保全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意志、保全自己的健全的个性及其生活方式。”[11]294
其次,“独孤剑法”与华山地理和文化内涵相吻合。令狐冲所以能够“笑傲江湖”,内在固然是因为对“自由自在”的不懈追求,外在则是因为掌握了“独孤剑法”这一利器。而这一剑法正与华山地理和文化内涵相吻合。其一,华山海拔虽然不是最高,但险峻挺拔,其奇险以“剑”喻之毫不为过。唐代诗人张乔曾有诗云:“谁将倚天剑,削出倚天峰。”[12]7305金庸在《碧血剑》和《笑傲江湖》这两部主要描写华山派的小说中,将剑法作为华山派的主要也是最高武功,应是考虑了华山其“形”似“剑”的自然地理特征。让令狐冲从风清扬处获授“独孤剑法”,应当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独孤剑法”虽为非华山人士独孤求败所创,但经华山泰斗级人物风清扬掌握,再传华山弟子令狐冲,可视为华山剑法构成的一部分。“独孤剑法”因之具有了华山特点。其二,就“独孤剑法”的“剑理”而言,按书中风清扬传剑时的解说,是“无招胜有招”,破解任何武功只有“一剑”,而这“一剑”却可随对手招式变化而变化,无穷无尽,“无所施而无不可”。这正体现了道家之“道”的核心意涵,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3]道家与道教自然不同,但道教以道家思想为根本思想资源。“独孤剑法”的“剑理”因而与华山的文化内涵是吻合的。其三,《笑傲江湖》中主要有两种剑法,即“辟邪剑法”和“独孤剑法”。就其象征义而言,如果说“辟邪剑法”是“权力之剑”,意味着欲望、野心、王霸雄图以及因此产生的对人的束缚、扭曲、残害,那么“独孤剑法”就是“隐士之剑”,意味着自由、独立、超然物外以及因此获得的个性解放、生命本真。两种文化、两种人生追求、两种生命形态在江湖世界里借由两种武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直观呈现。而且,在小说中它们是相对抗的,即追逐权力,意欲雄霸天下的东方不败、左冷禅、岳不群等人以“辟邪剑法”与无视权力、只想“自由自在”存在的令狐冲以“独孤剑法”之间的对抗。而当以自由独立、个性解放为生命价值追求的令狐冲形象与“无招胜有招”的“独孤剑法”人剑合一,令狐冲因“独孤剑法”而获得自由独立,“独孤剑法”因令狐冲而施展得更加淋漓尽致,“独孤剑法”既可说是“隐士之剑”也可说是“令狐冲之剑”时,最能体现“笑傲江湖”精神内涵的令狐冲形象的华山特色也就更加浓厚而鲜明。
或许,将令狐冲设计为栖居于其他同样具有深厚道教文化的名山的江湖门派人物也不是不可以,但若综合名山的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文化内涵特色而论,同时再考虑金庸在《碧血剑》、《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等几部小说中对“华山”描绘的整体情况,金庸将令狐冲设计为华山人物,将“笑傲江湖”的精神内涵通过塑造华山人物令狐冲而予以表现,可谓合理而匠心独具。可以说,“华山”使令狐冲形象塑造得更加深刻而丰厚,令狐冲形象使“华山”彰显得更加生动而充满魅力,“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因之而影响巨大。
[1]金庸.笑傲江湖[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2]蔡邕.琴操·聂政刺韩王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谢苍霖,万芳珍.三千年文祸(修订本)[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
[5]金庸.笑傲江湖·后记[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2.
[6]陈墨.金庸小说赏析[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7]徐岱.侠士道:金庸小说与中国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8]王叔岷.列仙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7.
[9]葛洪.神仙传[M].胡守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田伯元.神话与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1]陈墨.金庸小说之谜[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
[12]张乔.华山[M]//全唐诗(卷六三八).北京:中华书局,1960.
[13]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责任编辑:朱 飞]
2016-06-16
徐渊(1965-),男,贵州印江人,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阐释学、金庸小说与武侠文学研究。
陕西省教育厅2012年科学研究项目“地域文化视阈下金庸小说中的陕西名山研究”(12JK0419)后续研究成果。
I207.42
A
1673-2936(2016)04-002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