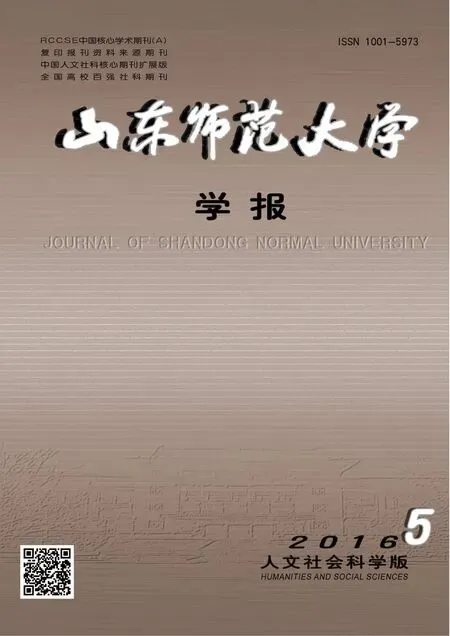蒲宁:在悖论中成就伟大与深邃*
李春林
( 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辽宁 沈阳,110031 )
蒲宁:在悖论中成就伟大与深邃*
李春林
( 辽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辽宁 沈阳,110031 )
蒲宁作为俄罗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却是一位充满了悖论的作家。蒲宁的国民性格的书写与自然环境的抒写构成了强烈反差,他将俄罗斯的大自然作为自己文学王国的主角,显现出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过渡趋向。蒲宁乃是今日所倡导的大自然文学的先行者之一,但他对于宗教是称颂与质疑相互纠结:一方面,宗教之美同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构成了蒲宁的美的三元世界;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发出质疑宗教的声音;美,特别是爱,才是蒲宁至高无上的宗教。蒲宁往往将自己的创作同人类的苦难胶结于一,但他否定文艺在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主张为自我而创作,创作成为他获得生命存在感的方式。蒲宁的创作方法首先是现实主义的;他反对现代主义,但又多所汲取。
蒲宁;自然观;宗教观;创作动机;创作方法;悖论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5.006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通体都是矛盾。竹内好亦曾说过,“鲁迅在本质上是个矛盾”*[日本]竹内好:《鲁迅》,李心峰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9页。。 世界上矛盾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没有矛盾,便没有世界;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发展;没有矛盾,更没有深刻。人的思想是在矛盾中发展和深化的,伟人是在矛盾或曰悖论中得以成就的。无矛盾无悖论只能成就平庸,无矛盾无悖论只能呈现扁平。凸圆和深邃无不凭借激烈而痛苦的矛盾、悖论得以成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是,鲁迅如是,蒲宁亦如是。
蒲宁自己也认为,任何人都写不出真实的蒲宁,连他自己也多次尝试,最终都放弃了。他说:“永远都没人能写,梅列日科夫斯基说得对,‘每本写拿破仑的新著都像落在他坟墓上的一块石头,妨碍我们理解并看清拿破仑。’我的情形当然也会这样。最好谁也不写,任何时候都不要写。”*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页。蒲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世界观中交织的重重矛盾,正如斯里维茨卡雅所说:“蒲宁的创作已成为一种现象,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走近,它都会给你留下矛盾的印象。”*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巴博列科甚至认为,蒲宁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对矛盾的迷恋”*[俄]巴博列科:《蒲宁传记》,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2004年,第22页。。
既如此,我觉得研究者的任务首先就是要认真地、真实地梳理作家的各个方面的悖论,然后考察这些悖论产生的原因与意义,进而昭示其不同凡响的伟大与深邃。
蒲宁的悖论几乎存在于他的人生与创作的所有方面,诸如对俄罗斯国民性的书写,对社会革命的态度,他的自然观、死亡观、宗教观、爱情观,他的创作动机与创作方法,等等,都存有激烈和深刻的矛盾冲突。本文仅涉及蒲宁的自然观、宗教观、创作动机与创作方法。
一、文学世界中人与自然的悖论
蒲宁因其“以严谨的艺术才能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而成为俄罗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然而,当你读完蒲宁的绝大部分散文(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散文”是指与韵文相对立的其他体裁,自然包括小说)作品后,你会发现,他对自然景色的描写要胜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蒲宁的国民性格的书写与自然环境的抒写构成了强烈反差,甚至成为表现民族国家的文学世界里的一种鲜明的悖论。通常认为,人生活的自然环境与人的性格多呈现为一种正关联关系,所谓“人杰地灵”、“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也。但蒲宁恰成反调:如果说蒲宁从总体上而言对于俄罗斯国民性格持一种批评态度,那么他对俄罗斯的大自然则是持一种肯定与欣赏的态度。卡拉巴耶娃说:“蒲宁在爱上自己和其他人之前,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大自然。”*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8页。岂止是热爱,简直是顶礼膜拜。
这与蒲宁的“非人类中心论”的世界观和泛神论自然观紧密相关。
“蒲宁在自然观上始终抱有朴素的泛神论思想。在他看来,宇宙生活是无边的海洋,而周遭充实的大自然正是充满了神性的辽阔宇宙最鲜明的表现,而人不过是这沧海中之一粟,他和自然中的一切都是造物主手中平等的被造之物。”*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9-40页。“鸟有巢窠,兽有洞穴。/当我离开家园的时候,/把‘别了’的话儿一说,/年轻的心多么难受!”*[俄]蒲宁:《鸟有巢窠,兽有洞穴……》,顾蕴璞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97页。鸟兽人完全是平等的存在物。在蒲宁笔下,年轻的女友与一颗老苹果树可以建立互文关系,共同阐释“年轻的暮年时光”*[俄]蒲宁:《一颗老苹果树》,顾蕴璞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87页。的美丽。
诚然,蒲宁也曾书写过恶劣的自然环境,写出了自然环境的恶化,树林被砍光,飞禽走兽都没了。周边充满了寒意:
寒风一阵阵吹来,天空阴云密布,天色越来越暗。院子里竖起两根柱子,中间架着一根横木,横木下像挂着圣像一样挂着一块铁板,那是供夜里敲打报警用的。院子里躺着几条干瘦的猎狗。一个八岁模样的男孩拖着一辆小车在猎狗之间跑来跑去,小车上载着他带一顶大黑帽的白头发弟弟,那小车发出极其尖锐的吱吱声,十分刺耳。房子死气沉沉,臃肿……*[俄]蒲宁:《乡村》,冯春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58页。
如此的环境描写与人物的生活、命运、性格谐调一致。在《乡村》中,类似的环境描写较多。其中有一段与鲁迅的《故乡》开篇处的风景描写很相近:
在青灰色的天空底下,白茫茫的田野显得更加广阔,更加荒凉。一座座农家小屋、干草棚、柳丛、干燥棚在第一场新雪衬托下显得更加清晰分明。后来又刮起了暴风雪,大风把雪刮到一起,积起了那么多的雪,整个乡村便显出了荒凉萧索的北方景象。*[俄]蒲宁:《乡村》,冯春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86页。
蒲宁对于自然景色的描写有时是很客观、很中性的。例如在《苏霍多尔》中抒写娜达莉亚的苦难时笔涉乡土风光的描写,就并非冷调,至多是中性的感伤(这恐怕与苏霍多尔的底层的性格特点及独特的主仆关系有关),绝无像对于人物那样时有充满了厌恶和憎恨。
事实上,无限热爱俄罗斯大自然的蒲宁,是无法控制他对大自然的倾心与歌赞的。所以,在这反映破败的乡村为主调的作品中,暖意仍不时迸发出来:
山沟那边一到晨光熹微时,村子里边家家升起袅袅炊烟,花园里散发出阵阵清香。中午太阳当空照耀着村子,天热起来,花园里的槭树和菩提树红成了一片,悄悄地飘落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树叶。一群鸽子整天在厨房的斜屋顶上晒太阳睡觉,在蔚蓝色的晴空中屋顶上新铺的麦秸显得更加橙黄灿烂。……太阳,坚实的道路,枯萎的杂草,变成褐色的苋菜,可爱的晚开浅蓝色菊苣花,随风飘荡的葱花……田野中的耕地在阳光下像一张绸缎般的蛛网闪闪发亮,伸展到无边的天地间去。菜园里枯萎的牛蒡上停着几只金翅雀。打谷场上寂然无声,只有在太阳晒热的地方,螽斯发出一阵高似一阵的嘶鸣……*[俄]蒲宁:《乡村》,冯春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71页。
这便是蒲宁笔下的“枯萎的”(此段落中作家用了两次这一修饰语)秋野:色彩明艳,生机勃勃。当然,这段书写是从具有一定亮色的人物库兹玛的视角观察的,然而库兹玛的视角观察并不总是如此:上引一段有“干瘦的猎狗”和男孩的充满寒意的描写同样出自库兹玛的视角。所以,此段描写的出现仍是基于作家本人对俄罗斯大自然的情热。
其实,在蒲宁这里,人物塑造与自然描写更多是呈现出一种悖论形态。请看《苏霍多尔》中的仆人格尔瓦西卡的形象:“他又高又大,却很不匀称,……他下巴和大嘴的嘴角上有两三撮稀稀拉拉的硬黑胡须,所以也没什么胡子可刮。关于他的大嘴有人这么说道:嘴长到了耳朵边上,不如给他两边缝上点。他块头大大的,胸部又宽又平,骨架全露着,头很小,眼窝很深,灰蓝色的薄嘴唇后面露出两排发青的大牙齿,简直是个古代的阿利安人,苏霍多尔的祆教徒,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长腿狗。”*[俄]蒲宁:《苏霍多尔》,刘宗次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48页。此处不独有讥讽、揶揄,甚至有骂詈。当然,格尔瓦西卡也委实是一个恶人,连主人都惧他三分,最终将老主人打死后逃走。而在发生如此凶案的早晨,作家笔下的自然仍是美丽的,充满了冬天的暖意。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我以为这与他对俄罗斯大自然和俄罗斯性格的总体认识与情感取向有关。蒲宁对俄罗斯母亲的情怀就是如此地分裂而又统一。当然,批判亦是根于深爱。这与鲁迅是一样的——所不同者乃在于鲁迅笔下的农村景色以冷调居多。
作家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对于大自然的欣赏和肯定性描写,与他对于生活的热爱紧密相关。他不时通过人物之口发出感叹:“天气多冷啊,露水多浓呀,活在世上又是多么美好啊!”*[俄]蒲宁:《安东诺夫卡苹果》,李静译,吴迪编译:《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页。事实上他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往往同对于生活的热爱胶结于一。天气冷也许使得许多人不那么喜欢,然而在蒲宁这里,自然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冷”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同样能使你感觉到生活的存在,生命的温度。
“蒲宁和白银时代不少相信只有美才能拯救世界的作家一样,努力在现实的丑恶生活中发现美。”*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3页。但我以为此种“努力在现实的丑恶生活中发现美”并非涵盖其全部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现。例如,他对某些底层人物的外貌、性格就很难说是在丑恶中发掘美,有时甚至使人感觉到仿佛是丑的集中与廓大;然而,作家对于自然(这是蒲宁表现的重要现实之一)却的确如此。诚如顾蕴璞所说:“蒲宁的……散文则从社会的矛盾和人与自然的对峙中定位其永恒主题。”*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9页。在蒲宁这里,确实存在着“人与自然的对峙”。事实上,蒲宁是以自然美对抗人间恶。“他在无数次目睹破坏、灾难、暴力和死亡之后热望为生活寻找一个支点,这个支点便是由人的双手和智慧创造出来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这个支点便是拯救世界的‘美’。”“美拯救世界”*冯玉律:《前言》,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6页。。我以为自然美也是蒲宁寻找的支点之一。
正是出于上述写作目的,蒲宁笔下的自然景物被赋予了社会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有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对这月夜的美景,树木也陶醉得入神了……”*[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96页。“白桦树……被秋天的魅力迷住了,感到很幸福,对其百依百顺,并且由于脚下枯叶的映衬而显得容光焕发。”*[俄]蒲宁:《祭文》,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8页。此处不独白桦树有着人的气息,整个秋天都有着人的风韵。
《圣山》是一篇抒写自然、宗教、人生的相互纠结所产生的感伤与忧郁之美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篇中,自然获得了更为鲜明的主体性,它们甚至会沉思、回忆和絮语。“现在,它们(田野上的土丘——引者注)在永恒的沉思之中只是模模糊糊地回忆得起遥远的往事、昔日的草原和昔日的人们。那些人的心灵要比我们更能理解它们的絮絮细语,这种细语传遍了自古便笼罩在沉寂之中的狂野,这种细语无声地诉说着人世生活是多么渺小。”“在南方草原上,每一个土丘似乎都是某一则充满诗意的无言纪念碑。”*[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0页。自然景物描写不再是纯客观的,自然景物俨然成为作品中的“人物”,并且成为抗拒人间恶、拯救人间于水火的至善的“美物”。 “远处依稀可闻的松涛正在含蓄地不住谈论着某种永恒的、庄严的生命……”*[俄]蒲宁:《松树》,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64页。这是《松树》的结尾:松树俨然业已成为与作家对话的哲学家。
大自然有时是提升作品诗意的酵素,是与作品情节内容相等的另一条平行线,甚至成为作品的主要内容。《米佳的爱情》中虽不乏以景色绮丽反衬人物痛苦的相反相成的描写,但从总体而言却是爱情悲剧因农村大自然的描写被诗化。对于自然的描写甚至超越了对爱情的描写,至少在文字数量上如此。
大自然也是作家与短促人生相抗衡的利器。在《寂静》中,作家一方面书写生命的短暂与孤独;同时又在刻意神化大自然、崇拜大自然,并以此为一种幸福。以大自然的永恒抗拒人生之短促的绵绵情思呼之欲出。
大自然其实乃是蒲宁终其一生的最为重要的伴侣。
其实,此种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崇拜在他早年的诗歌中已见端倪。《胸怀啊,你敞得更宽广些吧,好领受……》中即写道:
大自然啊,你向我敞开胸怀吧,
好让我和你的美紧密融合!……
你啊,广袤的绿色的田野!
只有你们才是我心的向往!*[俄]蒲宁:《胸怀啊,你敞得更宽广些吧,好领受……》,顾蕴璞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3页。
他甚至可以对大自然“双膝跪下,顶礼膜拜”*[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95页。。
作家说自己临死之际也会想起大自然:“我对大地和天空的色彩的真正神妙的含义,一向都有最深切的感受,这个结论是生活赐予我的,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结论之一。这种透过枝叶显露出来的淡紫色的蓝天,我临死也会想起。”*[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27页。大自然事实上成为作者最重要的依恋与伴侣,是他对抗人间恶的武器,是他抚慰心灵的又一部《圣经》,是他让短暂的生命获得永恒性的长明灯。
在蒲宁看来,大自然充满了神性,自然之美乃神性之美。“正是泛神的大自然安顿了蒲宁的灵魂”*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0页。,使他内心蕴含着丰沛的美感,并与大自然之美不停地互动,成就了他的创作,更成就了他的人生。
有研究者认为,蒲宁对于大自然很细微的特征的描写“令人感到索然无味”。我本人读蒲宁却没有如此感觉,从未产生过审美疲劳。那些初看起来似乎有点冗长、甚至未免重复的描写,结合到每一篇作品的具体情境,都有各自的韵味。有人曾乘坐大巴连续几个小时欣赏欧洲的原野,从不疲倦:因为每一个场景都跃动着生命的绿色,甚至使他本人感到了自己生命的贲张,与原野的脉搏一起律动。读蒲宁的大自然描写,我获得了同样的审美感受,甚至美得令你窒息,美得令你流泪。读蒲宁的大自然描写感觉疲劳,恐怕读时缺乏自身生命的融入。我读帕乌斯托夫斯基的蒲宁评论,就深切地感到了他对蒲宁作品的生命融入。
作品《苏霍多尔》中的许多景色描写犹如印象派绘画,而以猫头鹰的叫声反衬夜的寂静与安详,明显带有我国古诗“鸟鸣山更幽”的情调。景物又每每被人格化,如“只听见远方的某处有只小铃铛在哭泣”*[俄]蒲宁:《苏霍多尔》,刘宗次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45页。,以此为娜达莉亚的不幸预兆或铺垫。
有俄罗斯学者提出,蒲宁作品存在着“对大自然与人的世界的平行描写”*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十章《伊万·布宁》(此章布罗伊特曼、马戈梅多娃著,路雪莹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卷第83页。。我以为与其这样表述,不如说是“平等描写”更为恰切。蒲宁有着自觉地与其他生物平等相待的意识。“在蒲宁的‘字典’里,‘野兽般的’是一个完全褒义的形容词”*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这与鲁迅在批评中国国民性时对于“兽性”的看法颇相似*鲁迅在《而已集·略论中国人的脸》中写道:“人不过是人,不再夹杂着别的东西,当然再好没有了。倘不得已,我以为还不如带些兽性……”见《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4页。。蒲宁还这样写道:“我在自己的内心能感到所有祖先的存在,还能感到自己与‘野兽’的种种联系,我的嗅觉、我的眼睛、听觉不仅仅是人类的,它们内在的东西则是‘野兽般的’,所以,我像野兽般地热爱着生活。”*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73页。这已经是在自觉地脱离人类中心主义。
事实上,蒲宁是将俄罗斯的大自然作为自己文学王国的主角,至少在客观上显现出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过渡趋向,或曰两者并重趋向,甚至在某些作品中有着鲜明的生态道德质素,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高尔基所谓“文学即人学”的背离。蒲宁乃是今日所倡导的大自然文学的先行者之一。
二、对宗教的称颂与质疑
蒲宁的自然世界是一个泛神论的世界,大自然被赋予了神性。他对大自然有着宗教徒般的情怀。那么,蒲宁的宗教世界是何种样态呢?
关于蒲宁与宗教的关系,蒲宁的至交阿达莫维奇这样写道:“他尊重东正教会,他也珍视宗教仪式的美,但是仅此而已。真正的、严格的、永远惊恐不安的宗教性是与他格格不入的。”斯特鲁维也认为:“尽管虚无始终令蒲宁恐惧不已,你在他的笔下也找不到对上帝的否定,但在他的内心里对上帝的信仰和不信仰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8-59页。蒲宁的宗教观同样呈现出一种悖论状态。
蒲宁曾借《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同名主人公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我虽不理解上帝,但应该信任上帝,而为了生活得幸福,我也就相信上帝了。”*[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编选:《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96页。从中透视出蒲宁既信任上帝,又有所保留的信息:对宗教居然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我以为,这应是理解蒲宁的宗教观锁钥之所在。
对本民族多有批评的蒲宁,有时又对其发出由衷的赞美:“斯拉夫人的特点是高大的身材,亚麻色头发,勇敢、好客,崇拜太阳神、雷神和电神、敬树精、人鱼、水妖等‘自然力和自然现象’。”*[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编选:《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96页。
此处所写俄罗斯人基本是正面的,不独外貌很富阳刚之气,而且敬畏神祇——这里的语风显而易见是对俄罗斯人的笃信诸神予以礼赞。我以为尽管这里没有明确提出基督教,但应包括在内:在俄罗斯,信仰基督教乃是信仰多神教的必然发展。这也正昭示出蒲宁对基督教乃至一切宗教的心音——蒲宁对佛教也很敬仰。
《革尼撒勒湖》写的是作家为探求宗教与人生的奥秘的巴勒斯坦之旅,再现了耶稣布道形象,那大悲悯的情怀使人肃然起敬,表现出蒲宁对耶稣的崇拜与敬畏。
《寂静》讴歌“神化大自然”*[俄]蒲宁:《寂静》,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80页。,认为“无论在何时何地,新奇的自然风光之美,艺术和宗教之美总会在我们年轻的心中激起强烈的愿望,要让我们的生活也达到美的境界,使其充满真正的欢乐,并且同人们一起分享这种欢乐”*[俄]蒲宁:《寂静》,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81页。。宗教之美与自然之美、艺术之美构成了蒲宁的美的三元世界,它们对于人类的幸福和欢乐都是不可或缺的。宗教并非苦行,而是美的享受。这是一篇关于人生、幸福和美的寓言,是独特的对于宗教的礼赞。
《理性女神》中作家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一度要摧毁巴黎圣母院、让一个女演员扮演取代圣母的“理性女神”的狂想谬行给予了猛烈批判,唱出了对宗教的颂歌:
在人类的生活中,总是只有那些高尚的、善良的和美好的东西最终才得以留存下来,传之后世,仅此而已。一切邪恶的、卑鄙的和庸俗的、愚昧的东西归根到底会销声匿迹:它们将不复存在,再也不见踪影。那么留下的是什么呢?还有什么呢?优秀作品脍炙人口的篇章,关于荣誉、良心,关于自我牺牲,关于卓越功勋的传说,美妙的歌曲和雕像,伟大的、神圣的陵墓,古希腊的神殿,哥特式的教堂,像天堂一般神奇的彩色玻璃窗,管风琴所奏出的犹如雷鸣的和怨诉的音响,《震怒之日》和《弥撒曲》……留下和万世永存的是从爱和苦难的十字架走下来,向杀害他的凶手伸出双手的基督,留下的是圣母马利亚,唯一的女神中的女神,她的幸福王国永世长存。*[俄]蒲宁:《理性女神》,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18——219页。
这里,作家将基督和圣母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与一切罪恶相对立,尤其是与暴力革命相对立。本篇反映出蒲宁的社会观、历史观、文化观、人生观、乃至生命观和死亡观,特别是宗教观——在批判暴力革命的同时对于宗教的称颂,是他的宗教观一个突出特点。
《一段抒情叙事诗》抒写一个年老的朝圣者玛申卡对宗教的笃信与沉迷。她所讲述的一个关于凶残的公爵被狼咬死的故事,一方面透视出沙俄统治阶层的残暴所引起的天怒人怨,一方面昭示出上帝的惩恶意旨。所以,玛申卡称那头狼为“神兽,上天的狼”。狼俨然在替上帝行道。令人叫绝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却被命名为《一段抒情叙事诗》,固然是作品中引用了一首诗,更主要的我以为还是作家本人将这个在宗教的光环下野狼为人除害的故事当作了一首宗教赞美诗。于是,此篇也就成为蒲宁借用他者的故事而对基督教的肯定与称颂。
蒲宁作品中还往往涉及大量有关宗教(主要是东正教)的民俗描写,尤其是宗教节日的提及。如谢肉节(东正教和斯拉夫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每年的2月底至3月初的一周,旨在送冬迎春,具有祖先、农事、家族崇拜的特点,在谢肉节的一个星期内,按习俗吃油煎薄饼,乘车出游,进行宗教活动和各种娱乐活动,祈求丰年。20世纪之前,有“神圣纵欲”的成分)、赎罪日(在谢肉节节期内)、净罪的礼拜一(谢肉节之后为期7周的大斋期,大斋的第一天,称为净罪的礼拜一)、圣母进殿节(东正教12大节之一,俄历11月21日,纪念幼年圣母进殿献身于上帝)、圣母领报节(亦为东正教12大节之一,每年4月7日)、伊里亚节(雷神节,每年8月2日,在此节日之前,家里不点亮灯火)等。并且“净罪的礼拜一”还成为蒲宁一篇小说的篇名,作品女主人公身上体现出了汇合东西方两股潮流的俄罗斯文化的特点,同时又反映出俄罗斯性格中那种东正教徒“受诱惑——堕落——赎罪”的行为模式。《祭文》、《圣山》等作品名字都是借用了宗教词汇。此外,《娜达莉》中对于丧俗的描写,《噩梦》中关于如何解救难产的叙写,《祭文》中关于蛛网被称作“圣母的纺线”的提及,都有浓烈的宗教气息。
不仅如此,蒲宁甚至狂读圣徒传,长时间跪在圣像前祈祷,乃至有过穿修行衣、喝凉水、吃黑面包的类于苦行僧的生活(这自然与他所主张的宗教应是美的享受构成悖论)。宗教还一度成为他抗拒死亡的力量。他宣称:“我甚至还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然而,蒲宁对待宗教的态度有时又是犹疑的,甚至是有所质疑的。我们且看作家所抒写的自然、宗教、人生的相互纠结所产生的感伤与忧郁之美的《圣山》。
作品有这样的描写:
“我”看着朝圣者的执着,“心里一直想着古老的风尚,想着它所具有的神奇力量……这种力量从何而来,它意味着什么”*[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2页。?这是对宗教与风尚的复杂感情,既赞赏又犹疑。
修士为了祛除瘟疫,“他在各家院子里转啊转的,洒了圣水,可是什么用处也没有”*[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2页。。此处如实描写了宗教仪式,但对其作用则发出了明确的质疑。作家展开了对圣徒生活的追忆与想象,满含着敬意和深情,认为他“平凡而又心灵高尚”,有着“伟大的胸怀”*[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4页。。“我点起一支蜡烛,插上烛台,用以纪念那位身体虚弱的老人,他在当年那些可怕的夜晚,在修道院遭到围攻、四周燃起篝火的时候,坚持留在这所小教堂里叩拜祈祷……”*[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5页。看来,蒲宁对信仰对象与信仰者的态度有别:对信仰对象(宗教、神祇)时有质疑,对信仰者的人格与心灵却备加赞叹。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悖论。
“我……又想起了古老的风尚,想起了长眠在草原的坟墓中、在灰白色羽茅草的絮絮细语中的先人们……”*[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6页。全篇以此作结。
在此篇中,虽然对于宗教的作用有所怀疑,但从总体考察,还是以称颂为主——不过主要是对“先人”——以前的圣徒们的称颂:他们执着于信仰、勇于自我牺牲的宗教精神激动着作家的心;并非是对宗教本体的称颂。
《祭文》通篇所写乃是人与宗教之关系。
作品从叙写草原上的一个小村子的一个十字架写起:来到此地的第一个人竖起了一个十字架,并请来神父举行了祓除仪式,祈求圣母保佑。“自此之后,古老的圣像便日夜护卫着草原上这条古老的道路,并且不露形迹地赐福给辛勤劳动的农民。我们小时候对这个灰白色的十字架总是很害怕……还怀着崇敬之情。”*[俄]蒲宁:《祭文》,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7页。从小就对十字架这一圣物又怕又敬,既已隐伏下了对宗教的复杂态度。
“迷路的行人在狂风暴雪中看到从雪堆中露出的十字架,便会满怀希望地画起了十字,因为知道天上的圣母正在看顾白雪皑皑的荒原,护佑着村庄,护佑着这一片过早地死寂的田野。”*[俄]蒲宁:《祭文》,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8-29页。对于虔诚的信徒给予礼赞,然而对于圣母的作用略带一丝犹豫:在她护佑下田野依然“过早地死寂”。这里表现的仍是对宗教和信徒的双重感情。
作品后半发生了逆转:理性的认识愈来愈深刻:“生活不会止步不前,旧事物渐渐消失,我们常常会怀着巨大的悲痛同其告别。不过生活难道不是由于持续不断的更新而变得美好的吗?”*[俄]蒲宁:《祭文》,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0页。作家承认历史前进的正当性,但也有惜别和伤逝。接下来却写出了十字架开始朽烂,圣母也不再关切这片土地的命运,唱出了对宗教的挽歌及无奈。同时承认草原上出现了“一批新人”,“倒在地下的灰白色十字架将会被所有人遗忘……不过,新来的人们将依靠什么来庇护自己的新生活?他们在热火朝天的、喧腾的劳动中祈求的是谁的祝福呢?”*[俄]蒲宁:《祭文》,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1-32页。上帝死了,谁是人们的新的护佑者呢?在几近发出了否定宗教的声音后,作家陷入了新的探寻和思考——没有明确答案的探寻和思考,流露出呼唤新的信仰、新的宗教的意绪。这又可以看作是一种否定之否定。
这篇《祭文》事实上是一篇非同凡响的宗教诗,歌赞、叹惋、质疑、否定、否定之否定、新的呼唤,起承转合,互相纠结,表达了作家对宗教极为复杂的理性认知与感情世界。
倘若说《圣山》《祭文》是蒲宁以散文诗的形式直接发抒了自己对宗教的称颂与犹疑的纠结,那么《在异乡》则是截取客观生活的片段,以曲折的方式,表达了作家本人对宗教的复杂思绪。
作品写的是一众庄稼汉到外地逃难时在一个火车站等车之际,适逢候车室里举行复活节仪式,他们参与其中的场面。
“救世主基督今已复活,天使凯歌响彻天宇……”神父用清脆响亮的男高音急急忙忙地诵道。
……
……庄稼汉们赶快跪倒在地,急匆匆地画着十字,一会久久地把额头贴住门槛,一会儿又抬起瘦削的脸,带着饥饿的眼神,忧郁而又贪婪地朝明亮的大厅深处,朝灯火和圣像张望。
“吾主复活,审判世人!”
饥饿的庄稼汉们艰难困苦,企盼基督的拯救;然而他们的忧郁与瘦削,他们的贴住门槛的头,同明亮的大厅、神父的男高音,以及神父用自己的声音二度创作出来的复活的基督、凯歌的天使,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彰显的不独是天堂与人间的距离,也有希望与无望之间的一缕游思。“吾主复活,审判世人!”事实上与农夫产生了共鸣。作品从心灵深处剔挖出底层大众对宗教亦不乏矛盾的心态:他们敬畏基督,但他们心中不平,所盼望的乃是“吾主复活,审判世人!”蒲宁对于基督教的悖论在本篇中与这些不幸的农夫发生了互动。“天上的圣母正在看顾白雪皑皑的荒原,护佑着村庄,护佑着这一片过早地死寂的田野。”这一《祭文》中的意象也正是本篇所要表达的同样情思,或者说早年《在异乡》(1893)中的深刻感触后来升华为《祭文》(1900)中的“圣母护佑死寂田野”这一意象。
蒲宁塑造的神父形象也各有不同。《噩梦》中的神父临死时说:“难受的是到处都有那么多的痛苦,难道无法改变了吗?”*[俄]蒲宁:《噩梦》,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93页。他始终葆有宗教所应有的大悲悯情怀,他在生命终结之时向上苍、也向宗教发出了诘问。而《乡村》中的神父则虚伪、善变,惧怕富人。《快活的一家子》中的教职人员更虚伪,甚至猥琐。在为阿尼西娅举行的丧仪中,教堂执事惦记着自家的养蜂场,神父张望着一个柳条筐,那里装着“供神父的吃食”*[俄]蒲宁:《快活的一家子》,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
阿尼西娅临死之际,虽无牧师在场,却以亲吻一块盖着陶罐的木板(陶罐里没有任何吃食,仅有一只大苍蝇)——那上面居然有圣像画——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上帝的忠诚。这里有着深切而痛苦的寒意:圣像下面无人们最需要的食物,却有人们最讨厌的苍蝇!事实上这是对宗教的严厉叩问。然而,活活被饿死的阿尼西娅还是要表达对上帝的忠贞不二。是可怜抑或可敬?作家此种描写,将读者也势必引入到对于宗教的一种悖论状态。——当然,这也是作家本人的悖论,也是俄罗斯宗教自身的悖论。
而在《阿格拉雅》中蒲宁对于宗教的态度已经是出离愤怒了。年仅15岁的少女阿格拉雅在虔诚的教徒姐姐和一位长老的诱导下居然焚身殉教。这是无限珍视生命的蒲宁所无法容忍的。读罢此篇,我们对蒲宁公然宣称“我没有任何正式的宗教信仰”*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并对自己曾经参与过的东正教的宗教生活给予猛烈地批判,感觉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苏联著名女画家玛·楚拉科娃曾这样评说蒲宁:“我感觉蒲宁是站在俄罗斯民族世代相传的一条根本的道路之上,这也正是每一个俄罗斯人特有的一个特点,即对民族的理解和认识与东正教、与宗教联系在一起。”*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这揭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与宗教之关系,也昭示出蒲宁对宗教的悖论态度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俄罗斯宗教自身存在的悖论之关系。
那么,什么才是蒲宁心中至高无上的宗教呢?——“美是最高的宗教”*[俄]蒲宁:《耶利哥的玫瑰》,冯玉律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这就是蒲宁的回答。但我以为,蒲宁更是以爱为宗教。奥古斯丁用“爱”解释摩西十诫。针对《诗篇》所言“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他认为:“其中提到的十弦瑟正是摩西十诫,不过基督徒要用它唱新歌 ,而非像犹太人那样唱旧歌。所谓新歌,正是爱之歌,与其相对立的是旧的畏惧之歌。也就是说,基督徒对摩西十诫的理解和遵守必须出于爱并归于爱,而不能像犹太人那样出于畏惧,由于害怕惩罚才不敢触犯律法。唯有在爱的歌唱中,摩西十诫能给人带来自由,摆脱因畏惧而唱出的奴役之歌。”*孙帅:《奥古斯丁对摩西十诫的基督化理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3日。蒲宁质疑的宗教虚伪乃至残忍,也正是宗教的故意使人畏惧;他所崇仰的则是奥古斯丁挖掘的宗教的大爱。爱,才是蒲宁至高无上的宗教。他的宗教观的悖论在这一点上达到相反相成的最后统一。
三、为人类而写作与为自我而写作
蒲宁继承着俄罗斯文学的为人生而创作的主流宗旨,往往将自己的创作同人类的苦难胶结于一。
在蒲宁看来,“人类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流血的历史”*[俄]蒲宁:《众王之王的城市》,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24页。。他还很年轻时就感受到了人类的苦难。
蒲宁在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时写道:“我记得,在这个房间里我第一次读到拉吉舍夫的作品,使我赞叹不已。‘我举目四望,人类的苦难挫痛着我的心!’”*[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89页。产生了与拉吉舍夫的强烈共鸣。写于1909年的诗《狗》中,蒲宁宣称:“我注定要/分尝各国和历代的烦闷。”*[俄]蒲宁:《狗》,顾蕴璞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6页。竟然将自己的忧心和烦闷扩展到极为广阔而深远的时空。“在这个莫名其妙的世界上,无论怎么令人痛苦,叫人发愁,它总还是美丽的,我仍然热切希望做一个幸福的人,希望相互敬爱。”*[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74页。他热爱世界,热爱生命,热爱人类,认为自己的幸福与整个人类的相互敬爱紧密相关,不可分割。他关照着人类世界的全部,也观照着人类世界的细微:“我站在城里大教堂后边的悬崖上,俯瞰沿河两岸丘陵上的那些平房,看着腐朽了的木板房顶,看着里面十分肮脏的蓬门荜户,心里一直想着人间的生活,想着一切正要消逝,但又将重演,想着大概三百年前这儿也有过同样的黑黝黝的木板房顶,有过这些堆积在荒野和土丘上的垃圾。”*[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75页。以心灵关照全人类的苦难,以视觉观照每一处的不幸。正如同鲁迅一样,蒲宁的视野是整个世界:“在蒲宁笔下,人和他的生活被牢牢地同生存的广阔规模——同整个民族的与世界的历史,同自然宇宙的宏大联接在一起,与永恒相呼应。”*[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
人与历史、人与时代、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是他终生思考的问题,并且浸进自己创作中,成为他创作中的极为沉重而丰硕的思想内涵。
蒲宁有着一颗早醒的悲悯的心,幼时即已意识或曰感悟到自己与世界的关联:“我怀着悲伤的感情回忆自己的幼年。幼年每一时刻都是悲伤的,因为这个静静的世界贫瘠穷乏,而在这个世界中,却有一颗在生活上还没有完全觉醒的、对一切事物还感陌生的、胆怯的和柔弱的心灵在幻想着生活。”*[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08页。他充分地认识到人类世界是何等的不幸,怀着改变它的希望长大成人。
中篇小说《乡村》虽说是蒲宁早期的代表作,但即便仅此一部作品,亦可揭示出蒲宁创作与人生、与广大人们的深广关联。沃罗夫斯基认为:“尽管作者对农村中出现的新变化还估计不足,认识有片面性,但小说真实地展示了农村中贫困衰败的景象,它除了纯艺术价值之外还是一份重要的人类文献,也是对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9页。这就是说,《乡村》的意义不仅是俄罗斯的,而且是全人类的,它既是作家对于俄国现实生活的反映,也是作家对于人类苦难与不幸的沉思。“蒲宁的思考要宏观得多:社会的不平等对他来说,只是更深刻、也更隐蔽的原因引起的后果。”*[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4页。事实上,蒲宁的早期作品既已将人们的种种不辛与人性的弱点相连属,使得作品不独成为社会生活长卷,而且成为民族性格的病理解剖图。高尔基在1910年12月给蒲宁的信中写道:“这种深藏在心头的为故乡所发出的悲叹,这种高尚的忧国忧民之情十分可贵,……除其第一流的艺术价值之外,蒲宁的《乡村》是一个推动力,它促使风雨飘摇中的俄国社会反省,目前应考虑的已不仅是有关农民的问题,甚至不仅是有关普通人民的问题,而且是俄罗斯能否存在下去的问题。”*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8页。可以说,《乡村》对于俄国社会现实的反映之力度业已超越了他的许多前辈作家。在他之前,很少有将自己的创作与民族的生存与灭亡问题如此胶结,这无异于敲响了民族危机的黄钟大吕。“为人生的文学”全然成为了“为民族生存的文学”乃至“为人类的文学”。
需要指出的是,蒲宁对于人生、对于民族、对于人类的大悲悯情怀,与他同宗教的关系相关。他不仅从宗教典籍接受营养,而且几次到宗教圣地考察。不单接受基督教,也对佛教有着浓烈的兴趣。他在《众王之王的城市》中曾提及中国高僧法显,对佛教圣地锡兰(斯里兰卡)的阿纳拉特哈浦拉(即“众王之王的城市”) 充满了崇拜与怅惘之情。这些都陶冶了蒲宁对于全人类的悲悯情怀(诚然,蒲宁对于宗教的态度有时也是矛盾的,我们在前面已作探讨)。
然而,尽管蒲宁创作表现出浓烈的家国和人类情怀,却始终十分重视创作的个性与自由。在他的创作中,“其中自我、个人的考虑始终占主要地位”*[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93页。。“蒲宁特别重视个性的自由。因此即使与高尔基合作,……他也从不参加集体创作的活动,保持了自己独立的艺术原则。”*[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此处所说似乎是一种作家的工作方式与形态,其实所昭示的是蒲宁对个性自由的高度重视。这也必然要体现在具体创作中,那就是,在他的创作中,个性往往压倒了血缘性、集团性、阶级性乃至民族性。《乡村》中的兄弟二人个性全然不同,许多作品中的下层人物对于上层人物的仁爱之心,恐怕也只能从个性来解释。《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中的女主人公索斯诺夫斯卡娅的复调性格,特别是她在爱与死方面的独特心理(将婚恋作为死亡仪式)更是只能从个性来解释。“蒲宁坚定不移地专注于个性生存中的美好的与悲哀的东西……对他来说,个性存在的意义总是明显地要比某种社会思想的目标更宽泛得多。……蒲宁在创作的成熟时期几乎总是写到人的生存之谜。他赋予自己许多的主人公一种能力:在危机考验的关头更加充分地体验生命。对蒲宁来说,人的最重要的能力,可以说几乎就是牢记并善于体验生命的美好,尽量充分地感受生命的悲剧性壮美,视自然界为永恒不移的价值。”*[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126页。如此看来,蒲宁的个性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有所不同:他并不是要通过个性表现共性,也不是单纯地追求个性鲜明,而是以个性为载体,剔挖生命本真的奥秘和意义,进而达到对于人类和整个自然界的新的求索与理解。“个人之我在这一画卷中只是同其他事物平等的一个因素,是无垠宇宙的一粒沙子。”*[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他将自我视为与宇宙其他万物个体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有生命的个体。个性所体现出来的是生命性,是生命的永恒价值。每一个个体生命通过鲜活的个性而昭示出自己的美好存在,从而将短暂的存在升华为意义的恒久。蒲宁是通过个性抒写人类乃至宇宙时空的。
我们在前面分析了蒲宁作品的社会作用,乃至他本人对于民族和人类的使命感。可是,他有时对此又是给予否定的。他曾这样说过:
写!应该写屋顶,写套鞋,写背影,绝不是为了“同专制和暴力作斗争,保卫被压迫和受穷困的人们,塑造鲜明的典型,描绘社会、时代及其情绪和思潮的巨幅图画!”……“社会对比!”我走过雪亮的橱窗,心里挖苦道,还想着要故意刺激某些人……到了莫斯科大街,我走进一家车夫茶馆,坐在人声鼎沸、拥挤闷热的房间里,观察那些鲜红的肥脸、那些红胡子、那摆在我面前的托盘,托盘生锈剥落,上面摆两把白茶壶,壶盖和壶把有根湿绳子拴住……是观察人民日常生活吗?你们错了——只不过是观察这个托盘,这根湿绳子!*[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90页。
这是对于自己的文艺观的明确自述:否定文艺在社会变革方面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对比”予以嘲弄;否定表现人物的重要性;简直以观察(表现)外在世界的琐碎为第一要义,尽管在实际创作中有所背离,甚至是严重的背离。这里充分表现出蒲宁创作思想的悖论性。因之,他得到下面这样的评价也就不足为奇:
很多同代人觉得,蒲宁像个不动声色的“傲视者”,是位出色但“冷峻”的艺术家,而他对俄罗斯、俄国人和俄国历史发表的见解过于旁观而表面。……虽然蒲宁一向深刻地感到自己属于俄国文化,属于“祖先的一族”,属于俄罗斯的古老和伟大,但他努力与眼前的社会动荡保持一定的距离……*[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页。
他总是避免作家对生活的“冲动而疾速的”干预。*[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显而易见,此处的评说与我们前引的沃罗夫斯基和高尔基的评判全然相反,但也都符合事实,只不过抓取了不同向度。
那么,蒲宁究竟为何写作呢?我的回答是:为写作而写作!为自我写作!追求个人幸福是他人生与写作的目的。
小说《书》中写道: “永久的痛苦——就是永久的沉默,就是恰恰不能说出的你心中的真挚的、自然的、真正的,正是需要更加充分合法地表白出来的东西……”*[俄]布宁(按:即蒲宁):《书》,何晓曦译, 吴迪编译:《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此语透视出作家对记录生活本身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同时揭示出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深层原因:这是他的一种内心需要,是他证明自我生命存在的需要,是他享受生活和生命的愉悦感的需要——一旦不能说出真挚和自然,一旦沉默下来,就是无涯的痛苦,就是生命的消逝。
在中学的最后一年,他已意识到:“生活中确有一件令人神往的非常美的东西——文艺创作。”*[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79页。他将写作当作人生极美的一件事,他为了追求美而写作,而创作。“世间的事物,还有许多未被写下来的,这或出于无知,或出于健忘,要是写了下来,那确实是令人鼓舞的……”*[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07页。写作成为他获得存在感、生命的愉悦感、充实感、满足感的方式。他似乎是为写作而诞生的。
同时,他又觉得:“众多的事与物,如果不写出来,就会陷入黑暗而埋藏坟墓,写出来就好像获得了生命……”*[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此处似乎又在昭示,他的写作是为了外在世界获得生命。因而他的写作既是为了自我,又是为了身外——为了两个世界而写作。“作家注意的焦点,不仅是、或者说不是理性理解的生活范围,而是经验所及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能让人们哪怕在瞬间接触生存中神秘的、形而上的奥妙(形而上的东西,是处在人对自然现象的感知范围之外的东西;是那些无法进行理性思考的东西)。”*[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蒲宁事实上更加追求的乃是探求永恒的秘密,“对生活中一个瞬间进行外在的宁静的描写……,让读者想到了永恒,暗示着世界生活的融合性与整体性”*[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应当说更有“世界生活”的复杂性和深邃性。简言之,蒲宁对于形而上的东西更感兴趣,这又与他所表示过的对生活琐碎感兴趣的说法构成了悖论。其实,往往是由形而下的琐碎生发为形而上的深刻,使得一件小事能够与整个人类、历史、自然构成多种关联,为人类心理和外在世界提供了或引发了对多种多样的时而互不矛盾、时而相互冲突的形形色色的解释。如散文诗《蚁道》以一条空旷的道路引发出千年历史和无限宇宙,让人思索其中的秘密与堂奥。文本极小(仅由64个词组成)而容量极大,从而成为一篇经典。我们在鲁迅的《野草》中是可以感受到此种意味的。这就是蒲宁的为写作而写作。写作乃是他与时空相联系的唯一存在方式,许多时候并无明确的动机与目的,他的独具个性的存在成为了他写作或曰创作的内驱力。
蒲宁从事文学创作还基于他对记忆、回忆的看重。他是一个记忆力极好并擅长回忆的人。尤其是在他离开故国之后,回忆成为了他的重要生活内容,或者说他整天沉浸于回忆之中。将回忆付之于纸笔,就成为了创作。他重视“回忆的创作力量”。“艺术家的记忆在晚期蒲宁看来,能够使人超越逝去生活的混乱,因为与实际情况的直接影响相比,记忆的真实性毫不逊色,而是更胜一筹。”*[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顾蕴璞先生也认为,因为彼时彼地他“囿于自己流亡的狭窄空间,不得不把远逝的现实,即记忆作为灵感的主要源泉,而且在晚期的蒲宁看来,记忆中的真实比生活中的真实毫不逊色,能使人超越已逝生活中的混乱,可以让早已被湮没的历史获得新的审美价值”*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3页。(对于《藤野先生》的细节真实性问题亦可这样理解。)。
蒲宁是位文学大师,也是位“回忆大师”,在他的对过往的回忆中营造了繁复的时空。《苏霍多尔》在抒写对于庄园的回忆时往往呈现出三度时空:当下——回忆幼时——追索幼时的回忆。极具历史纵深感,并平添了感情的厚度。譬如第三章对于老屋的回忆。先是写老屋的现状:地板歪斜,阳台朽坏,台阶消失……,接着展开对老屋的种种回忆,而在回忆幼时往事时,回忆与娜达莉亚的对话占了大部分,在这对话中又展开了对于对话前发生的种种的回忆,从而形成了三度时空。一度时空与二度时空的分水岭就在于一度时空(现在时)老屋的台阶已经消失,二度时空(过去时)则依然存在。所以,“我们”(叙述人和妹妹)与娜达莉亚对话中对往事的回叙,属于回忆中的回忆,即三度时空(过过去时)。
值得注意的是,蒲宁不独自己生活于记忆之中,他作品中的人物亦每每如是。《在异乡》中,逃难者在异乡等火车之际以回忆往事(诸如到教堂做礼拜前后的种种情境)来获得心灵的慰藉乃至幸福感。回忆不是蒲宁的专利,他笔下的主人公,无论是上层抑或底层,无论是个体或群体,回忆都是其重要生活内容。
《圣山》中还有这样的妙文:
斜坡上还有一些灰色的羽茅草,其实那是羽茅草可怜的残茎,正随风轻轻地摆动。我想,它们的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它们在永恒的沉思之中只是模模糊糊地回忆得起遥远的往事、昔日的草原和昔日的人们。那些人的心灵要比我们更能理解它们的絮絮细语,这种细语传遍了自古便笼罩在沉寂之中的旷野,这种细语无声地诉说着人世生活是多么渺小。*[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自然景物也会回忆。“在南方草原上,每一个土丘似乎都是某一则充满诗意的传说的无言纪念碑。”*[俄]蒲宁:《圣山》,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0页。自然景物被赋予了主体性,当然会“回忆”。 事实上,在蒲宁这里有多层次的回忆主体,作家本人、作品人物、自然景物。多层次回忆主体的出现,自然关键还在于作家本人以回忆作为生命的要义,并因之外烁于自己的人物和景物,并使之交互感应和增强效应。他的作品的挽歌似的忧郁情调也正与此相关。
回忆往昔的美好,是一种忧郁的幸福;对于古风与先人的回忆,更使他得以借此将生命向前延伸(如《圣山》)。但回忆往昔的不幸,恐怕就是一种痛苦了。他曾这样写道:“回忆只能折磨人,只能使人上当,以为那就是幸福,就是不可理解的,尚未享用过的幸福。”*[俄]蒲宁:《素昧平生的友人》,戴聪译,《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2页。这是蒲宁借作品中的人物而发,不知作家本人是否赞成此种观点,或许是作家对于本人一直坚持的对于回忆的肯定性评价在某一时刻产生了怀疑?不得而知。在《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中,则说得非常明白:“回忆是一种使人沉痛、使人恐惧的东西,它甚至需要有专门的祈祷文才能解脱。”*[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836页。这是在回忆女友离开自己的情境时写下的文字。作家委实对“回忆”又爱又痛。看来,蒲宁在回忆问题上也是一种悖论。不过,回忆在文学创作中的巨大作用,则是应予肯定的。
除以上诸点之外,蒲宁觉得写作可以使作家与读者的灵魂结合于一,而这又是一种极大的人生享受,可以从中获得幸福感。
《素昧平生的友人》是一个假想的读者致一位作家的几封信。谈及的是艺术与人生的关系,艺术的功能和力量,人的孤独感、追求美的天性等问题。事实上是作家本人的内心独白。
作品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提出艺术可以“激发起对个人幸福的憧憬”,可以“体味到了人的灵魂的高尚美好”,感到“生活毕竟是美好的”*[俄]蒲宁:《素昧平生的友人》,戴聪译,《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8页。等等重要艺术观点。尤为突出的是,这位读者对作家这样倾诉:“您的思想感情成了我的,成了我们两人共同的思想感情。的的确确融合成了一个灵魂,两人在世界上所共有的一个灵魂。”*[俄]蒲宁:《素昧平生的友人》,戴聪译,《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9页。这是蒲宁对自己作品的征服力的自信,也是他从事创作的最好回报,更是他的创作的深层动机之一。
四、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对峙与胶结
有学者指出:“蒲宁的艺术观包含了两个维度,即超验的维度与现实的维度。在第一个维度上他与现代主义极其相近,但在第二个维度上他却与现代主义坚决决裂,这正是蒲宁的矛盾,同时又是其独特之所在。”*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委实如此。
蒲宁在思想和创作上深受托尔斯泰影响,但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创作上,与托翁的距离显得更大一些:托尔斯泰完全拒绝现代主义*李春林:《鲁迅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下编),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但在蒲宁这里现实主义虽说居于主导地位,可是现代主义的营养也被汲取。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蒲宁这里,自然如同它们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有其对峙方面,然而更多地是相互交融。从而显示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致的风格来,尽管有时蒲宁公开表示他并不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居然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觉得未免有点以偏概全——陀思妥耶夫斯基最著名的代表作《地下室手记》难道主要是讲故事?蒲宁的《幽暗的林荫小径》难道不是讲了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
我觉得,传统现实主义有两大要素:一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一是细节的高度真实性。
有人认为蒲宁在人物塑造方面成就不是特别突出。若是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此种评判有其合理性,但他也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乡村》中的哥哥吉洪那两只“疯狂的眼睛”,弟弟库兹玛那双“忧伤的眼睛”;《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主人公的通体都是矛盾;《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中建构了生命、死亡、爱情相互并峙而又矛盾冲突的三元世界的女主人公索斯诺夫斯卡娅;《米佳的爱情》中视爱情为人生第一要义乃至具有宗教的神圣性的米佳……都可谓成功的典型人物。否则,1933年诺奖评委会因其“以严谨的艺术才能在文学散文中塑造了典型的俄罗斯性格”而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我也承认,蒲宁对于俄罗斯大自然的描绘胜过他的人物描写。事实上,他是将俄罗斯大自然作为“人物”和“性格”来塑造的。而其之所以成功,乃在于他为我们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乃至错觉等多种角度捕捉和再现出大自然的所有细节,有的细节看似重复,其实绝不雷同,各有各的个性。“对事物的细节描写……乃是他艺术上最强的方面之一。……这种外在描写的分外集中,再加上作者追求极端简约、凝练的表达,结果便要求读者放慢阅读速度。读蒲宁的作品不能‘一气呵成’、‘一饮而尽’;要体会他对语言的精湛掌握,不能靠阅读的数量,而应靠深入与仔细。值得注意的是,在感情充沛、描写据实的前提下,任何一个细节还都充分地以作家的准确知识为基础:对描绘的准确与具体,蒲宁的要求是很苛刻的。”*[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这正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本质特点之一。同时,我们在此也发现了他与鲁迅相似的风格,尤其是他们的作品都必须慢阅读。
同时在蒲宁的作品中,“每个细节(无论是言语的,还是风景的)仿佛都有同样的重要性与独立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不可分割的、充满抒情性的整体。在描写的各要素之间没有主次的等级之分,中心与非中心之别。个别的单个的事物却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这样简单地概括蒲宁艺术世界的这一建构原则。”*[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3-124页。我以为,蒲宁的细节与总体的关系,很有点托尔斯泰“史诗微积分”的意味。我甚至觉得,蒲宁以微积分的手法建构了他的庞大的俄罗斯自然史诗。万千作家和普通读者为蒲宁笔下的大自然而流泪和窒息,原因即在此。这就是蒲宁的现实主义的力量。
但他的现实主义又别具一格:“反映现实与反思历史的并驾齐驱,在对现实的批判中包孕了对往事的伤逝之情。”*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8页。蒲宁是位心灵廓大、目光深远的伟大作家。“蒲宁的视野是整个世界。……在蒲宁笔下,人和他的生活被牢牢地同生存的广阔规模——同整个民族的与世界的历史,同自然宇宙的宏大联接在一起,与永恒相呼应。”*[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他站在人类历史和自然宇宙的高度审视现实,掘发历史,所以他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表现入木三分,勃留索夫认为“布宁很冷,几乎没有激情”*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二卷第十章《伊万·布宁》(本章布罗伊特曼、马戈梅多娃著,路雪莹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80页。,成为与鲁迅相类的冷峻的现实主义者;即便是《从旧金山来的绅士》这篇书写一个美国富商在意大利水域的一艘轮船上的死亡的作品,也从一个逼仄的有限时空,向更广大的领域扩展延伸,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制度的批评深化到对全人类的冷漠、隔膜等人性不良方面的思索。同时,他又有对于俄罗斯祖国和人民深沉而忧郁的爱,并灌溶进其对人的生命的美丽和大自然的魅力的抒写中,记忆中充溢着忧郁与感伤。所以,他又是一位有温度的现实主义者。这固然与冷峻的现实主义构成悖论,《乡村》《从旧金山来的绅士》等篇的冷峻的现实主义显然与《安东诺夫卡苹果》《幽暗的林荫小径》等篇的有温度的现实主义相对峙。但更多的作品两者共居一体,这自然以《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最为典型。但无论是冷峻的现实主义,抑或有温度的现实主义,蒲宁“从不粉饰目睹的一切,而是真实地予以反映”*冯玉律:《前言》,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8页。。这才是蒲宁现实主义之要旨所在。
在叙述视角方面,蒲宁与经典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多采取全知全能的视角。但他的“全知全能”的视角具有时间上和空间上的无限广延性。时间不单是以天数、月数来计算(如《中暑》《米佳的爱情》),许多作品是以几千年来计算的,而视野所达空间,亦能直通宇宙。一条“蚁道”可以拥有数千年历史,能够伸展到广漠的俄罗斯大地,伸向无穷无尽的远方(《蚁道》);可以以一座修道院为中心,跨越千年时光(《圣山》)。鲁迅的《狂人日记》也有此种特点。这样的全知全能视角,就使得其作品尽管多数为短篇小说,却都有着极大的容量,从而“投射出巨大的、有时甚至是宇宙规模的生存景象”*[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蒲宁的现实主义讲求描绘的精湛与准确,但不追求繁缛与华丽。质朴、简洁、恰如其分,不用过于夸张的词语,无论写人还是状物,均是如此。这又显现出与托翁相近的风格。与托翁不同的是,蒲宁描述的情节是相当淡化的,以致许多篇章几无情节,与其称为小说,不如视为散文,如《耶利哥的玫瑰》《圣山》《祭文》等。蒲宁说过:“十个作家中有九个,哪怕是最负盛名,也不过是讲故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与艺术毫无共通之处。”*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9页。(不知在诺奖颁奖会上以《讲故事的人》为题作答辞的莫言先生看见此语作何感想?)蒲宁更为重视的是“瞬间”和“碎片”,在“瞬间”和“碎片”中挖掘生活、生命、心灵的奥秘。同鲁迅一样,蒲宁小说中常有形象和语言的重复出现,营造了某种旋律与节奏。如《米佳的爱情》中令人忧伤的诗句的复沓,使得痛苦获得了节奏感,或曰阵痛感、加重感。
蒲宁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内容的深刻往往提升了美感。
蒲宁继承了托翁的现实主义,但在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方面,与托尔斯泰恰成反调。托尔斯泰视现代主义为仇寇,蒲宁则一方面对现代主义表示不恭,另一方面又顺应着当时文学发展的态势,对现代主义多有汲取。所以,蒲宁在对待自己的导师托尔斯泰的整体态度上也处于悖论状态。
“蒲宁的作品具有现代主义重直觉轻理性等特点:……既是主人公身边的现实,更是作者自己已远逝的直觉,既是心理逻辑的虚构,也不失为生活逻辑的复制……小说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特征:夹杂一些意识流的手法,采用叙事文学的双重主体、情节的淡化和乐感的增值等。”*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3页。这里事实上是在揭示蒲宁作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汇:“身边现实”、 “生活逻辑”等无不属于现实主义范畴,而“远逝的直觉”、“心理逻辑”、“ 意识流的手法”等则属于现代主义范畴。“《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作者通过这个长篇所要表现的主题不是描绘某个人的命运,而是要捕捉人生的岁月长河中不断漂移的不连贯的思想感情的‘意识流’(‘回忆流’),从对过去的紊乱回忆和对未来的模糊猜测中破译人生的真谛。”*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2-13页。从创作立意来看,与法国现代主义作家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是相似的。
其实,蒲宁作品的意识流手法的运用确实也相当突出,在抒情名作《安东诺夫卡苹果》中有非常典型的意识流描写。
“……梦展开她黑暗的双翼,盖住了我们半球的表层土地;梦从她的翅膀上抖落下来罂粟花和幻想……幻想……可是痛苦的厄运却往往是经常持久的!……”一串串亲切古老的词汇闪现在眼前:悬崖与柞木林,苍白的月牙与孤独,鬼魂与幽灵,“厄洛斯们”(按: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们),玫瑰与百合花,“小顽童的淘气与恶作剧”,百合花般的纤手,柳德米拉与阿林娜……喏,这里还有几本刊有茹科夫斯基、巴丘希科夫、皇村学校学生普希金名字的杂志。于是我惆怅地思念起我的祖母……*布宁:《安东诺夫卡苹果》,李静译,吴迪编译:《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1页。
这些梦幻中的景物、人物、神祇、鬼魂、诗人、刊物等的交叉、重叠,极具跳跃性。前半(引号中的)是当时(过去时)的内心独白,后半(引号外的)则是此时(现在时)的内心分析。看来蒲宁很熟悉当时意识流的用法:内心独白通常加引号,内心分析则不加。此处二度时空相衔接,充满了怅惘和怀念之情。在《快活的一家子》中,意识流的运用更加厚重,母亲临死之际的意识流竟然有六七页之多。
蒲宁还很善于表现形形色色的感觉印象——这是意识流表现的第三种手法。
且看视觉印象:
“火车……开过后匀称而又浓密的松林的绿色树梢在至高无极的灿烂天穹画下一个个圆。”*[俄]蒲宁:《佐伊卡和瓦列莉亚》,王立业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这是由于人在运动中所产生的独特视觉:绿色树梢成为了具有艺术气质的行为主体。
“这道闪电无论颜色还是光亮之中都含有一种非尘世的东西。闪电于瞬息之间洞烛了一切,把所有的窗户,连同每一个窗格都照得又亮又大,但随即又用浓重的黑暗淹没了它们,只是在刹那间留下一抹令人目眩的铁皮般的红通通的颜色。”*[俄]蒲宁:《娜达莉》,蒲宁:《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戴聪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41页。这是对闪电的视觉印象,既是客观描写,又带有明显的主观的独特的感觉色彩,可谓主客观的合一。
听觉印象:
“夜显得越来越清澈,似乎一碰就会发出铮铮的响声……”*[俄]蒲宁:《伊格纳特》,戴聪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498页。这事实上是一种幻听,突出夜的寂静与清澈。
“从附近的池塘里传来呱呱蛙鸣,犹如幸灾乐祸的笑声……”*[俄]蒲宁:《在异乡》,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13页。这是主观印象与客观实际的融合甚至是主观对客观的点染与外烁。
“钟声毫无意义地在船首单调地响着,不知什么地方隐隐传出抑郁愁苦的‘警笛’……也许,那声音本不存在,不过是紧张造成的幻听,茫无涯际的神秘海雾中,似乎总有什么声音回响于耳际……”*[俄]蒲宁:《雾》,杨怀玉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61页。此种幻听遵循的不是生活逻辑,而是心理逻辑。
嗅觉印象:
“一阵寒风,吹来一股一月的暴风雪所特有的清新气息,这气息十分强烈,味道就像切开的西瓜。”*[俄]蒲宁:《松树》,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54页。风雪的气息(嗅觉)被通感为味觉,并且像西瓜,真是独特的譬喻,独特的感觉印象。
“旅馆前广场的集市上人声鼎沸,散发出干草、松焦油的气味,以及俄罗斯县城所特有的种种浑浊而又浓郁的芬芳。”*[俄]蒲宁:《中暑》,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232页。此句前半是现实主义的,后半则带有现代主义的气息:以“浑浊”修饰“芬芳”有点通感色彩(以视觉修饰嗅觉),同时又有点“逆喻”意味。
更多的是多种感觉印象的复合:
“她知道的关于暴风雪的所有故事我都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所以只是机械地捕捉着她的一词一句,而这些词句又同我自己的内心话语奇怪地交织在一起。”*[俄]蒲宁:《松树》,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55页。此处恐怕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听觉印象,只能说是一种奇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了。
“你知道这些秋天里被踏出来的道路吗?富有弹性,就像踩在雪青色的橡胶上,上面满是被马掌铁刺划过的痕迹,在夕阳下像金带一般发出炫目的闪光。”*[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74页。这是触觉印象与视觉印象的综合。
“山谷那边的整个地平线似乎随着蛤蟆无休止的颤音而抖动,这寂静和黑暗也似乎被蛤蟆的颤音诅咒,永远处于麻痹的状态之中。”*[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820页。这是听觉印象与视觉印象的综合,带有更为浓烈的主观色彩。
错觉印象:
“小树的绿叶不知怎的发出一种不自然的亮光,或许这是因为紧靠深灰色的墙壁而造成的一种错觉吧。”*[俄]蒲宁:《骑兵少尉叶拉金案件》,戴聪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569页。这种细节的捕捉及对其形成原因的剔挖,透视出蒲宁犹如印象派画家的艺术观察力。
在《安东诺夫卡苹果》中还有着这样的描写:
在黑暗中,在果园深处,——冒出了一幅童话般的画面:地狱的一角,窝棚边腾起了血红的火舌,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黑暗。烤火人漆黑的轮廓,就像用乌木刻成的人形在篝火四周游动。随之,他们投在苹果树上的巨大的黑影也在来回摇晃。一会儿,一只足有几俄尺长的大黑手伸了出来,把整整一棵树捂住了;一会儿,又清清楚楚地伸出了两条巨腿——两条黑森森的大柱子。蓦地,这一切又都从苹果树上滑了下来,——落到林荫道上,盖住了整体道路,从窝棚一直到篱笆门……*[俄]布宁:《安东诺夫卡苹果》,李静译,吴迪编译:《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8-89页。
此处的描写不独带有鲜明的印象派特征,而且是天才地运用了电影摇镜头的表现手法——要知道,此时(《安东诺夫卡苹果》写于1900年) 电影艺术尚未诞生。此种描写既是基于现实主义的对生活的深刻观察,又体现出作家对传统现实主义手法的某种超越。同时,为电影表现手法其实也是基于现实生活提供了力证。(焉知电影艺术家未从文学那里——例如蒲宁的创作——得到过启发?)
再如“电线上停落着许多靑鹰,活像乐谱上黑色的音符,简直是像极了!”*[俄]布宁:《安东诺夫卡苹果》,李静译,吴迪编译:《对另一种存在的烦恼——俄罗斯白银时代短篇小说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页。亦不仅是天才的比喻,亦如印象派绘画。楚可夫斯基曾这样评说蒲宁:“在他之前,我们哪里知道月光下的白马是青色的,它们的眼睛是紫色的,烟是雪青色的,黑色的土地是蓝幽幽的,而收割以后的天地是柠檬色的?在我们只能看到蓝色或红色的地方,他却能看出几十种不同的色调和中间色。”*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第二卷第十章《伊万·布宁》(本章布罗伊特曼、马戈梅多娃著,路雪莹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79页。此处既道出了蒲宁对生活和大自然的深刻观察,也昭示出蒲宁所具有的印象派画家的审美眼光和心灵。
“他写到事物、动作或状态,往往加上主观色彩的、表声情的或心理的修饰语或副词。……蒲宁爱用合成式的修饰语,而这位作家真正擅长的是逆喻。”*[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1页。
逆喻确实是蒲宁常用的修辞方式,是一种“反向相合”的修辞方式,修饰与被修饰处于悖论状态,强化被修饰者的浓度与烈度,在正反对立的状态下揭示人类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深邃性。如:
“苦涩的高兴”。 ——《佐伊卡和瓦列莉亚》
“痛苦的幸福”*《素昧平生的友人》,蒲宁:《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戴聪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7页。;“这种蔚蓝色美得令人痛苦”*《素昧平生的友人》,蒲宁:《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戴聪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93页。。——《素昧平生的友人》
“愉悦的忧愁”*[俄]蒲宁:《净罪的礼拜一》,冯玉律译,蒲宁:《幽暗的林荫小径——蒲宁中短篇小说选》,冯玉律、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7年,第265页。。——《净罪的礼拜一》
“……某种令人伤心的慰藉。”*[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89页。——《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
“逆喻”在其他作家那里也常有出现,如著名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的诗集《曲线浮板》里就存在“逆喻”:“总题名《曲线浮板》颇为新奇,无疑属于一种‘逆喻’。”*沈大力:《伊夫·博纳富瓦:一个“现实的梦幻者”》,《文艺报》,2016年7月15日。中国作家中路翎也喜用它。
虽说蒲宁的作品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但多以现实主义为本,以现代主义为辅。如《投宿》虽写的是异国他乡,但叙写极为细致,对小店内外环境的描写,并不亚于写俄罗斯,表现出了作家的观察力和表现力的不同凡响,再次昭示出其现实主义功力。然而在描写姑娘整理床铺时,一只萤火虫停在她前额刘海上,小姑娘由此进入了童话世界。整篇作品既是现实主义的,也带有明显的印象派画风。有时某些现代主义质素甚至处于贲张状态:“连这些小脚都喜欢自己的白嫩。”*[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615页。人体的部分成为了独立的主体,完全是现代意味的诗。
我们知道,现代主义作品的另一主要特点是文学与音乐、绘画艺术的交融。前文多次提及蒲宁作品的绘画性——特别是印象派绘画性;其实,蒲宁本人也十分看重音乐的力量。他认为,音乐能使人获得一种伟大的幻觉——“幻想有一个神秘的机会能成为无比幸福、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而这种幻觉只有音乐和别的一些诗作灵感才会给予的啊!”*[俄]蒲宁:《阿尔谢尼耶夫的人生(青少年时期)》,章其译,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740页。他赞赏音乐的伟大力量——其实不独是音乐,也是文学——他明确地将音乐与诗歌置于同一等高线上。
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过:“蒲宁的语言是朴素的,朴素得近乎吝啬,是纯洁的,生动的。但与此同时,就形象性和声音而言,他的语言又是极为丰富的,包容了从铙钹的乐声直到泉水的淙淙声,从有节奏的铿锵声直到柔情绵绵的絮语声,从清越的歌声直到《圣经》上气势汹汹的斥责声,从所有这一切声音直到活灵活现得令人惊叹的奥勒尔省农民的谈吐。”*戴聪:《译后记》,蒲宁:《米佳的爱情——蒲宁中短篇小说选》,戴聪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271页。这事实上已经揭示出蒲宁作品的音乐性——文学具有如此丰美的音乐性,令人叹为观止。
俄罗斯学者认为:“对蒲宁的创作来说,一部新作品的初始的、无所不包的、普遍适用的组织形式,就是感觉到构思作品的节奏,它的内在的音乐性。只要节奏找到了,乐谱定下来了,作品的其他成分便开始明朗化,逐渐获得了具体形式:情节构架起来,充填上了人和事。剩下的是倾听内在的音叉,据此求得画面的准确、具体和生动可信。同时也就推敲了他的语言层面。”*[俄]符·维·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2页。将作品的内在的音乐性归结到作品的节奏,这是一种诗歌分析法;蒲宁也确实还是一位诗人——其实,他全部作品都是诗,有些散文作品(如《圣山》《祭文》《耶利哥的玫瑰》)全然是典型的散文诗,而散文诗的诗性主要在于节奏而非韵脚。
顾蕴璞先生则指出,蒲宁的作品中“语言与绘画、音乐浑然天成的融合,即用语言营造的形象或意象,饱含着光与色的美和线条美,洋溢着节奏美和旋律美,蒲宁的语言虽然朴实、纯净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但在视觉形象和音响方面却是异常丰富的”*顾蕴璞:《编选者序:流而不亡的文学大师》,顾蕴璞:《蒲宁精选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年,第19页。。这是对蒲宁创作风格的总体概括,清楚地道出了其现代主义的特点。
蒲宁对于他人的现代主义创作也很支持。作为《南方评论报》的负责人,他曾刊发勃留索夫、索洛古勃、巴尔蒙特等象征主义诗人的诗歌,也曾刊登过莫雷阿、魏尔伦等西欧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他对流行于20世纪初的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施尼茨勒,波兰的泰特马耶尔、普日贝谢夫斯基等现代派作家都很熟悉。《净罪的礼拜一》中出现了男主人公给女主人公捎这些作家的书的桥段。这都显现出蒲宁与现代主义的密切关联,自然与他自觉地汲取现代主义手法不无关系。
但蒲宁又曾尖锐地批判过现代主义,甚至与勃留索夫闹翻。蒲宁的作品也确实与某些现代主义作家以创造形式为单一的写作目的,乃至要求内容完全从属于形式的创作有别。蒲宁要比许多现代派作家更执着于具体的现实生活。然而,他又反对被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作家。他就在他本人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悖论中成就了自己的特点与深刻。
“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无疑是白银时代文学运动的焦点。”*叶红:《蒲宁创作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7页。我们透过蒲宁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错综复杂、充满悖论的关系,可以透视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状貌之一。
责任编辑:寇金玲
Bunin: Great and Profound Achievements in Paradox
Li Chunli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Liaon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enyang Liaoning, 110031)
Bunin is the first Russian writer who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but also a writer full of paradox. Bunin's writing of national characters constituted a striking contrast with his natural environment description. He took Russia's great nature as the protagonist in his literary kingdom, showing the trend of transition from anthropocentrism to eco-centrism. It should be said that Bunin is still one of the first forerunners who advocate the literature of nature today. Bunin was entangled with praises for and doubts of religion. On the one hand, the beauty of religion, the beauty of nature and the beauty of art constitute the tri-world of Bunin's beauty. On the other, he voiced his doubt of religion from time to time: beauty, especially love, is Bunin's supreme religion. Bunin often integrated his creation closely with the suffering of human beings. But he denied the role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social changes and advocated creation for his own sake; creation became the way to obtain his sense of existence. Bunin's creation method was first and foremost realistic; he opposed modernism, but also drew a lot from it.
Bunin; natural view; religious view; motive of creation; creation method; paradox
2016-08-25
李春林(1942— ),男,河北玉田人,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I512.64
A
1001-5973(2016)05-00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