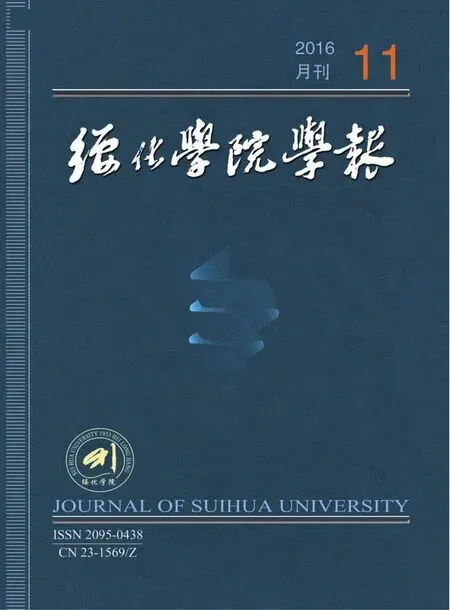《向苍天呼吁》中人物主体建构与社会权力含纳
黄力平
(郑州科技学院外语系 河南郑州 450064)
《向苍天呼吁》中人物主体建构与社会权力含纳
黄力平
(郑州科技学院外语系河南郑州450064)
不同的历史时期,种族歧视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未停止过。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黑人文学永恒的主题——反对种族歧视,呼唤民族意识。文章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解析二战后美国著名黑人小说家詹姆斯·鲍德温的小说《向苍天呼吁》,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文本如何参与建构社会权力关系,帮助读者发现所隐藏的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从而重新看待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种族歧视的新表现形势。
主体建构;社会权力;建构;含纳;
二战后的美国黑人小说在承接前期的黑人文学基础上,继续展开对黑人权利运动的书写,挑战所谓“主流文化”,更多地关注自身的生活及价值,涌现出了非常著名的黑人小说作品《隐形人》、《向苍天呼吁》、《所罗门之歌》、《宠儿》以及《紫色》等。作家们通过小说中人物主体的塑造来实现对美国种族歧视观念的颠覆,实现社会权力的公平和身份的平等,但通过细读以上小说文本,发现这种颠覆力量始终处于主导话语的规则体系之内,它通常总是被含纳,主导话语将重新指引这种颠覆力量回归到权力话语的程序和惯例中去。
限于篇幅,本文将以比较典型的黑人小说《向苍天呼吁》为例,简要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进行解析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人物主体的建构以及对社会权力的颠覆和含纳,进一步揭开帝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下的神秘的面纱。
一、二战后期美国社会主导的意识形态——对黑人等少数种族的歧视
“黑人小说中最鲜明的主题是对美国社会中依然存在的严重的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进行深刻揭露,反映美国黑人的痛苦生活,呼吁美国社会重视种族问题。”[1](P98)为何在美国社会中,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存在,并始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的意识形态,以下做简要分析:
(一)种族压迫史。自16世纪初期开始至19世纪,欧洲白人源源不断地将非洲黑人作为奴隶贩卖到美洲大陆,并在贩卖的途中大肆虐杀黑人奴隶。与此同时,为了建立牢固的白人根据地又对美洲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进行疯狂的捕杀,在黑人的血泪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家园。由于长期对黑人的奴役使白人在心里形成了一种优越感和对黑人的鄙视感,这种思想从贩卖奴隶的开始就产生并一直普遍存在于白人的灵魂最深处。
(二)宗教的影响。在美国,大部分的白种人信仰基督教。白人为了加深黑种人是劣等人种的观念,开始采用在黑人的群落中传播基督教。在最开始基督教是打着救苦救难的名义,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黑种人送去了希望,让他们看到了上帝是公平的。在他们对信仰的上帝深信不疑的时候,白种人就会让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是低等人种,他们生下来就有罪,就要给白人做牛做马来赎罪,这就是所谓的基督教中的原罪观,通过这种方式让黑人们心甘情愿的充当白种人的奴隶。
(三)种族教育。欧洲白人为了将自己的民族优越性更深层次地提高,为了巩固好自己掠夺的果实,不仅在肉体上面摧残黑人,而且将这种奴役渗透到黑人的内心,让他们的灵魂受到“白人优于黑人”的精神束缚。他们开始编造“美国白人是上帝的优等选民”,并且将这些思想放到学校、教堂以及教材中,大肆宣扬,将他们的这种种族主义思想发扬光大。
(四)国家机构的排斥。19世纪末期,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最终北方在战争中获胜,确立了北方大资产阶级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内战消灭了奴隶制,大批的南方乡村的奴隶开始涌入北方城市期望获得更好的发展,但结果并非如愿,政府、法院、国会等国家机器长期把持在白人手中,刚刚获得自由的黑人奴隶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遭到排斥和歧视,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
了解到种族歧视的渊源后,就不难总结出在二战后的美国社会中,一直存在的主导意识形态仍然是白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针对黑人等少数民族的歧视。
二、人物主体自我建构
主导意识形态中的种族歧视一直存在,并且变换着各种方式,因此,二战后的黑人文学的主题也从种族歧视向呼唤民族文化觉醒转变,开始追求自身的独立,寻求主体身份及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一)“主体”理论渊源。对主体的认识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先后经历了笛卡尔的“理性”,伏尔泰的“启蒙理性”到洛克的“经验”及康德的“感性理性的结合”等等,主要集中在主体的存在是先天还是后天,是个人还是社会的来源。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给出了对于主体社会性的认识的经典论证:“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P603)指明了主体的社会存在性。新历史主义学家格林布赖特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没有纯粹的,不受打击的主体性,事实上,人的主体开始时好像就不自由,只是特定的社会中权力关系的意识形态产物。”[3](P256)这就说明主体不仅受社会结构的制约,而且与社会结构之间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
(二)“主体”身份迷失。“主体”的社会性告诉我们,主体的身份是与社会紧密相连,当主体在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之外后,主体将会“丢失”。这也很好地说明了小说的第一部分“第七天”,在一开始时提到了在约翰14岁生日的那天早上,在他闲逛,想知道是否有人记得他的生日,以此来证明14年来他是否得到了这个家和社会的认可。但结果是连他的父亲都对他十分冷漠,让他感到无比的孤单与悲伤。这让他想起了在他出生的14年里,所经历的种种孤独、冷漠和恐惧。他黑怕他的教堂和他的上帝,他害怕两者都让他失望;他害怕周围的白人社会和环境会给他压力;他害怕自己的罪孽和对自己身份和命运的不确定。他最害怕的还是他的父亲,一直都不和善的父亲;他害怕父亲生起气来变得可怕的、无比残忍的脸。当他的兄弟罗伊受伤躺在沙发上时,他感到父亲是多么的恨他,多么想躺在那儿的是他而不是罗伊。他就像是一个流浪者,他不属于他父亲的屋子,他更得不到社会上的认可,他就像是无根的叶子一样到处飘荡。
(三)颠覆主导意识,构建自我主体。主体的自我建构逃脱不开那些来自宗教、种族、婚姻和法律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当主体身份不被特定历史时期内所建构的社会网络所认可就必须打破颠覆局限,积极争取构建自我。
1.质疑主导宗教。约翰从小的时候就与宗教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源自于他的父亲,确切地说是他的继父,一个牧师。在他14岁以前,小约翰长期的生活在浓郁的宗教氛围之中,“人人都说,约翰长大后准会当牧师。这话说得多了,约翰也就不假思索的信以为真了。”于是,在整篇的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与基督教圣经有关的文字,比如祷告词和忏悔录,比如圣经中的原文的引用,给读者造成了故事中的约翰肯定会对从小到大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基督教义深信不疑。但鲍德温将话锋一转,说到小约翰在14岁生日的当天早晨,在他所看到的经历中依然找不到自己存在感的事情后,他开始认认真真地琢磨伴随他从小到大的教义是否真地能够帮他找回存在感,他开始后悔了。
这一切说明,在过去的14年里,他经历过很多被抛弃与冷落的时候,他经常受到来自残酷社会的排挤,家庭中父亲的打骂,心灵上面饱受创伤。没人关心他,呵护他,于是他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上帝”那里,因为只有“上帝”最了解他。但是事与愿违,14年来他一直虔诚礼拜的上帝并没有帮助他,或者最起码也让他所讨厌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按照教义上面所说),每次做礼拜时狂歌乱舞的圣徒们,第五大道上的贵夫人们(不接受基督教义的洗礼),还有他那可怕的父亲(竟然是上帝派来的使者),竟然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一切都让他开始认真思索眼前的这个上帝。这个思索,正是对目前的主导教义进行质疑,让他明白了宗教只是黑人的麻醉剂,让黑人们产生一种虚幻的平等景象,而在现实生活中甘心被奴役的一种骗局罢了。
2.对抗父权神权。身为小约翰的继父加布里埃尔,脾气暴烈,对待他更是毫不留情,态度粗暴。从小的时候,约翰就对他的父亲有着无比的厌恶与恐惧。父亲的脸“向来令人生畏”,打他和他的母亲时更是“让他害怕之极”“毛骨悚然”。父亲还常常以基督教教义来威胁和恐吓约翰,使他幼小的心灵布满恐惧的阴影,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邪恶不洁”,感到“羞耻与恐怖”,害怕自己要下地狱。
而这样的父亲竟然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是一个牧师),在家中行使着至高无上的父权和神权,这正好与他唯一所能求助的上帝教义恰恰相反,给他造成了强烈的反差感和积聚的张力。他选择了对抗父亲以及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他诅咒、反抗继父,甚至一心想要杀死他,他恨不得马上逃离这个家。因此加布里埃尔经常说他是“长的撒旦的脸”,眼里充满着“撒旦凝视的目光”,他感觉到了小约翰身上强烈的反叛意识。
3.抵制刻板化印象。在白种人的教科书中,总是渲染黑人劣等人的形象,他们始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反应迟钝,穿着邋遢,蓬头垢面。这在小约翰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十分反感。但当他每周日早上,看到在去教堂的路上大部分的黑人同胞的形象时,他又十分窘困:在被社会抛弃,挣扎在贫困线下的黑人男人们“蓬头垢面,两眼无神”,衣服“又皱又脏”,女人们说话“粗声粗气”。
为了抵制这种刻板化印象,约翰在小的时候,就有着和他的同胞们不一样的决心,他永远不要像他的父亲和他的人民一样贫穷、一样卑贱,他也许会成为他的民族的“一位伟大领袖”。他将会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于他父亲的那个黑漆漆的房子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他会有美味的食物、华丽的服饰、昂贵的威士忌和香烟,而且只要他乐意可以随时看到电影;他会看起来与众不同,人们会敬仰他,把他看做是一个“英俊、高大、受欢迎的人物”。他会过着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
三、社会权力的含纳
由于社会能量具有流通性,文学就可以通过再现将社会能量再现、传播,影响观众,从而变革社会。福柯认为:“现代社会中,权力的模式更为微观,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4](P443)事物都是一一对应的相互矛盾的统一体,正是因为权力无处不在,才使得它的对立面反权力或者称为权力的颠覆也如影随行。而格林布赖特又指出:“颠覆力量是权力的产物,它拉长了权力的寿命,而同时,这种颠覆力量早就被它所要推翻的权力含纳于其中。”[5](P89)由此可见,权力的颠覆和含纳也是共同产生的,新历史批评将文本融入到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并和其它文本形成一种话语,而话语通过再现颠覆而有效的含纳它,并在一个界定的系统内控制颠覆。
(一)宣扬了白人宗教的救赎作用。整本小说作者的意图是旨在通过约翰的反叛,颠覆特定历史时期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和剥削,唤醒沉睡的民族意识。所以从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告诉读者约翰后悔了,他14年的信仰经历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他依然生活在被抛弃、被忽视、被冷落的境地,质疑了当前黑人们所信奉的基督教义都是骗人的,仁慈的“上帝”只是白人编造出来奴役黑人的另一种手段罢了。
但在小说的最后,鲍德温又肯定了“上帝”的作用,上帝严惩了罪恶,拯救了善良,让他令人恐怖的继父加里布埃尔妻离子散,大儿子横尸街头,二儿子放荡不羁,让虔诚的小约翰获得了救赎,在14岁生日当天意外收到了来自母亲的生日礼物,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同时还第一次在与圣徒伊莱沙的搏斗中战胜了他,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故事的结局客观上又加深了基督教义对黑人的奴役,宣扬了白人宗教的救赎,让读者们又感到了迷惑与不解。
(二)加深了黑人原罪观。小说中充满了浓郁的宗教色彩,基督教的教义深深地影响到作者。鲍德温早年的时候曾经在教堂里做过三年的牧师,这段经历对作者及其作品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告知他,上帝会安排好每个人的命运,人们应该默默地忍受着人世间的痛苦与摧残,死后才能得到上帝的恩宠。因此,黑人应该接受上帝的安排,默默承受比白人低劣的命运。作者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是白人借以蒙骗黑人并控制其身心的强有力的工具,并对其进行抨击,但是在其作品中还是有很多地方体现了基督教义原罪观对黑人身心的控制。
大部分的黑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的主导语境中,长期处于话语权丧失的地位,慢慢地将黑人种族低劣观念内化,使整个人处于严重的心里自卑的状态中无法自拔。约翰的姑姑弗洛伦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她讨厌自己的黑皮肤,经常坐在镜子前面往身上抹白净霜,可她明明知道这些起不了任何作用,以至于她经常铁青着脸大骂“买这些皮肤霜简直就是浪费钱”。在对待自己的婚姻上面,她嫁给了同样是黑人的弗兰克,但她却极力地反对她的丈夫与那些“粗俗”的黑人交往,为此他们经常吵架,以至于导致最终婚姻的破裂。弗兰克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吧,姑娘,我想你永远不愿看到我,不愿看到向我这样一个卑贱,有罪的黑人了。”
鲍德温在作品中流露出的黑人原罪观也是他自己长期受到原罪观的影响所致,他让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带上了罪的桎梏,成为罪恶感的牺牲品,给每个人物都打造了一个现实的牢笼。这种观念在小说中的流露只会加深了黑人的自卑感,成为了解决种族矛盾的又一个难题。鲍德温在他的另一个作品《下一次烈火》中也曾写到:“我意识到(圣经)是由白人写的,从很多基督徒中,我知道我是被诅咒的黑人的后代,所以我注定是一个奴隶。”[6](P167)
(三)强化了种族歧视。在抵制白种人对黑人的刻板化印象的过程中,作者赋予小约翰自己对于以后生活的追求。小约翰是个很有抱负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将来很有可能会干一番大事业,他自己也看不起自己身边的同胞,他脑海中浮现的是对于未来生活的向往,他的“黑人梦”恰是目前白人们的浮夸奢侈物质生活,他向往的大房子,向往的美味的食物、华丽的服饰、昂贵的烟酒以及人们的尊重等等都是目前白人所拥有的。
约翰是黑人中的佼佼者,每个人都认为他前程远大,认为他可能成为他的民族的“一位伟大的领袖”,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位优秀的黑人也得不到普通白人的认可,经常被抛弃,不被爱护,这更进一步加深了白人优于黑人的种族观念,让更多的黑人对白人更加渴望和敬仰,同时对于自身的自卑感更是挥之不去。
四、小结
包括鲍德温在内的二战后黑人小说家都试图通过颠覆主导意识,唤醒民族觉醒,但几乎所有黑人作家都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美国社会无处不在的种族歧视带给黑人民族的屈辱、愤怒以及深深的困惑。在白人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黑人作家既对白人的压制深恶痛绝,又囿于它的强横,找不到抵制它的力量,所以很多作品在主导语境的强压下,由最初的颠覆转为不自觉的被含纳。
本文站在新历史批评的角度来看,各种文学文本对于社会权力的颠覆是与含纳并存的,只有正确地辨证的看待权力的颠覆与含纳才能更好地为美国黑人以及少数族裔争取到更多的平等权力。
[1]许海燕.从反映种族歧视到呼唤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论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的思想发展轨迹[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Stephen Greenblatt.Renaisance Self-fashioning:From More toShakespeare[M].Chicagoand London:TheUniversityof ChicagoPress,1980.
[4]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Stephen Greenblatt.“The Invisible Bullets”,in Richard WilsonandRichardDutton,eds.,NewHistoricismandRenaissance Drama[M].Harlow:Longman,1992.
[6]Baldwin James,The Fire NextTime[M].New York:Dial Press,1963.
[7]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第二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8]詹姆斯·鲍德温.向苍天呼吁[M].霁虹,宏前,译.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9]石坚,王欣.似是故人来——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20世纪英美文学[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
[10]宓芬芳,谭惠娟.没有宗教的宗教——论詹姆斯·鲍德温对宗教的解构与回归[J].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9).
[11]吴远庆,王晓东.美国的种族歧视文化模式探析[J].东岳论丛,2010(7).
[12]薛玉凤.直面创伤的詹姆斯·鲍德温[J].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1(8).
[责任编辑王占峰]
I106
A
2095-0438(2016)011-0070-04
2016-03-09
黄力平(1982-),男,安徽芜湖人,郑州科技学院外语系英语教研室讲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英语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