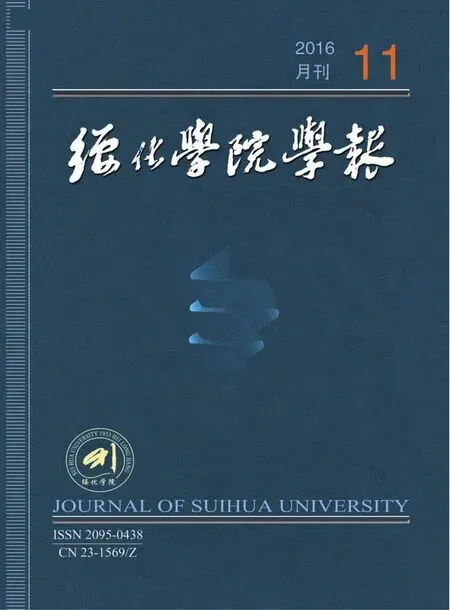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角力场
——评张炜长篇小说《古船》
崔金巧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开封 475001)
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角力场
——评张炜长篇小说《古船》
崔金巧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作为一个承载民族思想的文本,其表层囹圄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下的改革题材,内在形式显现的人性揭示与文化批判,又有着寻根、现代潮流悖论下叙事姿态的妥协,可以说是作为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角力场,从而引发了社会变革期的集体性焦虑。研究无论是触及人类性角度的内涵深度,对伦理文明的非理性倾向,还是社会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谱系无不彰显着历史文学叙事的立论原点,再现一种现代与传统理念并置的精神寄寓方式。
张炜;《古船》;现代;传统;意识形态
文学和历史作为两种不同的文本叙述方式,其联系区别向来是人文学界的争执点,而酝酿于中国文化思潮断裂时期的《古船》理所当然成为学界持续热议的焦点。纵观该文本批评研究的现有成果,论者虽从作品的意识形态、艺术真实、主题思想、人类性关注及文学审美等多种角度都有褒贬涉及,但回到文学现场影响批评来看,张炜的《古船》却一直是作为一个无法定位又不能忽略的言说方式而存在。于此,《古船》复活的多元思想冲击下的尴尬心态,以及所触及的当下思考可以说一直是文本的研究价值所在。
一、意识形态与文本产生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主要是从历史引发主体对当下历史性意义复活的角度谈及的。所谓文变染乎世情,文学承担着阐释或反思消解变革的功能。而《古船》之所以能够引发关注,主要还是源于作者张炜艺术上的扎实以及精神上衍化出的一种省思。当然,真正的文学性思路,往往能够以文学穿越文化政治的思维代替文化政治推动文学的思维[1](P306)。
作为一种精神上的突破,《古船》的确是在努力摆脱“载道”这种意识形态写作模式的,作品中对恢宏历史观的处理可以说极为背景化,然而却以一种非史学的眼光揭示了人的历史。
首先是叙事焦点的转变。张炜将文本视点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转移到了关注人物生存的视域中来,展示了胶东小镇独特的风土人情、纠结缠绕的人际关系及波诡云谲的多种力量博弈,聚焦美丑善恶,批露社会本相。从这个层面上说,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不仅是关乎人的,更是关乎社会的,这也是很多论者于整个思潮遮蔽下的无意识疏忽。
其次是叙事策略的转变。作者从“典型环境塑造典型性格”的经典原则中抽离,着重将人物的真实存在笼罩在环境的真实之后。家族与人物叙事寄寓于同一时空的胶合之中,思想触角探入民族历史和文化的深处,将现实与历史、社会与灵魂、纪实与虚构相融合,形成一种历史的混沌性。在文中十分典型地表现出两个“物化”维度:历史和现实。比如张炜将“洼狸镇”的当代现实与50多年来风云变幻的历史动荡勾连在一起,光明与黑暗、生机与危机并生并存。
再者是叙事手法的转变。作品多维度向既往传统叙事发起挑战:横向涉及社会现实的原态展露,纵向的进入历史底蕴的开掘,同时设置主人公隋抱朴以历史真实的亲历者身份,见证忏悔的“时间涵量”,迫使文本叙事向现代转化。运用现代主义手法以大量的意象隐喻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内蕴,“古城墙”、“地震”、“地下流”以及具有“历史龙骨”意义的“古船”等意象以实写虚,提出了对民族历史的个人化思考。苦难和死亡构成了古镇40年来的全部历史,因而文本在不断由“现实”回溯“历史”的努力中,所得到的结果都是此段历史类同于前段历史的“无所进展”。[2]
当然,不可否认,《古船》的文本艺术根本上是异于先锋文学的“纯形式”借鉴的,同时与后兴起的寻根文学也有着精神质感上的区别。于此,正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一定程度上说,小说文本展现的是一种现在时的表达。作者张炜也是携着形而上悲怆和文化操守努力超越各种限制,追求达到更高远的思想境界。
新时期文学引起争议的作品不在少数,但像张炜《古船》这样引起如此激烈争论的作品却是屈指可数。《古船》较之张炜的早期作品,思想视角既有延续又有超越,把对“人”的思考引向更为纵深也更复杂的境界。历史存在着本质的东西,而文学则将生活的本质现象化,呈现于可感领域内。重读《古船》我们不难发现,作品反思历史的叙述可以说不无个人体验的悲剧渲染,但真实情况是,抛却叙事者自身的心理投射,我们读者本身不也在无意识中投合着自己的心理体验吗?叙事时间的前后边界可以窥探整个中国大陆苦难史的物化空间,而整个洼狸镇所承受苦难的心理时间却呈现一种先验性失语。当然,这也表征了作者张炜所经受的历史与现实之困惑:在时代强制灌输政治理念的现实主义场域中,还是会有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归属感。比如抱朴在老磨屋里看《共产党宣言》的情节,这个被批评家向来予以诟病的文本设置最为典型。又如,让人费解的结局设置。隋抱朴这一中心人物作为历史重负的承载者与思想者,其实孕育着强烈而深沉的反抗性力量,然而,终于走出老磨屋接纳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成长应该说到了一个关键点,作者本可以好好写写有一定理论修养的隋抱朴如何管理公司,如何帮助全镇人脱离苦难,以契合成长这个主题,小说却突然结束了。在此,如果说是人物思想局限的话,倒不如说是作者张炜自身价值之无所适从,这也印证了作品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精神徘徊。但作家开始以独立个体身份思考历史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张炜已经不是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下的经营叙事,而且相比同是“拨乱反正”时期的《芙蓉镇》《灵旗》等,多了对生活本身、人与历史以及自我思想的省思,这也是《古船》文本内蕴深刻的原因。
关于有关论者提出“重新表述实际上是一种排它性表述”的论断,笔者表示不认可态度。《古船》尽管突破意识形态话语不断回穿民族历史文化,这与“寻根”小说有着相当的契合之处,但并非当下所理解的“排他性讲述”,而是一种重返式关照。小说文本是处于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一种观念颠覆,对于传统历史叙事的一种反拨,文中对王书记这个类似“高大全”人物的增设本身也说明了问题。新时期读者或者说写作者的历史理性,作为一种逃离意识形态的意识,本身就是历史话语多方合力的作用。历史小说需要官方意志的叙述,同时也需要碎片化的历史记忆,两者不该是非此即彼的。张炜本身也是一位性情保守的知识分子,加上建国后政治禁锢和文化封闭,作家的思想始终主动或被动地限制在雷池之内,结合《古船》中所彰显出来的文化保守性与整体启蒙语境之间的叙事妥协,客观的说,张炜似乎更愿意接受隋抱朴式的“修改”或“补充”历史的态度。当然回到意识形态领域上来,《当代》编辑用“史诗”二字评说《古船》,一定程度上仍然沿用了十七年文学批评思想的话语遮蔽,动态主流话语的转型影响可见一斑,而作品本身自然而然成了现代与传统价值选择的引爆点。
二、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
张炜是个思索型作家,《古船》的发表一定程度上也是作者主体情怀的文本冒险,有着对心灵、文化、原生态真实的批露,从自我反省达至现代启蒙性与民族性的契合。然而,文化裂变时期,张炜试图探索古今中外所有问题之期冀,却使下意识的启蒙反叛无奈成为无意识层面的启蒙反证。正如《古船》作品中闪现出的信念与悲壮气势,张炜的理想主义与反政治的民间乌托邦不同,作者始终携着一种自食的忏悔精神,以文学道德穿越现实道德展现出一种现代与传统价值选择冲突的挣扎与坚守。
新时期文学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上接受了西方的“新现实主义”思潮,如何透视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冲突成了最大的敏感节点。这样回到《古船》的叙事现场,就会发现其中的悲剧意蕴不言自明。尽管张炜写作之前已然有了必要的资料搜集工作,但作者在思考生活和历史的本质性问题中,不得不用先验理论去推理事件的起因源流,不免加入虚构的真实,但是这种手法恰恰又在影响程度上超越了伤痕文学,甚至寻根先锋也接踵而至,可以说,新时期文学之所以被学界苛责,很大原因也在于其文学的无方向感。有关论者说过,没有历史分析的文学注定是不能真正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3](P69),确实,新时期文学仍然需要史诗性的文学作品。所谓现实主义的真实观,从十七年的《红旗谱》到《创业史》再到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等都是一脉相传的。回到《古船》上来,张炜的痛苦便在于,旧的文化信仰的失效与新的社会伦理无依着感之间的焦虑,以及人与人之间无法理解的痛苦。当然,张炜在《古船》中试图将许多已成为思维定势的文学现象以问题化的表达呈现出来,开启了历史话语下的遮蔽镜像。
首先是心灵世界的发现。《古船》在写实上呈现出的乡土情怀是其民间立场所折射的一种显影,而转入到人性深处审视的笔触却是一种深刻。相比《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愤怒》,《古船》进入到人类自身心灵探索,将苦难推到台面上描写,作品中的人物抱朴、见素、含章、小葵无不裹挟在残酷之中,最为引人眼球的当然还是思想者的化身隋抱朴,他的隐忍忏悔甚至坚守让我们不得不进入人类性领域省思历史。
其次是文化空间的发现。文化空间的开拓使得现实大为丰富起来,因为文化可以自由的穿越时间,不在以平面的单维度铺陈,而是成为一种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多维立体存在,显示多元历史结构中人的本性,更高境界的真实。陕西作家陈忠实尽管年长张炜15岁依旧明确承认《白鹿原》曾以《古船》为师,站在民族文化的高度,整体结构上呈现出一种文化操守和民间立场的历史意识。
最后是历史现实的艺术发现。真实是文学的生命,《古船》突破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禁区,以现实生活赋予历史的色彩,破译着社会现实的矛盾种种,揭示出现实的内在危机。对于作品中人的苦难惨象的描绘,比如茴子之死亡惨状,含章那委曲求全的生存姿态等等,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所言的“人肉筵”论断。
不可否认,张炜的思想投射到隋抱朴身上显现出一种内敛性的不安,当然我们也无可怀疑张炜对于禁锢中国文坛的陈旧美学规范的挑战。
历史恢复其实还是在于一种话语恢复。《古船》站在“现在”的制高点上叙述历史,叙事立场从官方意志转到了民间立场上,对革命历史有了纵深的挖掘,凸显了民间历史的真实面目,强调了历史的神秘性与不可知性,相对还原了历史的复杂性。感性和理性成为这一时期作家价值理念选择的两难,20世纪50、60年代革命现实的迫切需要被当作历史本身,个人情感被集体单纯情感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从反思、反叛到结构,一方面是逃离历史化,一方面又有着渴望重新历史化的焦虑。《古船》以家族记忆与革命记忆双重叙述穿插进行,跨度涉及土地改革、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时段,书中对人性以及宿命的表达超出了经典现实主义权威主题的范围,有了民间与主流话语的交流。有论者指出一种“伪民间化”立场,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因自身思想无力而通过对民间的虚假意象营造出乌托邦,是对民间真相的刻意过滤与无限拔高,以之作为思想和叙事的资源。且不说这种论断是否有失偏颇,但张炜作为一个有精英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愤世嫉俗民间立场代言人,抛开《古船》对于民间的冷峻剖析,《九月寓言》等之后的一些列作品,更为加重了他对于民间的原始生命冲动推崇。思辨性过强确实会影响文本艺术性甚至是人物个性,走向现代启蒙的悖反道路。而现代性的维度之一便是用现代非理性审视现代理性,《古船》透漏出一种非理性倾向,预示着作家自己的伦理价值诉求。文本的外在形式内裹于其隐含意旨:隋、李、赵三大家族的兴衰错综复杂,仿似封建历史的朝代更迭。同时三大家族阶级属性的隐喻性也可谓是昭然若揭:隋家代表着旧式的地主阶级,有着昔日的荣耀,同时也是文化传统的负重者;赵家则代表着后起的无产阶级;李家与启蒙知识分子的处境有几分相像,开始反思知识与革新的可能,但是知识分子并没有真正的身份认同及独立意识,在两个家庭夹缝中迷失自我,比如李知常的父亲出家当了和尚,而他本人也患上了狂病,精神失常等等。就张炜小说创作的主旨而言,对抱朴普度众生理想的认同以及人性关怀的推衍,不难看出张玮对于集体主义时代对个人价值的有意观照,当然也便是这种民间立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审视心理,使得知识分子实践精神的局限性及宿命式的民间愚昧在隋抱朴这个人物身上找到了镜像折射。《古船》有着批判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复杂交织,人道主义人物的设置是作为力挽狂澜能力的承载者存在的,文本的理想主义倾向可见一斑,也正如在物化的现实生活中,理想主义与强大的物化时尚对阵,在物质欲望与道德人情的较量中,永远存在着那种内容之悲壮与形式之荒诞的美学法则。
三、小说文本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影响
张炜的《古船》一经发表便引发了学术界的诸多争论。一段蜕变演化的历史,既有时代的互动因子也有人精神意识的发展进阶,而作为现代和传统的精神角力场,该作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尝试。正如文本作品以大地的震动开篇,又以大地的复归于平静结束,小说文本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褒贬乏陈的风口浪尖,而且质疑声异常激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诸多学者大都给予了比较中肯的评价。
一个人的重要性在于其与一个时代的关系上,而张炜的整个青少年时期恰好处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正如作者在济南《古船》讨论会上所说的:“我当时更多的是写我真实经历的那段生活,那段恐惧的感觉。”[4](P371)而且20世纪80年代以前,张炜的小说创作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的“入世”情结,对社会道德的批判是其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表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商品经济大潮随之而来,启蒙话语严重受挫,青年张炜在创作中将眼光投向了现实生活的边缘历史风景,《古船》的历史叙事意义尚不突出,尤其是相关实践性发展更是不尽完善,斧凿的痕迹相对比较明显,但是对于人性中的恶因素描绘的却是淋漓尽致。张炜似乎发掘了存在主义的虚无性,以至于作者将整个洼狸镇的拯救重任安置给了道家色彩浓郁的隋抱朴身上。当然,老隋家三代人的生活是与近代以来的动乱纠葛、社会变迁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作者对整部作品思考的前瞻和局限也都在这里。正如有论者说的,与其说反映了张炜无奈的欲求以道家理想精神对人间苦难拯救的希望,不如说是张伟对人的存在价值质疑后思想的逃逸和对人生的幻灭,由此带来了小说沉重而困顿的叙事形态。[5](P91)的确,无论是《古船》对历史的叩问,还是《九月寓言》对大地的融入热情都有一些神秘主义在里面,这中间多少也揭示了人在时代面前的局限性。人类文明既包括生存意义又包括文化意义,当我们意识到文化上的发展传承要以生存根本上的血腥为代价时,问题就会变的极其复杂。“无论作者是伟大还是渺小,他的作品传递出去以后,无论传递的距离是多么短,有些东西也要损失一般,这是不可避免的损失”[4](P375)。张炜在《古船》中是深入人性与道德揭露苦难历史的荒诞性的,所有的故事都是历史潜在的道德事实,但是由于作者所处时代的追问过于踌躇不安,作者思想深处的不清晰便被遮蔽了。1986年《当代》杂志在初审《古船》的时候,提出的两点疑虑是比较值得思考的,对土改描写的分寸问题和隋抱朴读《共产党宣言》的牵强性问题[6]。以至于后来发表出来的作品则增加了王书记坚持执行党的政策、对无产阶级的乱打乱杀加以制止的情节,树立起必要的正面东西,不得不强调他所否定的是“左倾”和愚昧以及流氓无产者的过火行径[7](P495)。即便如此,作品发表之后依然引发了剧烈的争执。在艺术真实性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古船》作品本身的存在状态与人的主体性被压抑相一致,现实主义可谓是从十七年文学一脉相承下来的,历史真实是,在文学艺术创作中要毫无讳饰的铺陈真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张炜《古船》的写作可以说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作品中的理想与现实色调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与道德意识双向运动的统一。他并没有把人间的苦难甚至是恶因素同历史的发展道路完全对立起来,特别是作者给予人物的忏悔自省意识,在其情感与思想理性之间是一种有所游移的真实,不是简单的拾取历史发展过程中被遗忘或者不愿记起的内容,而是在传统与现代文明中给他们予以合理定位,在一定程度上,笔者认为,张炜有着与巴金《随想录》相通的真诚。张炜参加了两次座谈会,会议结果无定论性可以说是谨慎有加,争议的焦点不无疑问的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人性描写的阶级视点、隋抱朴人物的思想以及艺术真实等层面,于此,不难看出意识形态的批评仍然处于不弱的地位,至于张炜最后无缘茅盾文学奖当然也与现代文化转型期的时代特殊性不无关系。
回到文学批评影响上来,张炜的《古船》无论是在社会反思还是在叙事艺术上都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作品。作者基本上都保持与现实适度的距离和足够的清醒,始终站在现实的边上,审视、感叹和思考,传统的东西佩戴着各种各样的新面具继续演着旧戏,有的人甚至夺过别人痛打过自己的鞭子继续打人。[8](P135)这便是作者张炜所担心的苦难的延续,张炜以罪孽的笔触展述了一段民族秘史,并对其中的苦难与残酷、人性畸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甚至试图以思想者的姿态探寻化解背后的现实路径。面对历史真实,作者以反现代性的激进立场,站在了散发人道主义光芒的隋抱朴的一边,甚至《古船》作品中对《共产党宣言》的引入,都成为张炜隐遁气质中“以德报怨”的非理性之理性皈依,当然这种理解与其说是张炜个人道德光辉,倒不如说是对自己在文本中人物现代性立场的一种否定。但由此也产生一种矛盾,作品最后安排隋抱朴走出小磨屋,不正是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结合的一种妥协姿态吗?不可否认,意识形态永远起关键性作用,联想到贾平凹《浮躁》里一个情节,全书最后弄出“三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给人扶乩,这是颇有深意的。共产党头目必须是无神论者,却被人当神供,可以说是浮躁时代的病急乱投医,值得反思的是,老百姓往往没有资格成为推动时代的弄潮儿,却是时代的枷锁的背负者。历史的荒诞却是真实。《古船》中诸多意象叙事不也正说明对于奔腾而来的时代潮流慌乱价值背后的信仰追寻?比如清醒的李其生因为说了句真话,一颗玉米结十个棒槌是假的,于是被指认为疯子。正直的老汉宁愿把麦种下到井里也不去糟蹋土地,被视为反动。疯癫的隋不召说起春秋战国隋唐五代,看起来是张冠李戴、滑稽可笑,但不正揭示出历史一脉相承的作戏模式吗?正如有论者言,被历史埋入河底的古船虽然被重新挖掘了出来,再现了它当年的雄姿,但是它能否扬帆远航,走向大海呢?[8](P128)这或许是张炜通过《古船》想要昭示的一个时代课题。
综上所述,从文学史整体性研究角度,张炜的《古船》无论是从社会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谱系、人类性角度的内涵挖掘、现代话语精神突破与叙事姿态妥协之间的尴尬心态、甚至是文学批评界的极端褒贬责难等诸多方面无不显现着作品在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也正如有相关论者所言:“无论你能指出《古船》的多少不足,但是你不得不从心理承认,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数几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9]。”不可否认,《古船》作为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角力场,浓缩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反思深度,成为新时期文学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振兴以及文明转型批判前行的集中显现。
[1]吴炫.穿越中国当代文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7.
[2]秦振耀.叙事形式的精神承载:《古船》与《百年孤独》的历史意识[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文学艺术),2012(7).
[3]程光炜.当代文学的“历史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张炜.古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5]王辉,李军.穿越文本: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两级阅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6]何启治,杨晓帆.我与《古船》:八十年代《当代》纪事[J].长城,2011(6).
[7]张炜.激动与畅想//张炜文集(第一卷)[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8]蔡世连.古老土地上的痛苦选择:论张炜《古船》的文化意蕴[A].孔范今,施战军,主编.黄轶编选.张炜研究资料[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9]罗强烈.思想的雕像:论《古船》的主题意蕴[J].文学评论,1988(1).
[责任编辑王占峰]
本刊声明
为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加强知识信息推广力度,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CNKI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及相关稿酬,本刊均作为作者文章发表、出版、推广交流(含信息网络)以及赠送样刊之用途,即不再另行向作者支付。凡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I247.5
A
2095-0438(2016)11-0059-05
2016-06-13
崔金巧(1990-),女,河南鹤壁人,河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